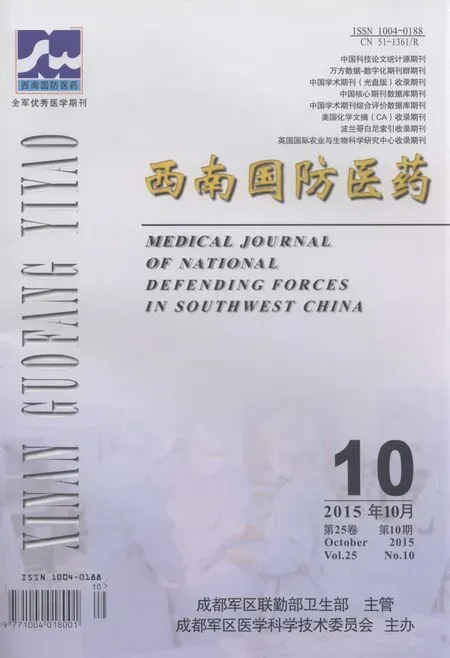基于基層軍醫能力建設的教育制度思考
董自西,趙 晉,劉 彬,王 勤
基層軍醫是軍隊衛勤力量的重要組成,擔負著平時基層部隊預防、醫療、康復、保健、衛生宣教和衛勤組織指揮“六位一體”的任務,更擔負著戰時基層部隊戰創傷救治任務[1]。培養什么樣的基層軍醫和如何培養合格的基層軍醫,是全面建設現代后勤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更是做好軍事斗爭衛勤準備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值得研究。
1 基層軍醫的屬性特點與能力要求
1.1 軍人職業屬性及其能力要求 軍醫的第一身份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打仗和準備打仗。作為軍人,基層軍醫必須全力做好軍事斗爭衛勤準備,承接好平戰時衛勤保障任務。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未對“軍醫”進行定義,但界定了“軍人素質”,即是指軍人在政治覺悟、軍事技能、戰斗精神、作風紀律、文化知識、軍事理論、體能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2]。 軍人素質是基層軍醫的基本能力要求。
1.2 醫生職業屬性及其能力要求 軍醫的第二身份是醫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規定:“醫師應當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和醫療執業水平。”從工作性質而言,基層軍醫相當于地方的全科醫生。 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基層軍醫必須掌握以“十項救治技術”為主的戰救技能,并滿足總部對于基層衛生機構“六種能力”的建設要求,真正做到“平時保健康、急時保響應、戰時保打贏”。
2 基層軍醫能力不足的原因剖析
基層衛生機構平臺較弱、轉診過度、衛勤訓練與軍事訓練長期脫節等現實問題,提示基層軍醫普遍存在能力不足、特別是傷病救治能力不足的問題。 基層軍醫現有能力水平與崗位職責間出現不相適應[3],這種不相適應歸因于軍醫教育的不足與教育間銜接的不順暢。
2.1 本科教育的不足是基層軍醫能力不足的源頭 目前基層軍醫來源于軍醫大學畢業生和地方院校培養的國防生。 軍醫大學雖確立本科教育為第一要務,但在實際工作中,更傾向于科學研究,有所偏離于軍事醫學人才的培養。 在“3 年學校+2 年醫院”的基本教學模式外,軍醫大學會安排在校學員暑假短期的基層體驗,但學員對基層工作環境的感知與任職要求的掌握并不深刻。這種偏離還體現在師資力量方面, 如某軍醫大學應屆本科生約700 人,但承擔戰(現)場急救基本技術教學任務的教員不足7 人,因師資力量不足、課時安排過少、場地條件受限等因素,影響了教學的質量[4]。 而且軍醫大學年輕教員多為畢業不久的研究生,自身尚對臨床醫學和軍事醫學認知不足,其教學就只能是理論到理論,教學質量較難保證。 國防生就更缺失軍事醫學的教與學。
2.2 任職教育的不足是基層軍醫能力不足的核心 針對某軍區基層軍醫的調查結果顯示,167 名軍醫中,僅44.3%通過執業醫師資格考試[5]。某單位邊防軍醫任職培訓有17 門課程,其中軍事醫學類課程僅有5 門,且均未涉及戰時衛勤保障能力的教學與實踐[6]。2010 年,某軍區開始對新畢業醫療專業干部開展崗前培訓, 由軍隊醫院具體負責。 2014 年,該軍區開始有計劃地組織師級以下部隊醫療專業干部培訓,明確了崗前培訓(12 個月)、部隊任職(不少于12 個月)和專科進修(12 個月)3 個階段。 但因軍隊醫院自身軍事醫學技能掌握有限,較難實現軍事醫學技能的培養目標。 國防生的任職教育由軍醫大學崗前教育和軍隊醫院崗前培訓組成,同樣缺少軍事醫學技能的專項訓練。
2.3 繼續教育的不足是基層軍醫能力不足的補充 基層軍醫繼續教育的主要途徑為院校專項進修。 有調查顯示,全軍24%的師旅醫院、36%的旅團衛生隊、27%的營衛生所缺編[7]。 衛生干部缺編嚴重、衛勤保障任務繁多等原因,造成基層軍醫學習機會很少。 全軍戰創傷救治訓練基地雖于1995 年正式建立,但截止2007 年,12 年間僅面向2300 多名軍醫進行相關培訓, 年培訓受眾不足200 人[8]。針對某軍區90 名基層軍醫對2010 年心肺復蘇新指南認知情況的調查結果顯示, 基層軍醫新指南知曉率僅為36.7%,要點考核平均成績僅為35.3 分[9]。 2012 年,有調查結果顯示: 某軍區175 名基層軍醫核化生防護知識缺乏,平均得分僅為總成績的55.3%[10]。
3 基層軍醫能力培養的教育制度構想
基層軍醫的能力培養應著眼于現代戰爭衛勤保障需求,以深化軍隊衛生改革為契機,以增強部隊衛生能力為牽引,以建設打仗型衛勤為根本方向,以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為有力保證,推進軍醫教育制度改革,將本科教育、任職教育、繼續教育統籌協調,明確各自功能定位與培養目標,實現基層軍醫能力培養的系統化運籌、模塊化組織和基地化實施。 本科教育、任職教育和繼續教育的基本劃分如表1 所示。
3.1 以本科教育解決“醫學入門”問題,打牢能力基礎基于國防生教育制度,為確保有限軍費投向和推進軍民融合發展,將軍醫的本科教育完全接軌于地方醫學教育,定向委托地方醫學院校(教學基地)負責。教學基地的認定由總后勤部負責,但課程體系應區別于地方,遵循目標相關性、學用相符性和課時合理性進行專門定制,體育貫穿教學全過程。 本科教育必須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以探究為基礎,以整合醫學為根本,注重“基礎+臨床”的系統化課程與學科重組的模塊化教學。 如肺炎的教學,可從“肺”的解剖講起,整合生理學、病理學、物理診斷學、實驗診斷學、影像學、藥理學等學科,切實將基礎與臨床融會貫通。 在“3 年學校+2 年醫院”基本教學模式的基礎上,把部分基礎和臨床課程劃歸任職教育范疇,將教育周期壓縮為4 年。 教學考核采取科目考核、年度考核和畢業考核相結合的序貫式考評體系。 建立終身制的個人教育檔案,新增檔案內容應公示,以供監督。

表1 基層軍醫教育制度基本情況
3.2 以任職教育解決“臨床執業”問題,提升能力水平任職教育由軍醫大學(規范化培訓基地)負責,軍醫大學師資力量全部投向于軍事醫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上來。任職教育為全科教育,不分專科。 課程體系完全圍繞基層部隊平戰時衛勤保障任務所需的理論與技能。教育周期為3 年, 第1 年在規培基地強化理論學習和臨床見習; 第2年安排6 個月專題學習軍事醫學理論與技能,掌握高技術武器損傷特征、致傷機理和病理生理變化,利用動物模型探究有效的損傷控制技術和救治技術,另安排6 個月到基層部隊進行崗位實習; 第3 年到規培基地進行臨床輪轉,其中呼吸內科、消化內科、皮膚科、普通外科、骨科、傳染病科等臨床科室為必須輪轉科室。學習情況填入個人教育檔案。 執業醫師考試改變現有臨床醫學(600 分)和軍事醫學(20 分)的考核模式,改為由軍隊自行組織。 同時,加大軍事醫學比重,采取階梯式考核方式,即逐項逐級考核。全部合格后,方可授予軍隊執業醫師資格證,也才能完成任職教育。 順利完成任職教育的軍醫學員,面向基層部隊進行全軍統一分配。
3.3 以繼續教育解決“崗位勝任”問題,強化能力素質繼續教育由軍區總醫院(衛勤訓練基地)負責。總后勤部建立衛勤訓練基地建設標準,在軍區總醫院建設衛勤訓練基地,負責戰區所有部隊全科軍醫的繼續教育。 課程體系可參考美軍模塊化培訓方式,設置理論培訓模塊、交互式外科手術模擬操作模塊、實戰病例分析處理模塊和動物手術模塊。 每名全科軍醫每年接受不少于1 個月的繼續教育,采取分批分層次輪訓的方式, 加強醫學新知識的傳授,重點開展戰救技能訓練,并結合現行救治階梯進行衛勤保障力量集成化的聯合演練,學習情況填入個人教育檔案。 同時,在現行部隊衛生干部選調基礎上,健全全科軍醫流動機制,增加年度選調比例。基層部隊工作滿4 年者,根據個人教學檔案擇優選入中心醫院或總醫院,并根據編制情況兼顧個人意向設定全科軍醫的專科方向;專科軍醫方可申請研究生教育。
[1] 汪初球,繆小勇,楊華才,等.探討軍醫四年制本科人才培養模式[J].第一軍醫大學分校學報,2004,27(1):26-27.
[2] 全軍軍事術語管理委員會,軍事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7.
[3] 王秀薇.基于勝任力模型的基層軍醫任職培養模式研究[D].重慶: 第三軍醫大學博士研究生論文,2008.
[4] 陸洲,向英,高宏杰,等.戰(現)場急救基本技術訓練模式探討[J].華南國防醫學雜志,2014,28(9):900-901.
[5] 曹毅.部隊基層軍醫全科醫學服務模式的研究[D].重慶:第三軍醫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
[6] 段清宏.邊防軍醫任職教育課程構建[J].衛生職業教育,2010,28(15):65-66.
[7] 王洪濤,羅長坤,黃建軍,等.基于職業生涯發展視角的基層軍醫任職教育培養模式改革初探[J].重慶醫學,2013,42(29):3574-3575.
[8] 柯新華,陳洪.“基地式培訓”的實踐與思考[J].西南國防醫藥,2007,17(5):652-654.
[9] 袁躍彬,姚玉川,趙京生,等.基層軍醫和衛生員心肺復蘇新指南認知調查分析[J].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2013,20(8):786-787.
[10] 趙京生,袁躍彬,胡波.軍醫和衛生員“三防”知識認知調查與干預[J].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2012,19(8):781-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