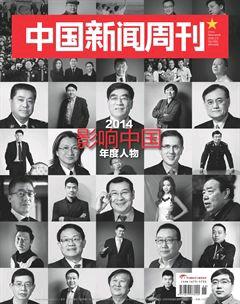劉東:不怕死,怕來不及完成
吳子茹

提名理由
他創辦并主持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是中國持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叢書之一。這兩套書從1980年代開始譯介優質漢學作品,并延續至今,旨在“為中國同行做很好的學術籌備,建立中西方學術對話的起點”。無論中國學術界還是普通讀者都受益匪淺。
劉東緩步穿過清華學堂一層走廊,依次經過墻上懸掛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的黑白照片,來到位于二樓的辦公室門口。辦公室門外正對著回廊式樓梯,冬日的陽光正好斜斜地照射進來,抖落一地木格窗花的剪影。
這是一棟兩層樓房,德國古典風格,坡頂陡起,青磚紅瓦,是上世紀初清華前身所在。墻上四幅照片,正是曾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作為重建的清華國學院,副院長劉東的辦公室和院長陳來比鄰。每次經過四大導師的照片時,劉東都會放慢腳步,心里一緊。是高山仰止,也是警醒自己。
“我比照片里他們去世時的年齡都大多了。”劉東脫掉風衣,一邊拿下帽子,一邊笑呵呵說道。他是看上去心寬體胖的那類人,聲如洪鐘,談笑自若。2015年元旦剛過,劉東進入花甲之年,這讓他更覺緊張。
很多事情要做,從最早進入學術生涯開始算起,三十多年“讀百家書”的學術準備已經妥當,最重要的著述生涯,似乎才剛剛開始,劉東覺得時間遠遠不夠。
“讀百家書,立一家言”
劉東在辦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打開電腦處理郵件。假期就快到了,忙完學校這堆事兒,他打算帶著家人去三亞海邊的房子度假,在那里繼續讀書、思考、寫作。他說那是真正的面朝大海,可以一直呆到春暖花開再回來。
這是劉東一年到頭最累的時候,編了二十多本書,教了這么多學生,還寫了好幾本書,每到年底,劉東都覺得“人困馬乏”。
關于寫作,劉東這一年計劃排得很滿。“今年至少有四本書要出。”他說。年至六十,劉東編書、教學,廣泛地讀書,現在,他覺得自己到了“立一家言”的時候。他時時有種緊迫感,他認為,一個大家,早年游學,到五十來歲時開始真正成熟地著述。“輸入的東西能不能輸出,那就得看他的天命和勤奮程度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學術界,劉東因主持創辦兩套叢書而獲盛名:“海外中國研究譯叢”和“人文與社會譯叢”。這兩套書從1980年代開始延續至今,譯介優質漢學作品,旨在“為中國同行做很好的學術籌備,建立中西方學術對話的起點”。
80年代,學院里一些理想主義者聚集在一起,以出書的形式完成社會啟蒙的理想。當時的出版社也大都歡迎這種合作形式,對他們來說,這相當于有一個成熟的編外團隊。
幾大叢書中,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譯叢”引人矚目。一個充滿理想和喧囂的時代落幕,其他叢書相繼宣告結束。但劉東繼續出書,“海外中國”和“人文與社會”逐漸成長為中國體量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叢書。
現在,編書仍然是劉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仍然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在這件事上,挑選他認為適合推介的書籍。劉東認為,這項事業不僅能“澤被世人”,更讓劉東自己吸取了大量養料。
近些年,他開始頻繁寫書,并以一年三四本的速度將其出版。2014年,他出版了《思想的浮冰》《再造傳統》等四本書。
劉東寫作很快,用他的同事、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的話說,“一個人能頂國學院半年的工作量”。劉東提到這時有點孩子氣般得意地笑了,“知道為什么嗎?”他問,隨即指指腦袋自答道:“因為準備得太充分了,這些書早都裝在這兒了!”
這時候,送水的人推門進來換水,剛剛還在探討學術的他趕緊拿了個大水杯,把剩下的純凈水都盛了出來。“別浪費了。”他說。
運動員、教練、裁判和領隊
盡管已經做好去三亞度假的準備,但要處理的事務仍然源源不斷。最熱鬧的是各種年底最值得推薦的書單、研討總結會議等等……劉東一邊念叨,一邊低頭處理郵件。十分鐘后,他抬起頭對記者笑笑,“有一個詞叫over socialization(過度社會化),我們大多數中國學者都有這個問題。”
大量的時間消耗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唯獨沒有時間做自己的主業。“這是一位學者要警惕的。”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副院長、中國兩大譯叢主編、博士生導師、業界著名學者,劉東發現自己也時常面臨“過度社會化”的危險。不必要的行政工作,院系工作必須的應酬,這些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
劉東用運動形容自己的學術生涯。運動員、教練、裁判、領隊,身兼數職。這天下午,劉東還要請他的博士生吃飯,他還帶了一大堆博士后。劉東講課時非常投入,這時,他就是教練的身份。作為兩個中國規模最大叢書的主編,劉東又變身裁判,哪些內容值得推薦出版,基本上是劉東說了算。
兩大譯叢給劉東帶來了盛名,但也偶有人批評他雜而不專。他喜歡編書,自己寫的書里“什么都談一點”,提倡“通識”,不像通常的路數,在學術上先占一個坑,“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吃老本一直到死。”
劉東為這兩套書花費太多時間,需要在市場和學術之間找到平衡,游說出版社一直做下去,這些都需要大量精力。
近期,學校的出版社讓他去做負責人,要變成文理綜合的出版社,“這都是領隊的事兒。”加在一起,“讓人很累。” 但劉東只想安安靜靜做運動員。2015年,他大概有四本書要出,他雄心勃勃地計劃寫一本希臘與中國的書,思考得差不多了,“大概能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
2009年,劉東從北大來到清華,清華大學高調成立國學研究院,這一新聞曾轟動一時,劉東任副院長。
清華國學研究院最初成立于1925年,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名。辦學四年,國學院畢業生近70名,其中50多人成為人文學界著名學者,四位教授被尊稱為國學院“四大導師”。
“為什么中國學者非得是上輩子賣命、
下輩子賣名呢”
劉東的辦公室很寬敞,滿滿幾大排書架,從傳統文化到哲學、醫學、音樂藝術,五花八門,什么都有。既是書架,也是書庫——每層外面一排擺放著劉東要讀的書,里面則密密麻麻地塞著他主編的叢書。
學術之外,劉東熱愛音樂,在南京大學讀書時,劉東曾是校文工團團長,因此有特權不上課。對付完學校的功課,其他時間,劉東自己大量讀書,“三四年級的時候,同學就知道我說話聽不懂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他在椅子上坐下來,那是一只功能椅,能舒服地半躺下來。劉東說自己一旦坐下就不想起來,因為擔心自己“萬一忘了下面那一句”。長年熬夜看書也讓他身體“到處都是毛病”。
劉東越來越感到自己身體的問題了,他跟陳來聊天,說別看大家現在看起來人形都挺好的,但其實都像個雪人,“不定哪天就漏點水”。他以極為戰戰兢兢的方式保養。每天吃三十種保健品,早上喝粥要有黑豆蓮子綠豆紅豆,“得有十幾樣”。
這一切不是因為怕死,是怕沒有完成。“上帝不會因為你有這么大學問就多給你一天,反而先把你的視網膜、坐骨神經先坐出來再說。”劉東在椅子上轉了轉胖胖的身體,哈哈大笑,“當然也不能這么說,要不孩子們都不做學問了。”
接受采訪的頭一天夜里,劉東剛看完《索爾仁尼琴傳》,看到凌晨兩點半。最觸動他的是,索爾仁尼琴拿到諾貝爾獎之后,又出版了《古拉格群島》。這對很多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諾貝爾獎是一個頂峰。
他以此對照國內學者。前些年他為自己主持的學術期刊《中國學術》征集稿件,向老朋友們約稿,一些人告訴他,年紀大了,自動為自己減少工作量,“大長篇的學術著作就不寫了”。
劉東不太明白,國外的同行七八十歲,還在認認真真寫作,中國學者基本上五十多歲就不寫了。“為什么中國學者非得是上輩子賣命、下輩子賣名呢?”
劉東自己想做的事情還很多。他曾想過要編一套1980年代叢書,趁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還活著,請他們來寫寫文章,回憶和反思當時方方面面的問題。比如他計劃請周其仁寫1980年代農村的改革。他想了幾十個選題,希望能借這套書發出一個警告,“那個時候我們其實走錯了,現在得重走”。
“我們現在中國發展的所有問題,都是那個時候提出還沒解決的。”他說。但根據眼下的形勢,這套書是做不出來了。劉東接下來最想寫的一本書是《中國與希臘》,分析比較這兩大文明的源頭,“希望能為我們找到一條可行的道路。”
劉東
著名學者。早年師從李澤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清華。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各洲。創辦并主持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