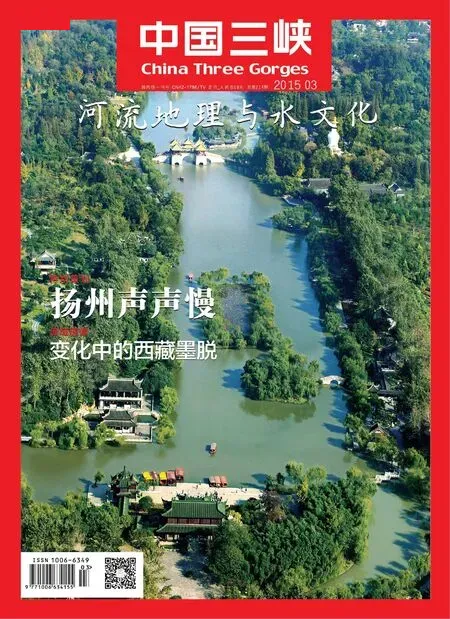揚(yáng)州訴話
揚(yáng)州訴話
一把扇,無舞臺,不化妝,無布景和音響,只需一襲長袍。一把折扇,一只醒堂木,一個人站臺上,歷史風(fēng)云、江湖恩怨就在抑揚(yáng)頓挫的揚(yáng)州方言中娓娓道來。去揚(yáng)州重寧寺,不為瞻仰“江南諸寺之冠”的百年名剎風(fēng)采,而是去揚(yáng)州曲藝團(tuán)見見平時只在古裝電影中才能看到的揚(yáng)州說書人。
才走進(jìn)寺門,咿咿呀呀的女子唱腔和嘈嘈切切的琵琶聲讓人尋聲望人。空曠的房間內(nèi),七八個年輕的女孩正抱著琵琶邊彈邊唱,歌聲和琵琶聲讓屋中兒女情長繞梁——揚(yáng)州戲曲評彈并稱,評話說的是英雄氣盛,彈詞唱的是兒女情長。

照片墻可以助人了解揚(yáng)州評話的歷史。在“昨夜星辰”分組中,排行第一個是王少堂的相片。“看戲要看梅蘭芳,聽書要聽王少堂”,早就聽過這句話,今日第一次見到評話宗師王少堂,不由仔細(xì)打量。一襲灰布長袍,張手甩開一把折扇,這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者,很符合我對評話藝人的想象。
正當(dāng)我準(zhǔn)備穿越到王先生說書的書場聽一場《武松打虎》時,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回頭一看,那是一位穿牛仔褲,手持iPhone的帥小伙,感覺臉熟,但又不知在哪兒見過。小伙子看出了我的迷惑,指了指相片墻,原來在“今日新星”分組中,他排行第一個,是青年藝人馬偉。
馬偉介紹,揚(yáng)州評話起源于明末清初,《柳敬亭傳》中所寫的說書先生柳敬亭是揚(yáng)州說書藝人公認(rèn)的祖師爺。揚(yáng)州評話興起之后,開始在江蘇、上海、安徽等地流傳,到上世紀(jì)中期出了揚(yáng)州評話史上宗師級人物王少堂,揚(yáng)州評話發(fā)展到巔峰。如今的揚(yáng)州評話,退守到揚(yáng)州,重出揚(yáng)州是王派第4代傳承人現(xiàn)階段的目標(biāo)。
1997年,馬偉決定報考揚(yáng)州曲藝團(tuán)。專業(yè)的評話藝人,演藝太苦,更重要的是當(dāng)時是揚(yáng)州評話最低潮的時期。之前在揚(yáng)州曲藝之友社,他把說書當(dāng)愛好,評話對他來說是新奇的,花幾天功夫背一個小段子,模仿說書藝人的動作擺幾個造型就會博得滿堂喝彩。然而,到揚(yáng)州曲藝團(tuán)后,說書就不再是一種興起而說、興敗下臺的愛好,變成了一門需要精益求精的藝術(shù),更成為了堅(jiān)守的事業(yè)。
做專業(yè)評書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背書。王派說書人的根基是《水滸傳》。一部《水滸傳》被王少堂按人物故事編成了《武松》、《宋江》、《石秀》、《盧俊義》四個“十回書”,每個王派說書人必須背得滾瓜爛熟。

左:慕名而來的外賓通過翻譯的講解觀看評話表演。

右:揚(yáng)州評話在表演時,根據(jù)劇情的不同,表演者會表現(xiàn)出各種夸張的表情和動作。
那時學(xué)藝不像現(xiàn)在用錄音筆記,用攝像機(jī)錄,師傅不允許用一點(diǎn)輔助手段,必須口傳心授。學(xué)藝的過程,徒弟痛苦,師傅也難受。但是這樣的記憶,一旦記住了,想忘也忘不掉。就像現(xiàn)在打字打多了,就不用看鍵盤,可以盲打了。評話藝人站在書場里,是沒有時間想臺詞的,必須張口就來。
馬偉背完四個“十回書”用了整整一年時間,終于進(jìn)入學(xué)藝的第二階段——表演,用身體去演示出書中的情景。當(dāng)表演得惟妙惟肖后再進(jìn)入第三階段——把二者重疊起來。
沒見過王少堂,從沒看過他的表演,是馬偉最大的遺憾,也是他最大的幸運(yùn)。遺憾,是因?yàn)闆]能和大師同場競技,少了提高的機(jī)會;幸運(yùn),是大師氣場太強(qiáng)大,他同時代的說書人都完全被他的氣場籠罩,這也算是揚(yáng)州評話一直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而馬偉從沒有這個顧慮。
華燈初上,老書客們早已泡好茶在揚(yáng)州甘泉路書場坐定,他們在等待今晚的評話表演。一個著中山裝的青年緩緩走出,手上沒拿折扇也沒醒堂木登場,說的內(nèi)容不是英雄豪杰也非江湖恩怨,而是名為朱懷鏡的現(xiàn)代人從升遷到最終被“雙規(guī)”的故事。這是馬偉歷時三年創(chuàng)作的長達(dá)100萬字的揚(yáng)州新評話《國話》中的內(nèi)容。馬偉認(rèn)為揚(yáng)州評話應(yīng)該借鑒海派清口的自由和即興,他將這部《國話》定位為“新編散打評話”。看來在經(jīng)歷了多年沉浸后,在評話新人身上,揚(yáng)州評話開始風(fēng)云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