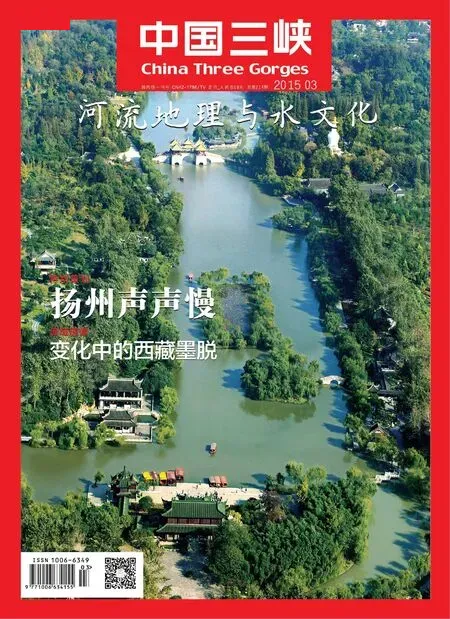達爾文的進化樹(三):畫一棵進化的樹
文/卡爾·齊默 譯/靳 萌 編輯/吳冠宇
達爾文的進化樹(三):畫一棵進化的樹
文/卡爾·齊默 譯/靳 萌 編輯/吳冠宇

丹麥格陵蘭島,塞爾米利克峽灣的冰山。 攝影/hemis/東方IC
珍妮·克拉克從丹麥格陵蘭島搬回來的一大堆巖石中,不僅有四足動物,也有魚類。1990年,她以前的學生兼野外工作助手珀·阿爾伯格(Per Ahlberg)把這些巖石帶到了他在牛津大學的新工作中。接下來的好幾年,他一直在研究一種鱗骨魚,它屬于肺魚較遠的親緣魚類。珀·阿爾伯格一直在研究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去格陵蘭島以前,他已經從博物館的抽屜里得到了許多化石,這些化石在那已經躺了好幾十年,一直沒有得到確認。當阿爾伯格來到牛津,他又把那里的抽屜打開了。那里有許多不知名的化石,都是在蘇格蘭朗莫爾伯恩沿岸的一個叫做斯坎特克雷格的地方挖掘出來的。阿爾伯格對這些化石都作了仔細的研究。這些骨頭都可以回溯到3.7億年前,比棘魚石螈和魚石螈還要早700萬年。
“這個地點是在19世紀20年代發現的,”阿爾伯格說道,“一些業余愛好者們在那20年里熱衷于這方面的收集。大概在那段時間人們就知道了在蘇格蘭存在著化石魚,甚至可以說蘇格蘭就是化石魚最后存在的地方。蘇格蘭到處都有這樣的業余愛好者,他們在斯坎特克雷格找到了一些殘骨,雖然這些骨頭是孤立的,但都保存得很好。很多化石都被收集起來,有關的文章也發表出來了。相關收藏品最后分散到了各個不同的地方。我發現在牛津有小部分的收藏品在歷時130年后還沒有被列入目錄。這是由伍斯特學院的院長和他的女兒在度假時收集的。他后來將此收藏品呈交給大學博物館的館長,還附上一份簡短的問候信,問館長的風濕病是否有點好轉。”

2014年5月,世界上首只試管企鵝寶寶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海洋世界出生,使用的是冷凍的精子,旨在使基因多樣性最大化。企鵝寶寶正在慢慢長大。 攝影/ZJAN/東方IC
阿爾伯格在仔細研究這些收藏品時,很快就發現里面有一條很不錯的鱗骨魚,于是他就專心研究起斯坎特克雷格的材料來,想要找出更多的鱗骨魚。“一旦開始一個標本接著一個標本的研究,我就不得不停下來考慮每一小片,”他說道,“一塊扁平的吻狀突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數的古生物學者也不太會注意這一細節,阿爾伯格之所以注意到了,是因為早幾年前他一直待在格陵蘭島的一座荒蕪的山上,想要弄明白他發現的骨頭到底是泥盆紀魚還是四足動物。所以現在他對一些模糊的東西特別敏感,比如說這些有著3.7億年歷史的吻狀突起。“如果你只接觸過后來的四足動物,那么當你看到斯坎特克雷格的東西時,你就會想到:‘哦,這就是魚。’”
阿爾伯格意識到,這塊吻狀突起的形狀說明它實際上是屬于四足動物的,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四足動物的骨頭。在抽屜中他發現了更多的四足動物的骨頭,而且不久后他就開始長途跋涉,在整個英格蘭和蘇格蘭境內尋找斯坎特克雷格化石的蹤跡。年復一年,他的收藏品越來越多,有下巴、吻狀突起、脛骨和一些股骨的碎片,這些東西都在櫥柜里藏了130年。他開始嘗試把這一動物(他把這個動物叫做埃爾金螈,是根據斯坎特克雷格附近的一個城鎮埃爾金命名的)重新還原,還原后的這個動物約有5英尺長,頭是尖的,腿是呈螺旋形的,像槳一樣,比棘魚石螈還要彎得厲害。
為了能看到連續的動態圖畫,古生物學者們不得不準確地描繪出這些動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現在是開始進行分類的時候了。
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已經確認的泥盆紀四足動物只有魚石螈,而現在四足動物中突然又有了一些諸如埃爾金螈之類的動物。這些化石不是孤立地向我們展示了泥盆紀的生命,實際上它們一步一步地向我們說明了四足動物的起源。但是為了能看到連續的動態圖畫,古生物學者們不得不準確地描繪出這些動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現在是開始進行分類的時候了。
分類有時候相當奇特。到底灌木之類的東西代表的是一個新種、新族、內部的一個新目,還是新亞綱,分類學家對此在私底下進行了爭論。后來分類學家意識到有些化石尾巴和外殼其實屬于同一種烏龜,但是卻有許多的名字。對于如何去除這些冗長的名稱,他們有一套嚴格的協定。如果田鼠下巴額外多了一顆牙齒,那這究竟是表明我們在研究一種新的種類呢,還是說這只是一種地域性的變種?在重塑生命歷史的過程中,分類學幾乎和動物標本制作術一樣至關重要。實際上進化生物學的主體正是依靠分類學而建立的。如果一開始就沒有對有機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精確地了解,那么就不可能明白新的有機體是如何形成的。
在近代生物學歷史中,分類學歷經了一些非常激烈的沖突。一些科學家,如瑞典的林奈(Linnaeus),以相似性為基點,把物種劃分到屬、目、科和更高的等級,但是在這個體系中,他們無法考慮到有機體之間是非常相似的這樣一個事實。有些有機體相似,或許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的物種原形;或許是因為它們形態相同,盡管互不相關。哺乳動物綱是由各種目組成的,如靈長目和嚙齒目,但是究竟哪些目之間聯系得更加緊密?哪些目最原始?后來生物學家終于明白其實分類學的模式就是進化的依據。自此他們就嘗試著把林奈和達爾文的觀點相調和。他們開始在不同的動物之間尋找相似性,無論是活著的動物,還是已成化石的動物,然后概略地描述出從物種原形到其后代的變化。做完這些,他們就可以畫出這些動物生命的世系圖了。從本質上來說,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就是人們如何用分類學去理解生物進化的。然而后來逐漸傳出一個關于德國昆蟲學家的消息。他叫威利·亨尼格(Willi Hennig),他寫了一本關于昆蟲分類的書,書非常難懂,在20世紀70年代被譯成英文。盡管此書不夠清晰簡潔,但是作者還是用自己的話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進行分類的新方法,而且人們可以對這種方法進行清楚的驗證。
在活著的蝴蝶中,只有這3種蝴蝶碰巧落在了你家門廊的屏風上。除非這3種蝴蝶是在同一時間從一個祖先進化而來(事實上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否則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是肯定有親疏遠近之別的。
假設你剛好遇到3只蝴蝶停在門廊的屏風上,翅膀輕輕地一張一合。其中一只蝴蝶的觸角較短,身體是紫色的,這種紫色讓人感到頭暈,它的翅膀是成蜘蛛網狀的。另一只蝴蝶觸角較長,顏色也是一樣的紫色,在每個翅膀的底端都有一個很大的斑點。還有一只蝴蝶的顏色也是紫色的,觸角也很長,在兩個翅膀的邊緣有一些紅色的雜斑。那么這些蝴蝶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它們都有一對翅膀,都是紫色的,讓人看得感到頭暈。它們的翅膀都有其獨特的模式。但是只有那兩個長觸角的蝴蝶才是相匹配的,那只短觸角的蝴蝶是被排除在外的。你可以像亨尼格那樣把這種相似性用譜系圖表現出來。現在你可以把它看做是視覺上的一種邏輯表示法,就像各個圓重疊起來的圖一樣。
既然這些蝴蝶都是自然的產物,也就是進化的產物,那么它們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祖先。那個蝴蝶祖先分化為許多種后代,而其后代又分化為更多的種類。在這過程中,新的特征得到發展,而一些舊的特征就消失了。許多種類絕種了,而在活著的蝴蝶中,只有這3種蝴蝶碰巧落在了你家門廊的屏風上。除非這3種蝴蝶是在同一時間從一個祖先進化而來(事實上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否則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是肯定有親疏遠近之別的。亨尼格宣稱,這就意味著這張邏輯表示法的譜系圖同樣也可以作為進化圖來使用,它說明了蝴蝶后代是如何分支演變的,是如何發展其獨特性的,比如說長長的觸角和翅膀的模式。
當然,進化也會開玩笑的。世系可以發展一種特性,然后又把這種特性丟失了。一些本來并沒有多大關系的動物會進化出相似的形態,其相似程度讓人吃驚。這些形態也許是由于在同樣的環境中過著同樣的生活,或者說因為它們的基因可變性都受到限制,所以可能產生出同一種的骨骼。也許那兩只有著長觸角的蝴蝶并不是同一個祖先的后代,但是它們各自長出了長觸角。為了克服這種生物學上的“詭計”,科學家們采用了我們熟悉的簡約原則。如果想研究一些生物體是如何進化的,他們就從與已知事實一致的最簡單的假設開始。這里所說的簡單是指,在尋找一張世系圖時盡可能涉及最少的進化步驟——要么是出現一種新的特征,要么是消失一種舊的特征——而同時仍然可以根據某些特性歸屬到同一物種。在3只蝴蝶的例子中,因為可以研究的物種和特性都很少,所以很難弄清楚它們真正的世系圖究竟是怎樣的。但是,如果科學家研究更多的物種和更多的特性,尤其是對正在討論的種群(如蝴蝶)和此種群以外的物種(如甲蟲和蚱蜢)進行對比,那么通常它們之間真正的關系就會顯得明了,而兩者的趨同就被覆蓋了。
亨尼格的進化樹是相當抽象的,僅靠這個圖譜,我們很難把一種物種和其特定的同一物種進行聯系。那只蛛網狀翅膀的蝴蝶比其他兩只蝴蝶,有著更久遠的源頭,但這不是說它就比那兩只蝴蝶更原始。在這一類的進化樹上,這兩大世系共同的同一物種只是作為一個部分為動物的聯系做準備。我們只能說,這3只蝴蝶共同的祖先可能就是一只紫色的長觸角的蝴蝶。同時這種進化樹也沒有包括其他從同一物種衍生下來的所有物種的分支。但是如果要解釋門廊屏風上的3只蝴蝶之間的關系以及生物進化是如何產生這種關系的,那么這種進化樹就足夠了。而其它的外延也足以用來建立一種新的生命分類了。

3只蝴蝶的進化分支圖
早期的分類學家因為大象都有各自獨特的特征,如象鼻和象牙,所以就將大象本身作為一個目。亨尼格的進化樹可以說明,其實這些象鼻和象牙都是出現在一種早就絕種了的原始大象的身上,是原始大象的后代繼承了這些特性。我們把大象歸入一個更大的群,這個群還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動物,如水獺、鼴鼠和人類,因為他們都有毛發,都是溫血動物,都進行新陳代謝,都有乳腺,以及其他特性。一句話,他們都是哺乳動物。沒有其他動物能夠表現出所有的這些特性,所以他們證明了所有的哺乳動物都是從同一物種發展而來的。在任何物種群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些特性只有一些動物才有,其他動物是沒有的,但是他們都享有一些比較原始的特性。根據進化世系對動物分類的方法,亨尼格使生物學家們遠離了林奈系統,走向了生命的分支,也就是進化支。他把他的進化樹稱之為進化分支圖。
就算你在同一個山坡鄰近的巖層中發現了兩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化石魚的物種,但還是不能說那個年代久一點的物種就是另一個的祖先。

德國錫沃斯多夫,一只蝴蝶棲息在公園里的一株花上。 攝影/Patrick Pleul/東方IC

站在一幅基因圖譜上的小雞。新的雞基因組將使基因定位變得更容易,尤其是反映復雜特性的基因。攝影/NRCS/FOTOE

進化樹
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發現了亨尼格的方法,即現在所說的遺傳分類學,他們覺得這比以前研究進化的方法更加清楚明了。遺傳分類學家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把他們所有的關于物種之間是如何聯系的假設一一羅列出來,按照特性來排列,而且這種排列的方式可以得到驗證。但就算是那些對遺傳分類學給予高度評價的人,在早期也是不喜歡畫進化分支圖的。他們不得不用紙和筆來勾畫這些圖,也就是把所有用最簡單的方式產生數據的步驟綜合起來,所以出現一種情況,那就是有關遺傳分類學的研究迅猛增長,讓人難以控制。如果你研究3只蝴蝶,就需要比較3種可能存在的進化樹,但是如果你要分析12只蝴蝶,那么就有可能存在上百萬種的進化樹。如果是分析100種蝴蝶(世界上有2萬種蝴蝶,100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你面對的進化樹比宇宙中的原子還要多。然而隨著圖靈機的出現,人們可以不用圖紙就制造出模型,這種理念大大推動了胚胎學的發展,也使得數學在新分類學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把進化樹分類的工作變得很簡單,這是計算機最擅長干的活了,我們只需眼睛盯在那里。生物學家可以下載一個關于遺傳分類學的程序,上面有關于許多物種的信息,這樣他就可以檢查這些物種的100塊甚至更多的骨骼,看清楚是否每一塊骨骼上都有某種斑點、某個腫塊,或者某些凹痕。計算機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細看那么多的所有可能的進化樹,而是通過統計學的捷徑找到幾百萬個最合適的進化樹作為備選,然后才從其中尋找最簡單的進化樹。
盡管一些古生物學者很快就開始從事遺傳分類學的研究,但是其中還是有很多人對此存有疑慮。遺傳分類學家在博物館里拋頭露面,講的都是一些深奧的行話,他們的字典里都是一些新詞。他們非常鐘愛自己的方法,雖然從他們的計算機里得出的結論經常只是證實了古生物學者已經知道了好幾十年的一些事實,但是遺傳分類學家還是想扔掉分類學的悠久傳統。一些遺傳分類學家甚至(錯誤地)聲稱化石與建立進化分支圖無關,因為與有血有肉的活著的動物相比,化石所能提供的特性太少了。
反過來,遺傳分類學家們認為他們在古生物學上的對立者中有許多人在對祖先的崇拜中迷失了方向,花了很多時間試圖準確地找出哪一種物種產生了哪一種物種,哪一綱起源于哪一種綱。但是我們從化石和活著的動物中得到的信息,從邏輯上講,還是不能告訴我們到底這種物種是另一物種的祖先,還是只是一種鄰近的分支。就算你在同一個山坡鄰近的巖層中發現了兩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化石魚的物種,但還是不能說那個年代久一點的物種就是另一個的祖先。遺傳分類學家認為,與其去追隨這些夢想,還不如去發現一種組成生命最客觀、最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方法,這才是更重要的事。
如今遺傳分類學在古生物學中已經是一個權威的工具了,盡管在博物館的大廳里你還會聽到有人抱怨它內容貧乏。遺傳分類學確實只是驗證了一些已經確定了很久的觀點,但同時古生物學家還用它去解決一些有爭議的關系,并支持某些觀點。比如說,鳥類一般被認為是從像鱷魚的爬行動物進化而來的,但實際上它們就是長著翅膀的恐龍。遺傳分類學就是支持這一觀點的。遺傳分類學家正工作在動物王國中,隨著他們的計算機不斷得出大量的數據,一個新的長滿進化論小樹苗的小樹林正在形成。隨著人們發現越來越多的泥盆紀四足動物,古生物學者們已經開始建立進化分支圖,這些分支圖也包括了動物的變遷。這幅著名的進化分支圖采用了最簡單的形式,是由邁克爾·科茨計算出來的。他把18種四足動物身上的76種不同特性的信息輸入計算機。為了能讓人們理解這一進化分支圖究竟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分支的,他把動物化石的年齡寫在了分支上,從而形成了進化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