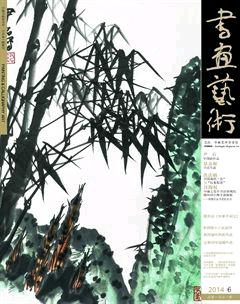人生因藝術(shù)追求而美好
盧炘

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中國(guó)畫(huà)系85年以來(lái),可謂孕育中國(guó)畫(huà)人才最有效率的搖籃,任憑社會(huì)政治、各種意識(shí)形態(tài)以及來(lái)自經(jīng)濟(jì)的波動(dòng),教學(xué)也幾經(jīng)顛簸,但她的母性不變,在這里畢業(yè)的學(xué)生總是接受了比其他院校和場(chǎng)所更多的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奶汁。尤其是上世紀(jì)60年代在潘天壽先生執(zhí)掌期間,潘天壽、吳茀之、諸樂(lè)三、顧坤伯、陸抑非、陸儼少、陸維釗等名教授親自執(zhí)教,學(xué)生于繪畫(huà)思想、筆墨技法、創(chuàng)作理念打下的全面基礎(chǔ)和正規(guī)訓(xùn)練,足以讓后來(lái)者欣羨。歷數(shù)如今的名畫(huà)家那幾屆畢業(yè)生最多,即使回到小縣城教中學(xué)美術(shù)或者搞文化館群眾美術(shù),他們也表現(xiàn)得與眾不同。尤其是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的30多年,他們?cè)诟鞯孛佬g(shù)界的凝聚力和影響力誠(chéng)非小覷。
王秉初先生就是“回到小縣城教中學(xué)美術(shù)或者搞文化館群眾美術(shù)”頗為低調(diào)的中國(guó)畫(huà)家中的一位,不在北京、上海、杭州這樣的大城市,也不在美術(shù)高等院校任教,當(dāng)然比不得居高位叱咤風(fēng)云的大畫(huà)家,然而他們對(duì)藝術(shù)的追求始終不渝,身兼著地方縣市的畫(huà)院院長(zhǎng)或僅僅是普通的美術(shù)工作者,同樣成果斐然讓人感佩和敬重。
王秉初先生有過(guò)高等美術(shù)院校任教的機(jī)會(huì),那是文革后福建泉州華僑大學(xué)藝術(shù)系缺少傳統(tǒng)花鳥(niǎo)畫(huà)教師,請(qǐng)浙江美院的老師推薦人選。1987年4月7日著名花鳥(niǎo)畫(huà)家朱穎人老師親筆修書(shū)推薦王秉初前往就職,并發(fā)信通知在嵊縣鄉(xiāng)村教中學(xué)的王秉初。華僑大學(xué)為國(guó)務(wù)院僑辦直屬的副部級(jí)大學(xué),各方面條件都很好。藝術(shù)系江松老師5月29日專函告知,除朱老師以外,還有曾宓、陸秀競(jìng)等先生也推薦他,認(rèn)為其“作品質(zhì)量很高,留在中學(xué)教可惜了”“不能再拖了”“華大氣候等條件均很好”,很歡迎他去。然而,當(dāng)時(shí)王秉初擔(dān)心自己離開(kāi)家鄉(xiāng)老母親無(wú)人照料放不下心,婉言謝絕正式調(diào)動(dòng),只是去教過(guò)兩個(gè)月的課。就這樣44歲的王秉初與高等美術(shù)教育崗位失之交臂,依然留在了嵊縣。
王秉初,原名王炳初,1962年入學(xué)浙江美院中國(guó)畫(huà)系。當(dāng)年招的學(xué)生很少,一個(gè)專業(yè)往往只有五六個(gè)學(xué)生,他與姜寶林、李延聲、李子侯、馮運(yùn)榆、俞建華、徐君陶、陸秀競(jìng)、郭志光、王含英等為國(guó)畫(huà)系同學(xué),油畫(huà)系潘鴻海、王慶裕、顧盼,版畫(huà)系王兆達(dá)等也為同屆同學(xué),如今個(gè)個(gè)名馳藝苑和出版界。1994年書(shū)法家俞建華先生曾撰寫回憶文章,稱贊王秉初入學(xué)前已有“嫻熟畫(huà)技”,曾得到美院學(xué)長(zhǎng)、他的鄉(xiāng)賢“商敬誠(chéng)先生的悉心指點(diǎn)”,來(lái)到美院“好像是一條終于歡泳于大海之中的山澗之魚(yú),在自己的眼前展示了一條騰化之路。那些心高氣傲的同窗們,不管出身貧富、不論才具利鈍,無(wú)不為他一手嫻熟的陳白陽(yáng)筆墨所折服。”甚至比他高一級(jí)的同學(xué)也知道他基礎(chǔ)特別好,花鳥(niǎo)畫(huà)家徐家昌先生就親口對(duì)我說(shuō)起過(guò),贊口不絕。
在校那些年他們是幸運(yùn)的,教師力量很強(qiáng),章培筠教基礎(chǔ)課白描,陸抑非教沒(méi)骨花鳥(niǎo)和兼工帶寫,諸樂(lè)三教大寫意花鳥(niǎo),陸維釗剛從杭州大學(xué)調(diào)到美院教他們書(shū)法。其時(shí)“潘天壽畫(huà)展”在京舉辦,花鳥(niǎo)畫(huà)又得到重視,且有“陸志庠、葉淺予、黃胄速寫展”和石魯帶長(zhǎng)安畫(huà)派來(lái)院辦畫(huà)展,南京傅抱石先生被請(qǐng)來(lái)講課,李長(zhǎng)白先生也來(lái)教過(guò)一學(xué)期他們的工筆課,與全國(guó)其他美術(shù)院校相比,此時(shí)浙江美院的學(xué)習(xí)氛圍是不錯(cuò)的。
時(shí)至大四,遭遇文革,停課鬧革命,推遲畢業(yè),他們那屆竟然在校度過(guò)了7個(gè)年頭。王秉初生性憨厚,在運(yùn)動(dòng)中不善拋頭露面,他選擇了抄寫大字報(bào)的任務(wù),又背地里悄悄臨摹古帖練書(shū)法,俞建華說(shuō)他當(dāng)時(shí)迷上了蒼涼雄健的顏真卿行書(shū),所耗白紙二三百斤。他還從同學(xué)馮運(yùn)榆那里借閱羅曼·羅蘭的名著巨人三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書(shū),所以受到當(dāng)時(shí)進(jìn)駐美院的工宣隊(duì)的嚴(yán)厲批評(píng),成了全校有名的逍遙派。
畢業(yè)后王秉初分配天臺(tái)縣文化館,4年后調(diào)回嵊縣(即今嵊州)在鄉(xiāng)間中學(xué)任教。文革結(jié)束美院恢復(fù)招收研究生,專業(yè)老師勸他報(bào)名,認(rèn)為憑他扎實(shí)的基礎(chǔ)準(zhǔn)能考上,可他也是不愿離開(kāi)老母親而放棄了。故此,朱穎人先生與我談起王秉初,第一句話就說(shuō)他是個(gè)孝子,也深為其可惜。
王秉初就這樣錯(cuò)過(guò)考研究生的機(jī)會(huì),直到1984年才有了轉(zhuǎn)機(jī)。他在當(dāng)?shù)匾皇洲k起了一個(gè)工藝美術(shù)班,后來(lái)又辦了木雕班和服裝班,后來(lái)改為嵊州工藝美校。至今嵊州作為全國(guó)根雕之鄉(xiāng),二三百家根雕企業(yè)的專業(yè)人員絕大多數(shù)出自他的那所學(xué)校,嵊州的中學(xué)美術(shù)教師也多數(shù)出于此。正因?yàn)楣Σ豢蓻](méi),1993年他被調(diào)到市教師進(jìn)修學(xué)校,并被選為嵊州市政協(xié)副主席,兼職10年,直至退休。
步入古稀之年的王秉初現(xiàn)為浙江省花鳥(niǎo)畫(huà)家協(xié)會(huì)主席團(tuán)成員、藝委會(huì)委員、浙江省嵊州市政協(xié)書(shū)畫(huà)院院長(zhǎng),與他的老同學(xué)一樣,他們依然活躍于畫(huà)壇,聯(lián)展、個(gè)展不斷。交談中我發(fā)現(xiàn)每當(dāng)談及深入生活和創(chuàng)作,那種一往深情的眼神和天真燦爛的笑容,足以撼動(dòng)對(duì)方。當(dāng)一個(gè)畫(huà)家是多么快樂(lè),宇宙在于手,幸福便在筆下。
早在1973年他的作品六尺整張的工筆花鳥(niǎo)畫(huà)《公社新渠道》引起美術(shù)界關(guān)注,畫(huà)面六只大白鵝,姿態(tài)各異地暢飲抽水機(jī)泵出的清泉,以動(dòng)物的歡快表現(xiàn)公社社員的喜悅。此作后來(lái)他與何水法又合作畫(huà)過(guò)一次,發(fā)表于《工農(nóng)兵畫(huà)報(bào)》,并送北京飯店陳列。有趣的是此件2005年西泠秋拍,收藏者將落款作了挖補(bǔ),單獨(dú)以何水法的名義拍出了高價(jià)。
1994年王秉初的《墨梅》入選八屆全國(guó)美展,1998年《荷花》獲浙江省中國(guó)畫(huà)小品展金獎(jiǎng),2000年《金銀花》獲浙江省第二屆中青年花鳥(niǎo)畫(huà)展銀獎(jiǎng)。其個(gè)展先后于杭州、廣州、蕭山、紹興等地舉辦,他本人隨書(shū)畫(huà)代表團(tuán)出訪日本等國(guó),有《王炳初畫(huà)集》《中國(guó)畫(huà)二十家?王炳初》等專輯多種出版。
2011年,他捐獻(xiàn)作品數(shù)十件,天臺(tái)博物館為之特設(shè)“王炳初花鳥(niǎo)畫(huà)陳列室”常年對(duì)外開(kāi)放。
對(duì)于中國(guó)畫(huà)的發(fā)展,百余年來(lái)總是爭(zhēng)論不斷,有“變革者”主張中西融合以“彩墨畫(huà)”代之,有 “改良者”訴之于“新水墨”拓展,也有“堅(jiān)守者”重視固本傳統(tǒng)而以傳承創(chuàng)新為宗旨,當(dāng)然也不乏全盤否定的“廢棄論者”,揚(yáng)言中國(guó)畫(huà)已氣息奄奄窮途末路。相對(duì)于作品實(shí)踐,種種論爭(zhēng)必須有所依附,得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的支撐、印證,否則誰(shuí)也說(shuō)服不了誰(shuí)。當(dāng)今中國(guó)畫(huà)理論爭(zhēng)執(zhí)尚未到可以引領(lǐng)繪畫(huà)實(shí)踐發(fā)展而讓人信服的時(shí)候。
王秉初數(shù)十年來(lái)一方面從事基礎(chǔ)教育,貢獻(xiàn)有目共睹,為專業(yè)院校輸送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他個(gè)人的創(chuàng)作亦大有可觀之處,當(dāng)刮目相看。往大處說(shuō),中國(guó)畫(huà)之所以有扎實(shí)的群眾基礎(chǔ)和良好濃郁的氛圍,與基層美術(shù)工作者關(guān)系甚大。王秉初沒(méi)有寫過(guò)什么理論討論的文章,但不等于他不關(guān)心這場(chǎng)討論,他是畫(huà)家,他是以實(shí)際的作品說(shuō)話,用這種方式參與了中國(guó)畫(huà)發(fā)展方向的大討論。
此次出版畫(huà)冊(cè),王秉初執(zhí)意傳統(tǒng)花鳥(niǎo)畫(huà)的作品一律不收,工筆花鳥(niǎo)以后也不會(huì)再畫(huà)了。倒不是跟傳統(tǒng)過(guò)不去,而是認(rèn)為那些作品是自己學(xué)習(xí)中國(guó)畫(huà)的階段成果,現(xiàn)在他要拿出后階段新東西給大家看,聽(tīng)取意見(jiàn),請(qǐng)老同學(xué)和美術(shù)界同仁品評(píng)。
考察王秉初的藝術(shù)道路基本可分三個(gè)階段:
第一階段,學(xué)習(xí)傳統(tǒng)繪畫(huà),打?qū)崌?guó)畫(huà)基礎(chǔ)。
少年王炳初師承本地商敬誠(chéng)先生,學(xué)陳白陽(yáng)、周之冕一路。白陽(yáng)擅水墨大寫意,與徐渭并稱為“白陽(yáng)青藤”;周之冕則以勾花點(diǎn)葉著世。商敬誠(chéng)師1946年入學(xué)國(guó)立藝專,與朱恒有(朱恒)同班,得潘天壽、黃賓虹親炙,畢業(yè)后一直執(zhí)教于嵊縣長(zhǎng)樂(lè)中學(xué),為家鄉(xiāng)培養(yǎng)了許多繪畫(huà)人才,除了王秉初,曾任浙江省文聯(lián)黨組書(shū)記、主席,省美協(xié)副主席、浙江畫(huà)院名譽(yù)院長(zhǎng)的花鳥(niǎo)畫(huà)家張浩也是他長(zhǎng)樂(lè)中學(xué)的學(xué)生,浙江美院曾有意調(diào)商敬誠(chéng)回校任教亦未能成行,其畫(huà)筆墨老辣,自成風(fēng)格,其人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王秉初1962年考入浙江美院中國(guó)畫(huà)系,那一手嫻熟的陳白陽(yáng)花鳥(niǎo)令同窗欣羨自然不足為奇了。大學(xué)里他接受了更加嚴(yán)格的傳統(tǒng)國(guó)畫(huà)教學(xué),后來(lái)著迷于吳昌碩的大寫意筆法,追求氣勢(shì)雄強(qiáng),古拙渾厚,書(shū)法則攻顏真卿一路。所以他既有《公社新渠道》一類工筆畫(huà),也有入選全國(guó)美展的《墨梅》一類傳統(tǒng)大寫意花鳥(niǎo)作品,至此為王秉初習(xí)畫(huà)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研習(xí)民間藝術(shù),染指西方畫(huà)法。
文革期間的鄉(xiāng)村中學(xué),教師匱乏,課程刪減,美術(shù)被其他學(xué)科擠壓,王秉初教語(yǔ)文、又教歷史、地理等多門課程,甚至用鋼板刻了兩年蠟紙,將近11年沒(méi)有畫(huà)畫(huà)。其實(shí)一點(diǎn)也不奇怪,那個(gè)時(shí)期專業(yè)人才幾乎都有類似的經(jīng)歷。可喜的是,他沒(méi)有忘記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特長(zhǎng),1984年由于市場(chǎng)有需求,他在石璜中學(xué)辦起了工藝美術(shù)班,這在省內(nèi)尚無(wú)先例,招生、考試、錄取等均由他一手操辦。接著木雕班、服裝班一個(gè)個(gè)都辦了起來(lái)。經(jīng)過(guò)一些美術(shù)訓(xùn)練的學(xué)員在社會(huì)上尤其是藝術(shù)產(chǎn)業(yè)中有明顯的優(yōu)勢(shì),因而越辦越紅火,石璜中學(xué)也一度更名為嵊州市工藝學(xué)校。王秉初為學(xué)生設(shè)立三門課:素描、色彩和圖案。
其實(shí)王秉初在浙江美院中國(guó)畫(huà)系當(dāng)學(xué)生時(shí)并沒(méi)有花時(shí)間學(xué)過(guò)素描、色彩和圖案,此時(shí)促使他開(kāi)始了邊學(xué)邊教;同時(shí)接觸了大量民間藝術(shù)。沒(méi)想到這次染指西畫(huà)和“問(wèn)津于門神、木雕”卻對(duì)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影響,當(dāng)他重新拿起毛筆時(shí),思考如何使傳統(tǒng)花鳥(niǎo)畫(huà)有新的面貌,西方繪畫(huà)和民間藝術(shù)就給了他豐富的養(yǎng)料;而且構(gòu)圖形式和色彩開(kāi)始有了新的感覺(jué),民間木雕、工藝的裝飾因素慢慢呈現(xiàn)于畫(huà)面。這第二個(gè)階段對(duì)于王秉初來(lái)說(shuō)也還是采蜜作繭的階段,他什么都畫(huà),甚至于借鑒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嘗試搞些特技,在墨水中加洗衣粉或洗潔精,然后施以潑墨潑水,讓墨韻呈現(xiàn)意想不到的肌理效果。有新意也有失意,種種嘗試展現(xiàn)了他求新的欲望,卻并未找到滿意的路子,他摸索著踽踽獨(dú)行,時(shí)而向前,時(shí)而倒退,依然是迷茫。何時(shí)才能覓見(jiàn)希望的曙光,他等待著破繭成蝶。我覺(jué)得王秉初自己有一段話也許可以概括其一、二兩個(gè)階段,這是他二十年前第一本個(gè)人畫(huà)集扉頁(yè)寄言:“奔走于老缶門下,問(wèn)津于門神、木雕。百姓有諺:‘羊百草。我就是這樣一只羊。”王秉初生于1943年,正是癸未羊年,也算得是一頭倔強(qiáng)的老公羊了。
不滿足于傳統(tǒng)梅蘭竹菊畫(huà)法的金科玉律,王秉初開(kāi)始擴(kuò)展視野,注意審美發(fā)現(xiàn)。這個(gè)階段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他的荷花系列,用畫(huà)面記錄“藕花深處”之妙。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李清照的名句,“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zhēng)渡,爭(zhēng)渡,驚起一灘鷗鷺”。那種“日暮”“沉醉”“不知?dú)w路”的感受,甚至于小舟誤入茂密的荷干蓮葉下面,忽然間滿眼的綠,醒目的荷,白的紅的,飽滿、嬌嫩、水珠欲滴,還有那禽鳥(niǎo),靜棲的、驚飛的。無(wú)論是花朵還是想象中靜居其間的禽鳥(niǎo),這畫(huà)面的主體分明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墨寫的荷葉枝干縱橫交錯(cuò),大片的黃色、橘紅色是荷叢外面的陽(yáng)光,有日落的斜輝,也有正午的驕陽(yáng),還有陰天蓮葉蔽日的石綠色調(diào)以及秋風(fēng)乍起的通透之感。花亦自有含苞待發(fā)者,或正值怒放者,同樣還有殘秋余馥的低頭者。林林總總,各有情趣,又取了不同的畫(huà)題:《秋光爛漫》《蓮風(fēng)遽起》《翠帷半窺》《葉底熏風(fēng)》《雨潤(rùn)芳姿》《殘秋余馥》《鬧紅一舸》《香韻秋池》《蓮塘霞光》,全是人的感覺(jué)。同樣翠鳥(niǎo)有伺獵撲食者,則取畫(huà)題《深溪伺獵》;休憩安詳而雙雙成對(duì)者,則取《秋波儷影》;泛游成雙者自然得其名《葦塘雙泛》。
這里傳統(tǒng)花鳥(niǎo)畫(huà)的借喻、移情、寓意及擬人化的手法都用上了,但形式是新的,章法上四面出枝、層出不窮,筆墨也頗為豐富,色彩也更艷麗了。所以此類作品不乏形式感、現(xiàn)代感,沒(méi)有不中不西的感覺(jué),與傳統(tǒng)似曾相識(shí),與西畫(huà)若即若離,十分巧妙。
第三階段,涉足熱帶雨林,捕捉造化神功。
古人云“讀萬(wàn)卷書(shū),行萬(wàn)里路”,藝術(shù)家必須到大自然中到生活中去尋找生機(jī),捕捉美感。2000年他隨商敬誠(chéng)先生應(yīng)邀出席海口的“全國(guó)二十個(gè)城市畫(huà)家寫生暨展覽”活動(dòng),第一次南行,王秉初立刻被海南島的植物所吸引。那種熱帶雨林所特有的植被,茂密濃重,色彩艷麗,搖曳多姿,與他家鄉(xiāng)迥然有別。他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作的沖動(dòng),努力捕捉熱帶叢林中的原生態(tài)的美感,畫(huà)了許多寫生作品。正是這次南國(guó)之行改變了他的畫(huà)法和題材,看似偶然其中卻蘊(yùn)含著必然的成分。
他意識(shí)到轉(zhuǎn)機(jī)來(lái)了,于是接二連三南下采風(fēng),福建、云南、海南、泰國(guó)、老撾、緬甸,幾乎每年去一次,至今已愈13個(gè)年頭了,退休給他帶來(lái)了諸多方便。他身臨其境,感受大自然的奧妙,鉆進(jìn)了遮天蔽日的叢林,尋找各種美的感覺(jué)和趣味,妙悟通常難以觸摸的神秘,拍攝了上萬(wàn)幀照片,收集了各時(shí)間段,各種不同植物的生長(zhǎng)圖片和資料。在深圳他又買到兩本攝影集,在圖片時(shí)代當(dāng)然不能拒絕享受時(shí)代帶來(lái)的便捷,他的兒子成了自己最好的助手和搭檔,父子倆興趣相同,浸潤(rùn)其里,樂(lè)在其中。
王秉初選擇了熱帶蘭、榕樹(shù)、木棉等作為新的畫(huà)材。其實(shí)這種題材過(guò)去也有人畫(huà)過(guò),譬如賴少其先生晚年在廣州就有相當(dāng)精彩的作品,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展覽,也沒(méi)有出畫(huà)冊(cè),一般人并不知道。王秉初決意要畫(huà)出熱帶植物的神韻和大自然的神功,他開(kāi)始采用兼工帶寫的技法進(jìn)行表現(xiàn),不過(guò)癮,最后還是走大寫意的道路。他原本就具吳昌碩以金石書(shū)法入畫(huà)之長(zhǎng),對(duì)顏真卿行書(shū)筆意也有研究,所以揚(yáng)長(zhǎng)避短,求異求變。
他借西畫(huà)的滿構(gòu)圖特點(diǎn),力求飽滿充實(shí)而一變傳統(tǒng)花鳥(niǎo)的的清靈明豁;取方構(gòu)圖,改變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長(zhǎng)寬比例;往往取一個(gè)局部而不是全景,增加裝飾性現(xiàn)代感;并借鑒山水畫(huà)的技法,還用了花鳥(niǎo)畫(huà)不經(jīng)意的許多山石皴法,有皴有擦,用積墨表現(xiàn)肌理;用色大膽,常常是大塊石綠、桃紅、藤黃的映襯,絢爛而不艷俗。總體感覺(jué)作品氣格碩大,厚重強(qiáng)烈,有震撼力,特具自己的面目。他既不是吳昌碩、齊白石一路,也不是揚(yáng)州八怪、徐青藤一路,自然亦非潘天壽的路子。他與他的同學(xué)全部拉開(kāi)了距離,因此2012年10月同屆同學(xué)在母校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館展出時(shí),在眾多名畫(huà)家的優(yōu)秀作品中他的作品顯得特異、鮮明,學(xué)生時(shí)代的王炳初畫(huà)風(fēng)已面貌全非,而性格還是那樣內(nèi)向,不善言辭。
著名美術(shù)史家王伯敏先生早就贊其“筆致奔放,亂而不亂;似不經(jīng)意,而又極經(jīng)意,得如此上乘之法,實(shí)在不容易。”學(xué)長(zhǎng)盧坤峰先生曾評(píng)其畫(huà):“用墨用色不拘泥一草一花的濃淡變化,而講究大塊的黑與白、疏與密、粗與細(xì)、冷與暖的對(duì)比,畫(huà)面有一種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效果。在章法上突破了前人的陳規(guī),經(jīng)常是四面出枝,畫(huà)面豐富飽滿,給人以意境開(kāi)闊、布局完整之感,很不容易。”
如今老同學(xué)相見(jiàn)更是欣喜,姜寶林深情地說(shuō):“他的大寫意更放了,筆畫(huà)更精到了,語(yǔ)言更豐富了,手法更多樣了,形式更現(xiàn)代了。古人云,人品既高,畫(huà)品不得不高。王炳初即是。”著名花鳥(niǎo)畫(huà)家何水法也稱其作品:“頗具生命力,顯得生動(dòng)而豐富有逸趣。”
有一位80多歲的花鳥(niǎo)畫(huà)老教授把他拉到邊上,悄悄地說(shuō):“你應(yīng)該到北京去辦個(gè)展。”王秉初還是笑笑,搖搖頭。但王秉初是明白人,他說(shuō)過(guò):“我的創(chuàng)作遠(yuǎn)未結(jié)殼,現(xiàn)在正處于成熟期,未來(lái)五年,我將專心繪事,創(chuàng)作出系列大作品。”說(shuō)得對(duì),他的創(chuàng)作沒(méi)有結(jié)殼。他說(shuō)潘老的畫(huà)不敢學(xué),風(fēng)格太強(qiáng),齊白石也一樣,學(xué)了不容易跳出來(lái)。但我認(rèn)為他還是學(xué)了,學(xué)潘天壽他學(xué)的是精神,譬如潘天壽的雁蕩山花,擺脫了傳統(tǒng)花鳥(niǎo)畫(huà)譜的局限,從表現(xiàn)折枝花卉走向表現(xiàn)大自然中花鳥(niǎo)山水的生機(jī)勃勃。王秉初也注重自然造化的展現(xiàn),特別是著力于局部的原生態(tài)表現(xiàn),盡力捕捉造化神功,巧奪天工展現(xiàn)大美。
他的作品印成畫(huà)冊(cè)似乎尺幅不大,其實(shí)除了四尺對(duì)開(kāi),六尺對(duì)開(kāi),也有橫卷三四米長(zhǎng)的,甚至五米寬二米高的巨幅,這些作品更是氣勢(shì)磅礴,氣韻生動(dòng)。其中《雨林深處系列》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畫(huà)了又畫(huà),仍然意猶未盡。
當(dāng)然,也有論者認(rèn)為他“整體上并未完全擺脫商、吳兩大畫(huà)派對(duì)他的影響,而達(dá)到一種自由的表達(dá)境界”;可有的卻認(rèn)為他已經(jīng)放開(kāi)了,重要的是有些局部粗糙了些;有同學(xué)希望他在畫(huà)中再增加些書(shū)法用筆的長(zhǎng)線條,用最傳統(tǒng)的筆墨來(lái)表現(xiàn),這本來(lái)就是他的長(zhǎng)處;也有人以文人畫(huà)的要求希望他在詩(shī)文傳統(tǒng)國(guó)學(xué)方面再豐厚自己。對(duì)于這些善意的提醒他十分感謝,但按他的性格,我想凡是符合既定目標(biāo)的他會(huì)吸取,反之則一如既往。
所以,有一位花鳥(niǎo)畫(huà)學(xué)長(zhǎng)、著名花鳥(niǎo)畫(huà)家看他的展覽先后來(lái)了三次,沒(méi)多講,臨別說(shuō)了三個(gè)字:“畫(huà)下去。”這正是我也想說(shuō)的,繼續(xù)畫(huà)下去,盡其所能捕捉造化神功,并以此來(lái)作為本文的結(jié)束語(y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