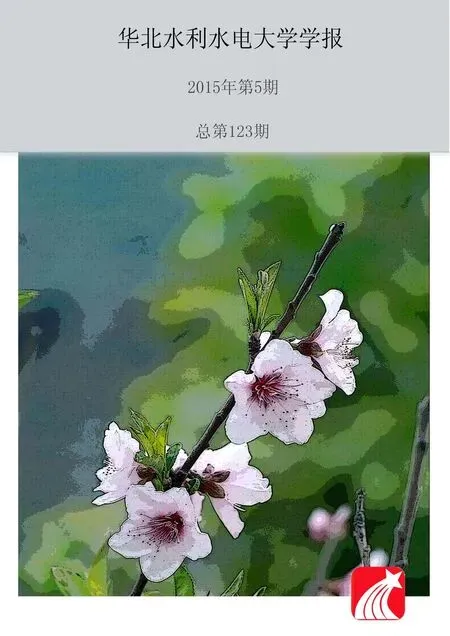賈平凹筆下“瘋子·女神·城里人”的敘事模式
——以《商州》《秦腔》為例
黃鋆鋆
(鄭州大學文學院,河南鄭州450001)
賈平凹筆下“瘋子·女神·城里人”的敘事模式
——以《商州》《秦腔》為例
黃鋆鋆
(鄭州大學文學院,河南鄭州450001)
“瘋子·女神·城里人”是賈平凹鄉土小說中所開創的一種獨特模式。寄寓著鄉土之美、傳統文化的女神,在代表鄉村非理性、丑陋一面的瘋子和“農裔城籍”的城里人之間進行的選擇,也是現代社會中以賈平凹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面對城鄉所進行的自覺的價值選擇——拋棄鄉土、入贅城市。這一選擇所面臨的直接后果便是無根和失落。這不僅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更是鄉土和文化本身的悲劇。
賈平凹;女神;城鄉選擇;農裔城籍
賈平凹是當代文壇中最貼近“中國之心”和“中國精神”的作家,也是一位不斷超越自己,永遠在探索和前進中的作家。他的鄉土書寫為我們提供了真實鄉村日常生活的盛宴,把鄉村的存在和可能性展示給我們看,并在此間將外在自然和內在自然(人性)融為一體,向鄉土中國的精神內核無限靠近。但在多產和探索中,他的創作常出現某些固定的模式,比如女性形象的單一化、情節結構的定型化等。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一女二男的敘事結構。而在一女二男中,又以“瘋子·女神·城里人”最為典型,也最能表現賈平凹對鄉土之根尋找的失落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漂泊、無根無依的狀態。
《商州》是賈平凹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分為鄉土文化和鄉土選擇(即地方志與故事)兩部分,呈現出尋覓鄉土之根的焦慮和失落。在其新世紀的大作,被譽為“鄉土文學的絕唱”《秦腔》中,鄉土的衰落和故鄉的喪失讓“農裔城籍”的知識分子呈現出更深的絕望和更大的悲劇感。毫無例外,這兩部作品的悲劇感與鄉土社會沒落的無奈都間接地由“瘋子·女神·城里人”的敘事模式隱現出來。女神對男性的選擇也成為鄉土文化的美神對鄉村與城市的選擇的一種隱喻。
一、“瘋子·女神·城里人”的敘事模式
女神的形象是賈平凹筆下不變的堅守,也是他“地母情結”的一種顯現。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如師娘(《天狗》)、小水(《浮躁》)、珍子(《商州》)、白雪(《秦腔》),都是鄉土培育出的美的精華,作家把自己心中所有關于美的定義統統賦予她們,她們“都有美麗而博大、神圣而苦難、平凡而難以企及的特征,是男主人公為之奮斗的動力和苦難遭遇的避風港。……她們是賈平凹創作中的生命力顯示”[1]。“瘋子”們則是土生土長、又有缺陷的一群農村人,嚴格來說,他們并不都是一般意義上的“瘋子”,卻都有著瘋狂和癡傻的特質,是原汁原味的、非理性的、甚至是丑陋的鄉土的孩子。至于城里人,則是一群非城非鄉,表面打著城市標簽的精神漂泊者。他們或被城市放逐,或被鄉村驅逐,成為無根的一代,也是“農裔城籍”的作家的化身。
這三種形象構成了三角戀的結構:瘋子癡情地追隨女神,而女神所愛的卻是優越的城里人。但最終,女神的選擇并未給自己帶來幸福,傳統文化也終究在城市和鄉村的選擇中陷入失落和無奈。
(一)《商州》:禿子——珍子——劉成
在《商州》里,賈平凹沿著河流地勢,從根上梳理了故鄉所在的商州地區文化,然后向著省城西安返回。雖說是尋根之旅,可作家所托身的“后生”走的卻是一個“離城——去鄉——回城”之路,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城市。剛剛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知識分子從農村走出,在向往的城市安身立命,
久之,便成了圈在籠中的鷹,即使被放歸,也不能在天空中獲得歸屬感。那么,拋棄故土的知識分子就真的能尋回自己的根嗎?
在作家和讀者皆為之癡迷的商州,賈平凹構造了一個禿子——珍子——劉成的三角戀愛故事。我們以為商州的鄉土人文風情就是賈平凹尋到的根,但他卻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寫了一個“不相干”的故事。在這故事中,城與鄉的對比在人物角色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劉成擔當起從城里歸來的“農裔城籍”的城里人角色,與返鄉的“后生”腳步相接,也是喬裝的作者本人。他有錢、帥氣,但也沖動、缺乏原則。與之相對的,是來自農村的禿子,丑陋、猥瑣卻癡情、無私。他頭上鮮明的癩疤正如鄉土之根的皴皮。這又老又丑的禿子卻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珍子,為保護搭夜車去城里找劉成的珍子,他失去了自己最寶貴的伴侶——黃狗。女神珍子來自自古出美女的山陽,集天地靈秀與傳統文化于一身,面對禿子和劉成,她的選擇是明晰而決絕的:從始至終,她都只愛劉成這個城里人,對癡情付出的禿子卻只是由討厭到憐憫。女神的價值選擇也代表了這一階段作者本人的立場,不論故鄉多么美好,一心向往城市的知識分子卻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安排了一個別具深意的結尾:劉成和珍子在城鄉交界的華山落腳,準備開始幸福的生活,但一場洪水毀了所有,劉成和珍子雙雙死去。來自城市的追捕力量和來自鄉村的追求力量間接參與了對二人的謀殺。作者有意告訴我們,劉成和珍子在死之前并未達成身體上的結合,這是否意味著城市與鄉村之美是難以真正結合的?城里人和女神的結合以死告終,軀體留在了鄉土。而作為根的鄉土有的卻是深深的無力感,留不住孩子的心,只能留住冰冷的軀殼。于是,尋根之旅最終在死亡面前失敗了,作為根的鄉土也開始了潰敗的歷程。城市與鄉村的爭斗,最終是沒有勝者的。
(二)《秦腔》:引生——白雪——夏風
《秦腔》可謂是實實在在的鄉土的碩果。作者回到生活的原點,從最瑣細的日常生活入手,在一磚一瓦中建構了鄉土,又解構了鄉土。城市此時已成為巨大的鄉土舞臺后不可遮蔽的背景,它以強大的力量壓迫著古老而虛弱的鄉村,讓鄉村傳統的長老統治在政治權利的擠壓下先潰敗后滅亡。“最后一個農民”夏天義的死成為鄉村失去自我的標志,鄉不鄉、城不城。鄉村最終淪為城市的一個附著物。
“瘋子·女神·城里人”的模式在《秦腔》的時代呈現出了更大的悲劇意味。在這場追逐中,三人都沒有幸福可言,甚至連精神的結合都不曾有,唯有肉體的結合給他們帶來“怪胎”的后代與最惡毒的詛咒。所有的結合都面臨無根的結果,鄉村不僅失去了孩子,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瘋子引生作為小說的第一人稱視角,承擔起“作家、隱形敘述人、敘述人、小說人物”的四重角色,“生活是由他結構的,同時也是由他解構的”[2]。作為鄉村的代言人,他不僅早早失去了和女神接觸的資格,還在開篇不久便自殘閹割了自己的生命之根,讓鄉土在精神和肉體上都有了缺陷。而夏風這位“農裔城籍”的城里人徹底被鄉村放逐,他的活動舞臺更多是城市,他在鄉村的身份成為一種虛無、罪惡和權力,同時也是“負心漢”和“不孝子”。雪隨風而舞,風卻棄雪而走。堅守和游離成為白雪和夏風之間最大的鴻溝。兩人面臨著較珍子和劉成更為失敗和痛苦的結局,精神難以結合,身體也難以歸根,因而他們的后代只能是畸形兒。
在這部小說中,對城市與鄉村的抉擇于女神來說更為悲痛,新世紀城鄉關系也較之20世紀80年代更為緊張和特殊。鄉村對美的追求已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而女神對城市的攀附也了無希望。鄉村與女神最終面臨的都是失落,而鄉土的生命和美也就此無處安放。
二、三角戀里的城鄉抉擇
一女二男的敘事模式是賈平凹富有寓意性的設置,男女的感情不但牽涉愛情婚姻,更影射時代的變遷和人性的轉變。創作兼具數量與質量的賈平凹,既能保證情節的生動有趣,又能達到藝術的高度與深度,往往是既講了故事,又講了道理。他筆下的女神形象即是一種典型的代表,女神表面是勤勞美麗的農家少女,內在卻有鄉土中國的符號意蘊。女神的選擇也成為透視作者本人城鄉抉擇的一扇窗口。
(一)女神的寓意
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原型一般有三類:地母原型,如母親、女神等;寡婦原型,如狐妖、妓女等;惡婦原型,如后媽、巫婆等。賈平凹的女性書寫中以女神型為主,而像石華(《浮躁》)、黑娥、白娥(《秦腔》)、唐宛兒、柳月(《廢都》)此類女妖型仍在少數,且不夠成熟。作為女神的珍子、白雪,因地母的原型被賦予了鄉土的根性與生命力,她們成為鄉土社會的希望和根本。反過來,她們又給予鄉村根的給養和美的凈化,鄉土只有在她們的存在和庇護下才能保持生命和發展。
但不幸的是,女神們在依附城市的努力化為泡影后,不僅讓鄉土的根性和生命難以維系,也把自身污染了。引生總說白雪從城里回來后臉變黃了,即是表明最純潔的白雪已經污濁,鄉村的美和生命又如何維系?因此,瘋子引生在超現實的言說中對鄉土之根、對鄉土社會的命運發出了最大的哀嚎和憂慮:鄉土到底能不能存活下去?
傳統文化是女神的另一重身份。珍子和白雪不無巧合地都是地方戲曲的演唱者和傳承者,她們都是戲曲的象征。作為鄉土社會的文化結晶——戲曲,實則是鄉土中國的文化之根。從這一層面上,女神又是傳統文化的象征。賈平凹的創作也就不僅是鄉土的挽歌,更是文化的挽歌。在《秦腔》中,文化與鄉村成為并置的兩個維度,“最后一個文化人”夏天智在清風街、在夏家無疑更具有長老的資質,是比夏天義更為強大和厚重的存在。然而,兩個“最后一個”終究都逝去了,希望就落在了無血緣的女兒白雪的身上。相比于鄉土的失落和消逝,賈平凹顯然更憂心文化的沒落和喪失,這一點在《秦腔》中表現得極為明顯。小說借助秦腔長歌當哭,為鄉土和文化的消逝而哭。正如陳曉明所說:“原來的那個宏大的鄉土敘事,具有歷史發展方向和愿景的鄉土中國正在走向終結,并且攜帶著它的更為久遠的文化傳統。”[3]因此,《秦腔》相比賈平凹以往的鄉土寫作,獲得了更高的評價以及文學史的地位。
(二)女神的選擇與作者的城鄉抉擇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全方位、深入、主動地融入現代化的大潮,也是這現代化帶來了城鄉的二元對立。在現代化對鄉土中國的全面進攻中,農村和農民也在不可遏制地發生著質變。從《浮躁》里的人心不古,到《商州》里工業化、商業化對農村的滲透,再到《秦腔》中“最后一個農民”的逝去,鄉村早已不是知識分子傳統思維中的桃花源、鄉土烏托邦、精神家園,就連被稱之為根的土地也在修路、建廠中一點一點地退守底線,而這底線能不能守住,仍是一個未知數。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賈平凹所做的選擇也正是無數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抑或鄉土中國人們的選擇,具有時代的代表性。
從《商州》到《秦腔》,女神對男性的選擇總體上都是擇“城里人”而棄“瘋子”,向城市靠攏的趨勢和心理是不變的。一邊是繁華、光鮮、發達、優越的城市,一邊是土氣、丑陋、落后、卑微的鄉村,不論我們嘴上、心里多么熱愛鄉村,實際上卻都是心照不宣地選擇城市。歷史再次把國家的命運寄寓在女性的身上,古老的鄉村和文化多么希望抓住現代的契機,不遺余力地跟上時代的步伐。然而,傳統和現代作為異質性的二元存在,一方向另一方的靠近也就意味著自身的消泯甚至滅亡。
作為城市的媳婦,鄉村的女兒,女神們選擇了城市卻仍舊離不了鄉土。她們的活動場域從來沒有真正走入城市,大多是在城鄉之間徘徊。鄉土仍是她們想要降落的地方和精神的家園,她們作出了時代的選擇,但充滿焦慮和失落。
農裔城籍是賈平凹非常突出的身份特征,他同女神一樣選擇成為城市的入贅者,但卻始終不敢忘卻自己的鄉土之母。在明確了走進城市的無根焦慮和死亡威脅之后,賈平凹們仍懷著一顆鄉土之心,向著鄉村深情地回望,企圖在這里找到賴以生存的根系和信仰。但這轉身亦是一種徒勞和悲劇,他們的鄉村已經質變,他們自己也已質變,被城市放逐的“他者”只能再次被鄉村放逐。尋根的結果是無根,于是,無根的一代只能繼續漂泊、流浪。
[1]張學昕.回到生活原點的寫作——賈平凹《秦腔》的敘事形態[J].當代作家評論,2006(3):53.
[2]閻建濱.月亮符號·女神崇拜與文化代碼——賈平凹創作深層魅力新探[J].當代作家評論,1991(1):10.
[3]陳曉明.他能穿過“廢都”,如佛一樣——賈平凹創作歷程論略[J].延河,2013(5):74.
(責任編輯:王菊芹)
The Narrative Mode of“the Madman,the Goddess and the Oppidan”of Jia Pingwa——With Shangzhou and Qinqiang as an Example
HUANG Yunyun
(College of Art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The madman,the goddess and the oppidan is a unique mode of Jia Pingwa’s local novels.The goddess of the local beau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gives a choice between the madman which represents the irrational,ugly sid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oppidan of"city of agricultural origin",which is also the conscious choice of the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Jia Pingwa when faced the value choi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own initiative:leave the country and enter the city.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choice is no root and lost,which is not only the tragedy of this generation intellectuals,but also it is the tragedy of native and the culture themselves.
Jia Pingwa;goddess;urban and rural choice;city of agricultural origin
I206.7
A
1008—4444(2015)05—0125—03
2015-08-28
黃鋆鋆(1992—),女,河南平頂山人,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