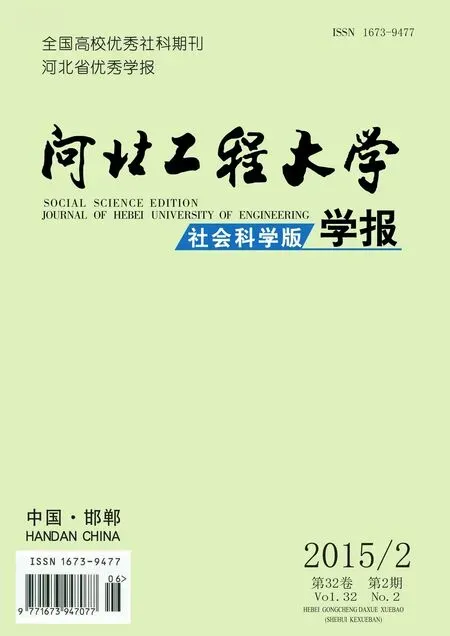民國《良友》畫報與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
滿建
(宿州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文學史給予且的定位是現代通俗小說家,但他最初卻是以隨筆散文為讀者所熟悉的。1943年,譚維翰在《記予且》一文中回憶十余年前對予且的印象時寫道: “‘予且’兩個字,我最初發現它大概是在《良友畫報》上。那時我還是一個初中的學生,我并不懂什么叫做文學,可是‘予且隨筆’卻使我在課余得到不少的喜慰;只是每當我看得起勁的時候,底下沒有了,我常常問自己,這樣好的文字為什么不多登兩段呢?”[1]這段話道出了予且早期散文的魅力,凸顯出了散文以系列形式發表的吸引力,以及《良友》畫報之于予且散文傳播的意義。那么,《良友》畫報和予且散文有著何種的偶合?予且早期散文以什么樣的特色引起讀者的興致,對海派文學及中國現代散文又有何貢獻?
一
予且的早期散文,最初發表在趙家壁主編的《中國學生》月刊上。該刊創刊于1928年11月,由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主要面對大學生,介紹全國各大學學生校刊及優秀作品,因此在文學界的影響有限,存世也不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停刊。
1931年9月,予且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良友》的第61期上。其時適逢《良友》創辦六周年,該刊為了提升自身的品位,增加了文學作品的刊登比重。梁得所在該期《編后記》中介紹到:“文字比前約多三倍,因為每月只出一期的刊物,應該較為充實。本期所刊,予且先生的《飯后談話》共分六段,每段一題,將按期發表。”[2]這組散文發表《良友》第61—66期上,分別為《飯后的臉》(第61期)、《吃飯的藝術》(第62期)、《何以解憂》(第63期)、《淡巴菇》(第64期)、《茶之幸運與而厄運》(第65期)、《司飯之神》(第66期)。此后,予且相繼在《良友》雜志上發表的散文作品還有《福祿壽財喜》(第 67期)、《龍鳳思想》(第 68期)、《酒色財氣》(第 69期)、《天地君親師》(第70期)、《予且隨筆》(包括《坐》、《甜蜜的家》2篇,第143期)等。從發表時間來看,除第143期的兩篇散文發表在1939年外,其余諸篇均發表在1931—1932年間,正值予且創作的早期階段。這些散文作品在刊出后,受到讀者的極大歡迎。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們迥異于表達文人抱負或情致的傳統散文,具有濃厚的市民趣味,適應了《良友》畫報的刊載需要。
《良友》畫報創刊于1926年,30年代初期已成為上海、中國乃至世界華人界最受歡迎的畫報,素有“《良友》遍天下”的美譽。之所以產生這么大的影響,是和其趣味化辦刊宗旨是分不開的。該刊第2期的卷首語曾談到:“做工作到勞倦之時,拿本《良友》來看了一躺,包你氣力勃發,作工還要好。常在電影院里,音樂未奏,銀幕未開之時,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較四面顧盼還要好。坐在家里沒事干,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較拍麻雀還要好。臥在床上眼睛還沒有倦,拿本《良友》看了一本,比較眼睜睜臥在床上胡思亂想還要好。”[3]這種趣味性的辦刊追求,迥異于嚴肅性社會政治宣傳刊物,極易受到讀者市場的歡迎。作為圖文兼重的畫報,它不僅僅表現在刊登的圖片所展現的色彩斑斕的都市時尚圖景上,也表現在文學作品上。該畫報在第61期的宣傳欄中寫道:“本刊以后增加有趣味有價值之文章,使讀者除領略美術圖片之外,復得有實際的知識文字,讀之有味,手不肯釋,材料異常充實。”這一點是和予且的散文追求不謀而合的。在《說寫做》一文中他談到:“人生出來只有哭、笑、睡覺、更無所謂莊嚴”,“我們的文章是用笑臉寫出來,方才有趣味,趣味便是文章的靈魂。”[4]對于趣味化的共同追求,使得予且散文能夠在《良友》畫報上頻頻亮相。
二
1934年末,《良友》第100期紀念特號刊登了一組“本志讀者一斑”的照片,展示了該雜志讀者遍布的社會各個階層,包括主婦、現代女性、工人、巡捕、掌柜先生、戲院的顧客、茶室里的茶客、公園的游客等等。為滿足畫報市民讀者的閱讀需要,予且早期散文所寫的都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見話題,所表現的是普通市民的趣味。
予且的散文表現出對市民價值觀念的認同。他曾這樣自陳過:“這種表只要一塊八毛錢一個,壞了我便丟了它,也不拿去修理,然后再買一只新的。就算一年換兩個表,也花不了四塊錢,而且我可以隨時地用新表”[5],體現的是市民階級只追新潮不求永恒的價值觀念。予且為《良友》畫報寫作的散文處處都表現出他對市民價值觀念的肯定,在《吃飯的藝術》一文中寫到:“食是吃飯,色是性欲,二者同等的重要。因為不吃飯就餓死,無性欲就沒有家庭社會”, 強調了食色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性。在一些散文中,他還通過生活具體情態,來消解宏大的主題,反映市民階級的趣味。對于蕭統《陶淵明傳》中描寫的“葛巾漉酒”這一表現文人灑脫的逸事,他用世俗化的筆法還原了當時的情形:一個窮苦的老頭子,在烈日下拄著拐杖奔赴友人家,用沾滿了油垢和汗漬的頭巾濾酒喝了,再把濕漉漉的頭巾戴上(《何以解憂》),在對生活細節的還原中,消解了陶淵明真率超脫的詩化境界。
予且重視市民日常生活的意義,并能從中挖掘出趣味來。在《飯后的臉》中寫到:“我看見過一個剛吃飽了奶的小兒,真可愛。又看見過一個餐后閉目養神的老人,覺得人類真是美的,雖老而不衰。又看見一群商人,醉飽之后聚談,令我覺得大地春回,生氣蓬勃。又看見主人請客,亦醉亦飽,賓主盡歡,笑態可掬”。接下來,他談到,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小孩子的鼻子上有許多青筋暴起來,老人臉上的皮如同桑樹皮,商人的臉上有著市儈氣,請客的主人滿頭是瘡、客人中有流清鼻涕的——不在于日常生活本身如何,而是如何去看待它,不同的目光注視下,會有不同的景象和境界。予且在對市民日常生活細致入微觀察后升華出淺顯的生活哲理:“社會上許多好東西,因為認真一考察,便毫無趣味了。一個美人臉,顯微鏡下便是一根根粗毛附著皮,就不說顯微鏡,看久了也是生厭的。”[6]
予且所談對象都是發生在普通市民身邊瑣屑小事,無論是談吃飯(《飯后的臉》),還是說抽煙(《淡巴菇》),抑或是論喝茶(《茶之幸運與而厄運》),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從而表現出濃郁的市民趣味。予且對都市世俗生活和市民的人生滿懷著熱情,因而能對市民生活有著細密的觀察和體悟。他用無數逼真的細節來豐富其散文內容,生活色彩濃厚。在《吃飯的藝術》中,他舉出某人用筷子的技術極其高明:“他在一桌筵席上,一樣菜有一樣菜的夾法,從沒有失著,滑的,粘的,硬的,大的,箝挾起來,無不稱心如意”,他寫不善用筷子者的狼狽心理和動作:“他改挾的時節,心里是老大不高興,他偷偷地四面一望,恐怕有人笑他夾不起來,末了他發現著人家都在高談闊論的沒有注意到他,他方將那一塊低等的菜,放入口中,也陪著大家一下”[7]。他又用簡單的語言,傳神地寫出囚犯、電影上的男女、小孩子、學生、教員、孀婦、義賑會里的人、乞丐、病人、兵隊、送行者、街上的男女等等不同人吃飯的不同方式。沒有對市民生活極大興趣和傾心的融入,是無法寫出來的。
三
在開始刊載予且散文的第61期的《良友》編后記中,梁得所寫道:“消解生活的枯燥,是《良友》的一種責任。善意的建設,也是我們的主張,增長知識和輔助修養的圖畫文字,用趣味的方式來發表”[8]。予且早期發表在《良友》畫報上的以“市民趣味”為表現對象的散文作品,在藝術形式形成了鮮明的特色。
首先,這些作品體現了予且的連類無窮的生活想象力,由此及彼,由一及多,由具象而抽象,給讀者以無窮的藝術享受。 在和予且有著密切交往的譚維翰看來,予且談鋒很健,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領,就是在連續談論兩三個小時的話后,自己和談話對象都不會感到厭倦。予且的這種談話風被他運用到了散文創作中。他的散文多為議論性的隨筆,形成雜談式的文體風格。
金克木認為中國人思維多是線性思維,他說:“就我們中國人熟悉的說,思維往往是線性的, 達不到平面, 知道線外還有點和線也置之不顧。只愿有一,不喜有二,好同惡異”[9]。予且的思維方式卻是發散式的,他具有聯類無窮的聯想力,由某事物生發開去,向日常生活散開,呈現出無所不談、縱談無窮的特點。在《吃飯的藝術》一文中,予且放談“吃飯”這門藝術。針對有人認為吃飯就是簡單地張開口塞進食物再咽下去,而無藝術性可言,予且指出,如是這樣便不會有破唇破舌燙嘴的細節了,進而寫到人之吃東西不是蛇之食蛙,蛙之食蟲,牛之食草,再進而指出牛之食草的“反芻”也有藝術意味,接著聯想到其他脊椎動物,比如貓吃老鼠就是意味深長。他還繼續談到,說到吃,就會聯想到嘴,進而聯想到牙齒,聯想到舌,進而聯想到小兒的舌和老人的舌,進而聯想到狗舌。接下來,他談到:“吃,是一個行為,而且一個復雜的行為。這繁雜的行為,有屬于外部的,有屬于內部的,討論的范圍,是從手中得物時起,送入口中,嚼后入胃為止,做食品的方法不在內,得食品時之狀況不在內,食品入口之次序也不在內。”[10]在予且看來,吃這樣的“藝術”如果不劃定范圍就無法談下去,話題是無窮無盡的,任何一個點都可以盡情而談,無休無止。在《淡巴菰》中,他僅從“淡”、“巴”、“菰”三個字眼借題發揮,就能生發出關于香煙和生活的無窮聯想。
其次,予且散文趣味性以豐富的日常知識作為基礎,因而并不淺薄。予且有上海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的教育背景,知識淵博,中西皆通,這就使得他的散文取材廣泛,不管什么話題,都能談論自如,無論是福祿壽財喜,還是天地君親師,龍鳳思想,酒色財氣,他無所不懂,無所不談。尤其是在市民日常生活題材作品中,他也能夠自如地運用自己了解的知識、典故、風俗、軼聞等去進行比照。如在《吃飯的藝術》一文,在談到有人不善用筷、只好吃筷子上的余瀝時,他以日本故事中的大神伊奘那岐伊奘那美用長矛在太平洋中蘸水、滴成日本的高山做比喻;在談到將吃飯作為藝術來學習時,他列出了學習書法和學習小提琴的種種復雜的技法;在談到用手拿食物的時候,他剖析了中西吃飯分別用箸和刀叉的心理根源;他談到了內地老板以讓出首座辭退店員的習俗、舊式婚禮媳婦到婆婆家在中堂坐席的習俗,談到中國和羅馬的新娘新郎都有將共食的一晚稱為團圓飯的風俗等等。予且散文中的這些豐富的知識,其用意并不是炫耀高深,而是融入到世俗話題的議論中,拓展了生活的維度,增加了散文的可讀性。
第三,予且散文的趣味性以日常智慧作為調適,在肆意放談中生發出智慧的閃光,使得散文妙趣橫生。他認為書這一人類表現思想最高深、最久遠、最完全的東西,一大半都是為了混飯吃而編而用而讀的,無論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書籍,還是國文百日通、自薦尺牘、商人秘笈,以及生利指南、發財新法等書均是如此,甚至還有人用圣經佛經拿來混飯吃。當然,教人禁絕煙火者和白日飛升者除外。這些即興發揮的議論沒有什么邏輯的必然性,但從社會生活的實際來看,又有一定的道理,因此能讓人發出會心的微笑。《天地君親師》所談的是對被人供在中堂永受香火的所謂“五大”的種種不同解釋。前兩種解釋雖然莊重且冠冕堂皇,但作者都在質疑后將之推翻。最后是作者給出的解釋:針對學生不長進,老師解釋說,“天地君親師”五者中自己被排在最后,責任最小。這種出乎意料的解釋屬于神來之筆,雖無多少實際意義,但能讓人忍俊不禁。
四
《良友》畫報為予且提供了作品發表的園地,予且則以其散文對市民趣味的體察和表現,加強了《良友》畫報對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現。《良友》畫報上刊載予且的“市民趣味”系列散文,具有一定的文學史意義。
首先,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體現了海派文學精神的整體性和前后一貫性。在當下的文學史敘述中,20世紀30年代的海派文學以使用現代主義手法表現目迷五色的都市新感覺而著稱,40年代的海派文學則轉向了飲食男女日常生活的表現。事實上,現代都市上海作為多面體,其摩登光鮮的一面和普通日常的一面是同時存在的,對其表現也應該如此。《良友》畫報的圖片在展現爵士樂隊、摩天大樓、賽馬場、賽狗場、回力球場、電影海報的場景及聲光電化的現代都市生活的同時,也有“人行道上的上海”的組圖,鋪排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場景。《良友》畫報刊載的文學作品同樣如此,既有穆時英的《黑牡丹》、葉靈風的《朱古律的回憶》、施蟄存的《春陽》等新感覺派的摩登小說,也有予且對普通市民生活的情趣的表現。予且散文的這種審美維度,展現了海派文學豐富性,是40年代海派文學表現市民生活的先聲。
其次,予且的“市民趣味”散文,開拓了中國現代散文的表現領域。中國被稱為散文大國,散文具有悠久的創作傳統。從功能上看, “文以載道”的觀念根深蒂固,散文長期被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多表達宏大嚴肅的政治主題。從傳播角度來看,古代散文主要用于上奏朝廷或是在文人之間小圈子流傳,其讀者對象是達官貴族、文人名士等。進入現代社會后,這種情形發生了改變,有人指出,“現代傳媒對于作家的寫作的意義在于,使他們通過報紙期刊真正面對了市民為主體的讀者對象,從而改變了散文作家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散文文體的文化功能,使散文成為現代報刊的特殊文體類型”[11]。刊載在《良友》畫報上的予且散文一反傳統散文的慣例,展示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市民日常生活一面,以其較強的市民趣味適應了市民讀者對象閱讀喜好,從而拓寬了我國散文的表現領域。《良友》畫報其時“每期印行四萬份,每月讀者五十萬人”,無疑對具有濃厚市民氣息的中國都市散文的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
許道明先生在談論到予且散文時指出:“無論怎樣,‘趣味’還是他的中心,他的那條風景線是屬于市民的。市民慣常的興趣,街頭巷尾的情調和茶館酒肆間的意興,養就了他的作風。”[12]予且在散文中表現出來的趣味是和《良友》畫報“藉趣味的取材,作閱者之良友”的宗旨相一致的。這些散文都是用平常話寫的平常人事,并不能給人蕩氣回腸的感受,但真切的生活感及其蘊含的趣味性,卻能和《良友》圖片一道,給市民階級以某種消遣性的滿足。
[1][5]譚維翰.記予且[J].天地,1943(1):22.
[2][8]梁得所.編后記[J].良友,1931(61):2.
[3]卷首語[J].良友,1926(2):1.
[4]許道明.海派文學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312.
[6]予且.飯后的臉[J].良友,1931(61):44.
[7][10]予且.吃飯的藝術[J].良友,1931(62):44.
[9]金克木.蝸角古今談[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25.
[11]周海波.現代傳媒視野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8:342.
[12]許道明 馮金牛.潘序祖集:飯后茶余[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