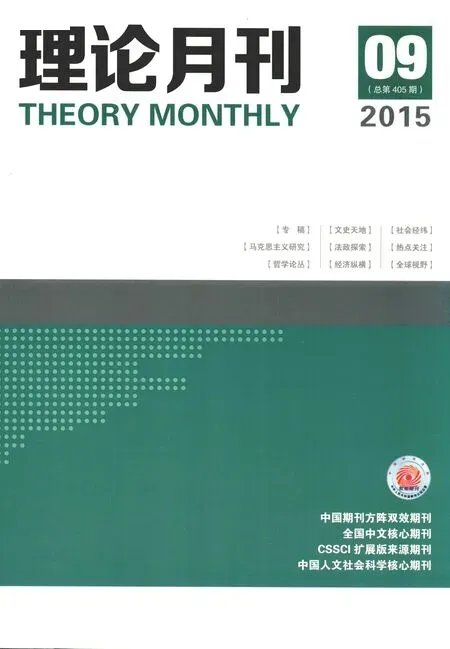馬克思哲學價值關懷終極內涵新解
□劉興盛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馬克思哲學價值關懷終極內涵新解
□劉興盛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馬克思哲學的價值關懷是人的解放,而通常對人的解放的內涵的理解是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人的全面發展還有其更深刻的思想內涵,應該對這一內涵進行進一步揭示,這一內涵就是人的個性的解放。將個性解放確認為馬克思哲學關于人的解放的核心內涵,既彰顯了解放的主體——現實個人,又突出了解放的內容——人的本性,因而是形式與內容、物質與精神、主體與客體的統一。而通過回溯馬克思思想發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內涵在馬克思哲學中的核心地位及其生成過程。
馬克思哲學;價值關懷;終極內涵;個性解放
馬克思哲學的價值關懷是人的解放,這是無可置疑也是廣為學界發揚的,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產生了豐富成果。但是縱觀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大多數成果將人的解放的內涵最終歸結為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不錯的,但對人的全面發展所蘊藏的內涵還應進一步揭示,這一內涵就是人的個性的解放,即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是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對此,馬克思在不同時期做過不同的表述,典型表述如“個性的充分發展”、“自由個性”等等。種種表述表達的是馬克思對人的個性解放的關懷,事實上馬克思正是將人的個性的自由全面發展視為人類實現解放的理想狀態。
1 個性解放在馬克思哲學中的蘊意
何以馬克思將人的個性解放視為人類解放的理想狀態并作為終生持守、不懈奮斗的價值追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需從“個性”一詞的內涵說起。
1.1“個性”的內涵
與通常的理解不同,我認為馬克思“個性”一詞指代的是“個體身上的人的本性”,因而個性解放就是使個體身上的人性或人的本性、本質得到解放,亦即個人身上的人性或人的本性得到自由全面地發展。對此,恩格斯的話可以看作對這個觀點的佐證,他在論述共產主義本質的時候說道:“我們談的是為所有的人創造生活條件,以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他的人的本性”。[1](P626)這里需注意的是“本性”一詞的含義,“本性”加上“人的”限定詞,其意義在于區別動物式的本性,動物式的本性例如吃、喝、生殖等不是人作為人的那種本性,人的特殊本性是超越動物式的本性的,人的解放所要自由發展的正是這種超越動物本性的人的“本性”,這種本性實際上是人的“類特性”。
從解放本身來說,主體即是解放者又是被解放者,而解放的內容只是被解放者,因此內容是統一于主體即現實的個人身上的。這樣,“個性”本身就是一個合題,即體現了形式維度和內容維度、主體維度與客體維度相統一的合題。具體說來,“個”即個體,標示的是主體的維度,它表征的是活動的載體、承擔者;“性”即本性,標示的是活動內容的維度,表征的是被發展和被實現的內容,是人的活動的對象、客體。
既然主體是現實的個人,而“個性”不過是人的本性在個體身上的現實化,那么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人的本性的內容是什么?在我看來,人的本性是動態的、不定的、無限豐富的,不過我們可以通過幾個重要方面來提示和理解人的本性的內容。這幾個基本方面就是人的感覺、人的需要、人的能力和人的關系,馬克思非常重視和強調人的這幾個方面的發展。如前所述,這里的感覺、需要也不是動物式的那種原始的感覺、需要(實際上動物式的感覺、需要不過是條件反射),而是超越了動物的人的感覺、人的需要。由此合乎邏輯的就是實現人的感覺、需要的能力以及實現這種感覺、需要的活動所造成的人們之間的關系也必然為人所固有,因此能力和關系也是人的本性,這是每一個現實的人所固有的。馬克思十分重視和強調人的本性的這幾個方面,例如:對于人的感覺,馬克思說“已經生成的社會,創造著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的人,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的現實”;[2](P88)對于人的需要,馬克思說“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3](P333)對于人的能力,馬克思指出“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4](P108)對于人的關系,無疑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P56)是最為大家所耳熟能詳的表述。
個體是實實在在的主體,類本性是共同的普遍的本質,這種共同的普遍的本性只有體現在個體主體身上,才是真正現實的。而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活動的類本性是 “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2](P57)它優先于并決定了人的活動內容如感覺、需要、能力、關系。然而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個人至今無法實現自由自覺的活動,所以這種類本性在個體身上無法得到自由全面地發展,這就是個人與類本質的異化現象。在這種異化當中,人類的本質力量作為維持個人動物式的生存手段而存在,在運用人類本質力量的時候個人不是覺得自我肯定而是覺得自我否定,不是在享受活動而是在活動中遭受痛苦和折磨,所以馬克思說“我的個性同我自己疏遠到這種程度,以致這種活動為我所痛恨,它對我來說是一種痛苦”。[6](P38)從這里可以明顯看出,馬克思的“個性”一詞并不是日常所理解的那種意指“獨特性”、“與眾不同性”的含義,因為如果指代的是“獨特性”、“與眾不同性”則不會有“疏遠”之說,即是說“獨特性”、“與眾不同性”是無所謂“疏遠”不“疏遠”的。而如果將“個性”理解為人的本性則合乎“疏遠”的內涵,實際上,馬克思想表達的正是異化勞動使個人與人類本性相疏遠、背離。
因此人類自由自覺活動的類本質在目前階段只能存在于人們對它的意識即類意識之中,馬克思據此說道“在今天,普遍意識是現實生活的抽象,并且作為這樣的抽象是與現實生活相敵對的”,[2](P84)這里的“普遍意識”就是個人對于人的自由自覺的類本性的意識即類意識。所以馬克思多次說到要重新占有和發展人的本質、本性,而共產主義就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2](P81)而人對自己本質的占有、豐富和完美就是真正自如地運用和發展人的類本性及其力量,而這就是“自由個性”。
馬克思指出,之所以人的個性到目前為止未能得到自由全面地發展,其根源在于現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一方面,人類的生產能力、社會財富水平制約了個性的發展,突出表現在前現代社會,個人受制于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或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制約了個性的發展,突出表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具備了一定高度的生產能力的同時,個人仍然受制于強制分工而扭曲、片面地發展,活動著的個人仍然遭受精神與肉體的摧殘。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指出了自由個性是 “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4](P104)這正是針對阻礙人的個性自由全面發展的生產能力和生產關系而言的,因此個性解放是統一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中的,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追求的價值核心。
實現自由個性的這兩個方面的條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所做出的與自由個性相對應的規定。“發展”一詞傾向的是凸顯動詞性的活動形式、主體的方面,而與主體的發展不同,“生產能力”則傾向于凸顯名詞性的活動內容、客體的方面,因為生產力必須客體化才能成為真正的生產力。馬克思在這里之所以僅僅指出“生產能力”,是因為生產能力是人的活動的最具根本性、決定性的內容,人的本性的其他方面的內容例如感覺、需要、關系都是由生產的能力決定的,這是符合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的,馬克思始終強調生產能力的發展就在于它的這種根本性和決定性。
因此,關于“個性”一詞內涵雖有多種多樣的定義如心理特征說、個別差異說、諸因素綜合說、積極意義說、人的本質的特殊表現說、主體性說等等,[7](P33)尤其是后兩者已經揭示出了“個性”的重要含義,但是就定義的表達來說,都不能說是從最本己、最圓滿的意義來表述的,我認為最本己、最圓滿的定義應該是個人身上的人的本性這一表述,這個定義是將前述各種定義綜合進來的根本性、總體性的哲學規定。
1.2個人主體的核心地位
通過以上對“個性”一詞內涵的讀解,我們發現解放的內容統一于解放的主體即現實的個人身上,因此“現實的個人”或者說“活動著的個人”就成為馬克思全部學說的出發點和歸宿,它是“馬克思主義所有基本范疇的前提和基礎”。[8](P4)現實個人作為主體在馬克思哲學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可以通過如下幾點進行說明。
第一,從歷史的本質來看。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9](P11)毫無疑問,這是在指明現實的個人是全部歷史的前提和出發點。另一方面,馬克思還指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10](P532)這實質上在說現實的個人是全部歷史發展的結果和歸宿。第三,馬克思還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P118)表達了歷史過程的本質是處于社會中進行物質生產生活的個體之世代延續的創造活動。因此我們可以說,“歷史”什么也沒有做,它沒有進行過勞作、交往和戰斗,而真正進行勞作、進行交往、進行發展、進行戰斗等活動的主體,乃是每一個站在橢圓形大地上呼吸著自然力的真實個人。因此,個人既是歷史的前提又是歷史的結果,還是歷史發展的過程本身,歷史的前提、過程、結果三者正是這樣三位一體地統一在了個人及其活動之中,這就是歷史的本質真相,因而人的解放歸根結底是每個現實個人的解放。
第二,從人的生產活動來看。生產活動對人來說具有生存論的根本意義,而生產的前提和立足點就是現實的個人,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一定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11](P1)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不過是‘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的‘一種社會力量’”。[5](P85)對于在生產活動基礎上產生的各種關系而言,馬克思說到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5](P80)或者說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5](P123)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由于生產活動造成的,而從事生產活動的人不是存在于頭腦中、觀念中、想象中的那種人,而“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5](P67)此外,馬克思還指出生產方式的本質是“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一定的生活方式”,[5](P67)因而生產方式變革的根源就在于 “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5](P124)等等。如此對現實個人的強調數不勝數、不勝枚舉,原因就在于社會歷史的真正主體正是一個個現實的個人,因而人的解放也就是對每個現實的個人進行的解放。
第三,從階級斗爭來看。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解放是所有人的解放而非某部分人的解放,正所謂“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5](P57)表明馬克思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對人類解放的主體和對象進行考慮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里,能夠獲得解放的永遠都只是一部分人那就是統治階級的人,而另一部分人則無法獲得解放。就是說在階級社會當中,受統治的人的解放至多只能是頭腦中的想象的解放,比如資產階級宣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那種解放,這種所謂的每個人的絕對自由和解放除了存在于人的意識以外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部分人的解放是虛假的、非真正的人類解放,真正的人類解放是所有個人即每個現實的人的解放。就此而言,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實際上指出的是人的解放的途徑、方法、范圍,而人的個性的解放則是人的解放本身,即包括馬克思哲學在內的馬克思全部學說的目標和價值所指,因此后者是前者的目標,前者是為實現后者服務的,即進行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人的個性解放。
2 馬克思個性解放思想的發展歷程
既然個性解放是馬克思哲學價值關懷的核心和終極所指,那么回溯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來揭示和佐證這一內涵就是十分必要的。事實上,馬克思個性解放思想的確立正是經歷了純粹思辨哲學內部的言說,在思辨與現實之間徘徊,最后到真正在現實中確立的過程。
2.1在思辨哲學內部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傾心于原子偏斜的運思已然包含著對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眷注,這一眷注和關懷從始至終貫穿馬克思一生和他所有的工作,是其內心深層的志愿與祈向,只不過這個時候他還只能以一種純粹思辨哲學的方式來表達。
馬克思在他的論文中指出:“一個物體……在它自己所描繪的直線中——是一個喪失了個別性的點。”[12](P211)即是說如果只重視點的運動軌跡,以點的運動軌跡為主體,那么運動的真實載體——原子就被抹殺了,表達了馬克思對個體性被湮沒的憂慮。德謨克利特對原子運動的描述是自由落體似的運動和線性碰撞,而伊壁鳩魯的原子運動,除了這兩種類型的運動以外,還介紹了原子的偏斜運動。這種偏斜正是馬克思最為欣賞和看重的,因為偏斜運動彰顯著個體的自由性。原子偏斜代表的自我決定打破了外在的機械決定,象征著個體的自我意識,顯示了個體性的內在自由,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對直線的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瓦解恒定的必然性,這恒定的必然性“是命運、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創造者”,[12](P203)原子的偏斜使定在擺脫被必然性所牽累的宿命,從而賦予定在以“最高的自由和獨立性、完整性”。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才表達了運動是個體的自我運動,從而表征了個體的自我意識的自由發展性,這內在的自由發展也只有在擺脫直線性運動的過程中才凸顯出來。
馬克思告訴人們“一個人,只有當同他發生關系的另一個人不是一個不同于他的存在……這個人才不再是自然的產物。”[12](P216)原子之間的碰撞排斥是由原子的自我決定,是自己規定自己,表現著不由外在之物來規范自己的人的自我規定的特性,但是人的自我規定之確認又是如原子的碰撞、排斥一樣在于與他人的交往關系。以原子托比于個人,偏斜表達的是人的自我決斷的自由發展性,排斥則表達的是必須在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個人本身才能獲得自我實現的確證。
打破命運束縛的個體自由發展的價值,這就是馬克思在伊壁鳩魯哲學中發現的東西,盡管馬克思那時總是冠之以自我意識的名義。按照馬克思對伊壁鳩魯關于原子運動哲學的闡釋思路,馬克思的個性就是個體的物質的規定與性質的形式的規定的和合,即個性表征著的是個體的“質料”與“形式”內在互攝的統一性。德謨克利特關于原子運動的哲學所表達的只是原子物質性的一面,而單純的物質性僅僅只能象征載體和承擔者,馬克思對伊壁鳩魯關于原子的偏離直線的運動的評價是 “他以原子偏離直線的運動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12](P212)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運動是將“純粹形式”的內涵注入到物質性載體之中,二者雖是矛盾性的存在,但是只有二者真正結合一體才能使主體真正的“活化”起來,而這精神的規定性意味著自由全面發展的性質。
在原子的第三種運動形式中,眾多原子的對沖排擠,使馬克思得出一個看法,即原子個體的質料與形式合一的看法,馬克思直接地以這種旨趣來指稱個人,從而表達了他對人的本質的觀點,這就是人“必須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對的定在”。[12](P216)純粹自然的力量表征著的是人身上的純粹的物質性規定的惰性,屬于“質料”方面,而作為屬人的能動的精神性規定則在于對這種惰性的純粹物質性規定的打破,這“形式”的方面意味著的就是人的自由發展。單純的無精神或形式的定在是純粹的自然物,必須輔以自由發展的超越的精神形式。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是超越的、批判的、否定性的存在,在于他能超越物質局限,突破為肉體所拘,主宰自然欲望而不是被自然欲望所主宰。
在這篇論文中,馬克思雖十分贊賞伊壁鳩魯給予個體以自由發展的特性,但馬克思不無批評的指出,“抽象的個別性是脫離定在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發亮”,[12](P228)這就是說伊壁鳩魯的個體自由運動仍然是抽象的,并不具備真實的主體性。“定在”對應具備現實性的特定的個體物質存在,“發亮”意味著具備自由發展的精神形式或性質。這對原子自由運動的特性進行的帶有思辨色彩的論說,在馬克思漸次成熟的世界觀中逐步轉變為對現實個人自由發展他的人的本性的說明。這“在定在之光中發亮”,或可看作日后成熟的自由個性理論在博士論文中埋下的伏筆。
2.2在思辨與現實之間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表達只有個人的自我意識才具有最高的神性,而個人最高神性的現實化就是人的現實的自由個性。但這一終極關懷的現實化,還必須沖破思辨哲學的束縛才能獲得,這對思辨哲學束縛的沖破已經預告了革命的歷史觀在將來不久的生成。這種沖破,最初是因著對出版自由的呼聲、對法典作為人民自由圣經的吶喊,乃至最終凝結在對維護君主制的《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雖然馬克思此時還未深入到事實的本質,因而只能以應然的哲學理念來批判現實,但無疑觸及到了現實。
當時的普魯士統治者將法律作為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以所謂書報檢查令對個人的言論自由橫加壓制。馬克思對普魯士官方許諾自由但又表里不一的虛偽行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馬克思寫道“每一滴露水……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都只準產生一種色彩”,[13](P7)這被準許產生的唯一色彩就是普魯士政府的色彩,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的真正自由是無從談起的。訴諸于人的自由個性,馬克思在關于科倫日報的評述中表述了理想的國家應該是 “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聯合體”[13](P118)的考慮和旨趣。從這熟悉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此后的《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對共產主義理想狀態的論說,是對這種信念的始終連貫如一的延伸。雖然此時的馬克思距離全新歷史觀的創制尚有一段距離,因而對國家和法的認識還并未深入本質,但即使是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也從不放棄對個人價值與地位的看重與訴求。因此在那篇無產階級宣言書中的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實可看作馬克思所作“科倫日報”社論對“個人的目的變成大家的目的”、“使整體在每個個人的意識中得到反映”[13](P118)的深入闡發與連貫如一的探尋。
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法哲學對普魯士王權所作的辯護,凸顯了個人作為社會真實主體的性質。黑格爾認為國家的主要環節在于國家本身的職能和活動,這種職能和活動由個人來實現,但他又說個人和國家的職能、活動的這種實現之間的聯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也就是說主體不是實現這些職能和活動的個人而是國家,個人之于國家乃是外在的偶然存在。馬克思批判道黑格爾“忘記了特殊的個體性是人的個體性,國家的職能和活動是人的職能”,[13](P270)因而并不是個人的存在需要從國家那里獲得確證,倒是國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必須通過個人的現實存在來確證,通過人的社會存在和活動方式來確證。這同時也表達了人的真實個性與社會性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
黑格爾在法哲學中表示,家庭、市民社會的意義是作為國家理念的潛在環節,而在代表著永恒正義的倫理理念看來 “個人的忙忙碌碌不過是玩蹺蹺板的游戲罷了”。[14](P165)與此相應的觀點是,現實的個人是被分配給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有限的群體分子或現實材料,這種分配方式不過是理念自我實現的手段。貫穿于個人自身活動中的精神不是出于個人自我,而是來自不同于活動著的個人精神的其他精神。馬克思批判道,這種做法是 “把身為理念的主體的東西當成理念的產物,當成理念的謂語”。[13](P259)顛倒了的主客關系還必須被重新矯正過來,因此正確的理解就是“從現實的主體出發,并把它的客體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13](P273)這現實的主體只能是將人的本質客體化、現實化于生存活動中的個人,因此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順序應該是活動著的個人構成家庭、市民社會從而構成國家,而不是相反。
馬克思以處于現實社會歷史中活生生的個人取代黑格爾的絕對理念,顯露出的是對個人自由發展的價值關懷,表明了人的自由個性是馬克思最基本的哲學原則。
2.3在現實中確立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重要作用在于,馬克思正是因為這一工作將眼光逐步轉向市民社會領域,從而使關注點從國家、法等上層理念逐步下降到它們最根本的塵世基礎。
轉向伊始,馬克思分析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對立的情況下人的生存境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同時存在使個人具有雙重存在的景觀,一方面個人作為公民存在于政治國家中,另一面作為市民存在于市民社會中,這樣人便處于一種分裂的狀態。馬克思說道:“在市民社會中……是實在的個人的地方,人是沒有真實性的現象。相反的,在國家中……失去了實在的個人生活,充滿了非實在的普遍性。”[13](P428)世俗社會中的個人處于現實的物質利益關系之中,具備實在的性質,一如博士論文中的“定在”,但直接為生存的自然需要的物質交往關系滿足的只不過是動物式的需要,在這里人的本質顯現不出,因而缺乏精神性的人的特質。在國家中的個人具備人的本性,但是這里的個人不具備實在的生活,不是“定在”的實在性。馬克思對此概括道“只有利己主義的個人才是現實的人,只有抽象的公民才是真正的人。”[13](P443)因此,在單純進行政治革命的社會里人的個性是分裂的,馬克思基于這種洞察與剖析,明確了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標:使個人的存在既是“形式的原則同時也是物質的原則”。[13](P282)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個人在私有財產支配下的異化勞動進行了論述,在揭露異化勞動對人的個性的壓迫的同時,也對解放人的個性的現實運動做了初步探索。馬克思認為,勞動應該是豐富人的個性的現實途徑和方式,然而私有財產使體現著人的一般本質的類生活僅僅變成維持個人生存的手段,從而人的類本質與現實個人之間產生了異化、對立,人的個性無法得到自由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指出,異化和異化的揚棄的道路是相同的,勞動實踐既然可以壓制人的個性,也同樣可以使人的個性得到解放。而人的個性解放在于它需要一種現實的運動,這運動造就的社會 “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覺的人”,[2](P88)它是“個體與類之間斗爭的真正解決”,[2](P81)因而使人的類本質同豐富人的個性統一起來,這就是共產主義理論的緣起。
在標志著唯物史觀創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幾乎隨處可見強調個人或人的個性的論述,即是說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表達了“個人的自主活動”及其現實命意的通向:“確立個人對偶然性和關系的統治,以之代替關系和偶然性對個人的統治”。[15](P515)作為馬克思終生持守并為之奮斗不懈、持之以恒的價值信念,已于此毫無遮蔽的顯露出來了:個性對關系和偶然性的掌控不就是 “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嗎?它構成了最初表達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全新歷史觀的核心價值。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5](P266)就是說,在異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人的個性被壓抑,人的生存表現只不過是喪失了個性的一種人的“生存外觀”。馬克思指出,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共產主義運動是 “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這揚棄異化的途徑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實踐,這種社會實踐的組織形式的關鍵在于 “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總和的占有”。[15](P76)它在“保存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生產形式下使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重新回歸人本身,這獲得自由個性的人的全面豐富性的確證在于 “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P87)
馬克思以《共產黨宣言》來宣告資本主義必然終結的命運,同時也是對人的個性解放的莊嚴宣告。但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非一無是處,它在建立后的不到一百年的生產中創造出了比過去各時代的總和還要多的財富,而這巨大的生產力就是人類實現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個人的獨立自主以及人的需要、能力、關系等等才全面發展起來,從而為人類實現自由個性創造條件。因此人類完全可以憑借資本創造的生產力,汲取精神、智慧和力量完全站立起來,為自己打造無愧于個性解放的生存狀態,這狀態誠如無產階級的宣言書所表述的那樣:“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5](P294)
從“在定在之光中發亮”到“個人是國家職能和權力的承擔者”再到“確立個人對偶然性和關系的統治”乃至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哲學價值關懷的終極內涵——人的個性解放終于修成正果,漸次臻于現實、完滿,并且始終不曾改變。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遲克舉.試論唯物史觀視野中的人的個性范疇[J].哲學研究,1991,(3).
[8]王貴明.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個性與自由主義的個人優先性[J].哲學研究,2001,(4).
[9]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4]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責任編輯劉宏蘭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05
A811
A
1004-0544(2015)09-0025-06
劉興盛(1990-),男,遼寧鞍山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