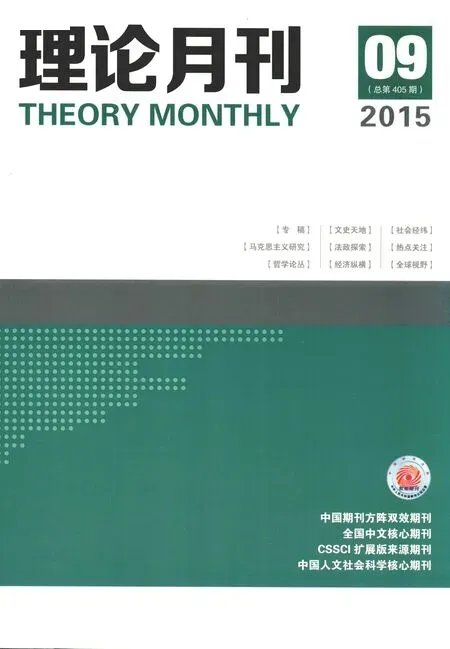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分析及其治理
□劉艷
(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無錫214122)
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分析及其治理
□劉艷
(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無錫214122)
公眾人物的“公眾性”特性決定其肩負著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當前中國某些公眾人物的道德引領和示范效應式微,道德失范亂象頻發,應當值得充分重視。公眾人物道德失范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經濟社會發展“硬實力”的刺激、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價值體系紊亂、個體承擔道德責任的自覺性下降等。當前重建當代公眾人物道德責任任重道遠,亟需通過兩個層面全面推進,即最低層面,其迫切任務是強化社會“他律”;最高層面,其終極目標是實現個體道德自律意識的覺醒和樹立。
公眾人物;道德責任;二律背反;重建
道德建設問題是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令人頭痛和困惑的問題之一,公眾人物道德失范問題,更是我國道德建設領域問題集中的焦點。近年來,明星嫖娼、醉駕、吸毒被抓及官員貪污腐敗被控等負面現象屢見報端,折射出社會公眾人物種種悖逆倫理道德的現象,“精神支柱方面的拜金主義和責任意識的弱化,凝聚力方面的離心離德和責任意識的逆反,文明秩序方面的道德虛無和責任意識的逃避,個人生活方面的享樂主義和責任意識的遠離,存在意識方面的人情冷漠和責任意識疲軟”,[1]公眾人物一次次沖上道德輿論的風口浪尖。近年來,從郭德綱侵占公共綠地、縱徒行兇、兜售“三俗”事件曝光,到黃海波、薛蠻子因嫖娼被抓,再到寧財神、柯震東、房祖名因吸毒被控等,社會公眾人物的負面新聞扎堆,道德失范現象愈演愈烈。①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比較典型的事件有:2009年滿文軍吸毒事,侯耀華假代言,臧天朔聚眾斗毆判刑,余秋雨詐捐門事件,周杰,胡彥斌撞車門等;2010年郭德綱搶占公共綠地,唐駿涉嫌假文憑,劉芳菲涉王益案,周杰陷還珠罵戰,周立波微博罵戰,章子怡潑墨門、小三門、詐捐門“三重門”;2011年孫興和莫少聰吸毒,高曉松醉駕,那英警車開道等;2012年韓寒方舟子代筆罵戰,李陽家暴,張藝謀“超生門”,蘇永康吸毒等;2013年韓紅挪用機動車牌照,薛蠻子嫖娼,孫楊無證駕駛交通肇事;2014年黃海波、王全安嫖娼,文章出軌門,王牧笛“想拿刀砍人”微博論,編劇寧財神、歌手李代沫、演員高虎、何盛東、張默、柯震東、房祖名吸毒等。近日,“畢福劍言論不雅視頻”更是“一石驚起千重浪”,引發輿論熱議。公眾人物的“公眾性”特性決定其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但相當部分公眾人物卻肆意踐踏道德底線、制造道德失范亂象。如何切實有效地制約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剖析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的根源并從中摸索走出道德失范危機的途徑,是當前哲學和倫理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1 公眾人物道德責任承擔的基本依據
“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 or Public Personage)一詞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 “沙利文訴 《紐約時報》案”、“聯合公司訴沃克案”和“柯蒂斯出版公司訴巴茨案”等一系列司法審判案例。《布萊克法律詞典》將公眾人物解釋為:贏得一定社會地位、聲望或名譽之人,或者自愿參與公共事務、介入公共紛爭之人。2002年,我國法律界在著名足球明星范志毅訴《東方體育日報》名譽侵權案件中首次引入這個概念。在法學界,一般認為公眾人物是指因某種職業、成就或生活方式等而成為社會公眾關注對象或輿論焦點的人。雖然目前國內學界尚沒有統一公認的“公眾人物”概念,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借鑒中外學者的觀點提煉出公眾人物的共性,做出初步性界定。筆者認為,公眾人物即具有公眾性身份和一定社會知名度、辨識度、影響力的人,“其以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公共利益相關性為構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2]一般而言,公眾人物主要包括兩類:一是政治公眾人物,主要指政府官員;二是社會公眾人物,包括文藝界、娛樂界、體育界的明星,文學家、科學家、知名學者、勞動模范等知名人士。前者更多地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后者則主要涉及公眾興趣和日常生活。[3]不管是何種類型,公眾人物在社會道德引領和建構角度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1社會價值引領的應然責任
公眾人物作為社會公共空間的特殊主體,總是頻繁、深入地介入公共領域,與各種社會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和公共輿論緊密相連,吸引、聚焦和壟斷大量的注意力資源,時刻處于大眾視線和社會聚光燈之下,是信息傳播過程的中介、過濾或放大環節,具有鮮明的“公眾性”特性。尤其是當前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交往更為頻繁、人的社會化程度更高、行業依賴性更為強烈、社會公共活動領域更加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大眾傳媒特別是網絡、微博、微信的迅速普及使得社會大眾參與公眾人物主導的 “公共空間”可能性迅速提高,公眾人物的“公眾性”屬性愈加明顯。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一旦在公共領域曝光,就會在核裂變式的現代傳播模式下瞬間聚集和產生巨大的言論能量,迅速成為大眾關注和媒體熱議的話題。具體而言,“公眾性”特性意味公眾人物是大眾所廣泛熟知和關注的焦點,甚至是大眾的人氣偶像、社會的文化符號和引領某種價值追求的“風向標”。他們的價值取向、言論舉止和行為做派等時刻受到大眾的密切關注,牽動著社會輿論走向,具有深遠社會影響和廣泛輻射效應,能在短時限內對大眾施加無意識的正面或負面的示范效應。正如孔子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4]因此,這就意味著公眾人物要在道德層面上作出表率,成為道德的榜樣和楷模。否則,如果公眾人物率先悖逆社會的道德原則和倫理規范,將會在大眾之間產生廣泛的反面示范效應。這種反面示范效應伴隨媒體的深入挖掘和滾雪球式曝光、傳播勢必會產生強烈的“蝴蝶效應”,催生社會道德危機或潛在的社會道德危機,乃至演變成一種“集體無意識”,久而久之就會引發災難性的社會道德危機。
1.2資源交換的正義要求
公眾人物對于公共資源的優先享有和利用,注定了其必須承擔社會期待(普通民眾并不一定需要承擔)的特定義務,這在法哲學上是一種交換正義的現實表述。“公眾性”特性使公眾人物置于公共空間的優勢地位,而公共空間肩負著承載民眾意志及一般社會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重要作用,對社會道德倫理整體走向有著無以代之的指引作用。因而,公眾人物在享用現時代稀缺的社會資源——公眾注意力,直接或間接地獲得諸多便利和收益(如媒體追捧、公眾擁戴、公職待遇、社會名望)的同時,就必須在公共空間承擔起相應的道德責任,在樹立道德典范、引領道德風尚、強化社會道德體系等方面做出應有貢獻。換言之,“享受公共空間資源”和“承擔相應的社會道德責任”從權利和義務的對等層面構成公共空間的兩大契約要素,公眾人物要接受和享用公共空間資源的權利讓渡,就必須接受道德義務的約束,用相應的社會責任對沖權利與義務之間的落差,以體現權利與義務、利益與情理、收益與代價之間的對等。正如哈耶克(Hayek)所指出:“人將自身的部分利益交割出去,交由國家、社會經管,并匯總成公共利益,同時公共利益也對人的利益構成限制。”[5]這既是順應社會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和權利義務平衡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現代社會實現公平正義的基石。
2 當前中國公眾人物道德失范歸因分析
在當前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公眾人物的道德現狀令人堪憂,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甚至道德墮落的趨勢。一方面,部分政治公眾人物私用手中掌控的政治權利等社會公共權力資源,肆無忌憚地侵犯民眾的基本權利并沉溺于腐化墮落、卑鄙齷齪的生活。“有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有的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有的貪圖享樂、玩物喪志,有的官氣熏天、橫行霸道,有的信念喪失、求神拜佛,有的趣味低級、包養情婦”。[6]各種違法亂紀、貪污腐敗等現象頻頻出現,不斷刺激公眾的敏感神經、挑戰公眾的道德底線。另一方面,部分社會公眾人物公德意識淡薄、拜金主義泛濫、價值理想失落。他們或是為追名逐利、以言求名、博得關注,濫用社會公共傳媒資源賦予他們的話語權和傳播權兜售“私貨”,“在電視節目里、博客微博中,一些公眾人物‘語不驚人死不休’,或‘曝光’他人私下言論,以他人的‘陰暗’反襯自己的高大;或以自己的社會聲望撐腰,蠻橫地給他人扣上異類的帽子;甚至 ‘脫下西裝’,與網友爆粗對罵”;[7]或是盲目拜金、貪圖享樂、放縱自我、放逐道德底線,在物欲、情欲的極度擴張中迷失自我。初唐虞世南有言,“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社會公眾人物負面道德帶來的不僅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的輿論爭議,比這些爭議更嚴重的是潛伏著更深層次的社會道德和信仰危機。應當指出,當下公眾人物道德“失范”事件頻發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多層面的發展變遷及問題的綜合反映,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現實原因、主觀原因與客觀原因、個體原因與群體原因等。
2.1經濟社會發展“硬實力”的刺激
恩格斯曾經深刻地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8]近年來,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頻發,雖然不能完全歸咎于市場經濟,但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過度追逐物質利益有著不可割裂的關系。在市場經濟下,往往出現理想信念和倫理道德的神圣性讓位于經濟利益、個體利益的現實性問題,部分公眾人物受功利主義和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驅使,蟄伏于內心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欲望迅速滋長,自覺不自覺地把人間溫情、社會正義和道德責任一律拋入冰冷的經濟利益關系之中。部分政治公眾人物甚至直接將手中權力“待價而沽”,不惜鋌而走險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又如傳統演藝界特別強調戲比天大、德比地厚,而當今娛樂界卻過度關注“票房”、“收視率”、“發行量”等硬指標,一切以“效益”為目的,“只要能‘逗樂’或‘過把癮’,即使‘關公逗秦瓊’或是唐伯虎變成了小流氓都何妨”。[9]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在貨幣的驅使下,一些人 “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愚蠢變成明智”、“把惡行變成德行”。[10]這一切反映在道德觀念上,就是妍媸美丑、是非曲直標準顛倒和道德失范亂象叢生。
2.2個體道德選擇的自覺性下降
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曾經指出:“認識自我是解決所有關聯著人的存在及其意義問題的阿基米德點。”[11]當前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頻發,雖然其根源和肇始于市場經濟的變遷發展及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價值體系紊亂,但是公眾人物個體的心性道德缺失及倫理觀念錯位也是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傳統社會,人們歷來安靜地陶醉于社會共同體之中,其自我認知與自身扮演的社會角色高度統一,“某種道德束縛置于那些角色承擔者的人格之中”,[12]角色即意味著個體的義務和責任。而在現代社會,人們進入個性極度張揚和凸顯的現代性自我狀態,成為自我支配、自我選擇的主體。從文明社會發展演變的進程角度分析,凸顯自我狀態,崇尚個人自由無疑具有正當性,是社會發展走向以人為本、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經階段,但是很多人僅“把這種自我選擇的權利當作一種任性的自由,任意按照自身意志和欲望使用這種權利,擺脫一切他生活于其中的與之相關的義務和責任,成為一種無負擔性的存在”。[13]因而,在事實上就是,人們秉持“自由”精神的同時將義務和責任拋之腦后,個體道德追求與精神修煉越來越成為稀缺的社會現象。可以認為,當前公眾人物不同程度地呈現出放縱自我的道德虛無主義傾向,與其道德責任意識淡漠、主體自覺性下降呈正相關,他們在享受公眾注意力及這種注意力帶來的豐厚收益的同時,常常難抵內心私欲的誘惑,或耽于物欲情欲不能自拔,或自甘墮落迷失自我,將自身肩負的道德責任遺忘殆盡,肆意逾越道德底線。
2.3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價值評價體系多元紊亂化趨勢明顯
我國當前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舊的道德觀念體系已被打破,人們原有的道德本位意識和靜態社會秩序逐步消融,許多行之有效的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和規范作用日漸衰微,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道德體系尚在孕育之中,并未及時建立。道德價值體系的新舊更替以及當下多元道德價值體系——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價值體系、市場經濟道德價值體系、社會主義道德價值體系及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道德價值體系的相互沖突和融合,人們陷入道德選擇的盲區。一方面,這種多元道德價值體系的并存催生道德標準的多樣性和道德評價的不確定性。究竟孰是孰非,人們難以進行價值判斷。似乎人們作出何種道德選擇均有其“合理性”,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圓其說”的理論辯護。當前最為典型的實例是,賣淫嫖娼行為自古以來就是傳統道德理念(萬惡淫為首)首當其中抨擊否定的行為類型,但黃海波嫖娼案發生后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認為可恥且應受懲罰,相反卻替其說話、為其開脫,認為他是“好演員”、“真性情、真男人”!甚至有網友評論:“黃海波作為未婚知名男演員寧可冒著違法被抓的危險去嫖娼,也不利用自身積累的資源優勢去糟蹋剛入圈的年輕女演員——真是好人吶!”道德標準在現實生活中混亂迷惘的現象不得不引起人們的反思。另外,還需格外注意的是,新舊道德體系更替過程中出現一些斷層或無序狀態,如社會道德調控機制和監督機制缺失、行政管理水平和法治建設相對滯后等,為部分人刻意鉆體制和輿論的空擋提供了條件。因而,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內,包括社會公眾人物在內的社會公眾在多重多元的道德價值體系中左右搖擺、無所適從,道德失范行為在這樣一種缺乏道德引導的環境中也就隨之滋生。
3 當代中國公眾人物道德責任重建的基本路徑
當代中國公眾人物道德失范行為已經進入亟需整頓治理的“大時代”,公眾人物道德責任重建任重而道遠,亟需通過兩個層面全面推進。
3.1道德自律意識內省式覺醒
公眾人物道德自律意識的覺醒和樹立,是公眾人物道德責任重建的長遠任務和根本目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曾經指出:“道德責任以自覺自愿地承擔為最高境界。”馬克思多次強調:“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14]“一個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爭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沖擊,怎能安靜地從事活動呢?”[15]對于一個社會的穩定來說,固然離不開強力和管理,但是這也只是一種“事后治標”之策,而要從根本上杜絕人們的越軌行為,關鍵還取決于人們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是指道德主體在社會實踐中自覺擺脫外在因素的制約,用理性審視自身的愿望和動機,自主自愿地認同、遵循、踐行并內化社會道德規范所形成的內在約束。道德自律作為道德主體的自我立法、自我監管、自我約束、自我服從,即是道德主體為自身特設的必然性。相對于強力和管理的他律形式,道德自律的調控效果更為深入、持久和穩定,且道德主體的行為方向、價值選擇和道德水準較少因外界因素的干擾而發生變動,故屬于高層次的道德控制。任何外在的強力和管理及其他社會性的道德他律形式,只有通過道德主體的自律和自省,才能最終內化為人們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成為“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16]外化為人們自主自覺的踐履篤行。正如黑格爾所指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了自己履行了義務這樣的一種意識。”[17]否則,“如果沒有個人主觀的表現,如果社會命令不向個人的內在精神過渡,道德是不可想象的。”
當前公眾人物道德自律意識的形成應主要解決兩個大問題:一是構建和培育公眾人物的核心價值觀,形成道德自律的“基準點”。當前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價值體系紊亂,是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的重要癥候所在。如何在道德價值沖突中找到一種能夠有效整合多種道德規則、引導多元價值取向和統攝個體分散的行為選擇的社會主導倫理價值原則,既是破解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窘境的關鍵,也是公眾人物道德自律形成的“基準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建構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價值認同體系,無疑與這種現實需要內在契合。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宏觀指導性,要使公眾人物這一特殊群體更有效地遵守這一價值體系,還必須從微觀入手構建和培育適合公眾人物、傳遞鮮明導向的核心價值觀,如“為民、務實、清廉”的政治公眾人物核心價值觀及“德為先、藝為本”“德藝雙馨、行為世范、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社會公眾人物核心價值觀,從而為公眾人物實現道德自律提供價值準繩和內在尺度。2014年5月,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時不僅指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抓好 “四大重點群體”——領導干部、公眾人物、青少年、先進模范,把黨員干部和公眾人物置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重中之重,而且著重強調“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貴在堅持知行合一,堅持行勝于言,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常化、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個人都能感知它、領悟它,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實際行動,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要面向全社會做好這項工作”,[18]這就為構建和培育公眾人物核心價值觀指明了方向。二是注重構建“慎獨”的文化生態和自律機制。“慎獨”一詞源自《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指人們即使在獨處無人監督之時仍能憑著高度自覺嚴于律己、獨善其身,嚴格按照一定道德原則行事,這應是包括公眾人物在內的社會一切公眾道德自律的最高層次和最高規范要求。在應然角度,公眾人物更應把“慎獨”作為一種自我道德修養方法和修養目標來遵循,堅持慎初、慎微、慎欲、慎獨,“去小惡以保本真,積小善以成大德”,自覺守住潔身自好的“第一條防線”,如政治公眾人物要繃緊拒腐防變這根弦,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社會公眾人物要自律自愛,堅持傳播“正能量”、弘揚社會主旋律,從而真正達到“內圣外王”道德之境——既有德行心性修養的“內圣”魅力,又有正能量奉獻社會的“外王”感召力。
3.2強化社會“他律”
首先,制定和配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相匹配的道德規范紅線和準則 (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等),把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納入到法律范疇和制度體系之中,借助規范的力量厘清公眾人物道德責任的邊界,使抽象的、隱性的道德責任轉化為顯性的、細化的、量化的規范責任,并通過法律強制力和其他行業規范強力將其一以貫之。這是因為,一方面伴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公眾人物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步提升,其對自身行為的利益要求遠遠高于對自身行為的道德責任要求,“權利本位”觀念已逐漸取代“義務本位”思想。在權利欲求和義務擔當失衡發展的社會中,完全依靠公眾人物自覺按照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意識約束自身行為,自愿踐履道德責任,已經難以取得預期實效。因此,必須通過道德制度化和道德立法,依靠法律的外部強制力和威懾力從義務與權利相對等的角度去調節和規約社會公眾人物的各種關系與活動,使公眾人物的活動置于嚴格而有效地法律監督之下,從而產生普遍的、客觀的社會道德效果。如當前一些政治公眾人物“金屋藏嬌”、經常性出入娛樂場所等現象頻發,盡管這些都屬于個人私生活范圍,但作為執掌國家公權的公眾人物,他們的不道德行為卻足以讓民眾對權力的公正性產生“合理懷疑”,因而國家應該對這些道德范疇的內容都一一立法并予以嚴厲懲戒;又如目前社會公眾人物虛假代言、詐捐、濫用話語權等有悖倫理道德的行為還難以“懲之以法”,也有必要對此進行立法并予嚴懲。①值得特別指出的是,2014年8月,在北京市演藝界“拒絕毒品 陽光生活”禁毒主題倡議活動上,北京市演出行業協會和四十多家演出公司簽訂了《北京市演藝界禁毒承諾書》,承諾不錄用、不組織涉毒藝人。這就以行業協會為基體,以行業行為規范和團體紀律強制力的形式為規約社會公眾人物行為提供依據。這在當前道德規約社會公眾人物疲軟乏力的娛樂圈尤為重要,也為今后以法律強制力的形式敦促社會公眾人物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指明了進路。正如普里馬克所建議,必要時求助于立法來制約當事人的行為,這條進路日益有效。[19]另一方面,道德和法律作為現代社會兩種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形式,兩者之間關系密切,“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絕非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內在的、必然的。或者說,法律之所以與道德相關聯,其終極的根源就在于,法律原本是倫理的產物”。[20]這就為道德走向法制化軌道,以剛性的力量和嚴格的程序保障“德藝雙馨、以德為先”用人標準的具體落實提供了可能。雖然較之于傳統的道德教化,依靠法律規約公眾人物的道德行為并不高尚甚至頗顯無奈,但是它畢竟能夠在客觀上產生立竿見影的道德效果,有效遏制公眾人物道德失范現象,切實提高公眾人物的道德水準,保證社會最大程度的向善和公正。
其次,明確權利保障邊界,強化輿論監督的權力色彩。19世紀初,美國著名思想家杰佛遜曾把輿論監督形象地譽為“第四權力”,將其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上升到成為制衡立法、司法、行政的“第四權力”的地位。輿論監督作為現代化民主社會的重要標志,其發展程度與水平標志著一個國家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與水平,及其政權的群眾基礎的廣泛程度。[21]近年來,我國社會主流媒體(包括互聯網、電視、廣播、報刊等)監督力量發展迅猛,在揭露社會丑惡、曝光悖逆法律和道德的行為、制約權力腐化、維護公民合法權利、引導社會輿論走向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穩定的利器。但是由于我國輿論監督的立法尚不完善、體制機制尚不健全,我國的輿論監督無論在認識層面還是操作層面,都還處于探索起步階段。由于法律對輿論監督范圍的界定尚不明確,導致輿論監督與公眾人物的法律權利沖突不斷;由于部分輿論監督主體片面追求轟動效應,任意夸大或捏造事實甚至栽贓丑化公眾人物,導致輿論監督的公信力下降,等等。因此,完善輿論監督外部環境的制度建設、建立輿論監督主體的自律機制,形成多管齊下、綜合管制的輿論監督局面,是當前推進公眾人物道德責任重建的必然選擇。
[1]向廷虎.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強化人生責任開放意識[EB/ol]http://jstjb.red-net.eom.en.2005-12-20.
[2]任靜偉.部分公眾人物道德缺失的現狀、原因及應對[J].探索,2014,(6).
[3]尹鴻.公眾性決定公眾人物話語責任[N].人民日報,2010-12-09,(006).
[4]論語·顏淵[M].
[5]〔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自由與立法:第2,3卷[M].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
[6]周偉,李興文,伍曉陽,戴勁松.透視官德缺失之痛[J].半月談,2010,(16).
[7]范以錦.公眾人物如何用好話語權困境[N].人民日報,2010-12-09.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0-111.
[9]張汝倫.思考與批判[M].上海:三聯書店,1999.556.
[10]何明.中國當代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重建[J].江西社會科學,2004,(1).
[11]〔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12]〔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5.
[13]黃瑾宏.論現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J].晉陽學刊,2011,(4).
[14][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5.
[16]〔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韓水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77.
[17]〔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局,1979.157.
[18]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強調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不斷提高城市核心競爭力[N].人民日報,2014-05-25.
[19]J.Primack,“ScientistasCitizens”,F.von Hippel,Citizen Scientist,A Touchstone Book,Published by Simon&Schuster,1991,P3-15.
[20]胡旭晟.法律的道德歷程—法律史的倫理解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3-34.
[21]田大憲.新聞輿論監督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139.
責任編輯文嶸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10
B824
A
1004-0544(2015)09-0051-06
江蘇省決策咨詢研究基地立項課題(15SSL045);江南大學社科項目(Z2015113000315)。
劉艷(1984-),女,山東日照人,法學博士,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