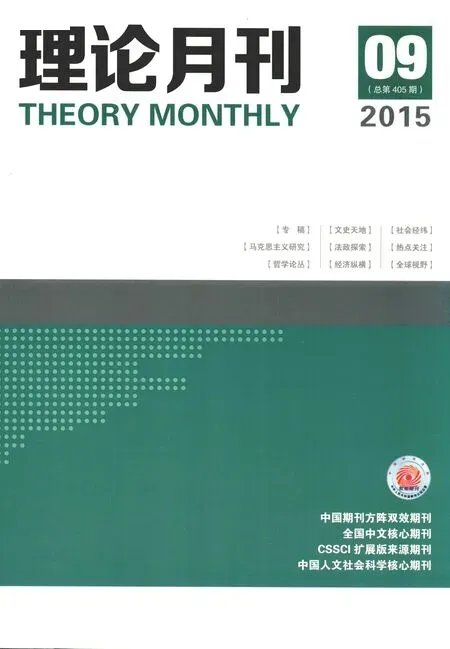集體腐敗的非正式規則及其規制路徑分析
□趙宸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集體腐敗的非正式規則及其規制路徑分析
□趙宸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近年來集體腐敗成為我國一種高發的腐敗形態。集體腐敗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一種合作的行為模式,它的形成與社會中長期存在的非正式規則不可分離。非正式規則是人們在日常交往中,通過自覺或不自覺的傳遞信息形成的行為約束,其形成與社會中的文化、傳統不可分離。非正式規則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也影響到正式制度的實踐效果。信任和服從是集體腐敗形成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非正式規則,故對集體腐敗的治理也應在制度設計時將對信任、服從等非正式規則的回應制度化、法制化。
集體腐敗;非正式規則;信任;服從
1 引言
集體腐敗又稱窩案,指多名官員結成同盟,共同開展腐敗行為,并將腐敗收益歸自己所有。近年來,集體腐敗已經成為我國一種主要的腐敗形態。200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韓杼濱檢察長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窩案”、“串案”增多已成為我國腐敗活動的新特點。[1]十八大后,我國針對腐敗的查處進一步體現出腐敗行為集體化的趨勢。2013年一年,除中石油、鐵道部兩個大型集體腐敗案件外,僅媒體就爆出了10多起集體腐敗案件,涉案人數達數百人,個案的最高涉案金額超過2000萬元。[2]在這些案件中,行賄者、受賄者及其他參與人員的行為相互依賴,人際關系與權力地位相互結合,形成一種縱橫交錯跨行業、跨地區的腐敗網絡。[3]集體中的成員為規避風險,最大化自身利益相互綁定,訂立攻守同盟,形成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共同利害關系。[4](P9)
集體腐敗的危害不僅在于其零和博弈的特點無益于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更在于這種腐敗行為導致內部監督統統失靈,使得權力這只老虎肆意妄為。集體腐敗中,許多核心成員既是掌權者,又是監督者,如市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5]為尋找保護傘,小團體往往主動滲透司法、紀檢等專門監督機關,將監督人員拉入腐敗網絡。這種“執法者犯法,反腐者變腐”的局面很容易使民眾將針對具體事件的不滿轉化為普遍性的信任危機,傷害政府的公信力。故而如何規制集體腐敗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
對于集體腐敗的成因,目前學界多將之歸結為法律的缺失,主張通過立法限制權力,避免腐敗行為的發生。近年也有學者從人際關系的角度對集體腐敗現象進行了分析,主張通過網絡監督和加重刑事處罰對之進行規制。[6]本文認為,在我國有關法律不斷完善的情況下,集體腐敗的大量出現表明了現有的社會條件中必然存在孕育集體腐敗的制度基礎。個體做出某種行為并非由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更多的是由于他處在怎樣的環境。同理,個體在特定的社會約束框架下有意識地選擇了 “合作”腐敗既不能簡單的歸于法律的缺失,也不能僅僅歸責于中國看重“人情”。當前司法實踐中,對集體腐敗的查處方式已體現出對非法律層面的關注,但尚未上升到理論層面。本文希望利用制度經濟學對非正式規則的研究框架對集體腐敗的形成機制予以分析,對集體腐敗的規制從理論層面進行探索,促進集體腐敗治理的法治化。
2 集體腐敗中的非正式規則
2.1制度與非正式規則
根據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的定義:“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地說,他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7](P3)個體層面上,這些約束減少了人們行為的不確定性,使個體可以通過分析有關約束條件,在政治、經濟或社會領域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策。國家層面上,這些約束會形成一個約束矩陣,決定社會中不同組織的行為方式,形成特定的社會治理結構等。[7](P7)諾斯的定義直白地將制度的對象全部涵蓋了進去。具體而言,他將這些約束分為了三類: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以及實施的形式與有效性。正式規則是由國家和政府有意識制定的,包括了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7](P65)非正式規則指人們在與他人的日常互動中無意識形成的約束,包括習慣、行為準則、思想意識等。[7](P50-51)它們多源于人們在日常交往中自覺或不自覺傳遞的信息而非國家的強制規定,是制度的內在體現。[8](P47)實施機制通過影響契約執行的成本影響權利保障方面的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對應的經濟績效。[8](P81-83)這三種約束共同作用,形成了特定的社會制度,并決定社會中個體的行為模式。
在這三種約束中,非正式規則是在人類長期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穩定的信念。它根植于群體的文化之中,賦予個體對社會行動與結果間聯系的意識傾向性。[9](P34-35)非正式規則在長期作用中形成了一套穩定的由群體內部制裁約束(socially sanctioned norms)的行為準則,當人們形成遵從慣例的習慣時,這些慣例便會凝聚道德力量,形成信念。由于人們依據信念行事的成本較低,因此,這種習慣一旦形成便容易產生依賴性。[7](P56)即使正式規則發生變化,相應的非正式規則也很難立即連動,從而導致改變后的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間的緊張。[10](P351-352)也因此,若想將一項新的正式規則植入社會,相應的非正式規則必須改變。
2.2集體腐敗與非正式規則
近年來,學界在分析集體腐敗及其成因時,普遍認為現有法律的缺失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主張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加強懲治力度來抑制集體腐敗的發生,這是一種對“正式規則”的理解。事實上,當正式規則的運行不盡如人意時,我們更加應當考慮法律法規的失靈是否與社會中長期形成的非正式規則有關。集體腐敗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其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然而,人畢竟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其行為模式的選擇離不開社會環境因素。因此,從“非正式規則”角度分析人為什么會“合作”更為合適。
毋庸置疑,“信任”和“服從”是形成合作不可缺少的因素,也在集體腐敗的形成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2.1信任。“信任是一種心理狀態,它基于對對方行為意圖的積極期望而愿意接受由此帶來的風險。”[11](P7)信任包括依賴與風險兩個要素,前者指一方允許其行為選擇被另一方的行動所決定;后者指如果另一方不合作會使信任者損失某些利益。[11](P6)在任何一個群體里,信任的建立都是合作的基礎,而如何建立信任及建立信任的難易程度會受到非正式規則的重要影響。
中國社會尚處于“自然秩序”(natural state)向“開放社會”(open access)過渡的階段,政治關系具有不穩定性。[9](P27-31)在此情形下,人們往往習慣于通過熟人關系對政治關系進行鞏固,規避風險。而“家”作為中國人際關系網絡的基礎,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幾千年來形成的人際關系的“差序格局”便是其體現。[12]在“差序格局”中,人們以自己為中心,按照他人與自己的熟悉程度對圈子進行劃分,以血緣、地緣、業緣作為重要的連接方式。對“自己人”表現出極強的信任,對非自己人則表現出較強的不信任。[13](P69)
基于“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思想,人們往往對自己的親人最為信任。當親人遇到困難時,個體多不問具體原因盡一切可能去幫助親人解決問題。這解釋了集體腐敗出現“家族化”趨勢的原因,當親人,特別是子女需要時,父母往往想盡一切辦法給予幫助,其中當然也包括利用自己的權力提供方便。而公職人員如果主動濫用權力換取收益時,也往往相信自家人不會出賣他,而將自己的血親、姻親等一步步編織進腐敗網絡。近期被查處的大量集體腐敗案件多體現了這種特點,如中石油窩案中的周家,茂名官場窩案中的原市委書記羅家。[14]這些家族腐敗案往往一人當官全家受益,一旦案發也是一損俱損,全家落馬。
在親人圈以外是熟人圈,熟人圈多以老鄉、同學這些有共同生活經歷的人為主。共同的生活經歷使人與人之間產生天然的親近感,并在長期互動中不斷加深對彼此的了解和好感,如通過拜訪、問候,饋贈禮物等方式增進感情。在此基礎上,雙方采用人情法則相處,即當對方遇到難題時,給予對方幫助贈予人情。[6](P187)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人有德于我,雖小不可忘也”,這種“報答”的意識促使人情收受方建立了在人情的施予方以后有需要時給予相等或更多幫助的觀念。這種社會性的觀念也使得不按照人情法則行事的人遭到其他人的譴責和孤立,而通過人情法則考察的雙方關系則會更近一步,從工具性的交換關系逐漸上升為情感性的交換關系。[4](P10)當雙方關系變為情感性時,雙方的關注點也會從“利害”上升為“責任”,將信任和合作作為一種義務,雙方的交換關系也得以穩定。[4](P10)
在集體腐敗網絡中,圍繞著公職人員及其親屬這個最內層核心的多是老鄉、同學等熟人好友。他們首先通過地緣、業緣等與公職人員建立聯系。然后通過長期相處,與公職人員通過人情法則進行利益交換。通過一次次符合人情法則的相處,他們與公職人員關系愈發緊密,最終實現擬親化,與官員“稱兄道弟”,發展出人際信任關系。在2007年著名的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案中,鄭的一名福建老鄉也是廣州某藥企老總,在經濟上給與鄭極大的資助,讓在北京沒有任何背景和后臺的鄭筱萸放心地花錢活動官職。而當上國家藥監局長后,鄭筱萸投桃報李,在企業的新藥批文、注冊審批等方面給予了相應的回報。[15]
在熟人圈之外還有一層陌生人圈,在中國社會,人們對陌生人往往表現出極強的不信任。[16](P143)與陌生人的交往多是即時的公平交換,一分錢換一分貨,不可延期支付。從陌生人變成熟人第一步便是需要一個熟悉的中間人,通過這個中間人的斡旋,兩個陌生人方能建立最基礎的弱關系。然后的相處,便與熟人圈的相處模式相同了。只是這種相處需要經過更長時間、更多次互動才能完成擬親化的過程。在集體腐敗案件中,大部分的官商勾結都是通過這種形式。先通過別人的介紹,公職人員與商人相識。然后,權力掌握者利用自己對信息的占有優勢,充當中間人,牽線搭橋以獲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通過一次次的互相利用、互相勾結,形成穩定的聯盟。以鐵道部窩案中商人丁書苗與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關系為例,丁書苗1997年通過時任北京鐵路局臨汾分局副局長羅金寶介紹認識了劉志軍,與劉從陌生人變成了熟人。在之后的相處中,二人建立了良好的交換關系。劉試圖將丁的企業作為自己的仕途基礎,為自己提供資金支持,而丁為劉花錢也十分大方。最終,劉利用職權干預了多個項目的招標,幫助丁獲得總額1700多億元的項目,自己也從中收取了巨額好處。[17]
在上述三個圈子中,熟人和陌生人實現擬親化被納入自己人圈子的時間成本高,風險也較高,但是集體腐敗中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關鍵元素。因此,集體腐敗圈子的最終確立通常是個緩慢的過程,但其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與傳統社會人際關系相仿的封閉性與穩定性。處于網絡中的個人利用權力創設尋租機會,利用網絡中自己人易于協調與溝通的特點不斷汲取利益,并在小圈子內分享,使網絡中的自己人得到情感和利益上的滿足,激勵各主體進行下一輪尋租行為。[6](P187)通過不斷的互動,嚴密的腐敗關系網絡建立,圈子內的人互相認同與接納,圈子外的人則受到排擠、冷落與提防。
2.2.2服從。集體腐敗中,并非所有人自始就積極主動地參與腐敗行為,很多人是被動涉入的。他們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從事腐敗行為,未準確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后果。當腐敗行為擴散至他們意識到自己身處腐敗之中時,他們盡管不贊成腐敗行為,但已很難退出,被迫繼續卷入其中。[18](P97)這一現象表明,自身的價值觀不是社會生活中決定人們行為的唯一要素,存在著其他多種力量沖擊著人的價值觀,導致人們做著自己并不贊同的行為。[19](P7-8)其中,“服從”這一非正式規則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歷史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使得父權的權威思想根深蒂固,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演化為對權威的服從。[20](P174)人們每到一個場合都會通過打聽他人的信息,對地位進行排序,進而確定是否存在權威。一旦確認,人們便會在行為上對權威產生依賴,進入一種“代理狀態”,當權威發出指令時,人們認為自己對他負有義務,是執行其意愿的代理,同時由于自己處于代理狀態,對自己行為的內容便不用承擔具體的責任。[19](P148-150)
群體效應也促進了“服從”的產生。中國人在行為上對他人的意見、看法、標準等十分敏感。人們日常習慣打聽別人的觀點,特別是別人對自己行為的看法,據此使自己的行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不標新立異。總體而言,人們更傾向于使自己與他人保持一致,社會順從度很高。[20](P175)
集體腐敗案件中,權力碎片化導致的時間效應和結構效應使得很多公職人員出現理性的無知,盲目的服從上級的命令。由于收集與工作有關的完整信息成本過高,公職人員并無動力也無能力獲取組織運作所需的全部信息。收到上級指令時,個人往往覺得自己只需聽話,其他都不用過問。[21](P71-72)加上行政機關的運作存在結構距離,即由于組織中各層級與職能分割明確,組織中各成員只需負責總任務中的一小角。[18](P99)各成員對這一小角的工作與最終后果間的距離被拉大,使他們難以對組織目標進行切實思考。成員們習慣于以機械化的方式完成工作,這種對規則的強調,卻使得規則變成了目標本身,導致了目標的替換,間接的培育了腐敗的溫床。[21](P72)
在這樣的情形下,當腐敗行為累積到個體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性后果時,由于個體已在腐敗行為中投入了時間、努力等成本,當事人更加容易被腐敗束縛,從不自覺的涉入腐敗轉變為主動腐敗。[22](P126)即使個體希望退出腐敗集體,在“服從”思維的作用下,有效的退出也非易事。①當然,個體的這種選擇并非中國獨有,外國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只不過在我國,由于人們十分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在行為上更傾向于選擇服從而非退出。有關內容可參見Miceli.M.Near JP.What makes whistle blowers effective?--Three field studies.Human Relations,vol.55 2002。(首先,同事、上級往往會給個體施加巨大的壓力,告誡個體小集體所形成的規則便是正當制度。如果個體的反抗表現的較明顯,團體也會對該個體實施排擠或者打擊報復。在此情況下,個體忌憚于自己的前途可能受到不利影響而不得不繼續服從于集體的行動。其次,由于個體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無法接受“大家都說我錯了、不好”的情形,當自己所想與集體產生對立時,個體往往對自己產生不信任,傾向于服從集體。再次,當個體繼續從事腐敗行為時,他們會認為因為自己不得不聽命行事而不需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一切有領導擔當。)當然,在此過程中,個體會由于行為本身的不道德性而產生緊張感,他們常會通過躲避來屏蔽自己行為的感知后果,弱化心中的負罪感,如:少收他人一些財物、幫別人辦事時更加用心等等,他們也會通過自我欺騙來減輕心中的不安,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很多腐敗分子都曾經高舉“反腐”大旗,一邊強調廉潔、法治的重要性,一邊進行腐敗行為。[19](P178-179)
總之,在集體腐敗中,由于理性無知的作用,個體最初對于上級的指令總是習慣性的遵守。即使個體感覺到體系的目的可能具有違法性或破壞性,令個體對權威或上級的指令有所懷疑,個體也多是在內心進行痛苦的自我懷疑,極少會做出破除體系的行為。習慣性的服從令團體運行的某些規則上升為集體內部的一項制度,使個體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將腐敗行為嵌入到集體行為規則中,使之成為組織內部的慣例。[21](P69)當個體充分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后果時,其已被集體腐敗束縛無法退出,只能越陷越深。
3 集體腐敗的解決方式——從非正式規則入手
當我們面對腐敗問題時,常常想著從正式規則出發,以籠統的立法解決問題。在這個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法律當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法律并非總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核心。如果法律忽略了非正式規則及其成因,那么極有可能創造一個“法律很多但秩序很少的世界”。[10](P354)對于集體腐敗亦是如此,既然“信任”與“服從”對個體選擇“合作”腐敗有著深刻的影響,對集體腐敗的治理也不妨從這兩個角度著手,選擇針對這些非正式規則的方式入手。
第一,破壞連接點,解決內部監督失效的問題。如前文所述,腐敗網絡很多由地緣、血緣或業緣等關系相連接。針對這種連接形式,期待所有公職人員有意識地忽略這種關系顯然不切實際。但是,破壞其結點卻是一種可行的方式。采用公職人員輪崗、一把手空降、異地任職等措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地緣、業緣的連接,防止腐敗網絡的形成。同時,當內部監督可能因腐敗網絡的形成而失靈時,可以引入外部力量突破這一網絡,借助自媒體平臺引入民眾監督便是可行的方法。自媒體平臺是一種近距離且互動性較強的介質,它可以顯著降低民眾參與監督的成本,使這種免費外部監督的廣泛性和動態性得到進一步提升。民眾對權力的運行進行評議,對權力腐敗進行批評、抗議和控訴,這種信息的零距離傳播和公開的互動性使官方無法不理會民眾公開的信息,從而既可在成本一定的情況下提高腐敗被發現的概率,也可震懾潛在的腐敗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集體腐敗內部監督失靈的困境。[23](P237)
第二,梳理權力流程,使公職人員對自己的職責有整體的把握。如前文所述,公職人員最初無意識的涉足于腐敗很多是與權力碎片化有關的理性的無知而產生的。盡管分權有利于權力的制衡,但隨著專業化加深,分權可能導致權力的碎片化。公職人員可能無法了解自己行為的后果,或是行為的后果需要經過一定時間期限方能顯現。對于此類人群,當他們意識到自己陷入腐敗之后,短期的退出成本往往高于繼續腐敗的成本,使得他們多拒絕主動退出。因此,避免此類人群深陷集體腐敗深淵的有效措施是避免其第一步無意識的介入。針對這種情況,制定完整清楚的權力流程圖是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權力流程圖以圖形的方式將權力的運行程序、行使依據、承辦崗位、職責要求等內容表現出來,這種簡單明確的圖示可以使公職人員了解完整的權力運行模式,定位自己所處的環節,了解自己的行為后果,從而避免“無知”的涉入腐敗。
第三,修改公務員法第54條。公務員法第54條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后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一條款雖然在文字上賦予了公務員抗命權,但在實踐中卻極有可能加劇下級公務員對上級的服從。首先,法律沒有規定當公務員認為上級決定錯誤時向哪一級的上級提出意見。從法條語義推斷,這里的上級很可能是下命令的直接上級。此種情形下,由于我國公務員的考核和晉升很大程度上與直接上級對他的主觀評價密不可分,而提出異議卻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出于自己日后晉升的考慮,下級公務員并無提出不同意見的動力。其次,法律沒有規定公務員提出異議的方式,導致實踐中下級公務員就算提出異議,也極易被上級否認,導致上級向下級推卸責任。[24](P31)再者,條文中提到“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關于“明顯違法”該如何界定?如果是上級命令與法律規定明顯沖突的情況較容易處理,公務員可以意識到“明顯違法”。[25](P53)但如果命令針對的事項本身就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性或只是龐大計劃中的一小個環節,下級無法準確的判斷上級的決定是否“明顯違法”,也就只能依命令行事。而當違法結果產生時,上級可能以此違法后果威脅下級,使得下級不得不繼續聽命于上級。可見,盡管法律賦予公務員抗命權,但實踐中因為規定不明確,抗命權未必能起到有效作用。針對這一點,可以通過細化公務員法第54條的規定,明確抵抗權的行使方式,如參照德國規定,公務員對上級指令有異議時,可向更高一級上級而非直接上級反映。[26](P54)同時,本條亦可增加公職人員如果事后知曉上級決定違法后的退出和減輕責任機制,使得非自愿涉入腐敗的公職人員知情后可以退出甚至舉報,從而有效的瓦解集體腐敗。
4 結語
誠如習總書記指出的:“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離不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權力與利益間形成粘連,提供了腐敗滋生的土壤。而在中國社會信任與服從的非正式規則的影響下,集體腐敗更是成為了近年來的嚴重問題,阻礙了我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依法治國,規制集體腐敗勢在必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提出“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為腐敗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指明了方向。對集體腐敗的規制也應建立在法治和制度的框架之下。在進行制度設計時,我們應當注意人們行為模式的選擇離不開社會文化的土壤。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信任和服從這兩種非正式規則在集體腐敗行為模式的選擇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信任的作用使集體腐敗的圈子呈現出以親人圈為核心,熟人圈、陌生人圈環繞于周圍的混合網絡結構。服從的作用使許多個體從無意識的涉入腐敗轉化為被動嵌入腐敗網絡甚至主動參與腐敗,從而鞏固集體腐敗的網絡。因此,在對集體腐敗的治理中針對這兩項非正式規則對癥下藥,能夠破壞集體腐敗生長的土壤,強化反腐敗法律治理的效果。
本文所提出的集體腐敗非正式規則層面的分析既非認為非正式規則是導致集體腐敗的唯一因素,也非主張只有通過改變非正式規則方能對集體腐敗進行治理。本文只希望為集體腐敗的規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認識這一現象成因,從而更有針對性地對之進行規制。可喜的是,當前司法實踐中已經注意到非正式規則的存在。在對集體腐敗的查處中,實踐中多從公職人員親朋好友及工作中的上下級入手調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能進一步將對信任和服從這兩項非正式規則的回應系統化、制度化,不僅有助于對集體腐敗的懲處,更能有效的防止集體腐敗。
[1]韓杼濱.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EB/OL].(2006-02-22).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06-02-22/ 00018-292.html,2014-12-21.
[2]王選輝.357官員卷入貪腐“窩案”[EB/OL].(2013-09-16).http://www.fawan.com.cn/html/2013-09/16/ content_455058.html,2014-12-21.
[3]唐利如.腐敗網絡:特征、類型與機理——社會網絡理論視角的腐敗及其治理[J].蘭州大學學報,2011,(1).
[4]陳國權,毛益民.腐敗裂變式擴散:一種社會交換分析[J].浙江大學學報,2013,(2).
[5]王妹.24省份書記兼人大主任[EB/OL].(2013-02-07).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2/07/ content_409760.htm?div=-1,2014-12-21.
[6]汪明亮.人際關系視角中的腐敗犯罪窩案現象分析[J].現代法學,2011,(2)
[7]〔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8]〔美〕道格拉斯·C·諾思.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M].鐘正生,邢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9]〔美〕道格拉斯·C·諾思,約翰·約瑟夫·瓦利斯,巴里·R·溫格斯特.暴力與社會秩序—詮釋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的一個概念性框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10]〔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11]Rousseau,D.M.,Burt,R.S.,Sitkin,S.B.,&Camerer,C.(1998).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 view of trus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3,393-404.轉自:姚琦,馬華維.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當代信任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
[12]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3]王飛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較研究[J].社會學研究,1999,(2).
[14]新華社.親人協作便于互相漁利——透視家族腐敗案件頻發的根源[EB/OL].(2014-06-28)[2014-12-23].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6/28/ c_1111363965.htm.
[15]趙何娟.鄭筱萸腐敗路線圖:負“人情債”起家“結團”尋租[EB/OL].(2007-04-10)[2014-12-23].http: //www.china.com.cn/news/txt/2007-04/10/content_80 93660.htm.
[16]鄒宇春,敖丹,李建棟.中國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會資本影響——以廣州為例[J].中國社會科學,2012,(5).
[17]何春梅.丁書苗被公訴 涉嫌非法經營和行賄[EB/ OL].(2013-9-7).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3-09-07/100579358.html,2014-12-23.
[18]薛剛.“涉入”與“知情”:集體腐敗道路上分離的兩點[J].政治學研究,2010,(1).
[19]〔美〕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對權威的服從——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學實驗[M].趙萍萍,王利群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20]侯玉波.社會心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1]張鵬.我國公務員集體腐敗問題研究——基于過程模型的視角[J].政治學研究,2011,(5).
[22]Donald Palmer,Extending the process model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42,2008.
[23]呂世倫.社會、國家與法的當代中國語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24]賀日開.公務員法中的制度創新與疏漏——兼與何穎教授商榷[J].中國行政管理,2006,(12).
[25]劉金榮.公務員不服從的行為研究[J].理論研究,2006,(2).
[26]〔德〕平特納.德國普通行政法[M].朱林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王友海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30
D630.8
A
1004-0544(2015)09-0163-06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4BFX005);江蘇省博士計劃項目和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APD)。
趙宸(1986-),女,江蘇南京人,法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