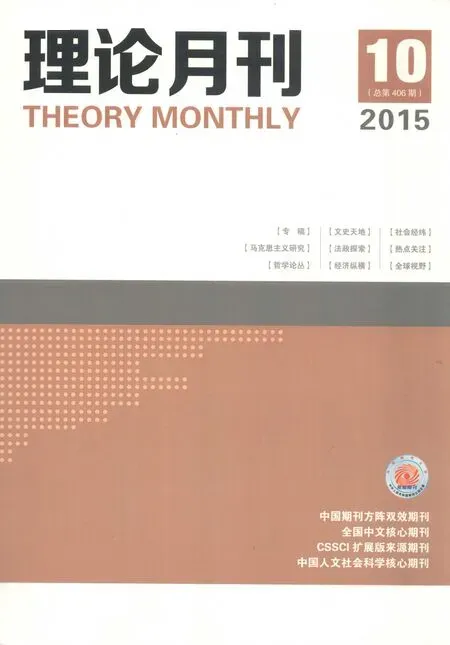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交往形式概念辨正
□張永慶(首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北京 100089)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交往形式概念辨正
□張永慶
(首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北京 100089)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交往形式不是語義含混的過渡性概念,而是貫穿歷史唯物主義整個理論體系的重要范疇。從現實的個人角度揭示交往形式概念的生成邏輯,可以看到現實的個人先后在交往形式一般、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三個概念中漸次獲得自身的總體性規定;同時,立足于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這一交往形式的內在批判,共產主義革命必然表現為一場交往形式的革命:追求在人格關系意義上實現現實的個人對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占有。交往形式概念的生成邏輯構成了馬克思把握現代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交往形式辯證法,它凸顯出歷史唯物主義所固有的交互主體性邏輯。恢復使用交往形式概念,能夠有效回應歷史唯物主義遇到的當代挑戰。
交往形式;現實的個人;交互主體性;歷史唯物主義
長期以來,人們對《德意志意識形態》交往形式概念存在很深的誤解。交往方式或被當作外延寬泛、內涵不明、可以與交往、交往關系隨意相互替換使用的“連體”概念叢;或被歸結成有待于發展為歷史唯物主義精確概念——生產關系的準備性概念,只具有過渡性價值。我的研究將要證明,以往的看法沒有把握到交往形式概念標舉的交互主體性內涵,低估了它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和發展中的理論地位,從而遮蔽了歷史唯物主義所固有的交互主體性邏輯。
1 交往形式的現象學還原:現實的個人生存其中的交互主體性世界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交往形式與市民社會是同義的。①《德意志意識形態》有兩處論述中,都表達了一個相同的看法: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40頁和第582-583頁。從現實的個人這個歷史唯物主義邏輯起點來看,市民社會在本質直觀的意義上無非是現實的個人的共同在世,即現實的個人的交往方式。現實的個人的交互主體性存在方式,同時必然顯示著其意向性存在的世界也同樣具有交互主體性的邏輯。
我們知道,自從胡塞爾提出意向性理論以來,這個描述思想和對象以及人和世界相互關系的觀念就成為20世紀哲學思想發展的重要指引。按照意向性理論,現象學還原所達到的自我,它總是有所意向的主體,與自身的對象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由此,理解主體與世界的關系獲得了一個超越近代哲學那種主客二分范式的新支點。若脫開外在的時間線索,從理論內在邏輯觀之,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論實則蘊含著意向性理論取向,率先運用了現象學方法。
1.1現實的個人與其意向性存在著的世界具有交互主體性邏輯
馬克思承認需求、需要是人之為人的主要標志,“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1](P514)但是,馬克思不是在抽象意義上理解人的需要,關鍵之點在于,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自身意向的世界同時存在的。在現實的個人那里,欲望或者需求是作為整體運動的一個要素、一個環節出現的,它不僅聯系著感性的物質對象,還在邏輯進程中生成為共同活動的交互主體性要素,即在共同活動中產生、滿足、發展的需求或欲望。可以說,有什么樣的需求、欲望就有什么樣的世界,有什么樣的世界也就會有什么樣的人及其需求、欲望。對于交互主體性邏輯主導下的人及其需求、欲望來講,市民社會這個人們共同存在的世界一個最為適合其本性的定義就是:交往形式。
1.2運用現象學方法把握交往形式
作為現實的個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會是包含有現實的個人 “在之中”此一生存論結構的 “世界之為世界”,所以,它本質上是處于生成中的生活世界。“在之中”與“世界之為世界”是由海德格爾表達“此在”生存論結構的兩個哲學術語,意在強調生成中的人與自己的周圍世界同樣具有始源性。對于同樣具有生成性質的市民社會,《德意志意識形態》在方法論上予以深入闡發:“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2](P526)這里,馬克思給出了一種現象學還原路徑,相當于“現象學剩余”的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結果的概括”。就市民社會的現象學還原來講,則是現實的個人生存其中的交互主體性世界。
1.3交往形式的交互主體性邏輯統攝市民社會的全部內容
在市民社會及其決定的上層建筑等所有的相關概念都趨向交互主體性的交往本質。感性、需要、生育、生產力、生產關系、交往關系、階級、國家和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都存在交互主體性邏輯。①我曾在共產主義謀求人的交互主體性解放意義上分析了市民社會及其決定的上層建筑都具有交互主體性面向。共產主義將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完成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顛倒”了的交互主體性生活進行再“顛倒”。參見拙文《共生式同一性:共產主義的辯證邏輯》,《理論月刊》2013年第11期,第10-15頁。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這里的分析,不同于國內學者已經提出的實踐中存在主體——主體關系那種交往概念。原則性區別是,我們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理論觀念出發。以往的研究雖然已經觸及到了歷史唯物主義交互主體性邏輯這一本質性的層面,但卻不徹底。因為,實踐觀作為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核心概念,盡管有利于恢復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哲學的思想水準,可并沒有全面深入地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賴以發起革命性哲學變革的基地——通過現代市民社會的研究而抵達歷史唯物主義新世界觀。在這個卓越的理論探索中,現實的個人在市民社會中的生產勞動始終是決定整個理論探索取向的主導問題。它不是從抽象的物質或精神出發,也不是從一般性地克服主客二分的、仍舊保持抽象性質的實踐觀出發,而是從“世界之為世界”的市民社會中的感性的活動出發。他們那種由上而下的貫通式的論證思路,難以真正描述出市民社會的交互主體性邏輯。
總之,作為現實的個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會,馬克思將它視為現實的個人生存其中的交互主體性世界,是有必要通過現象學直觀來科學把握的 “事情本身”。不過,這種現象學的思維要素只是馬克思以辯證法分析交往形式的一個構成環節,它只有在接觸現實中獲得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需要進一步分析處于生成、發展狀態中的交往形式總體規定性。
2 交往形式概念的發展邏輯:交往形式一般、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
《德意志意識形態》以現實的個人為邏輯起點,首次系統闡發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循著現實的個人概念的辯證發展線索,我們能夠梳理出與之交織的交往形式概念從抽象到具體的生成次序:交往形式一般、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
2.1馬克思恩格斯讓市民社會作為現實的個人之交往形式以最抽象的一般“出場”,這是交往形式概念辯證法的邏輯起點
這里,作為現實的個人“在之中”的“世界之為世界”,自然應該從什么是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的現實的個人說起。“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對于現實的個人的進一步分析,提出了生產勞動的核心意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接下來,馬克思第一次明確交待出與現實的個人密切相連的交往形式概念:“這種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2](P519-520)此時,交往形式概念處于自我否定發展的起點處,它自身雖然一開始就具有總體性的特點,但更多的具體內容尚有待發展階段。完整意義上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會概念將在后續的自身矛盾運動中獲得漸次豐富的規定性。
2.2交往形式是以生產關系面目出現的
這里,交往形式概念所反映的是現實的個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的“世界之為世界”。這個世界與現實的個人相互交織、相互纏繞、相互生成,構成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
由市民社會一般發展到生產關系概念,處理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把握現實的個人在市民社會中生產所呈現出來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當此之際,交往形式一般的規定性生成為生產勞動的社會性質。“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還是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2](P532)我們看到,在現實的個人概念發展為生產力概念的同時,他們的“在之中”的“世界之為世界”則體現為與生產力相統一“生產方式”。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論述:“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2](P533)這里的“人類的歷史”一語,是借用青年黑格爾派,尤其是費爾巴哈的語言所表達的社會概念,馬克思為了增加批判的反諷意味,對社會生活的真正本質采取反話正說而已。接下來,馬克思指出了生產力與社會狀況的實質性關系:“由此可見,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的聯系。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2](P533)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體,相對于生產力來考察現實的個人的“在世”世界,其實就是“生產關系”。
在生產關系意義上規定交往形式的含義及形態,并將之視為生產力的“世界之為世界”,對于市民社會辯證法來說,只是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與之相伴隨,歷史唯物主義獲得了新的理論內容,同時也實現了對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更深入的批判。就此,《德意志意識形態》對上述分析過程做了一個階段性總結。“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前面的敘述已經表明,這個社會是以簡單的家庭和復雜的家庭,即所謂部落制度作為自己的前提和基礎的……從這里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實關系而局限于言過其實的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的歷史觀是何等荒謬”。由于上述關于市民社會的討論是在生產關系意義上進行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還特別交待指出,“到現在為止,我們主要只是考察了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人改造自然”。[2](P540)我們看到,現實的個人由于一開始就是在市民社會總體性邏輯及其辯證運動中來獲得自身規定性,這里他們的“人改造自然”決非單純技術性活動,也不是以主客二分為思維方式前提的。當海德格爾以貌似惋惜的口氣提及馬克思“一度”深入到歷史中,但只是淺嘗輒止,最終錯失真正了解歷史的本真時間性質時,其實只是因為他沒有看到,與生產力密切相關的生產關系具有“世界之為世界”的規定性。因此,他看不清馬克思在何種意義上規定人的操勞、人的實踐,特別是人的生產力,換言之,他看不到經濟學意義及全部實證科學視野下的生產勞動與馬克思所講的生存論意義上生產力的原則區別。
2.3交往形式是以交往關系面目出現的
當交往形式即市民社會辯證法到達交往關系概念發展階段時,它表現為向交往形式一般規定性的回歸,這種回歸是將生產關系階段和交往關系階段的內容都統攝于一體的,展現出來交往形式的總運動。此時,交往形式一方面將前面的生產關系階段的內容收納入自身,另一方面又有這個階段的特殊性問題。這種回歸也是向現實的個人自身的回歸,即向人與人在人格意義上的相互關系意義的回歸。它主要包括:
2.3.1“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2](P581)是承認現實的個人主體地位的客觀條件。之所以必須是“現有的生產力總和”,不僅是說人的生存需要物質生活資料,更在于生產力在市民社會中的發展已經達到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世界交往的階段,比如在世界市場條件下人們已經不可能離開全球化的生產關系來實際地占有物質生活資料了。此外,占有之所以是“現有的生產力總和”,還在于,占有的主體方面不可能脫離現代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而單獨存在,他必須是,而且實際上他一直是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同步發展的現代社會主體。所以,這決定了占有的主體在實踐水平上與“現有的生產力總和”相匹配。
2.3.2實現現實的個人的個性自由全面的發展,對生產力的占有必須采取“聯合”這一形式。馬克思講,當現實的個人以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群體占有生產力時,他們必然“還受占有所必須采取的方式的制約”。馬克思指出“聯合”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發展出來的占有形式。“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權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權力被打倒,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普遍性質以及無產階級為實現這種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發展,同時無產階級將拋棄它迄今的社會地位遺留給它的一切東西”。[2](P581)
2.3.3生產和交往活動都成為現實的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內容。這里,一方面是活動本身的自由性質,另一方面是活動條件在“聯合”中由統治者轉化為從屬者。“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又是同各個人向完全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向自主活動的轉化,同過去受制約的交往向個人本身的交往的轉化,也是相互適應的。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條件總是表現為偶然的,而現在,各個人本身的獨自活動,即每一個人本身特殊的個人職業,才是偶然的”。[2](P582)
2.3.4共產主義革命是現實的個人將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置于人格關系——即“聯合”之下,現實的個人在理想的交往形式即理想的人格關系意義上的市民社會中的自由全面發展,從而最終在現實生活中完成了市民社會總體邏輯中終點向起點的復歸。“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2](P574)馬克思立足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這一交往形式的內在批判,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必然表現為一場交往形式的革命:追求在人格關系意義上實現人們對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占有。
當交往形式概念發展到交往關系邏輯階段時,現實的個人及其生產力形態在交往活動和交往形式中統一起來,從而完整地呈現出市民社會的總體性內容。“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范圍,盡管另一方面它對外必須作為民族起作用,對內仍必須組成為國家……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2](P582-583)至此,《德意志意識形態》通過對市民社會,即作為現實的個人的交往形式的辯證理解,已將個人、生產力、交往形式辯證統一起來。對此,馬克思闡發了三者之間矛盾運動全部社會歷史的意義。“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后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2](P575-576)
3 確立歷史唯物主義交互主體性邏輯的理論意義
圍繞現實的個人在交往形式中活動——這一生存論的始源性結構,《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闡述交往形式概念生成邏輯過程中勾勒出完整的社會生活圖景。由此可以推斷,立足市民社會即交往形式研究而確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具有交互主體性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恢復使用交往形式概念,有助于深入完整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并有效回應歷史唯物主義遇到的一系列當代挑戰。
3.1透過交往形式概念的生成邏輯深入把握現實的個人及其時代境遇
從交往形式一般、到生產關系、再到交往關系所構成的交往形式辯證法,它是揚棄現實的個人辯證運動于自身之中的邏輯總體,也是人們共同存在的世界。在達到交往形式辯證法的總體邏輯過程中,現實的個人辯證運動的自我否定圓圈與交往形式自我否定圓圈相互纏繞,不可分離。所以,交往形式辯證法的總體性,實際上表現為兩個方向相反的自我否定圓圈的共同運動,是兩個總體性的對立統一:現實的個人及其共同在世的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其中,現實的個人自我否定圓圈,永遠處于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意義上所揭示的現象學階段,永遠保持創造性、差異性、偶然性邏輯的優先地位;而交往形式概念運動總過程則揭示出回復到邏輯起點的現實的個人。作為現實的個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會,無論它處于生產關系階段,還是達到最后的交往關系階段,都被反向運動的現實的個人所影響,或表現為適應時的推進、建設、保護、改善,或表現為不適應時的牽制、抵抗、批判及顛覆。交往形式不是單向地受現實的個人所決定,現實的個人的意志、希望、理想反抗現實地統治著人們的一種歷史必然性——資本主義形態的市民社會,但是現實的個人在何種程度上達到自身目的需要通過交往形式提供的歷史條件來實現。依此觀之,馬克思所闡述的交往形式邏輯,特別是他有生之年系統闡發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邏輯——《資本論》,其實質是反彈琵琶,即為個性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理想來深入批判現實。直接來看,是論述資本對人和人類社會的全面統治,而行文的過程和最終理論旨趣皆在處處顯現基于現實的個人辯證法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否定性理解。但是,這種否定性理解不是阿多諾意義上的純粹否定,也不是后馬克思主義那種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夸大偶然性邏輯的政治實踐價值,而是把維護他性、差異性的偶然性邏輯與歷史中每一步達到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同一性邏輯現實地結合起來。
3.2交往形式辯證法的交互主體性邏輯為重新建構馬克思生產理論提供思想資源
一方面,在馬克思生產理論成為某些生態主義理論攻擊的靶子時,按照交往形式辯證法所規定的交互主體性邏輯來理解生產,特別是生產力,能夠有效地回應當代實踐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挑戰。以往,無論是對生產力概念作純粹工具理性的解釋,或者從外部尋找新的價值觀補充,都不能真正使生產力概念具有生態和倫理的內涵。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發現生產力概念并不缺少生態和倫理的維度。它囊括了感性、需要、生育(自然包含性別問題)、共同活動等等。并且,由于它始終作為現實的個人在交往形式中的共同世界中的存在,他自然具有對主客二分舊哲學及其衍生的工具理性意義上的生產活動的批判立場和革命要求。同時,在生產力概念內部的構成要素或環節那里,同樣趨向生產力指向的價值標準和革命目標。
另一方面,包括生產力理論在內的整個馬克思生產勞動觀念,常常被指責為陳舊的主體哲學范式下的形而上學。而在交往形式辯證法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勞動觀點已經包含交往和對話等公共性維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民社會作為現實的個人的交往形式呈現出物化或異化的狀態。共同存在的世界受制于某種交往活動的既成結果。如果說,資本體現的是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那么,在交往形式的交互主體性總邏輯之下,這種死的統治活的荒誕事實,則呈現為死的交往對活的交往的統治,是既有的交往規則對生動活潑的交往活動的壓制、否定、扭曲。這里,不難看出,20世紀后半葉哈貝馬斯提出的體制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觀念,其實也在一定意義上表達著與馬克思相近的看法。不過,由于沒有看到馬克思市民社會研究的交互主體性邏輯,哈貝馬斯誤判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范式,將歷史唯物主義歸結為一種尚籠罩在形而上學陰影下的主體哲學。而他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工作,只是在工具理性角度來理解生產勞動,在交互主體性討論中完全否定生產勞動這個奠基性環節,最終令自己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帶有烏托邦性質。
3.3從交往形式辯證法理解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彌補交往關系邏輯“缺環”及認識盲區
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表述中,將階級斗爭、社會革命、意識形態批判以及社會形態等理論視為“基本矛盾”的具體展開。若從我們揭示的交往形式辯證法來看,這種理解對于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把握尚不夠完整。主要問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等上層建筑原理存在邏輯上的“缺環”,因為只是談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對上層建筑的決定,難免忽視或遺落了這個決定關系在交往關系階段的實現方式以及交往關系對上層建筑的影響力。同時,這勢必進一步產生如下問題,比如,在某些邏輯階段上像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革命、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諸概念的已經確定的直接含義與有待發展到下一階段的間接含義的脫節;歷史唯物主義觀察現代社會的廣闊視野被人為地“窄化”了,似乎只有植入后現代哲學的所謂新觀念才有更新重生的可能;在后形而上學語境下歷史唯物主義被錯誤地批判為陳舊主體哲學話語;等等。所以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其一,交往關系在生產關系中所起到的潛在的影響作用,就是說,生產關系作為市民社會的本質關系同時還潛在地要實現人格關系意義上的交往關系;其二,生產關系作為市民社會的主導邏輯,還需要發展到能夠揭示更為具體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關系邏輯;其三,生產關系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有必要進一步經由交往關系邏輯來把握,使更多形態的政治實踐活動納入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分析中來。可以說,缺少交往形式辯證法的歷史唯物主義難免在上述問題上產生認識盲區。
3.4交往形式辯證法彰顯歷史唯物主義在交互主體性問題上的理論優勢,指明如何切實地把交互主體性邏輯從理論貫通到現實生活,從而與其他各種交互主體性理論劃清了界限
馬克思所展望的理想社會,是交往形式符合人們共同生活本性,沒有壓迫、平等相待的“真實的集體”。這個聯合體雖然也是現實的個人“在之中”的“世界之為世界”,但是完全有別于海德格爾對人的本真狀態的審美理解。應當承認,海德格爾超越近代哲學主客二分范式以及認識論形態來理解哲學和真理,這一生存論取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其中,關于人自身的理解,真正獲得了一種人與世界相統一的把握,即在此意義上的人,在生存論維度上規定為“操心”或“煩”。不過,現實性分析在海德格爾那里是極其匱乏的,人的共在只具有消極意義,并且,解決方式只是不干預現實的返回本真的存在。此后,這種本真狀態的人,在列維納斯那里轉向他人為中心的倫理形而上學,在黑爾德那里轉向以“羞怯”為始源狀態的世界現象學。總的來說,雖然他們逐步將人與人的共在引向正面意義的理解,但是仍然不能勝任向現實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切實貫通,只有馬克思通過現代社會交往形式研究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解答了這一理論難題。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劉宏蘭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03
A811
A
1004-0544(2015)10-0017-06
北京市教委項目(201110028010)。
張永慶(1969-),男,吉林農安人,哲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