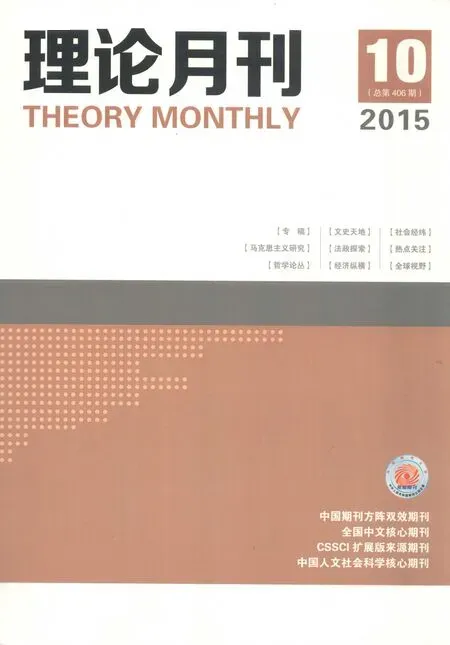論當代中國生態哲學思想
□王玉梅(華中師范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論當代中國生態哲學思想
□王玉梅
(華中師范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本文系統地闡述了當代中國生態哲學的核心內容和實踐意義。文中直面提出和明確回答了如下的重大難題:當代中國生態哲學思想究竟如何規定?應包含哪些內容?文中論證了當代中國生態世界觀的核心內容應包含:生態構成的整體觀、生態運行的和諧觀以及生態發展的持續觀,認為正是這三個基本觀點的緊密結合構成了當代中國生態哲學世界觀的核心理念。文中還論證了當代中國生態方法論的核心內容應包含:系統性原則、動態性原則以及多元性原則,認為正是這三個基本原則的緊密結合構成了當代中國生態方法論的規范準則。文章的最后部分則是論證當代中國生態哲學向實踐的轉化,即生態文明建設。認為生態哲學理念橫向運用即把它深刻融入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以形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布局;縱向運用即把生態哲學理念深入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的全過程,而就其發展的總目標而言就是要造就“美麗的中國”。
生態世界觀;生態方法論;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
每個時代的哲學思想都是它所處時代的精神結晶和思想精華。無疑地,當代新興的生態哲學亦代表著生態文明時代人類的哲學思考,是當今時代精神的精華。
馬克思主義認為,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體。世界觀是人們關于整個世界的根本觀點,即從理論上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樣”等具有最大普遍性的問題,它對人的一切認識和行動產生深刻的影響。方法論則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途徑或規范的學問,即指導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應當“怎么想”、“怎么做”等最一般的準則。正因如此,世界觀以其對人們的認識和實踐的普遍深刻影響而具有方法論的功能,而方法論也以其對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途徑的看法而具有世界觀的功能。也就是說,認識活動的根本觀念,無不具有方法論的品格,認識活動的規范方式,無不具有世界觀的品格。總之,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間本來就是同一學說的兩個方面,真正的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體。
對于任何一種哲學的解讀與評估,既可以從它的世界觀上評判,也可以從它的方法論上考量,這對于當代中國生態哲學而言也不例外。因而無可回避的難題是必須直面回答:生態哲學的世界觀究竟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包括著哪些根本觀點呢?同樣的疑問即:生態哲學的方法論究竟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包括著哪些基本準則呢?
生態哲學既是認識生態的理論和方法,又是保護和建設生態的理論和方法,因而它在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必然發揮著無比重大的作用。這里發人深思的則是,這種哲學思想轉化為實踐的進程,絕不是自發的演變過程,而是人們高度自覺地謀劃與實施的過程。那么,生態哲學究竟如何運用于當代現實而為實踐導向呢?即如何發揮哲理的先導作用,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呢?本文的主要旨趣是對以上諸問題做出明晰而中肯的回答。
1 生態世界觀的根本觀點
生態世界觀的崛起是人類世界觀演變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轉變。生態世界觀的形成、流傳以至主導則標志著人類的歷史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而進入新的生態文明時代,這種認識已被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所接受,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然而,生態世界觀究竟包容和覆蓋哪些思想內容呢?人們對此的認識大多是模糊不清的,尚缺少明晰的見解。筆者認為,生態世界觀的核心內涵應包含以下三個根本觀點。
第一,生態構成的整體觀。生態世界觀是一種整體觀,認為生態世界是由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各部分融合而成的統一整體,而且認為部分是依存于整體的,各部分的功能和作用是完全受整體制約的。猶如,人體是由各種組織器官的細胞構成的統一整體,而各種細胞都是依存于人體的,其功能和作用完全受人身整體的制約。
無疑,生態世界觀的核心或重心是“以整體為本”,而不是“以部分為本”。那種著眼于注重部分分析的世界觀不是生態的世界觀,生態世界觀是一種注重整體結構的世界觀。
依照生態世界觀,人們在對待生態構成的統一整體時,要求統籌兼顧、全面推進,科學地處理好整體發展進程中各部分、各方面、各領域的各種關系,防止某一要素孤立地片面發展,從而探尋實現整體效益的最優化對策。統籌兼顧是從整體出發,全面關注各個局部的訴求,強調各部分、各領域的協調發展,而不是離開全局的片面發展。任何部分都應把整體的發展需要內化于自身的發展之中,而對整體發揮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最終目的是從屬于取得最佳的整體效應。
第二,生態運行的和諧觀。生態世界觀認為,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它的各要素、各部分、各層次之間都處于協調發展,這樣才能維持整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我們考量各個部分時,必須率先考察每個部分與相鄰部分之間的關系,而且要準確地把握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聯度,認清各組成部分之間的有序互動和良性互補,即發現各部分之間及其與系統整體的關系處于和諧。
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轉化是一種遵循客觀規律的過程,在整個系統的運行中,每個組分都具有特定的功能,任何一種組分的功能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其他組分的功能,從而使整體呈現出多樣性特征。而且,整體的運行只有處于和諧即達到各部分之間協調互補、相輔相成時,整個生態系統才能實現穩定、有序與持續。正是這種協調互補、相輔相成的和諧,從而決定和保證了系統中多樣質能的整合以及系統運行的持續。所以,這種“協調互補、相輔相成”的和諧觀是生態世界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
總而言之,生態世界不僅是各個部分相互依存而具有復雜構成的統一整體,而且生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和發展,它的運行是和諧的。
第三,生態發展的持續觀。生態發展的可持續問題,不僅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持續的內涵至少包括三個命題:“一是人類的發展不應削弱自然界多樣性生存的能力;二是這部分人的發展不應削弱另一部分人的發展能力;三是當代人的發展不應削弱后代人發展的可能性。”[1]因此,可持續發展,不僅涉及某個國家、某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而且涉及全球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不僅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而且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需求。簡言之,我們要接受的是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兼顧當代人以及子孫后代需求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
生態哲學的持續觀意味著:發展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要納入經濟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軌道,發展要實現世世代代永續。顯然,這里所講的持續發展,不再是眼前的、一時一地的發展,而是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代內利益與代際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的發展。
綜上所述,生態構成的整體觀、生態運行的和諧觀、生態發展的持續觀是生態世界觀的根本理念,三者是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從三者區別的方面看,整體觀是從生態系統的整體和全局出發,用系統的、聯系的觀點來觀察和看待生態世界;和諧觀是從生態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層次、各要素之間相互協調的角度出發,用辯證的、運動的觀點分析和考察各部分之間的互動互補、相輔相成;持續觀是從歷時性的發展角度,以人類和生態的永續發展為出發點,對能源、資源和環境等提出保障滿足代際需求的問題;另則從三者的聯系方面看,整體觀與和諧觀是互為前提、互相貫通的,整體統一必然要求和諧運行,和諧運行也必然要求整體統一;而實現了整體統一、和諧運行,也必然要求實現持續發展。因此,生態世界觀既包括了橫向擴展的整體性觀念和和諧性觀念,也包括了縱向延伸的持續性觀念,這三個根本觀念的緊密結合和統一則構成了生態世界觀,成為一種新的生態哲學理論。
2 生態方法論的基本原則
世界觀與方法論是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對世界根本看法的不同,也就決定了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不同。生態世界觀要求人們用整體的觀點、和諧的觀點、持續發展的觀點去認識生態世界和理解生態世界,這也就決定了生態方法論是一種以整體觀為主導的規范方法論,它要求以系統的研究方式、動態的研究方式和多元視向的研究方式去考量和解決生態問題。這就是說,生態方法論的核心應包含著系統性原則、動態性原則和多元性原則。具體而言,運用生態方法論考察和處理生態問題,必須把握以下三個基本原則(規范準則)。
第一,系統性原則。生態是一個包括生物種與其周圍環境的眾多部分或因素而構成的復合巨系統。從結構上看,巨型生態系統是由不同層次和不同等級的子系統所構成的,即每個大的生態系統都由若干作為部分的小的子系統所組成,而各個子系統又是由若干更低層次的更小的子系統(或因素)組成的;從功能上看,每個生態系統中的任何部分(或因素)不管其復雜程度如何,都會以某種方式保持其特定的品性和功能,都會這樣或那樣地影響著整個系統,系統的整體結構呈現為各部分之間的網絡關系。正因系統的各個部分(或因素)之間相互制約、互動互補,從而使整個生態系統保持其內部結構的相對穩定性和運行變化的有序性與方向性。
誠然,當人們運用這種系統性原則來探討生態問題時,必然是從系統的整體出發,考察每一部分與其它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目的是探查各部分之間的協調互補和良性互動。
與整體的系統性原則相對立的是局部分析方法,局部分析法的局限性早就被揭露。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Hegel)曾經譏笑道:“用分析方法來研究對象就好像剝蔥一樣,將蔥皮一層又一層地剝掉,但原蔥已不在了”。[2]他還舉了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局部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一個化學家取一塊肉放在他的蒸餾器上,加以分解。于是告訴別人說,這塊肉是由氮、氧、碳等元素所構成的。但這些孤立單獨的元素已不再是肉了。這就說明,局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對于認識生態世界來說就更是如此。生態世界的基本特點就是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復雜性,因而,離開了系統性原則,對它的認識和理解則無從談起。
第二,動態性原則。生態世界的基本特征就是生生不息,處在連續不斷的演變、更新和進化之中。地球是人類的家園,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生態系統,它充滿生機、千變萬化,無時無刻不在新陳代謝。
宇宙是運動變化著的,地球是運動變化著的,長江流域是運動變化著的,……一切生態系統都是運動變化著的,這是有目共睹的。問題在于應當以什么樣的研究方式來考察和理解運動過程。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芝諾以為運動僅僅存在于感覺,而從理性上分析:運動是不真實的。芝諾以靜態的研究方式(“二分法”),振振有詞地論證了“飛矢不動說”,這是個著名的典型事例,表明以靜態的研究方式,不可能理解運動過程的真實性。
哲學史和科學史一再啟示后人,當代科學向復雜性、協調性、或然性進軍也頻頻揭示:若以靜態的研究方式去探討生態系統,那是根本行不通的。當今迫切需要的是以動態的研究方式去探索和理解生態的運行過程和機理。
第三,多元性原則。多元性觀念由來已久,世界萬物,其性無不多而雜。水很簡單,其構成卻是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其形態卻也是多樣,包含有液態、氣態和固態。無菌、無毒的水可以飲用。水若是污染了,不僅不能飲用,甚至作為生活用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都不適宜。正因認識對象(客觀實際)具有多元性,這就決定了認識方法(研究方式)也必需是多元性的。單是想到清潔水輸往境外出口可以賺錢,而沒想到水污染后輸出境外就得賠錢,那就不配擔任保護水源、防治水源之重任。研究和解決生態問題,必須依靠多元性原則,單方位、單向度的思維方式是無濟于事的,只有應用多元性的思維方式,才能將生態系統的各個方面、各種聯系的豐富多樣性完整地揭示。
現代科學倡導包容多元性的方法論,而且認定理論創新最有成效的方法是擁有多視角、多向度的兼顧互補。這早已有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的思維過程為范例。愛因斯坦本人曾對他提出廣義相對論的思維過程作了以下的描述:“正如電場是電磁感應產生的那樣,引力場也是相對存在的。因此,對于從屋頂上自由落下的一個觀測者來說,其降落期間是沒有引力場的,至少在最靠近他的周圍是不會有的。如果這個觀測者又從自己身上丟下一些物體,那么這些物體相對于觀測者來說,仍然是靜止的狀態,或者是勻速運動的狀態。而這與這些物體的具體的化學和物理性質無關 (在這種考慮中,當然要忽略空氣的阻力)。因此,觀測者有理由認為自己的狀態是‘靜止’的。”[3]由此愛因斯坦則發現加速度與引力場等效原理。美國精神病和行為科學教授盧森堡(Albert Rothenberg)把上述過程稱之為“兩面神”(羅馬的門神,有兩副面孔,能同時兼顧兩個相反的視向)思維。廣而言之,多向度、多方位的思維方式是通向理論創新的最佳途徑。[4]
對于生態方法論來說,多元性是個非常基本的原則。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遠不是簡單的誰主宰和誰從屬的關系,其中存在著既相互對立,又相輔相成,而且縱橫交錯的網絡關系。今日的北大荒早已不是冰天雪地的荒原,而是豐產糧食的“糧倉”。今日的“桃花源”,早已缺失田園詩所贊美的那樣抒情,而當今人們深感不安的是土壤和水源的嚴重污染,令人痛苦不堪!如果說在農耕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相對來說較為和諧,那么近現代社會經濟邁入工業化快車道之后,人與自然的關系就變得想象不到的復雜和嚴峻。南水北調、西氣東輸,這是人利用自然資源為社會造福。植被沙漠化,漫天沙塵暴,這又是自然對于人類破壞行為的無情懲罰。諸如此類的奧秘,絕不是一元的因果性所能解開的,它們是多元因果性環環相套的綜合效應。可見,人類與自然之間充滿著極其復雜的多元關系。這就要求人們在分析和解決生態問題時,不應以還原式的線性思維,單向度地分析這類復雜的關系,而應當直擊網絡關系開展多方位、多向度、多層次的總體性研究。
綜上所述,生態方法論的核心包含著:一是系統性原則。生態組成的所有部分之間都存在著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的網絡關系,借此聯結成為統一的系統;二是動態性原則。生態系統不只是一種復雜結構,更主要的表現為復雜運動過程,一切物種和環境因素都處于不斷地變化和發展的運動狀態;三是多元性原則。認識和解決生態問題是一項艱難的研究課題,需要動用多方位、多視向、多學科的協作進行總體的研究。[5]
3 當代中國生態哲學理論的實踐導向
真正的哲學不僅要科學地說明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指導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將理論導向實踐。如果沒有這種理論向實踐的轉化,那么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就只能是理論層面的抽象統一,尚欠在社會實踐中的具體統一。無疑地,把生態哲學理念實踐化為生態文明建設,這是一項偉大的創舉。這里的關鍵是首先將理論形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轉化成為設計實踐活動的具體部署。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6]這一論述表明,生態世界觀與方法論應當轉化為實踐活動,轉化為生態文明建設。
生態哲學的實踐化,就其橫向而言,就是將生態理念深刻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方方面面;而就其縱向而言,就是將生態理念貫穿于各項建設自始至終的全過程,引導人們的實踐“生態化”,目的是建成“美麗的中國”。
經濟建設的生態化。生態哲學為經濟建設明確規定了生態化的發展方向,要求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要承擔起節省資源、保護自然,創造良好生態環境的責任。人們發展經濟,不應當再像過去那樣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應當發展生態型經濟。生態型經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現在我們所大力提倡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雖然是從經濟活動的不同角度與層面來探討經濟模式的,但在本質上都是從屬于生態型經濟。低碳經濟強調的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而循環經濟則要求將生態理念運用于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全過程,是對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活動的總稱。顯然,中國必須開創出一條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經濟正在進行一場綠色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應當從“黑貓”變成世界最大的“綠貓”。
政治建設的生態化。把生態哲學理念融入政治建設,它為公共政策提供了優良的生態導向。這就意味著,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以尊重自然保護生態環境為立足點,政治建設需要一系列的深化改革和實踐創新。必須認真對當代中國所出現的生態危機進行深刻反思,把生態哲學理念滲透到政治建設的方方面面。現在我們所提倡的建立生態型政府,就是要用生態的理念來優化與選擇新的制度和設計新的施政操作方式。比如,建立綠色GDP政績考核體系、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稅收制度等生態政策體系,以及一系列保障生態的法制體系。必須采用非尋常方式改革政治體制、領導體制和運作機制等,不斷完善政治生態化建設。
文化建設的生態化。把生態哲學理念融入到文化事業中創造一種新文化——生態文化,即清除人掠奪自然的野蠻文化,而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文化。生態文化旨在弘揚生態的價值觀和賦予心靈活動健康的取向,使生態化(綠化)成為公眾心目中的責任意識,從而能夠有效地積聚起社會各方的力量,形成一股強大合力,共同維護生態和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生態文化將引導人們的思想行為發生根本性轉變,人人樹立起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和諧觀、代內代際需求上的平等觀以及尊重一切非人存在物所具有的生態價值。為了落實生態文化建設,要面向公眾積極開展生態文化宣傳教育,引導公眾自覺參與生態文化建設;要構建生態文化制度,形成系統的體制和實踐機制,實現生態文化在全社會的繁榮;要保護和發展民族的傳統生態文化;要吸收和借鑒國際優秀的生態文化;更為重要的是探尋生態文化的發展規律,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化品格。如此,則使中華文化的復興更具有獨特魅力。
社會建設的生態化。把生態哲學理念融入到社會活動中,構建一種以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為主導方向的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化是一項長期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不僅需要改變現代工業文明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運作方式,使之與自然界和諧協調發展,同時還需要從下述幾個方面促進社會活動自身的生態化:一是倡導綠色生活方式,形成健康、良好、文明的生活習慣,自覺抵制以消費主義為主導的奢侈、浪費、低俗生活方式的誘惑,從而造就追求綠色生活時尚的社會氛圍;二是加速綠化民居、社區以及公共交往場所,把保護生態觀念普及到家庭和社會的日常交際中去,擴大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使家家戶戶、村村鎮鎮珍惜資源與環境,追求綠化與公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三是努力落實社會環保工程的建設,眼前刻不容緩的是強制治理環境污染,嚴格禁止污染物排放超標,做好食物、飲水、呼吸等的安全保障。總之,社會建設生態化,就是要實現資源、環境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創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總而言之,中國正在崛起,生態哲學思想不僅激發了“美麗中國夢”,而且也為勤勞、勇敢、智慧的中國人民開辟了圓夢的成功之道。中華民族的生態文明建設必然對人類進入生態文明時代做出最卓越的、最宏偉的貢獻。
[1]余謀昌.生態哲學·序言[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4.
[2][德]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413.
[3]張巨青主編.辯證邏輯導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4.
[4][5]王玉梅.論生態研究方法的轉變[J].廣東社會科學,2013,(4):82.
[6]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9.
責任編輯文嶸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06
B262
A
1004-0544(2015)10-0034-05
王玉梅(1983—),女,內蒙古鄂爾多斯人,哲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