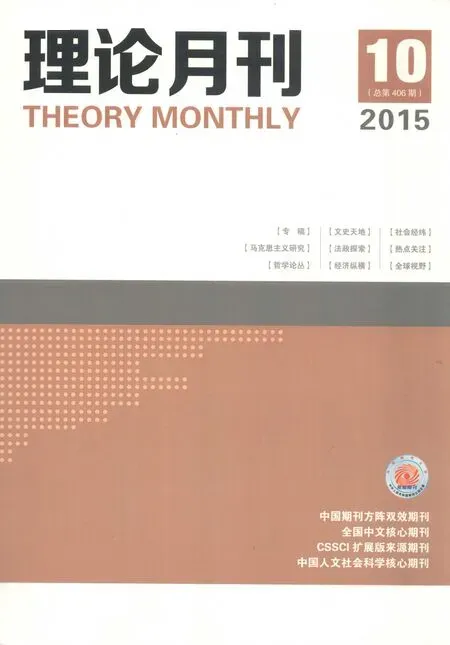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中間體系論”與生態文明建設
□孫玉健(河南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中間體系論”與生態文明建設
□孫玉健
(河南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分析環境破壞的原因進而探索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途徑,一直是西方環境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日本著名環境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宮本憲一,從社會的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的整體結構出發,提出了“中間體系論”,這是他繼“生產關系論”之后提出的新論斷,被稱為環境經濟學領域走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新環境經濟學。該理論不僅對當時日本的環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今天的全球環境治理也有一定的啟示。本文通過把握“中間體系論”的理論內涵和問題指向,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發掘“他山之石”。
生產關系說;中間體系論;生態文明建設
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一樣,是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1]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我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和面對的生態環境現狀是立足點,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是基本理論指南,而日本馬克思主義環境經濟學家宮本憲一的理論研究成果也有一定的啟示價值。
1 從“生產關系說”到“中間體系論”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值得我們學習,同時也需要我們認真反思,因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一方面帶來了財富的迅速增長,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嚴重的環境破壞,甚至威脅到人們的生存和健康。其中,從經濟體的角度被當作西方大國的日本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二戰之后,日本通過高速的工業化很快又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但是,到了上個世紀的80年代,日益嚴峻的環境公害成為困擾日本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引起日本許多學者的強烈關注和深刻反思。
既然經濟發展是人們共有的價值訴求,那么,如何看待發展帶來的這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里?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宮本憲一提出了 “生產關系說”,明確把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給公害的定義中就表明了他的這種觀點。他說:“公害又可以叫做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災害。它是由資本主義企業和私人經營的盲目性、無計劃地利用土地和資源,以及社會資本不足、城市計劃失調等原因造成的。”[2]可以看出,宮本憲一是從日本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來分析環境公害產生的根源,以“生產關系說”揭示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如何導致環境破壞,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的繼承和應用。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回顧一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生態批判。
作為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個重要視角,馬克思對資本條件下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并且成為后來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進一步闡發的核心論題。馬克思首先把人的生存環境作為人的異化存在的一個方面,通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人與自然的異化,控訴環境遭受污染的工人惡劣的生存條件。馬克思說:“任何一種感覺不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動物的方式存在。”[3]這就揭示了人的生活環境是與人相異化,生產者與自己的生存環境不再協調。接下來,馬克思又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具體分析,“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以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4]馬克思明確將工人生產與生活環境的惡化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聯系在一起,認為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導致的。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要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目的就是為新社會制度的產生和人類的解放提供有說服力的論證。正如當代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詹姆斯·杰克遜所言:“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概念是與他對通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來克服人類與自然分離的思考相聯系的。‘要想擺脫人類的異化狀態’,就必須‘以一種理性的方式控制與自然的物質代謝’,而這種目標只有在根除資本主義之后才能實現。”[5]回顧工業文明以來的社會發展史,可以發現,人類對生態文明的追求是價值理念的不斷提升、制度設計的不斷革命和發展模式不斷更新的產物,一句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批判和超越發展的結果,
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和批判相一致,宮本憲一揭示了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公害產生罪魁禍首,今天的公害說是社會殺人、社會傷害,確實恰如其分,而責任者就是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擁有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它們掌握著社會的支配權。因此,寄托在他們的支配權下的人們的生命與健康的責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6]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主體,他們通過科學技術和勞動力,以獲取利潤為根本,使用生產資料,開始了加速生產的工業時代,在創造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使所有人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
那么,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環境破壞問題就不發生了嗎?于是,反對者對“生產關系說”提出了詰難:難道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發生環境破壞嗎?當發現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同樣發生環境破壞這一事實時,宮本憲一開始反省“生產關系說”的簡單、片面性錯誤,認識到了“生產關系說”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不僅要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且應當從全部現存的政治經濟結構去說明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因此,他對自己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修改,以被稱作“中間領域”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分析不同所有制下的生態環境問題。這樣一來,“如果這些中間領域是決定環境的政治經濟結構,那么,不僅限于資本主義制度,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是決定公害及環境舒適性的政治經濟要素。”[7]以此為據,宮本憲一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環境破壞的性質和后果進行對比,得出的結論是:經濟體制的不同,所發生的公害及其與之相對應的后果也有所不同。就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因來說,這些國家由于落后的生產力,所以,在同資本主義競爭而發展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的過程中,以不同形式殘余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效率低下的官僚主義和軟弱乏力的民主主義,才導致生態環境破壞。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要杜絕公害問題的可能性是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大。可見,宮本憲一通過“中間體系論”來彌補“生產關系說”的不足,更客觀的解釋不同所有制下出現的環境破壞問題,從而形成了新的環境經濟學,為解決環境破壞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2 解決“市場”和“政府”失靈的新環境經濟學
在《環境經濟學》一書中,宮本憲一詳細歸納了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基本內容。社會經濟結構主要包括:(1)資本形成或資本積累的結構,即國民總支出的構成、公共及私人部門用于安全及保護自然、保護投資的質和量;(2)產業結構,就是每個業種的構成、物質再生利用的狀況,包括資源消耗量及污染物、噪音等;(3)地域結構,即城市內區位結構、沿海地區公共水域的利用規劃、人口過密或過疏的狀況,也就是城市和農村在國土上的配置,城市化、大都市圈的范圍和狀況,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整個交通系統,而以汽車為中心的交通系統是決定性因素;(4)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社區的協同生活狀況等。政治結構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國家公共力量干預的形態,另一方面是環境政策對經濟所起的反作用。對第二方面,他作了細致入微的考察:(1)基本的人權狀況,不僅是指財產權,而且還包括生存權,防止公害及環境保護方面的有效的社會權,以及社會權和財產權的比較優勢;(2)思想、言論、表現(出版、廣播等)、結社的自由,反對公害的輿論和運動能得到何種程度的保障;(3)民主主義的狀況,三權分立,特別是司法獨立、議會制民主主義、分權以及參與地方自治的制度能夠得到認可的程度;(4)國際化的狀況,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情況,大國的軍事力量和各國軍事力量的依存關系、跨國公司與國民國家的關系、國家間環境保護協定的狀況等。[8]在這里,宮本憲一把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環境倫理、民主狀況以及國際關系等多方面的交互關系作為自己環境經濟學的研究的主題,以新的方法論剖析和解決生態環境破壞問題。
宮本憲一對“中間體系”的界定以及隨后在《環境經濟學》一書的展開,突出這樣一個主題: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經濟學的“市場”和“政府”兩個因素,因為從生態環境破壞的角度來看,二者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已經失靈了,為此,反思市場或者政府主導下工業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大規模的生態系破壞和環境污染為表現形式的生態環境問題,來自人類工業化進程中的經濟活動。因此,人們的直覺一般是,經濟活動是當下環境問題的罪魁禍首,影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從對經濟活動的思考中汲取解決環境的策略,成了環境經濟學研究環境問題的直接切入點,進而研究市場、制度與環境間的多重互動。從分析的思路來看,環境經濟學一般從技術和制度兩個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或者認為支撐近代工業化的科學技術引起了環境破壞,或者認為主導近代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環境破壞的根源。這兩方面的分析思路說明,社會制度、物質和技術進步的外部效果都有可能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發生。然而,一定歷史發展階段,在既定的社會生產技術水平條件下,社會制度的差異必然成為影響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效果至關重要的因素。
作為工業化載體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以資本帶來利潤的最大化為主導價值觀,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必然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共同行為。人類的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的后果一定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被認為是一條不可持續的、反生態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運行機制的反思和批判,就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議題。而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一方面是市場機制,另一方面是政府機制。學者在對這兩種機制運行后果的反思中,提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兩種論斷。市場機制是一種成本損益經濟運作,市場成為資源配置最有效的方法,依照每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對他們的環境品質進行排序,高所得者享受高質量的生活環境,低所得者只有低質量的生活環境。然而,由于市場機制存在人的理性認知的有限性、市場壟斷、不完全和不對稱的信息以及社會公共物品、外部效應和市場交易費等等障礙,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當技術進步超越了以交換價值作為衡量標準的社會制度,并加大了市場的外部效應,則市場機制的合理性便會逐漸消失,這就是“市場失靈”。在宮本憲一看來,立足于“市場”來研究環境問題的傳統經濟學理論是不可能有效的,因為該方法論是把自然環境轉化為用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的商品,以現代技術和企業的經營為前提尋求“最適污染量”,用成本效益分析選擇實現社會保護環境的途徑,無視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存在的有限性問題。與市場機制相反,隨著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政府機制日益凸顯,政府應用管制、征稅、罰款、補貼等等非市場手段想使失靈的市場回歸正軌,人們希望在政府的導引與監督下對生態環境破壞進行管控。雖然在一定時期政府干預會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些政治性手段由于受制于資本主義的利潤,政府在采取干預行動的過程中沒有增進經濟效率,或政府通過再分配把收入給了那些不恰當的人,這就是“政府失靈”。在環境問題上需要政府干預的時候沒有進行及時干預,不需要政府干預的時候卻強行干預了,所以,宮本憲一認為政府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破壞問題。
既然“市場”與“政府”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上都會“失靈”,那么,探索新環境經濟學以超越“市場”和“政府”為主導因素的環境經濟學就成為當務之急,宮本憲一通過“中間體系論”思想的提出,就是構建這種新環境經濟學的嘗試。新環境經濟學力求通過對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整體,來把握生態環境問題的全貌,從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導致的后果和解決的對策等基本問題出發,闡明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與環境問題的重要關聯。
3 對“中間體系論”的評價及其啟示意義
宮本憲一以“中間體系論”取代“生產關系說”,不僅更有說服力地解釋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生態環境問題,而且探索解決環境破壞的新策略。對宮本憲一的這種理論變化,日本當代著名環境倫理學家巖佐茂給出兩方面的理論評價:一方面,認為宮本憲一的觀點在理論上缺少一致性。在巖佐茂看來,宮本憲一從“生產關系”以外的地方,即從社會的“中間體系”尋找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著公害的原因,與他把公害看作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發生的觀點不一致。要保持理論上的一致性,或者把社會主義公害當作環境問題,從概念上將公害和環境問題區別開來,或者就堅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不存在公害,在這兩者之間選擇其一;另一方面,認為宮本憲一之所以考察直接界定環境問題的“政治的經濟的要因”,是想彌補“生產關系說”的缺陷,但是,這樣一來,這個被看作是“中間領域”的“政治的經濟的要因”卻與“生產關系”的關系變得含混起來。既然不僅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而且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也可能發生社會公害,那么一再堅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不就是多此一舉嗎?[9]巖佐茂這兩方面的評價是有道理的,抓住了宮本憲一理論變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生產關系說”與“中間體系論”之間的理論差異。但是,不能過于追究宮本憲一在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因為,他是立足于解決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特別是為了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環境破壞的本質而調整自己的理論視點的,國內學者對“中間體系論”的評價正是以此為出發點的。
把宮本憲一的《環境經濟學》一書翻譯過來之后,我國學者對“中間體系論”基本上給予了積極肯定的評價,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第一,認為“中間體系論”克服了體制論所固有的缺陷,“中間體系論”不再以單獨的生產關系來分析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強調社會經濟體制與政治經濟結構在生態經濟學中的重要性,主張經濟與自然的循環發展以及人與自然間關系的研究,開拓了理論研究的新視野;第二,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作為環境經濟學的重要領域并使之明確化,說明對上層建筑因素的重視,是宮本憲一理論獨創的核心;第三,“中間體系論”為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政策法規、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尤其是對生態化政治經濟體制及其相關機制的建立開辟了新路。
結合以上評價,我們認為,宮本憲一的“中間體系論”以更加務實的理論視角,將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公害理論與社會主義的生態環境問題結合起來,這種分析思路對于我國目前的生態文明建設是有某種程度的啟示意義。第一,幫助人們正確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與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本質不同,正如奧康納所言:“雖然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生態問題,但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相比,它們有著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損耗和污染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經濟問題。”[10]在此基礎上,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是人民的健康生活而不僅僅是資本的贏利,或者說是以贏利為手段來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所以,盡管在一定發展時期,為了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財富的增長,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區域生態環境的破壞,但是,只要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目標不變,生態可持續性一定是我國社會的首要選擇。第二,有助于人們理解政治上層建筑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上的重要性,領會十八大報告下述論斷的政治意蘊:“必須更加自覺地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11]進而真正把握中國共產黨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自覺與政治追求。第三,讓人們更清楚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一種發展模式的改變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問題,而且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性問題,關涉到一個民族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不同民族國家之間利益的協調統一問題,進而明白全球生態環境問題一直得不到根本解決的原因,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為改善自身的生態環境狀況而轉嫁生態危機的做法。總之,宮本憲一以“中間體系論”為核心的新環境經濟學對全面思考我國目前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1]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23.
[2][6]〔日〕莊司光,宮本憲一.可怕的公害[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87.93,97.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5.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
[5]James Jackson.“The concept of Eco-Marxism”,http://environmental-activism.suite101.com/artical.cfm/the_concept_ecomarxism,accessed on 13 July 2010.
[7][8]〔日〕宮本憲一.環境經濟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4.57、55-56.
[9]〔日〕巖佐茂.環境的思想:環境保護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處[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22-23.
[10]〔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
主義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418.
[11]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責任編輯文嶸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10
F019
A
1004-0544(2015)10-0056-05
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 (2013BKS007);河南農業大學 “科學發展觀與農民權利研究中心”項目(KYZX201308)。
孫玉健(1969—),男,河南鹿邑人,河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