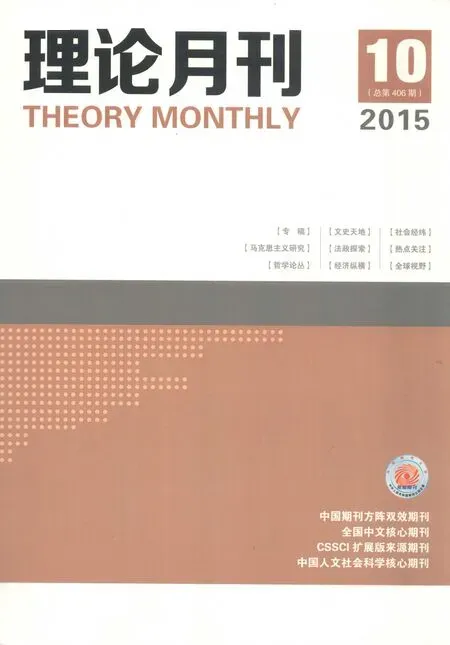性別話語下明清小說戲曲中的昭君投江敘事
□楊宗紅(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1331)
性別話語下明清小說戲曲中的昭君投江敘事
□楊宗紅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1331)
昭君和親是西漢歷史上的大事件,然而到了小說戲曲中,昭君卻由和親英雄變成了投江的貞節烈女。“投江”情節的增添,反映了男性話語對貞節的不斷加強。在男權視野中,昭君兼有天使與禍水的雙重隱喻,這就注定了“投江”的必然。投江敘事,隱藏著男權對女性貞節的規訓策略。五四以后,“去投江”敘事經歷了從反傳統到“情本”,女性本體意識逐漸被強化。
性別;昭君;投江;貞節
昭君和親,由于史書記載所留下的許多空白,為歷代文人吟詠、敘述留下了許多想象的空間。昭君怨、帝王恨、畫師丑圖等在詩文及戲曲小說中被不斷渲染,其中又增添了昭君投水之情節。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蘇珊·格巴指出,在文學創作中,“男性作為作家在創作中是主體,是基本的一方;而女性作為他的被動的創作物——一種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體,常常被加以相互矛盾的含義,卻從來沒有意義。”[1](P165)男性話語權下的女性書寫,即便不乏對女性的同情,卻總會染上深刻的男性意識。昭君和親故事中被硬加的“投江”情節,更是男權社會中男性中心意識的外化,是被強化的王權、夫權對女性倫理規范的必然。
1 “投江”情節的定型與男權地位強化之關系
昭君和親是西漢歷史上的大事。《漢書·元帝紀》詔曰“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漢書·匈奴傳》載:“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后漢書·南匈奴列傳》載王昭君至匈奴后,“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后單于閼氏焉。”前漢書中,昭君對和親態度不明,后漢書中,昭君則因怨而主動請求和親。兩漢書都揭示了一個重要史實,不論昭君態度如何,她都是漢帝“賜”予匈奴的禮物,是漢匈友好的使者,她留在匈奴、且改嫁,還生有子女。據翦伯贊《王昭君年譜》,昭君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后30年,享年84。所以,昭君投江,是莫須有之事。
文學表述與歷史敘述總有差異。昭君至匈奴后的史實被文學改寫,始于東漢蔡邕的《琴操》。據《琴操》,昭君到匈奴生一子,因不能接受“父死妻母”的胡俗,乃吞藥自殺。其后,晉代石崇、唐代儲光曦、王建等人的詠昭君詩,其重心都在昭君之怨。至《王昭君變文》,寫單于對昭君甚好,將其立為皇后,然昭君思鄉思漢,最終憔悴而亡。上述文學作品對昭君出塞的結局雖然側重其悲怨,卻仍隱含昭君嫁與匈奴王,在匈奴生活的事實。昭君去匈奴后結局的大改寫,馬致遠《漢宮秋》功居至偉。《漢宮秋》寫元帝面臨強大的匈奴與群臣的無能,只好讓昭君和親。昭君同意和親,卻在行至黑水時,投水自殺。此后,《昭君出塞》、《昭君夢》、《和戎記》、《吊琵琶》、《雙鳳奇緣》等,一致同構著昭君投江的凄美敘述。《吊琵琶》說王昭君投交河,《和戎記》說昭君投烏江,《雙鳳奇緣》說昭君投白洋河。小說如此,戲曲也是如此。《風月錦囊·正科入賺》之舊本戲文《王昭君》的劇情梗概中也有投江這一情節,云:“昭君含淚和戎,到邊城詒殺毛卿,勒取降書王印。跳入烏江,犬羊不混,[至今]青史留芳,令人堪羨。”[2](P4)“凡是老生常談,其間總隱藏著人們共同關心的話題”[3](P21)“只有一種對現在生活的興趣才能夠推動人去考查過去的事實。因為這個緣故,這種過去的事實并不是為了滿足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為了滿足一種現在的興趣。”[4](P334)自宋代開始,“夫為妻綱”被高度推崇,女性的貞節也被理學家提到“天理”的高度。寡婦改嫁被抨擊,守節被視為美德,各地方大興貞節牌坊。到明代,朱元璋發布榜文,鼓勵戲劇上演“義夫節婦”。他還下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免除本家差役。”[5](P1254)朝廷通過建牌坊、賜旌門的方式加以宣揚、鼓勵殉節的烈女。貞節婦女不僅給家族帶來榮耀,還為她們的宗族免除了徭役,解決了經濟問題。朱元璋還命儒臣修 《女誡》,作為天下婦女的教科書。明代,女性教科書除《女誡》之外,還有徐皇后的《內訓》,章圣皇太后的《女訓》,慈圣太后的《女鑒》等。至清代,理學進一步被強化,其間雖然出現鼓吹婚戀自主的論調,但節烈觀仍然風靡天下。
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女性貞節觀念在明代開始走向登峰造極,于是,“烈女”愈來愈多。據統計,自周代起至清代,節婦烈女的數量總計為 49383人,而明清兩代總人數就多達 48152人,占總人數的 97.5%,從人數上看,是歷代以來節婦烈女數量最多的時期。《明史·列女傳》中記載了265位忠孝、節烈婦女,其中貞婦、貞女占有很大比例。據《古今圖書集成》,有明一代節婦烈女多達35829人。[6](P112)
《漢宮秋》的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此時正是理學興起之時。雖然《漢宮秋》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做理學的傳聲筒,但仍難免留下理學的痕跡。其他小說和戲曲中的昭君形象,都打上了理學的烙印。虛無的投江“史實”與不斷反復言說的 “鑿鑿可信”的投江情節之間的悖論,顯示出男權社會中男性文人不斷強化自身地位的努力,以及整個過程的長期性和艱難性。
2 投江敘事的天使與禍水隱喻
男性以自身為中心衡量女性,將女性分為兩種類型:天使型與禍水型(在更多時候人們更愿意用“妖魔”來表達)。鄧尼斯指出,在男性社會中,女性從屬地位導致她們“或者被拔高為女神、貞女、母親,成為純潔、仁慈和愛的象征;或者被譴責為娼妓、巫婆、誘惑者,成為變節、惡毒和淫蕩的象征。”[7](P9)在昭君身上,天使與禍水共存。
昭君是天使。她不僅姿色卓絕,而且還有很多美德:多情、溫柔、善解人意,關心民生疾苦,她堅強、勇敢、聰慧、堅貞、果斷,勇于自我犧牲。她不賄賂畫工以求進;當國家面臨危難,她拋卻兒女私情前去和親,以解決兩國兵鋒。在不令兩國交惡的情況下,為貞節保持而投江。《漢宮秋》第三折中,面對匈奴百萬雄兵南侵,昭君也贊成和親。灞橋送別,昭君云:“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詩云:)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色!”“妾既蒙陛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與陛下闈房之情,怎生拋舍也!”[8](P314)昭君力圖通過和親免除戰爭,為丈夫掙得一個安穩的天下。《和戎記》云:“夫妻兩分離,奴心欲自盡,與君王相守難拋棄。中原堪嘆同胞弟,最苦交鋒休怨憶,安定江山封贈你。”[9](P80)又云:“能舍一人之命,保全萬載之邦,救萬民之難,免吾君之帝褂。與王分憂,妾死無怨。”[9](P104)“第一來難舍父娘恩,第二來難割衾枕,第三來損壞了黎民,第四來百萬鐵衣郎晝夜辛勤,第五來國家糧草都虛盡。今日昭君輸了身,萬年羞辱漢元君。寧作南朝黃泉客,不做夷邦掌國人。”[9](P116-117)由此,昭君離開漢宮之不舍,就不僅僅是強烈的故國情懷,還有強烈的夫妻深情。昭君在夫妻情與國家民族大義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展示了她的家庭天使形象與民族英雄形象——這正是男權對理想女性的要求。
但昭君也是“禍水”。“紅顏禍水”是文學中常見的母題,作為有意味的形式,蘊藏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甚至是民族的無意識。《新唐書·玄宗本紀贊》:“嗚呼,女子之禍于人者甚矣!”歐陽修認為,唐朝從高宗到玄宗,經歷了不少女禍,直接影響到唐王朝的國祚。清朝學者趙翼《廿二史札記校正》甚至專列“唐女禍”一條。古代文學中不乏女色害人的故事或議論。徐石麒《浮西施》雜劇借范鑫之口指斥西施“天生尤物,善笑工顰,遇一君則迷一君,在一國則傾一國”。[10]作為“紅顏”,昭君不可能脫離人們固有的“禍水”觀評價。宋代詩人喜愛反彈琵琶,在為毛延壽辯解時,更不惜將昭君指向紅顏禍水,將她與亡周的褒姒、滅吳的西施、引起安史之亂的楊玉環類比。蕭澥《昭君詞》:“琵琶馬上去躊躇,不是丹青偶誤渠。會得吳宮西子事,漢家此策未全疏。”陳僴《讀明妃引》:“驪山舉燼因褒姒,蜀道蒙塵為太真。能遣明妃嫁夷狄,畫工原是漢功臣。”鄭清之《偶記賦王昭君漫錄之》云:“伐國曾聞用女戎,忍留妖麗漢宮中?如知褒姒貽周患,須信巫臣為楚忠。青冢不遺芳草恨,白溝那得戰塵空?解攜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議功。”昭君成功使匈奴向漢稱臣,有功漢庭。但詩人們卻認為,昭君倘若不遠嫁匈奴,她在漢宮中的作用,與西施在吳宮中、楊貴妃在唐宮中的作用沒有區別——都會魅惑君王,令君王沉溺于美色,最終將令漢王朝落得國破家亡的結果,指控不可謂不嚴重。尤其是鄭清之直接以“妖麗”言昭君,足見其對“紅顏”的敵視與恐懼。女色禍國,毛延壽將禍水從漢宮引向匈奴,避免了漢宮重蹈吳宮覆轍,也避免了太真“蜀道蒙塵”的悲劇,當之無愧成為“功臣”。
“傳統的文學史是由一個個的‘文學經典’匯成的男性文學的歷史,這些經典將男性文本和男性經驗作為中心,處處顯露出對女性的歧視,甚至是憎恨。”[11](P 6 9)宋以后的昭君和親書寫,仍然不可避免的受紅顏禍水的影響。無論是小說還是戲曲,都無一例外的寫到單于垂涎于昭君的美貌而倚仗強兵索要昭君,否則就發動戰爭。如此看來,這些作者們都有意無意的將昭君視為引起兩國之爭的尤物或禍水。在具體敘述中,作者也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闡釋女色禍水的觀點。《漢宮秋》中,漢元帝初見昭君,說道:“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8](P309-310)漢元帝寵幸昭君后,如癡如醉,久不理朝綱,而且新添了毛病,“一般兒愁花病酒。”[8](P312)當單于索要昭君,尚書在一旁蠱惑漢帝:“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興兵吊伐。臣想紂王只為寵妲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8](P313)“不是臣等強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況自古以來,多有因女色敗國者。 ”[8](P314)
昭君的自殺與“被自殺”,是作為天使或禍水的必然。天使是圣潔的,善于自我犧牲。她們從身體到心靈都保持著純潔。一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既然成了漢帝妃子,相對于漢帝,昭君具有了臣子與妻子的雙重身份。作為臣子,應輔佐君王解國憂國患,致力于國家大事的解決;作為妻子,應堅守對丈夫的忠貞,憂丈夫之所憂,急丈夫之所急,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當國家面臨戰爭,和親可以解國難,這是臣子之職責,也是妻子之責。但妻子和親,是對丈夫絕對權威的挑戰,置丈夫于尷尬之境。“每一個女人都屬于某個家庭中的男子,女子的‘失貞’意味著她對‘這一個’男子的利益的徹底背叛;更是因為它觸動了女性的私人性質的人際關系,破壞了女性自身以‘性的服務’為前提的生存基礎,并因此危及到父權社會的基礎—父權私有家庭。”[12](P23)天使絕對不會損害夫權,也絕對無法忍受自己被“玷污”而淪于“不潔”。所以,她們采取果敢的行動以避免對丈夫的背叛與被“玷污”的命運。一方面要解危難,一方面要保貞節,昭君在和親之初就做好了“當效一死”(或自盡)的準備。最后的投江自然破解了國難與貞節的尷尬,于國于夫有利而無害,于己,則達到道德的完滿。有論者指出,女性自殺乃是一種道德的完善,“她們的選擇不約而同地通向一種道德完滿的極致,這固然也是為了免卻茍活和失節帶給一個婦女的種種不幸,但歸根到底,這種完滿和不完滿,幸福與不幸的所有結局都已經被社會所預定。”[13](P53)昭君投江雖然是莫須有之事,在紅顏禍水觀以及越來越強化的節烈觀主導下,卻似乎越來越“真實”了。
天使或禍水的自殺,實際上是男權社會在思想上以女性身體作為犧牲品以祭獻傳統社會道德。法國人類學家勒內·吉拉爾指出,人們在選擇替罪羊時,通常選擇那些極端者:極端富裕和極端貧窮,極端成功和極端失敗,極端漂亮和極端丑陋,極端惡習和極端德行,極能誘惑人或極令人討厭,婦女、兒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強者的極端強大都是眾矢之的[14](P23)。當現有各種社會秩序遭受破壞,必須尋找一個替罪羊代替群體受罰,洗除群體罪孽。選擇替罪羊時“不是罪狀起首要作用,而是受害者屬于特別易受迫害的種族。”[14](P21)當漢匈戰爭即將爆發,漢王朝陷于極不利境地,昭君的性別、身份、地位、美貌等決定了她的犧牲品或替罪羊命運。
作為天使,昭君主動選擇死亡以維護自我價值與國家價值;作為禍水,昭君則“被選擇”以死亡維護傳統價值。作為禍國的女色,歷來貶斥者多,對其結局的安排也是負面的。然而,王昭君雖是“禍水”,她和親的歷史事實和歷史功績不可能一概否定。男性作家巧妙地安排昭君投江自殺,以此消解昭君和親的歷史事實與現實節操觀之間的悖論,而且此舉給昭君披上了忠貞、愛國、愛君、愛夫的美麗紗幔,使之化身為天使,一來消解她“禍水“的沉重背負,二來掩蓋了將她作為替罪羊的事實,三來為昭君投江作鋪墊。天使也罷,禍水也罷,昭君“被投水”是封建社會大多數男性的共識,不可更改。
3 投江情結與貞節規訓
所謂情結,是指人內心的強烈的無意識的心理活動。宋以后的文人在昭君敘事中所具有的投江情結,不是偶然。
中國古代文人具有強烈的用世精神,但由于家國同體以及對帝王權威的認同,不可避免的產生臣妾心理。自屈原香草美人的思維方式建立之后,以臣妾自喻成為中國文學中獨特的文學現象。屈原投江賦予死亡詩意,投江因此成為男性忠貞愛國的另類表述。屈原“投江”這一情節所代表的悲怨及對節操的堅守,經過歷史的沉淀、發酵,越發醇厚濃香。當深受理學浸染的文人審視同為湖北秭歸出生的昭君及和番事件,便不自覺地將“投江”移植到昭君身上。《吊琵琶》中,王昭君到了番漢交界之地的交河,昭君涌起強烈的故國之思。“這一條,向南朝;那一條,向北朝。古詩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這不是交河,分明是白馬胥濤,汨羅江上潮。”[8](P330)在深受理學影響的文人看來,“存天理”,就必然要“滅人欲”,女性又怎么可能離夫另嫁呢?故而,小說戲曲不斷描述昭君對君王的不舍,對另嫁他人的抗拒,最終投江。昭君投江實際上是男性文人依照固有的臣妾心理,想象女性對待和親的態度以及應該采取的行為,代昭君言,代女性言。“所有男人寫關于女人的書都應加以懷疑。因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訟案中,是法官又是訴訟人。”[15](P10)男性文人的女性代言,不管有多接近女性本來的心理,仍然難免帶有他們對女性強加的“當然”。
昭君投江,是文人共同合謀的結果,是對女性貞節的規訓策略。
自宋以后,昭君的貞節受到文人的反復詠嘆。陶安《昭君圖》:“龍沙月照漢宮詞,毳錦衣裘換陸離。君命和親勞敢憚?夫綱定分死難移!”[8](P64)南宋末趙文《昭君詞》:“胡俗或妻母,何異豺與狼。仰天自引決,愛此夫婦綱。大忠與大義,二者俱堂堂。”[16](P189)小說或戲曲家將昭君由良家子改為深受漢帝寵愛的后宮妃嬪,而且二人之間感情深厚。他們注重昭君作為妻子的身份,不吝筆墨寫昭君與漢元帝的難分難舍,突出他們的恩愛之情,以此作為昭君忠貞的前提。《昭君夢》第二折:“如今已是數年,只到俺芙蓉如面柳如腰,那知我冰雪為心玉為骨。所以奴家忠心不死,每日里懸念皇朝,好生傷感人也。”[17]《和戎記》:“我身待學浣紗女,效取當年朱妙音。守節后來全大義,誰想烏江埋我身。……身體發膚難保全,傷風敗俗亂綱常。奴家不把清名朽,將身一命喪長江。”[9](P130-131)在太白金星的幫助下,昭君白雁傳書給漢王。“一表君臣之義,二全夫婦之情,三顯昭君貞節。”[9](P119)這里,作者突出“節義”與“綱常”,突出夫綱難移,冰雪之心與玉之骨,顯然倫理觀深入昭君靈魂深處。《雙鳳奇緣》虛構出昭君在胡地生活長達十六年,憑借自己的意志,也憑借九天玄女所賜的一件仙衣保護自己的貞節,最后還是投江自殺。昭君的投江,是為了要保留貞潔,——一個妻子對丈夫的貞節。投江,是對夫綱的維護。
倘若重新審視歷代關于昭君和親的言論,不難發現,不少人甚為鄙視這種“失節”之行。唐傳奇《周秦行記》中,牛秀才歇息時,戚夫人、潘妃、綠珠均以各種理由推辭陪宿,最后太后要昭君相陪。理由是:“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于是,“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予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18](P16)同為女性,昭君卻逃脫不了陪宿的命運,與一般妓女無二。昭君和親及改嫁的經歷成為她生命中不可洗刷的羞辱,使之成為太后令她陪宿的理由。更甚者,當牛秀才去昭君院,昭君不僅陪宿了,在離別之際,還“垂泣持別”。這個故事中,昭君并不是小說的中心人物,但簡單的敘事中,她水性楊花,毫無節操的形象躍然紙上。唐龍公開說昭君和親乃“女德之辱也”。明人李有朋《明妃新曲并序》云:“明妃漢宮人也,出嫁呼韓邪君命也。再媵復株累誰所命哉?妃方幸外國,無防可恣,其欲視為樂土,豈復登望鄉之臺乎?‘黃金何日贖蛾眉’,真浪語也!予病詠明妃者多敘其情,不求其節,節已隕矣,情于何有?為作明妃新曲。”[8](P82)李有朋認為,昭君出塞初嫁單于是因皇命難違,重嫁復株累根本就是出于情欲,更不存在思鄉了。有感于詠昭君之作多慨嘆其不幸及悲苦卻忽視了失節,李有朋作新曲,以“漢家遣色不遣節”為由,斥責昭君失節。《吊琵琶》中,蔡文姬祭奠昭君,其中有一句說道:“后人乃云:先嫁呼韓邪單于,復為株累單于婦。父子聚麀,豈不點污清白乎!”[8](P334)所謂“后人”之語,正是深受理學影響,一味強調女性貞節的道學家的一致看法。譴責昭君失節,在清人那里得到回響。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五中載某生在仙境中看到王昭君在女仙居住的景德樓里,于是質疑道:“景德樓中皆貞女、節婦所聚會,何以諸后妃又往?”祖師回答:“此諸后妃皆貞節之最純者也。人知貧賤之難葆貞節,而不知位至后妃,茍為事勢所迫,其艱難有十倍于平民者。”[19](P161-162)顯然,此處昭君能在景德樓居住,應不是她嫁與單于并有改嫁的事實,而應是她在和親之后“投江”等保持貞節的行為。否則,她只能成為失節之婦,斷然成不了仙的。
出于對失節行為的鄙視和對節操的崇拜,在敘述昭君和親時,文人們自然有兩種選擇:要么直接寫在匈奴“失節”后的生活,要么在失節之前死去。顯然,他們更傾向后一種選擇,哪怕這樣敘事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至少不違背他們心底的意愿,也更符合他們對女性的規訓策略。
男性規訓女性的策略之一,以“紅顏薄命”勸慰女性安于自己的性別,自己的身份及地位,以及遵循與之相應的要求。文學史上昭君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毛延壽的丑圖使其不能早得寵于漢帝,怨背井離鄉,怨異地的不同于中原的種種。然而宋代以后,昭君之怨減少了,男性聲音不斷重復“紅顏薄命”。歐陽修《再和明妃曲》:“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蘇軾《薄命佳人》:“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宋以后,男尊女卑思想被強化,男性以“他者”的聲音拙劣地表現女性的思想,想當然地認為這也是女性的真實想法。文徵明《明妃曲》云:“君王顧妾恩何厚,竟按臣工戮延壽。佳人自有命,畫工何能為。”“紅顏薄命古云然,不恨臣工況天子。”[8](P82)紅顏薄命之說為昭君的和親增添了濃郁的感傷特色,但也為昭君投江打下伏筆。
紅顏薄命,也可名垂千古,甚至成神成仙。事實上,昭君的功績不在她投江確保了民族節氣,而在她嫁給匈奴王并生子,避免兩國刀兵相見的史實。但在戲曲小說中,昭君最后成仙了,其原因也不是和親匈奴并生子,而是貞節。“戰亂年代,中國傳統文人在不堪重負的現實面前,常會生發出‘女性救國’的奇想。戰亂中以死御辱的女子為當時所稱道,如果能夠奮死御敵那就更值得世人崇仰了。”[20](P237)《二度梅全傳》第二十二回寫杏元到昭君廟,夜夢昭君,昭君說道:“想吾當日,毛延壽害我和番,到此殉節投河。蒙上帝憐憫我貞節,勒掌在此。又蒙國主建立廟宇,受此一方香火。吾只道后世的女子,水性楊花,貪生怕死,豈知還有烈性的佳人,愿其死而不愿其生,實為可敬!……吾神不若顯一威靈,將此女送至中原,以全他貞節之名,使后世女子,方肯效節烈,以顯我中原之光彩。”[21](P110)小說借昭君之口宣傳貞節。所以,昭君投江,是紅顏薄命,更是對貞節的維護。將貞節作為成仙的前提條件,對于薄命的紅顏來講,是一種極致誘惑。于是,自殺守貞便不是男權對女性的壓迫,而是女性自己主動選擇。昭君投江并不妨礙漢匈之間的關系,卻確保了漢帝丈夫的權威,成就了她自己的道德理想且能成神、成仙、名垂不朽。男性文人在昭君投江的敘事體現的貞節規訓策略,實在高明。
4 “去投江”化:女性平等意識的探索與追尋
1923年郭沫若創作的歷史劇《王昭君》與1979年曹禺創作的《王昭君》,依據兩漢書的實錄與空白,“還原”了昭君和親的歷史事實,完全擯棄了昭君投江情節及其所蘊含的悲怨色彩,摒棄了對于女性“三從四德”約束,將王昭君刻畫成和親英雄。在這兩部劇作中,王昭君剛烈、富于反抗精神。她鄙棄漢元帝,斥責他荒淫、丑陋。她深明大義,到匈奴后擯棄民族偏見,和匈奴人打成一片,完成兩國和睦的使命。
由此看來,“去投江”看似還原歷史真相,實則仍是時代意識形態的產物。王昭君是郭、曹二人的代言人。郭著《王昭君》是《三個叛逆的女人》之一,她的叛逆精神與五四運動中呼吁男女平等的聲音一致。誠如郭沫若自己所說:“我從她這種倔強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強地反抗元帝的一幕來。我想我的想象離事實怕是不很遠的罷。”[22](P74)這種想象的“叛逆”固然成功,但仍是作家的叛逆精神的代言,缺乏女性本位立場的生命關懷。曹著《王昭君》受周恩來總理托付而作,為宣傳民族和睦、民族平等而寫,政治意識形態明顯。郭、曹二著中的昭君看似在為女性爭取和男性同樣的價值,但是,由于“女性的付出必須得到男性的接納和確認才能最終實現其價值。整個和親事件始于父親的決定或囑托,成于丈夫的認可,和親的成功使女性回歸了社會的主流秩序。”[23](P62-63)在國家價值層面,“男性對女性的宰制,女性對男性的順從都有崇高的理由,那就是為了國家和百姓。以國族的名義打破的兩性權力結構又在國族的框架內得到了重建,男性的主體地位越來越穩固。”[23](P63)
相對于上個世紀的去“投江”敘事,新世紀的去“投江”更在于彰顯昭君作為女性本體的情感表述。張平的歌劇《昭君》中,昭君自請出塞主要不是緣于民族大義或愛國之情,而是緣于她與單于的愛情。到匈奴后,因為愛情、親情的作用,最終完成了和親重任。與以往的昭君和親敘事不同,新時期以昭君戲為代表的和親戲有三大特征:第一,不是通過女性奉獻自己來換取和平,主要靠情的力量解決各種矛盾。第二,女性不再是附屬于男性的工具,而是獨立的存在。她們有表達和決定的權利,能體現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具備相當強的主體性。第三,面對困難,兩性合力應對,很難區分他們誰發揮的作用更大,因為他們已融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23](P64)新世紀的《昭君》突出了女性主體地位,比以往的昭君戲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夸大了情的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將導致唯情論,對女性的權利、價值和主體性研究而言,仍有不足。從普通人的情感出發,全方位展示平凡女性的愛恨情仇,不是天使,不是魔鬼,不是高大全,也不是假丑惡,不是男性的對立面,而是凸顯女性真實面貌,這種“去投江”化的書寫才能成為真正的女性平等意識的表達。
[1]蘇珊·格巴.“空白之頁”與女性創造力問題[A].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孫崇濤,黃仕忠箋校.風月錦囊箋校[M].北京:中華書局,2000.
[3]斯蒂芬·歐文.追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克羅齊.歷史和編年史[A].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李東陽等敕撰.申時行等逢敕重修.大明會典:第七十九卷[Z].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
[6]董家遵.歷代節烈婦女的統計[A].鮑家麟.中國婦女史論集[C].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
[7]鄧尼絲·拉德納·卡莫迪.婦女與世界宗教[M].徐均堯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8]可永雪,余國欽編纂.歷代昭君文學作品集[C].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9]王昭君出塞和戎記[A].古本戲曲叢刊二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1954.
[10]徐石麒.浮西施[A].鄭振鐸編.清人雜劇二集[C].常樂鄭氏影印本.
[11]張巖冰.女權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12]李小江.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13]陳惠芬,馬元曦主編.當代中國女性文學文化批評文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4]勒內·吉拉爾.替罪羊[M].馮壽農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15]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王珊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16]可詠雪等編注.歷代吟詠昭君詩詞曲·全輯·評注[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9.
[17]薛旦.昭君夢[A].鄒式金.雜劇三集(影印本)[C].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18]牛僧儒.周秦行記[A].王弇洲編,孫葆真等校點.艷異編[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19]薛福成.庸庵筆記[M].丁鳳麟,張道貴校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20]張永廷.楊家將的歷史真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21]惜陰堂主人編輯,天花主人編次.二度梅全傳[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
[22]郭沫若作品經典:第2卷[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
[23]楊惠玲,趙曉紅.和親劇的性別文化解讀[J].廈門大學學報,2010,(4).
責任編輯段君峰
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12
I207.4=48
A
1004-0544(2015)10-0066-06
楊宗紅(196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