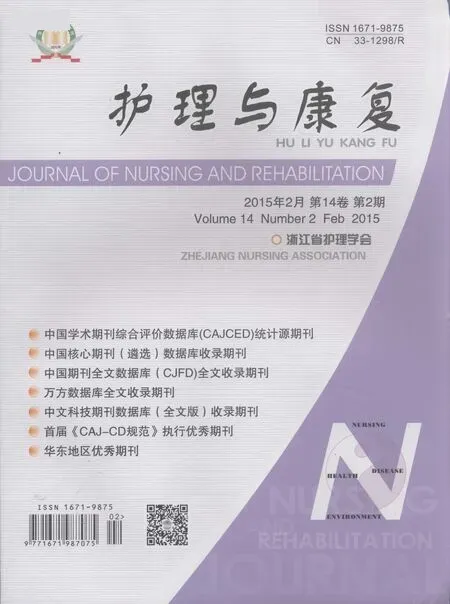埋藏式永久起搏器植入術后護理的研究進展
張端鳳,楊秀梅,尹安春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遼寧大連 116011)
隨著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工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已經成為治療心臟起搏障礙或傳導系統障礙的最有效方法[1]。截止2006年,心臟起搏器的植入量在我國已近10 臺/百萬人,并以每年15%的速度遞增[2]。埋藏式心臟起搏器的術后護理與患者術后恢復及生活質量密切相關,但仍存在較多爭議,且個體差異不盡相同。本文就埋藏式永久起搏器植入術后的護理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概 述
埋藏式永久起搏器植入術后的護理主要包括臥床時間與體位、沙袋壓迫、生活質量等方面。近年來,隨著起搏器電極導線工藝的不斷改進,臥床時間在適度范圍內逐漸縮短,提高了患者舒適度與生活質量,而且并未增加并發癥的發生率,壓迫時間與方式也在逐步改進。
2 術后護理
2.1 臥床時間與體位 術后常規護理為患者絕對臥床3~7d,固定術側肩肘關節[3],而長時間臥床不但會增加患者腰背痛的發生率,亦可導致便秘、尿潴留、壓瘡甚至深靜脈血栓形成等并發癥[4]。趙士榮等[5]對術后患者采取平臥位,床頭根據個人情況調整角度,48h后下床活動,無一例發生電極脫位,且術后應用鎮痛劑、緩瀉劑的比例及患者平均住院天數均低于常規護理者。有研究表明[6],縮短臥床時間對術后患者起搏器功能無影響,且有利于傷口愈合并減少并發癥的發生。而早在1987年,Belott[7]認為起搏器植入術后平均臥床5.7h安全、可行。此外,Haywood等[8]也證實了Belott的研究結果。國內學者孫中莉等[9]的研究結果為24h即可下床活動,且無并發癥,腹脹、便秘等發生率也較低。而芮治昊等[10]的研究將術后臥床時間縮短至12h,12h無不適者即可下床活動,術后并發癥并未增加,而患者舒適度增加。黃淑萍等[11]將術后患者平臥2h后抬高床頭30°,4h后無不適即可半臥位或坐位,4~6h可下床活動,結果發現早期活動不提高并發癥的發生率,且可以減輕長時間臥床的不適。Miracapillo等[12]研究發現,臥床3h與臥床24h在電極脫位、出血等并發癥發生率上無差異。此外,坐、立位比臥位更有利于電極固定于心尖部,可顯著減少電極脫位;在電極預留的長度足夠及囊袋內電極固定良好的前提下,適當地活動肩關節不至于引起電極脫位,而肘關節及前臂的活動與電極是否脫位無關[13]。綜上所述,患者術后臥床時間與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無確切相關性。隨著技術的進步,電極導線在工藝技術上出現了許多新的改進,翼狀電極因其尖端植入后可穩固地嵌入右心耳和肌小梁使電極脫位的發生率顯著降低[14]。因此,可根據患者的年齡、病情、耐受程度、電極類型等多方面因素在一定限度內減少臥床時間,從而減少臥床相關并發癥及住院天數,減輕患者經濟負擔并提高患者舒適度。
2.2 切口護理 永久起搏器植入術是器械植入性手術,感染風險較其他手術大,為防止術后切口發生感染,術前應嚴格備皮,術中嚴格無菌操作,術后按時換藥,必要時遵醫囑使用抗生素。而為預防術后囊袋出血,術后常規沙袋壓迫囊袋切口6~8h[1]。曾有學者[15]以1kg鹽袋壓迫切口并密切觀察,而張素巧等[16]認為鹽袋因包裝限制,四周上翹,不能與皮膚緊密接觸,受力面積小,壓迫止血效果不理想,易引起局部缺血,其采用間斷壓迫的方法與常規壓迫6h做比較,結果顯示常規壓迫引起皮膚壞死的概率遠遠高于間斷壓迫,而囊袋出血發生率兩者間并無差異。早年曾有研究表明[17],術后沙袋壓迫并不能有效防止囊袋出血,且壓迫不當影響血液循環可引起局部皮膚壞死。此外,在術中減少損傷、徹底止血、凝血功能正常的前提下,可減少甚至不使用沙袋壓迫[18-19]。但有學者認為術后沙袋壓迫6h至少可使在手術時因暴露空氣而收縮的微血管的再開放受到阻力,從而減少術后的滲血,仍建議使用[20]。選擇合適的沙袋進行無菌的間斷壓迫,以此來保證壓迫的有效性,同時避免皮膚壞死的發生。
2.3 觀察與監測 術后嚴密心電監測48~72h。Czunko等[21]提出需將術后起搏心電圖與術前心電圖中的P波、QRS波的形態和時限進行比較,從而判斷電極位置、起搏信號、起搏功能等是否正常,有無發生起搏脫落現象,起搏頻率是否在設置限定范圍,發現異常情況應及時與醫生溝通并進行必要的處理。同時監測生命體征,如體溫過高,需警惕是否出現切口感染;血壓過低或脈壓減小警惕心包填塞,血壓過高容易出現皮下血腫,應及時處理[22];嚴密監測脈搏,監測起搏器是否按起搏器設置參數正常工作。
2.4 生活護理
2.4.1 活動指導 指導患者臥床期間活動除術側肢體外的其他肢體,24h 后可進行術側上肢的前后輕微動作,3d后進行肩、肘關節的內旋、屈伸及輕微提肩動作,此后循序漸進[23]。Bavnbek等[24]認為對于起搏器植入術后患者活動指導應根據患者實際情況而非傳統習慣,并發現早期鼓勵患者進行全肩關節運動是安全的。術后1個月,可以恢復性生活,宜參加不太劇烈的運動,如洗澡、騎自行車、步行等。
2.4.2日常生活指導 出院時告知患者及家屬所安裝起搏器的類型、型號、使用年限及各種參數,出門應隨身攜帶起搏器登記卡;遵醫囑定期門診隨訪,最初半年每個月1 次,半年后3~6 個月1次,復查心電圖、胸部X 線攝片以了解起搏器的起搏功能、感知功能、帶動功能及起搏器電極位置并檢查電源情況及起搏器安裝處局部皮膚情況[25]。遠程隨訪在發達國家已廣泛應用于臨床[26],國內第1家遠程隨訪中心于1998年建于阜外心血管病醫院。起搏器具有家庭監護功能,可將收集到的信息經小型信息發送器,通過無線網傳輸至信息中心,分析處理再送達患者的主治醫生[27];指導患者學會自我監測,牢記醫生設定的起搏器頻率,每天至少兩次測量脈搏,如脈搏頻率比起搏器設定頻率少于5 次/min,或有頭暈、心悸、胸悶等不適時應及時就診[25]。注意遠離高電量、強磁場區域;避免使用電剃須刀、口腔電鉆等;勿大力揉搓起搏器處皮膚,勿穿緊身衣物,避免上肢用力過度;部分起搏器在患者進入睡眠狀態時,其基礎起搏頻率自動改變為睡眠頻率,以免引起患者不適[28]。起搏器睡眠頻率為仿真患者晝夜節律而增加的生理性起搏參數[29],如需出國或更改作息時間,應重新調試參數。遵醫囑定期復查程控[23]。疾病的長時間折磨、不可預估的治療效果、起搏器昂貴的價格等諸多因素都會導致安置起搏器的患者術后焦慮、抑郁發生率提高,甚至會產生軀體行為障礙[1]。術后長期隨訪及起搏器的程序控制可有效增加患者的安全心理[30]。醫護人員應耐心解釋手術相關事宜,引導患者說出自己的擔憂,有針對性地解答。
3 結 語
埋藏式永久起搏器植入術后護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圍手術期的護理在治療中具有重要作用,良好、完善、具體的護理可以有效減少并發癥,促進患者恢復。但目前就臥床時間、臥床體位及沙袋壓迫方式等方面仍有一定爭議,并且每例患者都存在個體差異性,因此起搏器圍手術期護理要在遵循原則的基礎上進行適度變通,最大限度減少并發癥的發生,提高患者的舒適度,促進心理健康,且術后隨訪對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影響亦不可忽視。
[1]楊玉文.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術42例圍術期護理[J].齊魯護理雜志,2012,18(1):26-27.
[2]劉平,張運,王蘇加.生物心臟起搏器[J].中華內科雜志,2006,45(2):152.
[3]林菊英,金喬.中華護理全書[M].南昌:江西科學出版社,1993:300.
[4]單玉香,郜玉珍.心臟起搏器術后早期活動的意義[J].護理研究,2006,20(12):3293-3294.
[5]趙士榮,何麗萍,孫蕾.不同體位對起搏器植入術后患者恢復的影響[J].中國醫藥導報,2011,8(2):168.
[6]何細飛,陶敏,周舸.不同臥床時間對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后患者功能恢復的影響[J].護理學雜志,2006,21(15):7-8.
[7]Belott PH.Outpatient pacemakers procedures[J].Int J Cardiol,1987,17:169-176.
[8]Haywood GA,Jones SM,Camm AJ,et al.Day case permanent pacing[J].PACE,1991,14:773-777.
[9]孫中莉,王廣.臥床時間與安置起搏器術后康復相關性的研究及護理[J].齊魯護理雜志,2005,10(12):911-913.
[10]芮治昊,吳燕平,戴文俊.起搏器植入術后不同臥床時間對老年病人的影響[J].護理研究(中旬版),2011,25(5):1288.
[11]黃淑萍,楊丹莉,梁遠紅.早期活動干預對起搏器植入患者術后不適癥狀的影響[J].護理學報,2011,18(8B):59-60.
[12]Miracapillo G,Costoli A,Addonisio L,et al.Early mobilization after pacemaker implantation[J].J Cardiovasc Med,2006,7(3):197-202.
[13]曾桂英,林豐.早期活動對起搏電極脫位的影響觀察[J].護士進修雜志,2007,22(19):1822-1823.
[14]Rosenqvist M.Cardiac pacing:new advances[M].Philadelphia:W.B.Saunders,1997:287-292.
[15]彭海燕.埋藏式三腔起搏除顫器術后護理體會[J].現代醫藥衛生,2011,27(2):238.
[16]張素巧,李彩英,劉玉茹.安裝起搏器術后沙袋壓迫方式改進的研究[J].護士進修雜志,2011,26(10):928-929.
[17]侯子山,邵明風,徐同龍.沙袋壓迫對防止起搏器術后囊袋出血的實際效果觀察[J].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1999,13(1):7.
[18]劉陸英,侯子山.起搏器安裝術后患者局部沙袋加壓的療效觀察[J].南方護理學報,2000,7(4):2-3.
[19]馬月華,伍海芬,何立新.對永久心臟起搏器安置術后患者早期康復護理的探討[J].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2006,27(1):83.
[20]江力勤,錢鋼,劉加芳,等.起搏器囊袋血腫的防治[J].心腦血管病防治,2006,6(5):329-330.
[21]Czunko A,Lelakowski J,Szczepkowski J.Usefulness of electrocardiographic and echocardiographic parameters for predicting the eficacy of atrioventricular synchronisation during a single lead VDD/R pacing[J].Kardiol Pol,2009,67(8A):1019-1028.
[22]徐靜.心臟再同步化治療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護理[J].護士進修雜志,2009,24(7):622-624.
[23]劉玉茹,張素巧,李彩英,等.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的護理流程和健康教育[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20(34):4424.
[24]Bavnbek K,Ahsan SY.Wound management and restrictive arm movement following cardiac device implantation-evidence for practice?[J].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Nursing,2010,9(2):85-91.
[25]劉夢姣,曾慧.永久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后患者的護理進展[J].中華現代護理雜志,2013,19(4):399-402.
[26]Sutton R.Guidelines for pacemaker follow up.Report of a British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Group(BPEG)[J].HEART,1996,76(5):458-460.
[27]朱靜靜.帶有家庭監護功能心臟起搏器植入的術后護理[J].中華現代護理,2010,16(2):179-180.
[28]趙娓,孫曉斐,丁文祥.人工生理性心臟起搏器的現代治療功能[J].生物醫學工程與臨床,2006,10(3):191-194.
[29]Simometta DD,Paolo V,Enrico MG.Sensors for rate responsive pacing[J].Indian Pacing Electrophysiol,2004,4:137.
[30]白彥越,張旭,劉丹,等.術后隨訪在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患者中的應用[J].解放軍護理雜志,2013,30(14):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