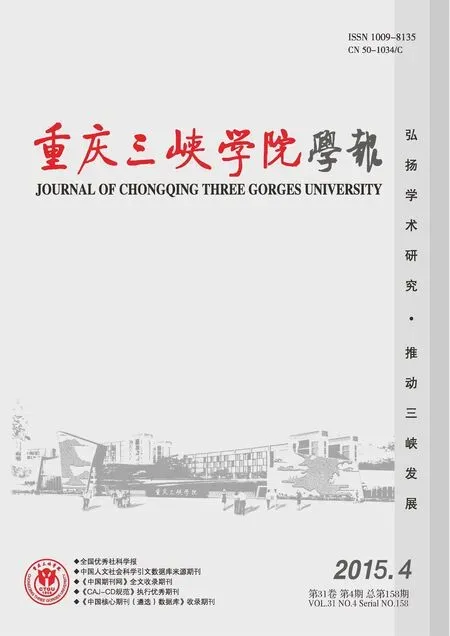魯迅小說的言語主體與抒情的話語及語用修辭
許祖華
?
魯迅小說的言語主體與抒情的話語及語用修辭
許祖華
(華中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湖北文學(xué)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湖北武漢 430079)
魯迅小說的言語主體主要有三類,一類是文外敘述者,一類是文內(nèi)敘述者,一類是小說中的人物。這些言語主體的抒情的話語,雖然由于言語主體的身份不同,在小說中所擔(dān)任的角色也不同,因此,這些抒情話語,不僅意味各不相同,而且,采用的修辭手段也各異,但無論是哪一類言語主體的抒情話語,從小說來看,都符合作為言語主體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也都具有話語修辭與語用修辭的匠心,并包含了眾多可資分析的內(nèi)容。當(dāng)然,在魯迅的小說中,言語主體的設(shè)置,有時又是較為靈活和較為復(fù)雜的,而言語主體設(shè)置的這種狀況,從一定意義上講,是魯迅小說的藝術(shù)匠心的一個方面。
魯迅小說;言語主體;抒情話語;修辭
李長之在論魯迅的創(chuàng)作時曾經(jīng)指出:“魯迅的筆根本是長于抒情的,雖然他不專在這方面運用它”[1]90。如果說,抒情就是指文字浸泡在情緒里的話,那么,李長之的這一判斷是很有道理的。僅就魯迅創(chuàng)作的小說來看,不僅各篇小說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的情感表露力透紙背,各類浸泡在情緒里的文字、話語比比皆是,而且,有的小說甚至全篇都是“純粹的抒情文字”[1]83,如《傷逝》,所以,李長之認(rèn)為:“廣泛的講,魯迅的作品可說都是抒情的。別人盡管以為他的東西潑辣,刻毒,但我以為這正是濃重的人道主義的別一面,和熱淚的一涌而出,只不過隔一層紙。”[1]76李長之的觀點,實際上揭示了魯迅作品兩個方面的特色,一個方面是人們較為公認(rèn)的“潑辣”、“刻毒”的特點,一個方面是他自己堅定認(rèn)可的“抒情”的特點,而對魯迅作品抒情特點的認(rèn)可,也正是李長之在魯迅研究方面的創(chuàng)意,因為,在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成果問世的20世紀(jì)30年代之前,還沒有人如此明快地認(rèn)為“魯迅的作品可說都是抒情的”。到了20世紀(jì)40年代,另一位研究魯迅小說的學(xué)者也如是說:“魯迅的小說,一般地說來是散記體的形態(tài),它的結(jié)構(gòu)是直述的散記,它的風(fēng)格是敘述的詩,含有情感的色彩,躍動著生命的呼吸”[2]465,更干脆地將魯迅小說的風(fēng)格與“敘述的詩”畫了等號。
一般說來,小說中的抒情有各自形式,既有直接抒情,也有間接抒情,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抒情,在小說中都主要是由三類言語主體的話語來體現(xiàn)和完成的,一類是文外敘述者的話語,即作者的話語;一類是小說中人物的話語;一類是文內(nèi)敘述者的話語,如,小說中的特殊人物“我”或其他事件的見證者、其他人物故事的講述者等的話語。魯迅小說的抒情也主要由這三類言語主體的話語所體現(xiàn)和完成。這三類言語主體,由于其身份或所擔(dān)任的角色不同,對小說藝術(shù)世界構(gòu)成的作用也不同,因此,其抒情話語的修辭,甚至構(gòu)成抒情話語的語用修辭也涇渭分明,它們不僅以其深邃、雋永、生動的審美性存在,直接體現(xiàn)了“魯迅的筆根本是長于抒情”的特點,而且也充分地彰顯了自身話語及語用修辭的特點與魅力。
一、文外與文內(nèi)敘述者的抒情話語及語用修辭
這里列舉的是魯迅小說中的幾段文外與文內(nèi)敘述者的抒情話語:
看哪,他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阿Q正傳》)
舜爺?shù)陌傩眨共⒉欢紨D在露出水面的上頂上,有的捆在樹頂,有的坐著木排,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從岸上看起來,很富于詩意。(《理水》)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于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一件小事》)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松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社戲》)
五段抒情話語,分別由兩類言語主體承擔(dān),第一例和第二例的言語主體是文外敘述者;第三例至第五例的言語主體是文內(nèi)敘述者。這兩類言語主體的話語雖然都具有抒情性,但意味與修辭卻有不同的情趣,而這些不同的情趣就導(dǎo)源于言語主體的身份及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魯迅就是按照這些言語主體的身份及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意識地采用的不同的修辭手法,從而賦予這些言說主體的抒情話語以不同意味的。
就文外敘述者的話語來看,這些話語雖然也具有抒情性,但這種抒情性卻明顯地具有一種“矯情”的意味,即,在不該抒情的地方,偏偏寫下了一段抒情話語,而這些抒情話語,不僅不怎么符合情理,而且也與這些抒情話語生成的語境十分地不協(xié)調(diào)。如第一例的抒情話語就是如此。這段抒情話語是直接針對阿Q欺負(fù)小尼姑“勝利”后的行為與心態(tài)展開的,而阿Q的這種向更弱者施暴的行為及所表現(xiàn)出的“得意”的神態(tài),無論是從情理上還是從魯迅的思想與情感傾向上來講,都是應(yīng)該批判與否定的,而且,在事實上魯迅已經(jīng)在這段抒情性話語出現(xiàn)之前的一段議論性話語中給予了諷刺與否定,認(rèn)為阿Q的這種“得意”是中國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種國民病態(tài)心理的反映,而不應(yīng)該、也不值得來一段抒情的,可是作為文外的敘述者的魯迅卻偏偏來了一句抒情;同樣,第二例的抒情話語的出現(xiàn),也是如此。面對滔滔洪水及掙扎在洪水中艱難地生活著的大眾所構(gòu)成的民不聊生的所謂“風(fēng)景”,即使不表達(dá)一下同情、哀嘆,至少不應(yīng)該用“很富于詩意”來抒情,可文外敘事者卻也偏偏來了這么一句抒情。所以說,這些文外敘述者的抒情話語充滿了“矯情”的意味。但也正是這種“矯揉造作”的抒情,在徹底而有效地消解了這兩段抒情話語的所有贊賞性意味的同時,也消解了這兩段抒情話語中詞語所指的贊賞性意義,而讓濃厚、尖銳的諷刺性意味力透紙背地發(fā)散出來,并且,這種諷刺性意味的發(fā)散還表現(xiàn)出這樣一種傾向,即,越是用贊賞性詞語修飾的抒情話語,其諷刺意味越濃厚、越尖刻,如“很富于詩意”這段抒情話語就是如此。這是因為,這兩篇小說中的文外敘述者,即作者,扮演的本來就是一個批判者的角色,一個力圖要“改造國民性”的角色,這兩段話語的抒情性并不是在文外敘述者“真誠”贊賞的基礎(chǔ)上誕生的,而是基于“真誠”的批判與否定的意識,即“改造國民性”的意識生成的,所以,這兩段抒情性的話語采用的修辭手段,雖然表面上似乎是“直抒胸臆”的修辭手段,而在實際上所采用的則是反諷的修辭手段,而且這種反諷還具有明確的針對性:第一例的反諷針對阿Q,第二例的反諷針對即將出場的那些聚集在“文化山”上看“風(fēng)景”的文人,這種反諷的修辭手段正是文外敘述者作為一個批判者鮮明的角色意識的體現(xiàn)。
就文內(nèi)敘述者的抒情話語來看,《故鄉(xiāng)》與《一件小事》中的抒情話語,充滿了質(zhì)疑和反省的意味,所采用的修辭手法一為“提問”的修辭手法,一為對比的修辭手法。而這些充滿了質(zhì)疑與反省意味的抒情話語及所采用的修辭手法也符合成年的“我”,這種接受過現(xiàn)代教育的知識分子身份及“我”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故鄉(xiāng)》中的“我”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見證者”的角色,即見證了故鄉(xiāng)的變化和人的變化的角色。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從小說的整體來看,對現(xiàn)象的思考是“我”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特點(小說后面“我”對閏土叫“我”“老爺”現(xiàn)象的議論正說明了這一點),更何況“我此次回鄉(xiāng),本沒有什么好心緒”,所以,面對“蒼黃的天底下,遠(yuǎn)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的故鄉(xiāng),“我”質(zhì)疑“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自在情理之中。作為一個“見證者”,在“我”的記憶中,“我所記得的故鄉(xiāng)全不如此。我的故鄉(xiāng)好得多了。”但眼見的現(xiàn)在的故鄉(xiāng)卻一派死氣沉沉,所以,這段抒情性的話語采用“提問”的修辭手法也與“我”作為一個“見證者”的角色相吻合。《一件小事》中的“我”雖然也是一位現(xiàn)代知識分子,“我”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也是一個“見證者”的角色,但“我”扮演的更為重要的角色則是“對比”的角色,即“我”與車夫的對比的角色,所以,這段抒情性話語也就主要采用了對比的修辭手法,用車夫的“大”來對比“我”的“小”。從語用修辭的角度看,這里所使用的打引號的“小”,固然可以從多個角度進(jìn)行解讀,但最為切近的解讀,則是“對比”修辭的角度,因為,無論將這個打引號的“小”的所指解讀為是什么,如“我”的“小心眼”、“我”的“小九九”等,但在客觀效果上都具有“對比”的效果,都指向“我”的人品、精神的“小”與車夫的人品、精神的“大”的對比。《社戲》中的抒情話語,充滿了快樂的意味,采用的修辭手法則是“直陳”胸臆的手法。這也是符合“我”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的。就“我”的身份來看,“我”不過是一個“十一二歲”少不更事的少年,就“我”的角色來看,就是一個喜歡看戲的角色。作為一個少年,“我”既沒有什么城府,也不善于壓抑自己想看戲的情感傾向,“我”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并表現(xiàn)在行動上,作為一個“喜歡看戲”的角色,“我”“現(xiàn)在”的所有追求都集中在一個事情上,就是想看戲,而由于不能去看戲,“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吃。”以至于“母親很為難”。所以,這段抒發(fā)“我”在得知“我”看戲的愿望可以實現(xiàn)時的情感的話語,也就主要采用了直陳的修辭手法。從語用修辭上看,這里使用了一個“大”來形容“我”的心情,也正與“我”作為一個少年對于詞語的直觀理解相吻合,也與“我”扮演的一個喜歡看戲的少年的角色相吻合,因為,“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卻在到趙莊去看戲。”也就是說,“看戲”不僅是“我”這個時候的最“大”愿望,而且也是“我”來這里做客“所第一盼望”的,當(dāng)“我”的這個最“大”和“第一盼望”的愿望就要實現(xiàn)的時候,用“我”的“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來形容,不僅形象、生動、新穎、有趣,而且也符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蘇雪林當(dāng)年在評魯迅小說的用語時曾經(jīng)指出“魯迅文字新穎獨創(chuàng)的優(yōu)點,正在這‘于詞必己出,’‘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上。”[3]141這自是中肯之言,而魯迅文字新穎獨創(chuàng)之所以能成功,并非是憑借天馬行空似的靈感偶然獲得的成功,而是在堅實的基礎(chǔ)之上培育的結(jié)果,這種堅實的基礎(chǔ)就是小說人物外在與內(nèi)在的規(guī)定性和語境的合理性,正是由于有如此堅實基礎(chǔ)的保障,才使魯迅小說中使用的任何“必己出”的詞語和“重加鑄造一樣言語”,都能經(jīng)受得起哪怕是最嚴(yán)格的檢驗,也就當(dāng)然獲得了良好的藝術(shù)效果。
二、人物的抒情話語及語用修辭
在展開論述之前,請先看例子:
“我真傻,真的。”(《祝福》)
“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么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么?”(《離婚》)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quán)利!”(《傷逝》)
這些抒情話語,雖然由于言語主體的身份不同,在小說中所擔(dān)任的角色也不同,因此,不僅意味各不相同,而且采用的修辭手段也各異,但都符合作為言語主體的人物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也都包含了眾多可資分析的內(nèi)容。
祥林嫂的這段抒情話語充滿了悲劇的意味,所采用的修辭手法則是將抒情滲透于敘事里的手法。這種悲劇的意味及所采用的修辭手法,也是符合祥林嫂的身份及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從身份來看,祥林嫂應(yīng)該是一個質(zhì)樸而沒有受過什么教育的下層勞動者,因為,從小說的敘述來看,沒有任何地方交代過她曾上過學(xué),也沒有任何描寫話語或其它話語暗示過她懂“子曰詩云”,再加上她本來就少言寡語,即使開口也是“別人問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所以,她的抒情話語完全采用的是下層人的口語,語用修辭上也基本以口語詞匯為主,句式基本都是陳述句,且“句子短、語調(diào)急促、節(jié)奏強烈”[4]251;從她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她是小說的主角,而且是一個苦難集于一身的主角,是一個“只有痛苦是家產(chǎn),別的么,是一無所有的”[1]83不幸遭遇的集合體,而她最大的痛苦和最痛苦的遭遇就是失去了最重要也是最后依靠的兒子這件最悲慘的事件,讓她最無法忘卻而刻骨銘心的事件也是這一事件,她最想向人講述的事件,也是這一事件,她的人生和情感所遭受的最重的打擊與傷害,也是這一事件,讓她最為悔恨的事件,還是這一事件,所以,小說采用將抒情滲透于她的敘事之中的修辭手法,自然也是符合她的身份以及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因為,不僅祥林嫂所敘述的這個事件,包含了祥林嫂最直接、最深厚、最悲痛的情感內(nèi)容,是最能體現(xiàn)她作為一個苦難集于一身的角色的事件,而且,祥林嫂飽含血淚地講述這個事件,也完全符合她作為一個目不識丁的下層勞動者不善于“直抒胸臆”而只會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自己親歷的故事來表情達(dá)意的身份與特點。
與祥林嫂相比,愛姑雖然也是一個普通農(nóng)家的女子,但其抒情性話語的意味卻充滿了“火藥”味,所采用的修辭手法既有借代,也有移就,而話語這種意味及所采用的這些修辭手法也同樣符合她的身份及所扮演的角色。沒有疑問,愛姑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像祥林嫂那么單純,她是一個較為復(fù)雜的角色,從她的言語行為來看,她最初出現(xiàn)在小說中時,她是一個具有抗?fàn)幮裕沂菬o所顧忌的抗?fàn)幮缘慕巧M管她的抗?fàn)幩罁?jù)的只是傳統(tǒng)婚姻賦予她的名分:“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抗?fàn)幍挠職鈦碜杂趥鹘y(tǒng)文化賦予她的虛幻的“合法性”,但畢竟表現(xiàn)出了維護(hù)自己“名分”的抗?fàn)幮浴6@里引用的她激憤地抒發(fā)情感的一段話語,正反映了她作為一個抗?fàn)幗巧奶攸c,而所采用的修辭手法,又正切合了她作為一個農(nóng)家女子和復(fù)雜的抗?fàn)幗巧奶攸c。從身份來看,她雖然是一個農(nóng)家女子,恪守著封建禮教的種種規(guī)范,自從嫁到婆家“真是低頭進(jìn),低頭出,一禮不缺”,可丈夫和公公卻“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鐘馗’”一樣虐待她,從而使她對自己的丈夫與公公又恨之入骨,而小說采用借代的修辭手法,讓她用“小畜生”來借指她的丈夫,用“老畜生”來借指她的公公,則正切合了她要表達(dá)強烈憎恨的情感需要和她作為一個“沒有現(xiàn)代性知識話語”[5]611的農(nóng)家女子的經(jīng)驗知識素養(yǎng)與身份;從她在整個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一方面,她固然是一個具有抗?fàn)幮缘慕巧硪环矫妫目範(fàn)幱种饕轻槍ψ约旱恼煞蚺c公公的,卻不敢挑戰(zhàn)鄉(xiāng)村的大人物“七大人”的權(quán)威,再加上這個時候,即她與父親一起到慰老爺家“會親”的時候,她又不知道“七大人”在“會親”的過程中對她的事會如何判決而又要表現(xiàn)出自己的“抗?fàn)帯笔恰袄碇睔鈮选钡模裕谏婕暗健捌叽笕恕钡臅r候,尤其是涉及到對“七大人”評價這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時,小說沒有采用如愛姑對自己的丈夫和公公的評價一樣的借代的修辭手法或者其它的修辭手法,而是采用了“移就”的修辭手法,將愛姑前面所指稱的“七大人”中的“人”“移就”到了后面“就不說人話了么”之中,從而滿足了她這個復(fù)雜的抗?fàn)幗巧磉_(dá)“復(fù)雜”情感的需要,因為,“移就”的修辭手法中使用的“人”,不具有挑戰(zhàn)性,更不具有顯在的謾罵性,只具有“寓情于物物不變”[6]251的特征,但又顯示了愛姑的“理直氣壯”和愛姑對“七大人”的復(fù)雜心態(tài)。同時,人物抒情話語的這種十分講究的修辭,不僅合乎情理,也十分精巧地為后面愛姑面對“七大人”的權(quán)威的最終妥協(xié)的結(jié)局埋下了伏筆,正是這種修辭手法的藝術(shù)匠心。
與祥林嫂和愛姑相比,《傷逝》中的主要人物子君的抒情話語則是另外一種意味,這就是“自信”而決絕的意味。這種意味所透射出的是對“個性解放”決絕追求的勇氣,有學(xué)者甚至認(rèn)為,子君這段抒情性話語本來就是從“個性解放”的思想意識中生發(fā)出來的,也是她追求個性解放的行動“宣言”。使用的修辭手法是直抒胸臆的“感嘆”手法。這段抒情話語的意味及所采用的修辭手法,不僅同樣符合子君這個人物的身份及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審美意味更為豐富。子君作為一個經(jīng)常與“我”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xí)慣,談男女平等的女性,很顯然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且是一個深受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因為,“我”與子君談的這些話題,都是新思潮的話題,所以,在爭取自己幸福的過程中子君用如此自信、決絕而充滿個性解放意味的話語來抒發(fā)情感,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及其知識背景。從子君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她無疑是一個悲劇性角色,不僅是一個承擔(dān)著生活悲劇的角色,更是一個承擔(dān)著精神悲劇的角色,而使她成為這樣一個“雙重”悲劇角色的思想依據(jù),不是別的,正是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都沒有干涉我的權(quán)利”這段抒情性話語所表達(dá)的“個性解放”的思想。因為,這段抒情話語固然昭示了子君決絕、自信的精神風(fēng)采,但這種似乎具有昂揚特征的精神風(fēng)采卻無法掩蓋子君思想的幼稚性。其幼稚性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她自己與“他們”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太天真,她只知道或者說只認(rèn)識到了她是她自己的,將自己從“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中孤立了出來,也只在主觀上認(rèn)為“他們”沒有權(quán)利干涉她,但卻沒有認(rèn)識到即使她的親朋好友不干涉她,可是,人(包括子君她自己)作為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雖然人(包括子君)不一定能干涉社會,但是,社會卻是一定會干涉人的,對于像子君這樣的人來說,社會不僅要干涉她,而且對于她的“個性解放”還要予以扼殺,這是因為“舊社會舊勢力并不是這樣好心腸和大氣度的,能容許這對愛人安享他們的幸福。這里還有第二道關(guān)口——比第一道關(guān)口更困難的、家庭以外的社會舊勢力的關(guān)口。不用說,當(dāng)時的封建舊家庭和社會舊勢力是一個整體;但社會舊勢力究竟比封建舊家庭更復(fù)雜,更不容易沖破。”正是因為子君和涓生沒有認(rèn)識到社會的如此強力,也當(dāng)然沒有任何的思想與行為的準(zhǔn)備,所以,“就在這第二道關(guān)口面前,子君卻悲慘地失敗了,屈服了。”[7]108二是她和涓生一樣,對“個性解放”的理解太膚淺,僅僅只將“個性解放”的要義狹隘地理解為“愛”,而子君這段自信十足地表現(xiàn)了她的勇敢與無畏的抒情話語,就正是建立在這種“愛”之上的言說,也就是涓生后來的反省所指出的:“她當(dāng)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而涓生所指出的:“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正揭示了她與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膚淺性。正因為“她當(dāng)時所追求的只是愛,超出愛以外的東西,例如打破舊習(xí)慣,實現(xiàn)男女平等,徹底解放婦女,以至于完全推翻封建制度等等,她并不十分理解”,這也就決定了“子君的悲劇并不因為她信奉了個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并不因為她信奉了民主主義,恰恰相反,是因為她缺乏充分的、堅定的個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缺乏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8]327由此看來,子君這段抒情話語的“感嘆”不僅符合子君的身份及在小說中所扮演的“雙重”悲劇角色,而且,將這段抒情話語及所采用的修辭手法從審美效果上分析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這段抒情話語的抒情性越強烈、越凸顯了子君的身份,子君所扮演的悲劇角色的意義也越鮮明;話語所具有的個性解放的意味越濃厚,則越顯示了個性解放的弊端及在當(dāng)時中國社會的虛幻性。對虛幻性的揭示,正是魯迅深刻的思想之一,也是支撐魯迅《傷逝》這篇小說的堅實思想基礎(chǔ)之一,也是這段抒情性話語的意義和價值。
陳鳴樹先生曾經(jīng)指出:在魯迅小說中,作者賦予抒情語言的主要有兩類人物,“一類是農(nóng)民或農(nóng)村勞動婦女,另一類是當(dāng)時進(jìn)步或比較進(jìn)步的知識分子。顯然,對這兩類人物所賦予的抒情語言,不但要表現(xiàn)他們不同的階級地位的特點,而且要表現(xiàn)他們在階級性制約下的個性化的特點,這還不夠,還必須表現(xiàn)他們這種階級性與個性辯證統(tǒng)一的思想情感如何在特定的情勢支配下的抒情方式。正是他們這種抒情方式,決定了他們的抒情語言的特色。”[4]250這種觀點雖然是從一般現(xiàn)實主義塑造人物的規(guī)范中總結(jié)出來的,并帶有十分鮮明的階級論的色彩,也沒有從言說主體的角度來分析人物抒情話語與人物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關(guān)系,但所揭示的人物的“抒情方式”與人物“抒情語言”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以及人物的抒情話語與人物自身的質(zhì)的規(guī)定性——一定階級與一定傾向的代表和人物自身個性之間的藝術(shù)關(guān)系,還是十分中肯與精當(dāng)?shù)模@也正是魯迅小說中人物抒情話語合理、生動并經(jīng)受得起生活邏輯與藝術(shù)邏輯檢驗的內(nèi)在原因。
三、魯迅小說言語主體設(shè)置的復(fù)雜性一瞥
上面雖然分析了魯迅小說三類言語主體及其抒情話語的修辭特點及語用修辭的特點,但,我們也要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魯迅小說中的言語主體的設(shè)置是十分靈活,也十分復(fù)雜的。有時,小說中的言語主體的設(shè)置十分規(guī)范,如,在《孔乙己》這篇小說中,文外敘述者、文內(nèi)敘述者(即咸亨酒店中的小伙計“我”)和人物孔乙己,三類言語主體設(shè)置齊備,有時又常會發(fā)生一些變化,尤其是文外敘述者與文內(nèi)敘述者這兩個言語主體,不僅設(shè)置靈活,常常忽隱忽現(xiàn),而且還常常角色混淆,無法界定,如《明天》這篇小說,言說的主體是文外敘述者與人物,文內(nèi)敘述者本來是隱身的,但在情節(jié)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這個本來隱身的文內(nèi)敘述者卻突然現(xiàn)身來了一句“我早經(jīng)說過:他是粗笨女人”;還有《阿Q正傳》中的第一章的言說主體是文內(nèi)敘述者“我”,而之后各章中這個文內(nèi)敘述者“我”又隱蔽起來了,將敘述與描寫的任務(wù)轉(zhuǎn)交給了文外敘事者。還有《出關(guān)》這篇小說,全篇本只有文外敘述者與人物這兩個言說主體,可在情節(jié)發(fā)展的中間,卻突然出現(xiàn)了這樣兩句話:“無奈這時魯般和墨翟還都沒有出世”和“那時眼鏡還沒有發(fā)明”,這兩句話究竟是屬于文外敘述者的話語呢,還是屬于文內(nèi)敘述者的話語呢?實在不好界定。
如何理解或解說魯迅小說中的言語主體如此設(shè)置的現(xiàn)象呢?在我看來,魯迅小說中的這些言語主體設(shè)置的變化甚至復(fù)雜狀況,也是魯迅小說藝術(shù)匠心的一個方面。有學(xué)者在研究《明天》這篇小說中文內(nèi)敘述者突然現(xiàn)身的現(xiàn)象時就曾指出,這是魯迅采用的一種強行介入小說敘事的修辭方法,其目的是為了提醒讀者注意人物的身份;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無論文外敘事者和文內(nèi)敘述者是現(xiàn)身還是隱蔽,甚至是混淆,這都是魯迅反傳統(tǒng)小說的范式和突破“文學(xué)概論”一類小說理論框框的創(chuàng)新性實踐,而且是很新穎、獨特的創(chuàng)新性實踐等等。這些觀點雖然只是見仁見智的論述,但也的確觸及到了魯迅在小說中如此做法的藝術(shù)匠心。但也正是由于魯迅在自己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采用了這樣一些獨運的匠心,從而也帶來了小說抒情話語依附的一個明顯現(xiàn)象,這就是,在魯迅小說中,抒情話語的言語主體,主要不是文外敘述者,也不是小說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而是小說中的“我”這個既是小說中一個獨立的人物形象,又常常是小說中典型的文內(nèi)敘述者,魯迅小說中的抒情話語,也常常由這個特殊的角色承擔(dān),而這個特殊角色的抒情性話語,不僅意味深長,而且話語修辭與語用修辭的手段也豐富多彩美不勝收。所以,分析魯迅小說抒情的話語修辭及語用修辭,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分析“我”的抒情話語。更何況,在魯迅的小說中,這些“我”的抒情話語所負(fù)載的情感內(nèi)容,雖然不等于就是魯迅自己的情感內(nèi)容,兩者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但兩者之間有密切的聯(lián)系,則應(yīng)該是不爭的事實,有學(xué)者就曾指出:“魯迅主要是個主觀作家,他寫的東西大抵都跟自己有很深感受的事情有關(guān),感情色彩很重的《傷逝》自然不能例外”[9]664。這雖然是一家之言,其判斷也可以商榷,但這種一家之言中所下的兩個判斷,即,魯迅的小說創(chuàng)作與魯迅自己“有很深感受的事情”的關(guān)系以及魯迅小說的“感情色彩”與魯迅這個“主觀作家”的密切聯(lián)系,還是較為中肯和經(jīng)受得起推敲的。如果基于這種密切的聯(lián)系對這些“我”的抒情話語展開分析,在我看來,不僅能更好地尋索魯迅采用各種修辭手段書寫這種抒情話語的藝術(shù)匠心,也不僅能從這樣一個特殊的角度來研究魯迅小說的審美性,而且,也能更清晰地透視魯迅豐富的情感世界。
[1]李長之.魯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呂熒.魯迅的藝術(shù)方法[C]//李宗英,張夢陽.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集: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2.
[3]蘇雪林.《阿Q正傳》及魯迅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C]//李宗英,張夢陽.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集: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2.
[4]陳鳴樹.魯迅小說論稿[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5]羅宗宇.“她”言說的虛妄——關(guān)于《離婚》中愛姑突變的一種解讀[C].譚桂林,朱曉進(jìn),楊洪承.文化經(jīng)典和精神象征——“魯迅與20世紀(jì)中國”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
[6]袁暉.論修辭中的“移就”辭[C].修辭學(xué)研究:第1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3.
[7]王西彥.第一塊基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陳安湖.魯迅研究三十年集[C].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8.
[9]張釗貽.《傷逝》是悼念弟兄喪失之作?——周作人強解的真意揣測[C]//譚桂林,朱曉進(jìn),楊洪承.文化經(jīng)典和精神象征——“魯迅與20世紀(jì)中國”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
(責(zé)任編輯:鄭宗榮)
Speech Subjects, Lyric Words and Pragmatic Rhetoric in Lu Xun's Novels
XU Zu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bei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Research Centre, Wuhan, Hubei 430079)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peech subjects in Lu Xun's novel: the outer narrator, the narrators and the characters. The lyric words vary with different speech subjects and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Likewise, the implications vary with the lyric words and rhetoric in the novel. In spite of these differences, the lyric words of any type of speech subjec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status and roles of the speech subjects and thus sophisticated in speech and pragmatic rhetoric and are rich in contents to be analyzed. Yet in Lu Xun's novel, there is sometimes some flexi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setting the speech subjects, which is a partial reflection of the artistry of Lu Xun’s novel.
Lu Xun's novel; speech subject; lyric discourse; rhetoric
I210.6
A
1009-8135(2015)04-0047-06
2015-04-07
許祖華(1955-),男,湖北仙桃人,華中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湖北文學(xué)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教育部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項目“魯迅小說修辭的三維透視與現(xiàn)代闡釋”(項目批準(zhǔn)號:13YJA75105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