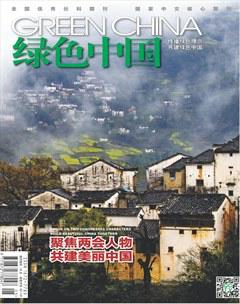陶人徐瑞鴻 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

“我終于在這里找到家了!”去年11月,徐瑞鴻在三陶軒古名窯的開爐點火儀式上,大聲吶喊道。半年前,徐瑞鴻將自己創辦的東海堂三陶軒陶瓷藝術公司由江西景德鎮遷址至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區全旺鎮樓馬蹊村陶谷。
站在初春鄉野的一派草長鶯飛中,徐瑞鴻緩步在全旺鎮樓山后村的濕潤綠意間,深深吸了一口帶著植物芳香的空氣:“大陸有兩個地方很像臺北,一個是成都,一個是衢州。成都像是我年少時期記憶中的那個臺北,熱鬧熙攘;而衢州更像是那個伴隨我一路長大的臺北,寧靜質樸。這里,正是我一直尋找的心靈歸處。”
徐瑞鴻是來自寶島臺灣的陶藝家,但相較于“陶藝家”的稱號,他更習慣將自己稱為“陶人”,他說,這輩子,自己只愛做陶一件事。徐瑞鴻畢業于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師從前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知名古陶瓷學者劉良佑教授與“臺灣現代陶藝之父”林藵家教授,對古陶瓷文化與現代陶藝的發展脈絡以及釉藥配方、燒制技術等方面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徐瑞鴻告訴記者,自己打算在樓山后這個美麗的村莊定居下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制坯燒瓷、烹茶飲酒,不必周游世界也很美好。”
陶生活:追尋失傳技藝的破解之路
綠格子襯衫,慢條斯理的說話聲,沉默、內斂、專注的神情。在徐瑞鴻身上,彌漫著那個陶瓷黃金年代的優雅與專注。
“我最理想的狀態是這樣——有幾棵大樹在工作室窗外,有陽光和雨露,有鳥鳴,有樹影。過路車不斷呼嘯而過,而樹葉靜止如同老僧禪定,待夜幕降臨時,我開燈、放音樂,開始一天的陶藝生活。寫釉式、調和釉藥、制坯、燒窯,日子一天一天的到來,我一天一天的去面對,假如堅持不住了,那就明天再繼續想辦法堅持,那樹那鳥天天守著我,而我守著我的滿室陶瓷。” 徐瑞鴻說。
在徐瑞鴻身后,一只暗青色的翠鳥荷爐幽香散淡,一縷細白煙霧正自翠鳥的喙中裊娜升起。這是他最負盛名的作品,采用的是汝窯窯變技術燒制而成,為百中存一的孤品,1300攝氏度的窯火,10小時以上的煅燒,荷花在這樣的窯溫中徐徐綻放,翠鳥自這樣的窯火中涅槃。這只香爐造型生動靈巧,荷花花瓣線條柔和,每片花瓣均于豆青釉色中呈現出淡淡的紅暈窯變,仿若云蒸霞蔚,令人稱奇。徐瑞鴻告訴記者,這只荷爐,將在今年夏天由保利拍賣行進行拍賣,拍賣所得,將全部投入對傳統汝窯技術的追尋和破解之中。
從十四歲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的知天命之年,徐瑞鴻坦言自己一直在尋找的就是那種慢工出細活的“陶藝生活”。翻開他二十多年來的藝術履歷,似乎都能覓到那一絲陶藝留下的芳蹤——
1991年,徐瑞鴻在臺北創立“恒春窯”,其作品大多模仿古代青銅的樣式燒造,造型古樸而端重,顏色純而不膩,淡而不寡,在當時的臺灣陶瓷界引起了轟動。
2000年,為了追尋失落的汝官窯燒制技藝,徐瑞鴻離開臺北,只身來到景德鎮,探訪古窯遺址,尋覓散落碎瓷片,展開一場尋夢之旅。
2001年,徐瑞鴻接手并投資了景德鎮改制后的國營華風瓷廠,成立了三陶軒工作室,成為第一批來景德鎮投資的臺資企業。終日與青山和窯址為伴,徐瑞鴻潛心專研青瓷的溫度范圍與呈色效果。
2005年,徐瑞鴻利用景德鎮本地原料,將一批造型典雅、美若古玉的宋代汝官窯青瓷作品呈現在人們視線中。
“以本地原料為基礎構建一套新的青瓷體系,是個長期摸索、試驗的過程,待到較有把握調配釉藥與掌控溫度,已歷5年的時間跨度。無論在釉色表現上是類玉似冰、雨過天青或為千峰翠色,在幾千年華夏歷史文明發展進程中,它早已脫離色彩學上的界定,演進為人們意念、情感上的深層次需求。”徐瑞鴻如是說。
汝瓷夢: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
汝瓷傳世珍品稀少,全世界現僅存65件。自古汝窯便有“天下名瓷,汝窯為魁”的美譽,在民間,也向來有著“縱有家產萬貫,不及汝瓷一片”的說法。
“汝瓷始于宋,也毀于宋,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一個孱弱的王朝消失了,隨同它一起消失的還有那撲朔迷離的汝窯燒制技術。我們現在所說的青花瓷,實際上是元代蒙古族的審美,在瓷器上繪上折枝藤蔓,五福百果,乃至折子戲。”一提起這個話題,徐瑞鴻的表情就顯得有些凝重:“汝窯反映了中國文人溫文爾雅、陰陽調和的美學追求,是中國古代文人特有的那種與世無爭的寧靜之美的最好折射,但在當今時代,我們已經很難感受到那種風骨和脈息。”
站在樓山后的青青草野間,徐瑞鴻向記者描述著自己第一次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初見汝窯瓷器時那份驚艷的心情:“當我隔著重重玻璃看到那件南宋汝官窯粉青筆筒時,那樣簡潔流暢的器物的造型,那樣寥若晨星的釉色,以及那份與世無爭的寧靜和單純一下子擊中了我。”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當初那份汝窯瓷器所帶來的美與震撼造就了徐瑞鴻與汝窯瓷器之間的難舍情緣。那份青如明鏡、沉實溫潤的汝瓷之色,也成為了他夢想的底色。
徐瑞鴻的作品,體現了對創作的不斷摸索和執著,也可看到陶藝家個人品格、美學修為的體現。經過二十年的不懈投入和探索,終于讓失傳千年的汝官窯技術得以重現。其作品,也以優雅、寧靜、大氣、精致著稱。由于對汝窯工藝的苛刻要求,極低的成品率造就了徐瑞鴻在業內的聲望:“市面上除三陶軒外沒有任何汝窯產品敢亮出破片,因絕大多數采用的都是瓷胎、乳濁釉的低端、假汝窯技術。”徐瑞鴻說。
“為了追求青如天、面如玉的效果,汝瓷常以瑪瑙入釉,從而形成了釉面上的小孔和細微氣泡,在光照下時隱時現,呈現出‘辰星稀的藝術美感,而根據溫度濕度變化,釉面會逐漸裂開如同蟬翼紋理一般的裂縫,也是業內所說的‘開片。瓷器出窯后,此起彼伏的開片聲蔚為壯觀。盛裝茶湯會加速這個過程。裝茶后,茶色會滲入裂紋之中,形成裝飾線。不同茶湯養出來的杯子,開片線的顏色也不同,綠茶、紅茶一般是金線;普洱則是黑線。”徐瑞鴻說:“每件器皿在使用過程中,仍會繼續開出新片,甚至開片變化會長達十年以上。所以,每一件器都是活的,會在主人使用過程中不斷變化,直至開出完美的開片。”
無論是在臺北,還是在景德鎮,甚至在衢州,徐瑞鴻都孜孜不倦地表達著自己的夢之聲:“雖然臺北故宮博物院是北宋汝官窯最大的藏家,但它文化的根在大陸。從十幾年汝窯燒制中,深感到古代汝窯富有哲學人文的哲理,溫文爾雅,含而不露,陰陽調和的美學,是中國宋元文化精髓的代表。我追尋汝窯,與其說是試圖找回那些失落的技藝,不如說更是在追逐一種情懷,一抹氣韻,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
三陶軒:讓傳世瓷器回歸尋常百姓家
“衢州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不疾不徐,好像天塌下來也不怕。這里高樓很少,他們告訴我是因為衢州有機場的緣故,但我寧可相信這是一種社會情緒。我喜歡這種慢慢來的感覺,人生本就不必追趕著前進。”徐瑞鴻透露,早在一年前,自己就被衢州濃厚的人文氛圍和歷史沉淀深深吸引,開始有了到衢州定居制瓷的念頭:“當所有人都在你追我趕,我們依然需要那些能夠回頭看看的人,需要一個能夠供我們供放心靈的地方。很顯然,衢州這片土地與我的陶藝觀不謀而合。”
去年4月,徐瑞鴻來到全旺鎮,考察了多個舊窯遺址,被兩弓塘宋代古窯遺址和特色文化所打動,就停住了腳步。“陶藝師的文化根,應回歸故土,全旺鎮所產的陶制品具有獨特的哲學人文之氣。我看陶制品,不僅看它的收藏價值,更想探究它背后的社會價值。為人類所用,才是陶制品真正的歸宿。”隨后,徐瑞鴻在衢州舉辦當代汝官窯作品展覽,展示了自己制作的香爐、茶具、文房陳設瓷50多件。
讓青瓷從被文人雅士收藏賞玩的領域,更多走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徐瑞鴻幾十年來一直致力的方向:“陶藝必須是創作者身體力行,跟釉藥、泥土和火發生接觸,而只有從創作者的手中傳遞到使用者的手里,才算完成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陶藝行為。”
徐瑞鴻的工作室名為三陶軒,對“三陶”,他有著這樣的定義:“蜒埴之器,引清微以為修身,引溫文以為養人,引淑世以為民用。”這其中,有汝瓷之美,有器物的服務之心,也有陶人澹泊的心性。縱觀他的作品,無論是小型香爐、茶具,還是文房四寶、佛教香器,無論是器物造型,還是寶光內斂、瑩潤的釉色,都傳神地還原了兩宋一脈風骨。仿古的外形,內核講述的卻是屬于今人的故事:“一件瓷器,擺在那里供人參觀,只是一件死物,唯有融入日常生活,它才能真正‘活起來。”徐瑞鴻說。
用生活陶藝來設計生活,對徐瑞鴻來說,自己的創作并非只是單純的工作:“中國陶瓷經歷了一段沒落,到處都是青花、釉下彩,釉下彩、青花,一些畫家指揮著一群陶工周而復始的在同一領域進行創作,這也是中國當下陶藝界的一個縮影,很多傳統珍貴的技藝遺產正在失傳。凡此種種,設計往往會走入一個誤區。而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回到傳統,重復練習。”
“陶藝文化本就根治于中國的文化土壤,只要符合社會需求,一切會自然而然地發生。”談及汝瓷今后的發展,徐瑞鴻的觀點是,實用陶藝、陶瓷設計制品的市場正日漸升溫,一個成熟創作環境的形成需要時間的積累與不斷的實踐。
二十載光陰仿如白駒過隙,陶者青絲染雪,唯見汝瓷如玉。青瓷創作的執著與探索,也可看作陶藝家個人品格與美學修為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