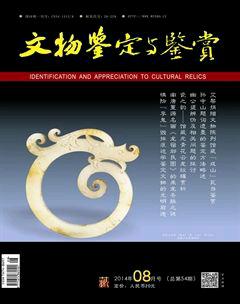揭開高安元代窖藏的神秘面紗
劉金成



【摘要】高安元代窖藏自發現至今,仍屬國內外專家關注的熱點。究其原因當屬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紅瓷器數量之多、品質之精、造型之眾、器形之碩大令世人矚目。窖藏發現30余年來,雖先前的窖藏研究對主人早有定論,然而隨著近來對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斷深入,有關主人及身份出現的諸多疑點也逐漸顯露。此次對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屬性、使用功能基礎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載的,元代瑞州路與之有關的史料為佐證,再結合《元史》中的相關記戴進行了比較分析,從而推論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本刊上兩期從“原窖藏主人認定之疑誤”“明正德《瑞州府志》與窖藏兩方面闡述了先前對窖藏主人認定存在的問題,并從窖藏出土的器物來剖析窖藏主人的身份。
四、窖藏主人及埋藏時間的推定
在目前沒發現記載有窖藏主人的前提下,只能借助史料、窖藏器物等推論出窖藏的主人。在此基礎上,該推論還應與元晚期瑞州路的時任官員、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相對應,才使得窖藏主人的推論具有說服力。
1.元末瑞州路官吏與窖藏的關系
查閱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五·秩官志·封爵>可知,至正年間在瑞州路任職的官員,所記載的多為蒙古族人或色目人。
不僅如此,《瑞州府志一地理志·建置沿革》還記載:“至元十三年丙子,改州為路以統州縣,瑞因得為上路,設達魯花赤,總管萬戶府,隸江西行省,統錄事司一,縣三。”由此可見早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丙子,瑞州因處要地(目前推論,元政府在當時瑞州路所轄境內的上高縣蒙山設有一大型銀礦澆鑄銀錠的緣故)設為上路。至正八年(1348年),禹蘇福從平江路(今江蘇省蘇州市)達魯花赤一職改任瑞州路總管,其爵號由到任前的正議大夫加封為“銀青榮祿大夫”,屬元朝從一品重臣。由此可見當時的瑞州路在大元帝國的重要性。
據史料記載,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版圖最為廣闊的時期,除元朝本土以外,其西域還有四大汗國,即欽伊利汗國、察合臺汗國、欽察汗國、窩闊臺汗國。該四大汗國分別是太祖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為汗王,之后成為元帝國的藩屬國,信奉伊斯蘭教。長久以來,四大汗國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均與大元帝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經貿往來頻繁,它們視大元帝國為宗親國(見圖38)。
有研究表明,元代景德鎮用于燒制青花瓷的鉆料俗稱“蘇麻泥青”,其原產地就是西域。以現藏于伊朗國家博物館(原藏于伊朗阿德比爾清真寺)的1件“元青花菱口大盤口沿上書寫的波斯文”舉例,它在景德鎮窯廠的燒制應出自熟悉波斯語言和文字的波斯工匠之手,是景德鎮精湛的瓷器燒造技藝與西域鈷料相互結合作用而產生的。2012年10月19日至20目,上海博物館在建館60周年慶典之際舉辦了“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展”,書寫有波斯文的“元青花菱口大盤”也在展覽之列。為了促進國內外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和交流,中國古陶瓷學會也在上海博物館舉辦了“元代青花瓷器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期間,有學者以該大盤上的阿拉伯文字為依據,分析是14世紀來自西域的波斯工匠將燒制青花瓷的技術及青花料引進景德鎮窯廠,從而促成了元青花瓷的燒制成功(見圖39)。
從推論高安窖藏主人身份的角度來分析,元朝進入中晚期以來,類似于禹蘇福這樣來自西域并在元帝國任職的官員眾多,從他們的身份、地位分析,應比來自西域的工匠更有先決條件,來執行元朝政府所頒布的祭祀政令。并將其所熟知的用于清真寺祭祀的裝飾鈷料連同工匠引進中原,效行朝廷于浙江行省龍泉窯燒制祭祀瓷器的做法,約于至治元年(1321年)至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31年間,在景德鎮燒制出成熟的青花瓷器,用以替代日益稀缺的祭祀用青銅禮器,以滿足瑞州路官府祭祀的需要(見表8、表9)。
《元史>記載景德鎮在元代屬饒州路管轄,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有載:“甲子,徐壽輝偽將項普略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也就是這一年起,元政府已徹底失去了對景德鎮的控治。之后,工匠是不可能再為元朝政府燒制瓷器的。
故高安窖藏的由景德鎮窯燒造的瓷器從理論上分析,是瑞州路官府在元至治元年(1321年)至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31年間,通過樞密院或景德鎮浮梁瓷局監燒而獲得的。這一推論也與朝廷記載在浙江行省燒制龍泉青瓷的時間同步。尤其是元青花成功燒制,是與在瑞州路任職的西域官員緊密相連的。
2.元末戰亂中的瑞州路與窖藏
元末拉開了大元帝國衰亡的序幕,農民起義風起云涌,時局動蕩不安。以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為代表的三股勢力長期在南方形成對峙之勢,他們為爭奪勢力范圍經常展開拉鋸戰,使南方戰事不斷。
據清同治瑞州府記載:
“至正十一年冬十一月江西妖人鄧南木作亂,攻瑞州,總管禹蘇福擒斬之。”
“至正十二年徐壽輝部將陶九陷瑞州,總管禹蘇福萬戶張岳敗之。紅巾賊況普天陷瑞州,縱火三日。天完將李養成王普敬據華林山為寇。”
以上記載表明至正十一年(1351年)至至正十二年(1352年)間,農民軍雖多次攻打瑞州府城,但均被元朝攻府所及時收復。
又查明正德《瑞州府志·郡縣表·州國郡路府》載:
“至正十三年總兵張岳偕左丞火逆赤復之。”
“至正二十二年陳友諒偽將劉五陷踞之。”
根據該記載從至正十三年(1353年)至至正二十一年(1362年),瑞州路仍然在元政府的統治控制之下。由此推論窖藏中這批位于祭祀倉庫中的祭祀器,此時還是由瑞州路官府掌控著。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陳友諒偽將劉五攻陷瑞州路,由此宣告元朝政府在瑞州路統治的結束。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陳友諒率軍與朱元璋的明軍血戰于鄱陽湖,史稱鄱陽湖大戰。從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至元末(1367年)的六年間為“陳友諒偽將劉五陷踞之”。這期間明正德《瑞州府志》有關瑞州路無詳細史料記載。
查明正德《瑞州府志·郡縣表·州國郡路府》載:“大明元年(1368年),瑞州劉五納欽。該記載表明洪武元年,陳友諒部將劉五歸順大明。劉五的歸順,使得瑞州路順利地過渡至大明政府。
由此推論劉五在攻陷瑞州后,他并沒有得到窖藏中的這批祭祀重器。窖藏的埋藏是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劉五攻陷瑞州之時,導致瑞州路大批官員的突然撤離才發生的。否則,這批器物也會因劉五的歸順而傳世至大明國、繼續履行著它的祭祀用途。
3.主人埋藏窖藏
如將窖藏的埋藏時間推定在劉五攻陷瑞州路的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是否可根據這一推定再結合《瑞州府志》中的城池史料記載,還原出窖藏入土的時刻?
查考明正德《瑞州府志(地理志·城池)》載:“本府子城舊址周圍三里,關四門,東抵進龍池,西抵平頭門,南即譙樓(今大觀樓),北抵朝天門,宋建炎太守黃次山始筑之……府前(今高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即譙樓為門,扁日瑞陽門,然城分南北,錦江中貫濱江兩崖,壘石為岸……按元至元間,仍宋舊南北二城,一十二門。弘治十二年,南昌道兵備僉事王純、知府周津北城建迎恩、拱辰、朝天、太平四門,南城建朝陽、靖安二門……”
上述記載已表明,明代瑞州府城墻始筑于宋代。元朝至元年間的南北二城仍是宋代的舊城。時值明弘治十二年,南昌道兵備僉事王純、知府周津不僅維修了元末頻遭戰亂損毀的南北二城,并在舊城池基礎上增建迎恩、太平及朝陽、靖安等六門(見圖40-圖42)。
如將以上記載與延續了宋元明三朝瑞州城池的舊圖對照,元代瑞州路城池防御已躍然明了,窖藏埋藏的時刻也因然大致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陳友諒部將劉五從武漢一直南下,直取瑞州路北城池總管府。為了保全性命,瑞州路官吏們攜帶家眷及貴重物品通過浮橋退守城南。為阻止起義軍進攻城南,瑞州路官員撤退城南后搗毀筑架于錦江之上連通南北二城的浮橋和石橋。但在阻擊未果、堅守南城無望之時那些來自蒙古或西域的官僚們,匆忙打理起少量可隨身攜帶的金銀等物品,并在城南浮橋頭西約100米處的城墻空地,挖掘一直徑為1.3米、深2米余的橢圓土形窖穴,將瑞州路官府常用來祭祀而又無法隨從的“國之重器”悉數下窖,之上蓋一層錫皮,覆土掩埋后攜帶家眷從南城出逃……
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此次瑞州路的戰亂出逃不像前幾次那樣時隔幾日就可幸運般地返回,而此次將“一去不復返”。有的官員在逃離漢地之后幸運地回到了漠北;而有的官員與家眷則在逃離瑞州后,隱姓埋名流落他鄉;一些老弱病殘者,則在逃亡途中遭遇疾病或兵禍身亡。最終使他們期待在平息戰亂后取回所埋藏器物的愿望無法實現,這一千古迷案也得以延續至20世紀80g代末重見天日(見圖43、圖44)。
五、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得出以下五點大致結論:
1.高安元代窖藏主人身份、窖藏器物用途及其埋藏年代的再考,首先明確了高安窖藏屬元代瑞州路總管府所有,糾正了之前推論窖藏主人為元代駙馬都尉伍興甫父子的錯誤觀點。
2.以明正德《瑞州府志》地方史料為依據,通過研究窖藏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清晰地還原出元代中晚期瑞州路的政治、經濟、文化部分狀況,尤其是祭祀文化的興盛,從而進一步明確了瑞州路官府與窖藏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糾正了之前《關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幾個問題》中將青花、釉里紅、卵白釉五爪龍紋器物等同于御用賞賜品的錯誤論斷。高安元代窖藏再考并用大量史實來佐證窖藏中的大部分器物在元中晚期燒制后是瑞州路用來祭祀的器具。尤以窖藏中的青花和釉里紅瓷器最為突出,均是當時擁有者用來替代青銅器用作祭祀的“國之重器”。
3.高安元代窖藏再考還以至治初年(約1321年)朝廷在浙江行省始燒瓷器用來替代青銅祭祀器的時間為上限,客觀地將窖藏中的青花、釉里紅、卵白釉、青白釉及龍泉窯等大部分器物的燒制年代界定在至治初年(約1321年)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31年間。因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壽輝偽將項普略陷饒州路(今景德鎮),故元政府隨即也結束了在景德鎮的最后統治。這與瑞州路(1348年)《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學記)》中有關總管禹蘇福維修郡學、祭祀場所、祭祀倉庫所記載的時間相對吻合。但從《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學記)》記述內容分析,窖藏中的一些器物應在其到任前就已燒制并在瑞州路用于祭祀。
4.高安元代窖藏再考是結合《元史》和明正德《瑞州府志》中的部分史料,將窖藏中的青花與元中晚期瑞州路來自蒙古及西域任職的這一特定群體進行了列表分析,從而窺探出元帝國在政治經濟、人文文化與藩屬國的密切交往,促使青花瓷器在元代中晚期的燒造及使用。后因元帝國的即將滅亡,致使至正二十二年瑞州路的主人將其埋入地下的這一歷史事實。
5.高安元代窖藏再考解決了關于元青花的燒造時間、元青花的燒造用途、元青花的燒制歷史背景等方面的問題,并將高安元代窖藏準確燒制時間界定在至治初年(約1321年)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31年間(從元青花瓷器的工藝、紋飾等分析,其大致燒制年限應界定在1321-1367年的46年間)。
尤其重要的是,高安元代窖藏再考對同樣出自于元代路、州、縣的江西萍鄉窖藏、安徽繁昌窖藏、內蒙古集寧路窖藏、河北保定窖藏、山東菏澤沉船等的研究均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