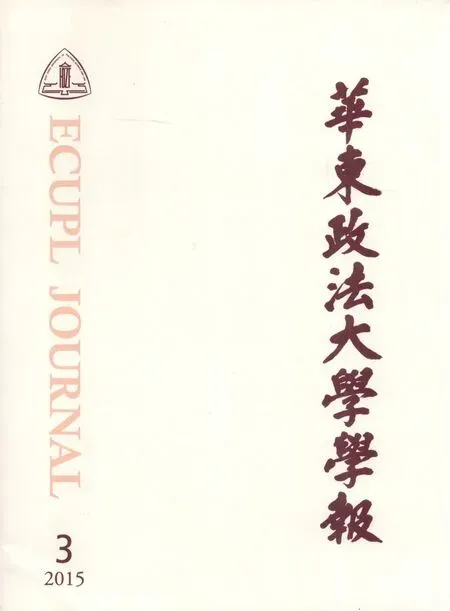公私合作合同:法律性質與權責配置——以基礎設施與公用事業領域為中心
李 霞
自20世紀末葉以來,伴隨著放松規制、新公共管理和合作治理的推進,公私合作合同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運用。在中國,公私合作合同的實踐也日漸活躍,在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領域尤其如此。〔1〕例如,財政部在2014年9月發布《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明確提出要“拓寬城鎮化建設融資渠道,促進政府職能加快轉變,完善財政投入及管理方式,盡快形成有利于促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發展的制度體系”;兩個多月后,財政部印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財金[2014]113號),對PPP合同體系尤其是其中項目合同的訂立和履行的全過程作出了指引性規范。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行政訴訟法》修正案,將部分與政府特許經營協議相關的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的軌道。〔2〕根據修正后的《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為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征收補償協議等協議”,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但目前,中國法律界對于包括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在內的公私合作合同尚缺乏系統的理論建構,不利于相關爭議的妥善解決和公私合作的順利開展。本文擬對公私合作合同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包括公私合作合同的概念及其勃興的原因、公私合作合同的性質、國家在公私合作合同中的擔保責任以及公私合作合同展開過程中的法制建構等予以闡述,以期推進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和認識。
一、公私合作合同的興起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PPP)〔3〕在我國官方文件中則被稱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參見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年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開發銀行:《關于推進開發性金融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有關工作的通知》(發改投資[2015]445號);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關于市政公用領域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推介工作的通知》(財建[2015]27號)等。是晚近各國行政改革中的熱門概念和流行做法。“公私合作”中的“公”,指的是(廣義的)國家,具體表現為政府部門或其他公共機構;“私”指私人主體,包括自然人和私法人;“合作”則是指公私雙方為共同履行公共任務而采取的協作行動。對公私合作這一概念所包含的范圍,有不同的界定。在最廣意義上,只要有私部門參與公共任務的履行,就可視為公私合作。這種界定的優點在于,可以凸顯私人在現代國家履行公共任務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缺點則在于涉及領域過于寬泛,難以為其建立一個有效的討論基礎和統一的法律框架。〔4〕詹振榮:《行政合作法之建制與開展》,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之法理/各國行政法學發展方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09頁。因此,有學者主張對公私合作的概念加以限縮,僅用以指稱公私部門在對等互惠和責任分擔的基礎上,出于自由意愿所形成的合作關系。〔5〕Jan Ziekow,Verankerung verwaltungsrechtlicher Kooperationsverh?ltnisse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Wissenschaftliches Gutachten,erstattet für das Bundersministerium des Innern,Juni 2001,S. 76 ff.這一界定將法律直接授權或要求私人履行公共任務等現象排除在公私合作的范圍之外,有利于保持概念的純粹性。還有學者基于私人參與公共建設在當代公私合作實踐中的重要地位,進一步將公私合作限定于該領域。〔6〕參見陳明燦、張蔚宏:《我國促參法下BOT之法制分析:以公私協力觀點為基礎》,載《公平交易季刊》2005年第2期;李洪雷:《其他承擔行政任務的主體》,載應松年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頁。由于第一種界定失之過寬,而第三種界定又略顯狹窄,本文對公私合作主要在前述第二種意義上加以運用,但為使一些問題的討論更加集中,將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中的公私合作作為重點考察對象。〔7〕實踐中我國對PPP的運用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例如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明確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界定為“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建立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但無論是哪一種意義上的公私合作,其發展都反映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關系的深刻轉型,這使得現代國家在“法治國家”、“社會國家”、“行政國家”與“規制國家”等稱號之外,還有了“合作國家”的別稱。〔8〕“合作國家”概念為德國學者Ernst-Hasso Ritter在1979年提出。See Ernst-Hasso Ritter,DerKooperative Staat.Bemerkungenzum Verh?ltnisvon Staatund Wirtschaft,A?R104(1979),S.389ff.中文參見張桐銳:《合作國家》,載《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78頁。
公私合作的運作邏輯,是公私部門為著共同目的分工合作,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并結成一種互補性的合作伙伴關系。〔9〕Graham Finney& DavidA.Grossman,“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FrederickS.Laneed.,Current Issuesin Public Administration,Belford/St.Martin’sPress,1999,p.341.另可參見[英]達霖·格力姆賽、[澳]莫文·K.劉易斯:《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基礎設施供給和項目融資的全球革命》,濟邦咨詢公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2頁。通過公私合作,可以將私部門的資本、專業知識、效率和靈活性引入公共行政當中,創造出有效結合公私部門優勢、資源和專業的效果,〔10〕DimaJamal,i“Successand Failure Mechanisms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sightsfrom the Lebanese Context”,17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414-430(2004).從而改善公部門績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提高服務品質,減少政府財政壓力。正是著眼于公私合作在這些方面的優勢,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f or Europe,UNECE)對其甚為推重,〔11〕UNECE,Guidebookon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the United Nations Econoic Comissionf or Europe,http://www.unece.org/ceci/publications/ppp.pdf/,accessed April15,2015.發展中國家的 PPP 也日漸盛行。〔12〕DimaJamal,i“Successand Failure Mechanisms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sightsfrom the Lebanese Context”,17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414-430(2004).
就我國而言,公私合作的特殊意義還在于它回應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因為奉行全能政府、計劃經濟,國家壟斷了一切公共事務,私人領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共化,極大禁錮了社會的活力。20世紀80年代以后,轉變政府職能被納入改革議程,并形成了一個延續至今的放權趨勢,呈現出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由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的態勢。而與“不是政府就是市場”、“不是公就是私”的簡單化思維相比,公私合作可以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提供另一種或許更符合實際的選項。在基礎設施建設與公用事業等領域,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
公私合作往往涉及多方錯綜復雜的關系,這使得公共部門亟須運用有效的工具來明確公私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風險與責任,以應對不可預見性和不確定性。立法規制和傳統行政規制手段卻都捉襟見肘:高度的法律化不僅受制于立法資源的不足而難以及時有效回應權利義務明確的需求,更存在阻礙公私雙方根據項目的特定情形靈活應對的弊端;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傳統規制進路亦與公私合作的理念和邏輯不合。在此背景下,以雙方平等協商、內容具體明確為特征的合同的重要性就得到凸顯:合同作為一種自律性的規范形成工具,其內容盡可能由合同當事人自由形成,而法律則僅對其作出框架性規范,這種機制特別適合于運用在公私合作領域。〔13〕李建良:《民營化時代的行政法新思維》,載李建良主編:《2011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2012年版,第1-27頁。
以公私合作中最具代表性的BOT模式為例,由于BOT主要用于公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涉及眾多利益攸關方、影響范圍廣、持續時間長、投資金額大,因此必須通過合同的形式來確定和維持合同各方約定的具體內容和彼此間的法律關系。BOT模式的實質,即是包括特許權、合資、融資、建設、管理、維修、收費、回購、保險、擔保等在內的一系列合同。
從BOT合同中,我們也可以一窺公私合作合同的特性。其一,公私合作合同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為一個由系列相關合同構成的龐大的“合同群”。其二,公私合作涉及具體項目的規劃、執行和結束的各個階段,合同的內容須涵蓋此長期合作關系的全過程。其三,由于公私合作存在于國家與社會的交叉領域(überschneidungsbereich),〔14〕G.F.Schuppert,Verwaltungswissenschaft:Verwaltung,Verwaltungsecht,Verwaltungslehre,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2000,S.174.公私合作合同中必然成為匯聚國家與市場、公部門與私部門等場域中不同行為主體意志與利益的混合架構。其四,公私合作合同通過書面的形式,將公、私部門的任務分工、責任分配與風險配置固定下來,在此基礎上發展作為“目標共同體”和“風險共同體”的公私伙伴關系。
二、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性質
對于秉持公私法二元劃分傳統的國家來說,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性質究竟屬公還是私,直接關系到公私合作合同的規則適用和司法救濟管道的選擇,〔15〕在有著公私法二元界分傳統的國家,公、私法建立在不同的規范旨趣上,公、私法糾紛也通過不同訴訟渠道加以解決。可以說,事物的法律性質決定著適用規范和訴訟渠道選擇方面的差異,進而可能產出完全不同的司法裁判結果。參見李建良:《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上)》,載《月旦法學教室》2003年第5期。更關涉到其整體價值取向和具體制度的設計。〔16〕若將公私合作合同認定為公法合同,意味著合同將對公共利益作更深入的考量,在具體制度上也會突出行政機關的單方優益權;將公私合作合同認定為私法合同,則意味著合同須更多強調兩造的平等,謹慎平衡合同兩造各自代表的公益和私益。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法律迄今鮮有明確規定,〔17〕除了修正后的《行政訴訟法》第12條將政府特許經營協議爭議部分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外,其他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等,均回避了對公私合作合同法律性質的規定。例如,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5年4月25日印發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對于特許經營協議的法律性質問題仍然進行了模糊化處理,見第六章“爭議解決”的規定。但比較該辦法與國家發展改革委法規司2015年1月19日發布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可以發現,后者第48條所規定的“特許經營者與實施機關就特許經營協議發生爭議并難以協商達成一致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訴訟或仲裁”被刪除。學理上也未有定論。〔18〕現階段對公私合作合同性質的學術討論也多圍繞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展開,有學者認為,政府特許經營協議是“具有濃厚行政色彩的公法上的契約”,參見邢鴻飛:《政府特許經營協議的行政性》,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6期;有學者則認為BOT合同應屬兼具公法和私法行政的混合合同,參見湛中樂、劉書燃:《PPP協議中的法律問題辨析》,載《法學》2007年第3期。
與公私合作合同的(公/私法)屬性之辨直接相關的問題,是公法合同與私法合同的區別。在這個問題上,“由于觀察角度不同,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19〕參見中國臺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82年度釋字324號。大致而言,公、私法合同的區分標準主要有主體、目的、標的、特殊權力保留和綜合判斷五種。其中合同標的說是以合同標的作為判斷公私合作合同法律性質的標準。也即如果合同產生、變更或終止了公法上的法律關系,則屬公法合同,反之,如果產生、變更或終止的是私法上的法律關系,則為民事合同。〔20〕參見于安編著:《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頁。合同標的標準“能夠清晰地說明將行政合同從民事合同中分離并加以規范的理由和必要性”,〔21〕參見余凌云:《論行政契約的含義——一種比較法上的認識》,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3期。大陸法系的諸多國家和地區(例如德國、葡萄牙、我國臺灣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等)均將其奉為通說,有些法域還在其行政程序法中明確了這一標準。
應注意的是,合同標的理論中判斷合同產生的法律關系屬公法或私法性質的依據,并非合同的自然本質,而是其規范依據——如果合同訂立依據的是公法,則屬行政合同。但當合同不存在直接依據,或者其所依據的既有公法也有私法時,如何對其定性,則存在困難。〔22〕參見程明修:《行政契約標的理論》,載程明修:《行政法之行為與法律關系理論》,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而這種情形在公私合作合同中恰恰是較為常見的。
本文認為,在這種情形下,應當圍繞合同的具體條款,結合下列因素來對合同性質進行綜合判斷。首先,考察是否有一方當事人為行政主體,且行政主體是否以高權地位參與合同締結。〔23〕參見余凌云:《論行政契約的含義——一種比較法上的認識》,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3期。其次,探究締結合同的行政機關的真實意思,判斷其締結行政合同是否為了“執行公務,實現行政目標”,或更寬泛地,是否為了“實現公共利益”。〔24〕對于判斷行政合同的目的,存在“公務說”和“公共利益說”的分歧。持“公務說”的學者占多數,有姜明安、楊解君等,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頁。持“公共利益說”的有邢鴻飛等,參見邢鴻飛、趙聯寧:《行政合同在BOT項目中的運用及其法律保障》,載《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在公私合作的背景下,“公共利益”標準更為適宜,因為單純強調公務和行政(管理)目標標準存在隱憂,可能會導致對相對人意思的忽視而片面強調“行政優益權”,不利于雙方合作關系的建立。最后,觀察合同內容中是否包含了超越私法的規則,即合同是否為行政機關保有特殊權力(the clauses exorbi tantes du droit commun))。〔25〕參見[英]L.賴維樂·布朗等:《法國行政法》,高秦偉、王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頁。
以公用事業的政府特許經營合同為例加以分析。根據前述判斷標準,政府特許經營合同應屬行政合同,這是因為政府特許經營合同的締結、變更或解除,對應的是公法上法律關系的建立、變更或消滅。具體判斷理由在于:政府特許經營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一方為“主管部門”——特許的授予方,另一方為“特許經營者”——特許的受讓方;〔26〕參見原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建設部令第126號)。其目標體現出濃厚的行政性和公益性;〔27〕參見國務院:《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60號);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財金[2014]113號);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等。政府特許經營是“一種政府監管手段”,〔28〕章志遠、李明超:《公用事業特許經營中的臨時接管制度研究——從“首例政府臨時接管特許經營權案”切入》,載《行政法學研究》2010年第1期。政府特許經營協議的簽訂和履行本質上是行政主體通過合同方式來實現監管目標,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其所確立的是行政法上的法律關系;并且,政府特許經營協議中,往往保留了大量的政府特權和主導性權利條款(例如,行政主體可依法調整產品和服務價格,行政主體擁有依法收回特許經營權、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行政主體可對特許經營人進行財務監管,等等)。〔29〕參見李霞:《論特許經營合同的法律性質——以公私合作為背景》,載《行政法學研究》2015年第1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5]9號)第十一條的規定——“行政機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在法定職責范圍內,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規定的行政協議”,與本文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通之處,例如強調行政協議的內容是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要求行政協議應由行政機關在法定職責范圍締結。至于本文所強調而在司法解釋中未提及的行政機關保有一些特別權力的問題,未嘗不可以從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要件、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要件中推導出來。
對于作為一個集合的公私合作合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編制的指南的觀察比較準確:“在屬于民法傳統或受民法傳統影響的許多法律制度中,公共服務的提供可能受到一些稱作‘行政法’的法律的管轄,這種法律規范著廣泛的政府職能。這種制度按這樣的原則運作,即政府可以通過行政行為或行政合同行使其權力和職能。人們還普遍認識到,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可以根據管轄私人商業合同的法律簽訂私法合同。這兩種合同之間的差別可能是很大的。”〔30〕UNCITRAL,Legislative Guideon Privately Financ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2000,Chapter VII,6.Ruleson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Administrative Law,p.24.簡言之,公私合作合同既可能是行政(公法)合同,也可能是民事(私法)合同。同時需要強調的是,即便屬于行政合同的公私合作合同,與一般的行政合同也是存在區別的:就理念而言,一般行政合同仍帶有傳統的公私對峙的意味,而公私合作則強調私部門作為公部門的平等和互助伙伴的地位;就法律關系而言,有別于一般行政合同的兩造線性關系,公私合作合同涉及的至少是三角、甚至多角的復雜關系;就制度而言,由于公私合作合同更具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所涉資金、資源和利益巨大,因而對于程序和內容規范都有更高的要求。
前文對于公私合作合同法律性質的討論,主要著眼于現行法律框架內的法律適用。而在法政策上,本文則主張跳脫公私法二元劃分的框框,在未來構建起關于公私合作合同的統一的實體與程序規則。這是因為,盡管公私法劃分仍然主導著現代法律的分析邏輯,但在國家與市場、社會交互融合的背景下,作為描述性的工具,公私法的界限已經日漸模糊,在許多新興的法律領域中其解釋能力也大幅弱化,難于回應客觀現實對法制建構的需要。具體到公私合作的法律性質問題上,片面強調公私合作合同的公、私定性而陷入僵化的公私二元嚴格區分的泥沼中,有以理論桎梏現實之嫌。因此,切不可因公私法的區分問題而阻滯公私合作合同的發展。〔31〕黃錦堂:《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研究》,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9頁。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德國的一些學理頗具啟發性。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行政合同作為上位概念,使之涵蓋所有行政機關參與締結的合同——其性質可為公法亦可為私法。〔32〕江嘉琪:《德國(含歐盟)行政契約理論發展之趨勢》,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之基礎理論、法理變革及實務趨勢/行政程序法之最新發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26頁。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修訂過程中的一種聲音是,在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大框架中,于公法合同法制之外建構獨立的公私合作合同法制,其理由之一即在于對公私合作合同定性困難。例如,Gunnar Folke Schuppert教授建議將聯邦行政程序法中有關行政合同的章節擴大為關于所有行政機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的總則性規定。具體做法是,在現行聯邦行政程序法規定的雙務合同和和解合同之外,另設一章規定“行政機關與私人之合作”,無論其行為屬性是公法還是私法,都適用行政程序法。另一位接受聯邦內政部委托進行公私合作合同法制化研究的Jan Ziekow教授,其基本立場與Shuppert教授相似,建議在原有規定之外增加“公共任務履行的合作”一章,規定“行政機關為履行其任務,得與自然人、私法人或無權利能力之私法團體以及其他行政機關合作。”〔33〕Vgl. G. F. Schuppert,Grundzüge eines zu entwickelnden Verwaltungskooperationsrechts ( Regelungsbedarf und Handlungsoptinnen eines Rechtsrahmens für Public Private Parnership) ; Jan Ziekow,Verankerung verwaltungsrechtlicher Kooperationsverh?ltnisse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Wissenschaftliches Gutachten,erstattet für das Bunderministerium des Innern,2001.參見詹鎮榮:《行政合作法之建制與展開》,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之法理/各國行政法學發展方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8頁以下;程明修:《公私協力與行政合作法—以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改革構想為中心》,載《興大法學》2010年第7期。
由于公私合作合同的運用范圍廣泛且類型眾多,在不易區分各類合同法律性質的情形下,將它們統合在“合作合同”(無分公/私)的名下,探尋其共通原理,為其建構一套有別于傳統公/私法的、相對統一和獨立的法律規范體系,以此來保證法律適用的明確性,〔34〕參見吳志光:《ETC裁判與行政契約—兼論德國行政契約法制之變革方向》,載《月旦法學雜志》2006年第135期。“使其……在合同權利義務關系、合同效力與人民權利保護等問題上,能有盡量趨于一致的結果”,〔35〕江嘉琪:《德國(含歐盟)行政契約理論發展之趨勢》,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之基礎理論、法理變革及實務趨勢/行政程序法之最新發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26頁。不失為一種經濟、可行的選擇。事實上,對于合作合同這樣一個跨公、私域的混合事物,指望在公或私的任何一個單獨法律體系中予以規范,其弊病都是不可克服的——單純以私法模式加以規范,將導致公共利益削弱的問題;單純以公法模式來規范,又缺乏對私方當事人利益的關照和平衡。在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體系及技術框架中,必須融入諸如公平、公開、理性和責任等體現公法價值的安排。
三、公私合作合同中的國家擔保責任
公私合作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或行政合同的又一個特征,是國家在其中的擔保人角色。公私合作可被視為擔保國家的展現形式,公私合作法制乃是以擔保國家理論為基礎。〔36〕許登科:《德國擔保國家理論為基礎之公私協力(?PP)法制——對我國促參法之啟示》,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頁。如同干預國家的形成和與干預行政法的成長有密切聯系,擔保國家(Gew?hrleistungsstaat)對當代“合作行政法”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37〕[德]米歇爾·史托萊斯:《當代德國公法與干預國家之形成》,載《法學叢刊》第205期(2007年),第160頁。擔保國家作為一種“國家模型”,是指國家自己不直接向私人提供服務,而是擔保其他人(主要是私人企業)履行適當的公共任務。正如Eifert所言:“擔保國家是以國家持續承擔公益責任為主要特征,但國家不再親自執行任務。盡管如此,一方面,擔保國家積極促成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仍然恪守社會法治國的原則,而負有對社會現狀與發展的最后責任。”〔38〕德國學者Eifert語,轉引自許登科:《德國擔保國家理論為基礎之公司協力法制——對我國促參法之啟示》,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6頁。
在19世紀的自由法治國家時期,國家的主要任務在于維護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與之相應,總量較少且類型較為單一的行政任務主要由國家行政機關直接履行。而到了福利國家時期,國家行政任務的數量急劇膨脹,為人民提供給付(服務)的任務大幅擴張。福利國家對于維護社會安全、促進社會正義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但與國家行政職能的大幅擴張相伴而來的是國家的“超載危機”:官僚機構過度膨脹,財政支出日益增加,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質量低下。自197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掀起了一場以推行“民營化”(Privatisierung,私人化或私部門化)和政府“瘦身”為中心內容的政府改革運動,使得21世紀儼然成為“民營化時代”。〔39〕[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與新行政法》,畢洪海、陳標沖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99頁。另可參見李建良:《民營化時代的行政法新思維》,載李建良主編:《2011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臺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2012年版,第1-27頁。在民營化以后,許多原本由國家直接承擔的公共任務轉由市場中的民營企業來承擔,公私合作也成為民營化的一種表現形式。〔40〕據Schuppert的分類,民營化可以分為六種類型,即組織民營化(形式民營化)、財產民營化、任務民營化(實質民營化)、功能民營化、程序民營化和財務民營化。其中財務民營化是指將公共建設的成本由納稅人負擔轉為由利用人負擔,并取得私人的資本與技術,這是公私合作的一種典型形式。參見陳愛娥:《德國行政法學的新發展》,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之法理/各國行政法學發展方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86頁。然而私人履行公共任務,并非意味著國家責任的湮滅,而只是在公、私之間重新分配責任:國家固然從直接履行的責任中解脫出來,但為保證公共服務的質量不因市場主體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因素的消極影響,保護公眾的利益,國家需要承擔起相應擔保責任(Gewahrleistungsverantwortung),也即確保公共任務履行的最終責任。〔41〕參見[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秩序建構》,林明鏘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頁以下;《德國“擔保國家”理念評介》,載《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7期。對于因私人組織行使公共權力的事實而使政府責任有所減輕的擔憂,早在公私合作發展之初就存在。參見 Miller,“Administration by Contract:ANew Concernf or the Administrative Lawyer”,36New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957,982(1961);Donald Frenzen,“Th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in the United States”,37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270-292(1968).國家擔保責任的憲法依據,除了社會法治國以外,最主要的是基本權利保護條款,也即國家承擔著對基本權利的保護與實現義務。〔42〕參見黃錦堂:《行政組織法》,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73頁;Martins,Grundrechtsdogmatikim Gew?hrleistungsstaat:Ra tionalisierung der Grundrechtsanwendung,D?V2007,S.456.我國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承擔著重要責任,這種責任既可以國家直接提供給付的形式出現,也可以國家委由私人提供、同時對私人進行規制與監督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國家對人權的保障義務同樣構成其在公私合作合同中承擔擔保責任的憲法基礎。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其中的“尊重”是對國家提出的消極要求,它要求國家不能濫用公權侵害私權。與之相對,“保障”則是對國家提出的積極要求,它既要求國家承擔人權的保護義務,即采取有效的組織與程序上的措施保護公民不受他人侵犯,或者在公民權利遭到侵犯時為其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也要求國家承擔對人權的“實現”義務,即采取有效措施幫助公民擁有實現其人權的基本條件。這種國家的保護與實現義務在行政法上就具體落實為擔保責任。
與私法上的瑕疵擔保責任相比較,行政法上的國家擔保責任,其目的不僅在于排除瑕疵狀態,以及在瑕疵出現后承擔一定法律責任,而且應擴展到“預防”瑕疵的出現。為確保私人執行公共任務能夠符合公共利益,國家還應建立一套完善且專業的系統對私部門加以控制,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私部門履行公私合作合同的控制。德國公法學家Wolfgang Weiss認為,國家的擔保責任體現在規制(Regulierung)和監督(Aufsicht)兩個方面,主要內容則是擔保公共服務的提供、創造并促進公平競爭以及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危險進行必要的防范。〔43〕Wolfgang Weiss,Beteiligung Privaterander Wahrnehmung ?ffentlicher Aufgabenund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DVBI.2002,S.1179ff.德國著名公法學家、聯邦憲法法院院長Andreas Vo?kuhle認為,為與國家的擔保責任相對應,應建構起擔保行政法的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其一,規范相關手段,以確保私人給付提供的質量與結果;其二,規范選擇私人合作對象之程序以及確保其質量之程序;其三,規范競爭者、使用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第三人保護機制;其四,設立相關機制,以擔保進行必要的創新與學習意愿;其五,賦予國家有效的撤回選擇權。〔44〕[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秩序建構》,林明鏘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頁。許宗力教授的觀點與此相近。他認為,民營化后國家的擔保責任應該包括:其一,給付不中斷的擔保義務,尤其是在涉及水、電、煤氣等具獨占性的基礎生存照顧的公用事業時,國家必須確保給付不中斷;其二,維持與促進競爭的擔保義務;其三,持續性的合理價格與一定給付質量的擔保義務;其四,既有員工的安置擔保義務;其五,人權保障義務與國家賠償責任之承擔。許宗力:《行政任務民營化》,載《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07—609頁。
四、公私合作合同關系的展開
公私合作合同關系的展開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以合同的締結作為時間節點,可分為締結前準備階段、締結階段和締結后的履行階段。〔45〕相似的觀察,參見陳愛娥:《政府業務委托民間辦理的法律規制——公私部門合作法制的建構》,載《月旦法學教室》2003年第8期。本部分圍繞這三個階段中行政機關所應具體承擔的職能,并以公用事業領域的公私合作為例,展開對相關法制建構的設想。正如美國研究公私合作的著名學者弗里曼所指出的,包括外包在內的公私合作,“對由公共資助、私人提供之服務的理性、公眾參與、公開以及責任性都提出嚴重且復雜的問題,這些擔憂對行政法學者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容易化解”。〔46〕[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與新行政法》,畢洪海、陳標沖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19頁。因此,建構公私合作合同法制,要將民主、法治國家、人權保障等憲法要求加以具體化,貫徹公開、公平、參與和問責等現代法治原則。〔47〕詹鎮榮教授參考德國學者A.Vo?kuhle的觀點,提出了行政合作法的五大基本建制原則,即經濟性原則,合作原則,國家執行責任確保原則,公益維系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Vgl.A.Vo?kuhle,Beteiligung Privaterander Wahrnehmung ?ffentlicher Aufgabenund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VVDStRL62(2003),S.332ff.詹鎮榮:《行政合作法之建制與展開》,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之法理/各國行政法學發展方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19頁以下。
在公私合作合同關系展開的第一階段,也即締約前準備階段,應根據具體公用事業的性質以及相關的法律規定,建立公正、科學、有效的決策機制,決定該項事業是否或應依何種方式委托私人辦理,并明確締約人須達到的標準。以公私合作方式運作的公用事業,應當具有公益性、長期性和可經營性,且風險可分擔。公共任務委托私人辦理,應保證“物有所值”,即與傳統政府投資模式相比,民間資本參與能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或者有效降低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特許經營應委托有關第三方機構進行可行性評估,評估內容主要包括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公共服務質量效率、經濟和社會效益、政府和特許經營者的風險分擔、政府付費項目財政承擔能力、用戶付費項目的公眾支付意愿和能力,以及市場主體的專業服務能力和參與意愿評估等。對于締約人的選定,在實體上,應綜合考量申請人提出的價格以及申請人的條件,包括專業技能、給付能力和可靠性;在程序上,應公開招標、開放競爭,貫徹公平無歧視、競爭和透明的原則,公開相關信息并保障所有參與者的地位平等。〔48〕許宗力:《論行政任務之民營化》,載《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82頁以下。應建立有外部專業人士參與的社會資本參與公用事業評審委員會,對參與者的資格和條件加以甄別和評審,選出最優申請人。
在第二階段,也即締約階段,應保證合同內容的公平合理,并建立公用事業切實履行的保障機制。公共部門與私人通過公私合作合同形成法律關系的目的是完成公用事業,這就要求合同應有效落實體現在法律中的政策目標,并形成一個確保公用事業切實履行的方案。具體而言,應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應明確私人提供公共服務數量、質量、時限等要求及績效監管標準,確定國家如何進行合法性與適當性的監督,包括進行檢查的權力,并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相關的信息。其次,應確保私人經營者能夠根據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持續地提供安全、方便、穩定和價格合理的公共服務。特許經營者應當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服務區域內所有用戶普遍地、無歧視地提供服務,不得對新增用戶實行差別待遇。再次,對于具有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基于衡平原則,應在合同中明確國家對私人經營者所提供服務的價格保持一定的影響力,且合同約定的期限不宜過長,同時約定對合同的定期更新機制。最后,應當為公用事業消費者或者公私合作合同關系的第三方,提供充分的表達和參與機會。在合同締結后,應公告合同的內容,以落實對第三人權益的保障和民主控制。
在第三階段,也即締約后的履行階段,行政機關應切實履行國家的擔保責任,有效規制與監督私人履行合同的行為。規制事項涉及價格規制、質量規制、普遍服務義務、公眾參與和知情權保障四個方面。〔49〕參見宋華琳:《公用事業特許與政府規制——中國水務民營化實踐的初步觀察》,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具體到質量規制和普遍服務義務的履行,行政機關應利用檢查、處理投訴等方式監督經營者,并可要求經營者提供相關信息。在經營存在瑕疵時,有關機關可運用限期改善、調整條款、終止合同乃至接管收回等手段,維護公眾利益。特許經營協議發生變更或者終止時,有關機關應采取有效措施,保證相應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持續性和穩定性。〔50〕對于公用事業特許合同中退出機制的研究,可參見宋華琳:《市政公用事業特許契約中的退出規制》,載余凌云主編:《全球時代下的行政契約》,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頁以下。
五、結語
自20世紀80年代始,我國嘗試在公共任務的履行中引入的公私合作模式,至今方興未艾。公私合作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公私合作的發展,反映著人們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理性反思、對私人部門獨特優勢的充分肯定、對公共部門有限能力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國家形態和責任的全新理解。
盡管合同對于公私合作的順利開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它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加以規范和約束,也許不僅無從發揮其功能和價值,反而會增加政治、社會和經濟風險。目前來看,我國公私合作合同法制仍很不完備,在公私合作合同相對人的選擇、合同內容的擬定、合同的履行和監督等方面均缺乏規范,導致良性競爭難以形成,對消費者權益保障不周,國家的擔保責任未能落實。從水電輪番漲價、高速公路超期收費、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危機等頻現報端的新聞當中,足可見人們對公私合作之空間和限度的疑慮,對公私合作蛻化為“公私合謀”的擔憂,對“公法遁入私法”之可能性的警惕,以及對公共任務的主體、內容和責任的思考。在行政法學的視野中研讀公私合作合同,本文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毋寧說僅提出了一些問題。可以期待,未來在實踐的推動和學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合作合同法乃至合作行政法的研究將逐步得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