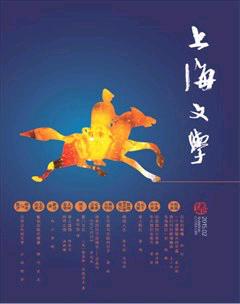花園洋房好讀書
鄭健
關(guān)于徐元章和上海寶慶路3號(hào),比較集中的報(bào)道是在懷舊風(fēng)很盛的本世紀(jì)初,當(dāng)時(shí)這幢著名的法租界花園老洋房常組織舞會(huì),名流薈萃,讓懷舊小資的媒體人眼熱。再次成為話題是七年前,寶慶路3號(hào)被拍賣,據(jù)說拍賣所得的一點(diǎn)八億元被屋主也就是徐元章外公周宗良的一百多位繼承人分走,徐元章不但一分未得,還必須遷出他住了五十多年的祖屋,搬到田林小區(qū)僅五十五平方米的安置房里去。
2014年12月3日,徐元章先生仙逝。一時(shí)間,有關(guān)這位命運(yùn)多舛的滬上“老克勒”和寶慶路3號(hào)這一幢神秘兮兮的花園洋房,再一次成為熱門話題。

一晃七八年過去,他竟然遠(yuǎn)行了。我還是寫一寫徐元章和寶慶路3號(hào)吧,再不寫,有些細(xì)節(jié)將永遠(yuǎn)湮沒于無形。
七八年前,我在MSN上開了博客,那時(shí)我也曾經(jīng)想來寫一寫寶慶路3號(hào),為此還做了不少案頭工作。都知道徐元章先生為人謙和,但骨子里,他真正瞧得上的人還真不多。
由于很特殊的原因,幾乎所有關(guān)于寶慶路3號(hào)的報(bào)道我都看過。恕我直言,其中只有程乃珊的文章算是基本準(zhǔn)足,這大概是徐元章比較接受程乃珊的緣故。同為滬上“顏料大王”,程乃珊丈夫的外公吳同文以及他在銅仁路上的“綠屋”,應(yīng)該不比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和寶慶路3號(hào)遜色。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我妹妹的短信:“趕快打開電視,徐元章上了《心靈花園》。”我內(nèi)心的感覺,一下子就不好了。我理解徐元章,他多半是為了影響輿論,讓這幢百年花園洋房有個(gè)好的歸宿,不惜拋頭露面,到那樣的平臺(tái)去游說。
但我還是很生氣。當(dāng)然,我沒有權(quán)利也沒有資格指點(diǎn)他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我是生我自己的氣,他去了《心靈花園》,將來我再回憶起他來的時(shí)候,從小到大,他在我腦子里的形象就變了呀。
第一次踏進(jìn)寶慶路3號(hào)是1958年,那年我才六歲。我踏進(jìn)的不是它的正屋和大草坪,是將近五千平方米的大花園的西北角,也就是圖中最靠左邊的那扇小門,再過去就是變電間。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這個(gè)西北角是他家的輔屋,一個(gè)一層的花房(或稱暖房、溫室),一個(gè)兩層的儲(chǔ)藏室(圖中建筑物即是,但那時(shí)是有百葉窗的),還有一排兩間平房,估計(jì)以前是下人住的。
一條斜斜的竹廊把這些輔屋以及一個(gè)小花園與園中其他建筑隔開,但竹廊的鏤空圍欄僅一米高,中間還開有矮門。若要穿過去,也是不費(fèi)吹灰之力的。
我之所以那么熟悉,是因?yàn)檫@幾間輔屋和小花園就是我的小學(xué),我在那里待了整整六年。那間只是一面有窗的花房是我的教室,那個(gè)儲(chǔ)藏室的底樓是另一個(gè)教室,樓上堆滿了雜物,現(xiàn)在想來,大概是從這幾間輔屋里清理出來的似乎還舍不得就扔掉的物品吧。
兩間下房就是辦公室,里面有三四個(gè)老師,一個(gè)語文老師和一個(gè)數(shù)學(xué)老師還兼班主任,都是大花園隔壁弄堂里讀過幾年書的居民。另一個(gè)數(shù)學(xué)老師是一個(gè)二十剛出頭的失業(yè)青年,和我同姓,算我本家。就是他,在四年級(jí)的時(shí)候,帶著我戰(zhàn)勝了所有公辦學(xué)校的參賽選手,成為了徐匯區(qū)的少年速算冠軍。音樂老師、繪畫老師和體育老師都沒有專門的辦公桌,他們只是上課的時(shí)候來,還有一個(gè)校工。那個(gè)音樂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因?yàn)樗贻p又漂亮,燙頭發(fā),穿旗袍,還涂口紅,走起路來裊裊婷婷,彈風(fēng)琴和唱歌都特別的嗲。
多年后,家母告訴我,幾乎所有民辦小學(xué)的音樂老師都是附近富人家的子女,民國年代家里請得起私人教師教鋼琴,結(jié)了婚便安心相夫教子,閑來無事,便到民辦小學(xué)來兼兼課。這個(gè)當(dāng)年只招了兩個(gè)班級(jí)的小學(xué)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市徐匯區(qū)新樂民辦中心小學(xué)二分校,離我家一百米還不到。
1950年代初,政府鼓勵(lì)“光榮媽媽”,即鼓勵(lì)多生育,算是對多年戰(zhàn)爭后人口銳減的補(bǔ)償。這一政策很快形成了一波生育高潮,我們這一代同齡人里,兄弟姐妹平均就有四五個(gè),弄堂里小六子小七子小九妹比比皆是。
盡管民國時(shí)期的上海有全國最充裕的教育資源,但還是不敷使用,1958年,當(dāng)局想出了一個(gè)“雞毛飛上天”的計(jì)劃,就是利用民間資源,大辦民辦小學(xué),解決“就學(xué)難”的問題。

所謂“雞毛飛上天”,就是把進(jìn)公立小學(xué)的孩子比作泰山,而把像我這樣進(jìn)民辦小學(xué)的孩子比作雞毛,但民辦小學(xué)也可以讓孩子成才,像雞毛一樣飛上天去,比如速算冠軍什么的。
民辦小學(xué)又稱“弄堂小學(xué)”,因?yàn)樾I岽蠖嗍桥美锎髴羧思易尦鰜淼摹N覀兊囊环中>驮诨春4髽呛竺妫淌液孟袷窃瓉淼幕ǚ浚挥幸粋€(gè)班級(jí)。總校則在華亭路的一處花園洋房,有三個(gè)班級(jí)及校長室、教導(dǎo)處。那里至今還是一個(gè)幼兒園。
1957年,徐元章的母親已去香港奔喪,估計(jì)寶慶路3號(hào)的這些輔屋是他父親同意讓出的,其間是否遭遇動(dòng)員、脅迫,已不得而知,但這件事徐家從未談起過。十年后,我告訴徐元章,我的小學(xué)就是在你家后院讀的,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哦,是嗎?”
其實(shí),徐元章是1951年他七歲的時(shí)候才跟父母一起住進(jìn)這座花園洋房的。早年她母親不顧家庭反對,毅然出走嫁給自己的家庭教師,幾乎是斷了六親的。1940年代末,周宗良舉家移居香港時(shí),既沒有帶走這個(gè)任性的女兒,連花園洋房也寧可空關(guān)而不給她住。后來,據(jù)說是女兒寫信求父親,與其空關(guān),不如由她幫著看屋吧。在征得周宗良的同意之后,一家數(shù)口才非常低調(diào)地入住了寶慶路3號(hào)。
六年后,周宗良在香港去世,徐元章母親去奔喪后再也沒回來過,只聽說她在法國成了一位小有名氣的畫家。這很可能是徐元章沒有這座花園洋房繼承權(quán)的原因。外公從未說過她母親可以繼承,她母親更是一句也未向徐元章提及過這房子的歸屬,最后失去了聯(lián)系。
小學(xué)天地雖小,卻也趣味十足,有假山和小池塘,花房前面有一塊水泥地,我們每天做體操玩游戲都在那里。還記得我們經(jīng)常玩的那個(gè)游戲叫“香蕉蘋果馬鈴鐺”。據(jù)說這是民國時(shí)滬上外國小朋友的游戲:兩個(gè)小孩拉手撐起如門,其他孩子魚貫穿過,一邊鉆,一邊嘴里還要唱,音樂停止,做“門”的孩子的手就會(huì)突然放下,誰正好被扣住就算輸,下一輪去做“門”,贏的孩子則加入邊鉆邊唱的隊(duì)伍。那音樂的調(diào)如“56 54│34 5│23 4│34 5│56 54│34 5│2 5│31 1?襓”。一直不明白香蕉、蘋果和馬鈴鐺這三樣?xùn)|西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后來學(xué)英文,才知道原歌詞應(yīng)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my fair lady!”(倫敦橋?qū)⒁顾玻腋哔F的淑女!)這才叫“神一樣的翻譯”呢。
印象最深的是北墻那邊,當(dāng)年是徐匯公安分局,再早則是法租界巡捕局,它的看守所正對著我們的操場,每天下午我們可以看到犯人放風(fēng)的情景。
一進(jìn)學(xué)校,老師就反復(fù)告誡我們,千萬不要穿過那條竹廊,隨便打擾人家的生活。男孩子總有好奇心,有時(shí)候下午老師早離校,我們就趁校工不備,穿過竹廊去探個(gè)究竟。現(xiàn)在還能想起來的是,也許在孩子的眼睛里,這花園實(shí)在太大了,每次都不敢太深入就跑回來了,連主人居住的屋子都沒正眼瞧過一回。
寶慶路3號(hào)的東面連著“上方花園”的第四條橫弄堂,俗稱“煤屑路”,其他橫弄堂都鋪了水泥。“煤屑路”比較寬,我們男孩子放了學(xué)就經(jīng)常在那里玩。路盡頭的那段籬笆里,就是寶慶路3號(hào)花園,趴在籬笆上往里看,可以看到一排兩層樓的平房,灰不溜秋的。后來才知道,周宗良當(dāng)年很喜歡德國人的做派,像電影《音樂之聲》里的那位奧地利上校一樣,對自己的孩子實(shí)行軍事化管理,便特意修了這排兵營式的兒女宿舍。
知道此處可以通寶慶路,弄堂里的男孩子當(dāng)然不會(huì)放過,很快竹籬笆就有了個(gè)洞,我也鉆進(jìn)去過,因?yàn)樗麄冋f可以直通學(xué)校操場。但每次都是偷偷摸摸,還是一次也沒看清過正屋等建筑,園中樹木密匝當(dāng)然是另一個(gè)原因了。
我們只知道,這個(gè)大花園里沒住幾個(gè)人。經(jīng)常能夠看到的是,放學(xué)時(shí)分,女仆模樣的人牽著一個(gè)大孩子的手從大門進(jìn)來,穿過竹廊,往花園深處走去。那大概就是徐元章了。但他從來不朝這邊看,因?yàn)槟菈K地方不再屬于他們家。
直到1967年,我才第一次從大門進(jìn)入寶慶路3號(hào),在徐元章的陪同下,穿過竹廊,往花園深處走去。那時(shí)候,徐元章成了我大哥的同事,他們同在里弄加工組上班。
我大哥因?yàn)樯眢w原因從上海中學(xué)退學(xué),一直待在家里;徐元章則是因?yàn)樽x到初二不想讀了而退學(xué)在家。“文革”年代,坐在家里吃閑飯是可恥的,人人都要參加勞動(dòng),于是他倆都被動(dòng)員去了里弄加工組,干一天給七毛錢。
我因?yàn)槭恰板羞b派”,哪派也不參加,哪派也不幫,便不大去學(xué)校。因從小與大哥走得近,百無聊賴中,便跟著他去上班。里弄加工組也沒啥制度,給個(gè)小板凳坐在一旁。

加工組在新樂路52號(hào),對面就是襄陽公園,斜對面就是著名的東正教教堂。這是一幢聯(lián)體花園洋房,雖然花園小些,也有三四十平米。主人可能在“文革”初期被掃地出門了,空房子就用來做加工組。這個(gè)加工組開始是繞線圈做“方棚”(滬語:“鎮(zhèn)流器”)的,后來很快就改做玩具了。至少我去的時(shí)候已經(jīng)不繞線圈了,但名稱一直沒變,叫“新樂線圈組”,所以很多寫徐元章的記者都以為他一直在繞線圈。
加工的玩具叫“六面畫”,一個(gè)正方體的積木,六面都貼上彩紙圖案,九塊積木翻來翻去可以拼出不同的圖案,類似后來的魔方。
徐元章真是一個(gè)大少爺,連這樣剪剪貼貼的簡單活也不會(huì)干,他做出來的玩具幾乎都是次品。他也毫無時(shí)間概念,幾乎每天“困失寣”(滬語:“遲到”)。但他的人緣真的很不錯(cuò),加工組的阿姨媽媽們不但不批評(píng)他,反過來還去幫助他,一開始幫他返工,后來幾乎把他的活全包下來了。他遲到來不及吃早飯,她們還幫他到襄陽北路的大餅攤?cè)ベI大餅油條。當(dāng)然,這大餅油條也不能白吃。吃了大餅油條,他上班的唯一任務(wù)就變成了講故事。他從小博覽群書,口才也不錯(cuò),記性也好,他看過的小說,尤其他喜歡的,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
后來我有機(jī)會(huì)見識(shí)了他家的書架,必須承認(rèn),這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量的私人藏書。而且每本書都包了封皮,都蓋上了自家的藏書章。
他的故事不但阿姨媽媽們愛聽,我大哥等一些同齡人也愛聽,我也哪兒都不去玩了,每天跟著我大哥上班聽故事。很快,加工組的小青年里,我大哥,還有一對程氏姐弟和徐元章成了比較要好的一群人,大家聽了故事不算,還纏著問他借書。
他借書很謹(jǐn)慎,而且諸多關(guān)照,比如只能攤開看,不能卷,不能折角,哪怕用電車票來當(dāng)書簽,當(dāng)然更不能在書頁上畫畫寫寫了。
那些書是絕對不敢?guī)У郊庸そM來的,他擔(dān)心覺悟高的阿姨媽媽會(huì)揭發(fā)。于是十四五歲的我就有事做了,做通信員,大家輪流看,都由我居中流轉(zhuǎn),每個(gè)人手里最多停留兩天,大家都靠熬通宵趕著看完。因?yàn)樗麄兪谴笕耍沂切『ⅲ杂械臅乙灿幸粌商炱谙蓿瑏聿患熬桶盐业臅r(shí)間縮短甚至卡掉,有些書我只能見縫插針地翻翻。
送書還書大多在晚間進(jìn)行,書也從不拿在手里,怕被巡邏的工人糾察隊(duì)發(fā)現(xiàn)。都是用報(bào)紙包好后,插在前褲腰或后褲腰,再用上衣遮住。有可疑的人靠近,立即撒腿狂奔。
一開始還書,我只是說好時(shí)間在寶慶路3號(hào)大門外等,徐元章按時(shí)出來,見四周無人,便迅速交接,儼然地下黨做派。
其他書我沒看成,我似乎也不甚懊惱,但那部上中下三冊的狄更斯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因?yàn)閷?shí)在太好看了,大家看了還要議論,弄得我心癢癢的,很不好受。我便鼓起勇氣在還書時(shí)私下央求徐元章寬限些時(shí)間。他很認(rèn)真地想了想說,“算了吧,就算我再給你幾天,你看完了,哪怕多出半天,你也會(huì)借給你同學(xué)的,而我又不好意思老是催,這樣的話,這書就得再在外面兜一圈,弄不好就回不來了,我不放心。但是既然你這么想看,我決定成全你。這樣吧,你到我家來看。”
那段時(shí)間,他正逢微恙在身,請著病假呢。他便叫我每天下午兩點(diǎn)鐘等他睡好午覺再來。于是,就有了我按門鈴,他領(lǐng)我穿過竹廊走向花園深處的一幕。
但我還是沒有機(jī)會(huì)見到正屋。他帶我來到一個(gè)小房間,里面只有一對沙發(fā),長長的百葉窗下有個(gè)圓桌,墻根墻角堆著些雜物。他把書從別的屋拿來,交給我,說:“你就坐在沙發(fā)上看,我在窗口畫畫。”
于是,他開始臨摹他的靜物,我開始看我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漸漸地,太陽光斜過去了,沙發(fā)放得太靠里面,坐在那里光線太暗,我就干脆坐在沙發(fā)前的地毯上看。
多少年后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gè)又一個(gè)長長的好日子。夢幻般的下午,陽光懶懶地透過百葉窗照進(jìn)來,卻不帶進(jìn)一絲外面的腥味,畢竟,這是“一月革命”后風(fēng)雨飄搖的1967年啊。
我們幾乎不交談,靜得像在另一個(gè)世界里。
直到夕陽西下,再也看不清書上的字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夾上帶來的電車票,把書恭恭敬敬地還到他手里,再沿竹廊走出去,回家,心里總是充滿莫名的惆悵。
有時(shí)候,他會(huì)問,“小愛米雷見到了她的舅舅嗎?”“大衛(wèi)的姑媽還沒出現(xiàn)啊?”后來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錯(cuò)過任何一段精彩的篇章,未到時(shí)忍不住要提醒我一聲,等過了以后又熱烈地向我談?wù)撃切┚省_@樣的導(dǎo)讀真是讓我終生受益。
也許是看我孺子可教吧,我后來在他家的那個(gè)小屋子里不但讀完了三卷本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還讀到了十多本其他世界名著。
徐元章也終于放心地把我?guī)У搅苏荩褪呛髞眍l頻舉行舞會(huì)的那個(gè)面朝大草坪的客廳。其實(shí)家具很簡單,而且都是他外公離開大陸時(shí)留下的,但一看就讓人覺得整潔、氣派。
我當(dāng)年最關(guān)心的就是那幾架書,整整齊齊地?cái)[在那里,像是幾十年沒被翻亂過。我曾經(jīng)為此問過我大哥,覆巢無完卵,何以經(jīng)歷了1966年夏天的狂風(fēng)暴雨,他家的書能保存下來呢?大哥說,徐元章的父親(作家徐興業(yè),長篇小說《金甌缺》曾獲第三屆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當(dāng)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巧在他既是黨員,又非當(dāng)權(quán)派,人緣又好,住的又是丈人家,造反派也許師出無名。
寶慶路3號(hào)就這樣躲過了看似完全躲不過的一劫,也許它是上海在“文革”中唯一沒有被查抄過的花園洋房。
那天,徐元章的興致似乎很高,他打開落地窗,帶我走出正屋,沿著籬笆在這個(gè)大花園里散了一圈步,談的當(dāng)然還是小說里的精彩。花園里也很簡樸,好像不記得有什么名貴樹木,只是一些冬青、黃楊、無花果、夾竹桃等等。
就是那天,我告訴他,我在他家后院上了六年小學(xué)。我還告訴他,東邊籬笆上的洞是我們弄堂里的小伙伴們扒開來的。他突然攥住我的胳膊,瞪著眼說:“原來就是你這個(gè)‘野蠻小鬼啊!”接著就哈哈大笑起來。盡管如此,還是嚇得我不輕。
我一直很困惑,徐家放著那么漂亮的正屋不住,卻老是住在那幾間小屋里。后來有人告訴我,一開始是因?yàn)橐钥次莸拿x入住,也許是怕周宗良留在上海的親戚來“賊差”(滬語:“突擊檢查”),所以不敢貿(mào)然放肆。這個(gè)說法是真是假,已無法稽考。再后來“文革”來了,徐家又要自覺地表現(xiàn)得艱苦樸素一些,雖然未抄家,群眾監(jiān)督還是真實(shí)存在過的。
所以,徐元章在這座花園洋房里真正有了些主人的感覺,可以大辦舞會(huì),頻繁社交,恣肆風(fēng)流,還是在本世紀(jì)初。而在當(dāng)年,徐元章幾乎不參加任何集體活動(dòng)。
我的老相冊里,有很多我大哥的照片,讓我想起當(dāng)年我們經(jīng)常一起去游園,去拍照,也經(jīng)常一起去淮海路吃小吃,但就是找不到一張有徐元章的合影。再仔細(xì)回想,那些活動(dòng),他確實(shí)幾乎都沒有參加。他是那種嚴(yán)格執(zhí)行“keep your distance”的英國規(guī)矩的紳士作派,永遠(yuǎn)群而不黨。
我還記得他為不想和大家一起拍照而找出的一條理由,他說他長得不漂亮,就不要嚇人了。他細(xì)眼尖鼻薄唇,確實(shí)很獨(dú)特。當(dāng)年我們都開玩笑說他像林彪,后來林彪摔死了,我們又說,林彪就是因?yàn)檠劬μ螅茐牧宋骞俚暮椭C而死于非命,而他五官皆細(xì),應(yīng)是大福之相。
徐元章就是這點(diǎn)好,拿他開玩笑,從來不生氣,永遠(yuǎn)只是笑笑。從認(rèn)識(shí)起,大家相互之間都直呼其名,只有他們叫我的小名健健,因?yàn)槲冶人麄冃×邭q。由于我們都極其喜歡那部《大衛(wèi)·科波菲爾》,我們還給他起過一個(gè)綽號(hào),就是書中八面玲瓏的管家李德默先生。他不但不生氣,還補(bǔ)充說,“什么李德默,應(yīng)該是徐德默。”
我們大家說他大福之相,其實(shí)也是有所指的。
那幾年,他正在熱戀中,他結(jié)婚那年,正是“九一三事件”發(fā)生那年。關(guān)于他妻子的情況,都是他自己親口告訴我們的,比如有四分之一日爾曼血統(tǒng)啦,比如漂亮的獅子鼻啦,又比如是跟她學(xué)畫的學(xué)生啦,再比如為什么名字叫“亨義”,其實(shí)是英文“honey”的音譯。這音譯也真是譯得古樸大氣,擱現(xiàn)在,準(zhǔn)是“哈妮”什么的。
在我們面前,他稱她為“阿拉h(huán)oney”。一口一個(gè)“阿拉h(huán)oney講的”,“阿拉h(huán)oney不會(huì)的”,加工組的阿姨媽媽們幾乎要被肉麻得昏過去了。
我終于有機(jī)會(huì)見到過兩三回“阿拉h(huán)oney”。我們兩家相隔不到一百米,因此從加工組下班,徐元章和我及我大哥是同路。我們總是一起從襄陽路轉(zhuǎn)淮海路朝西,有時(shí)“阿拉h(huán)oney”就會(huì)從華亭路斜刺里走出來,然后跟他一起回寶慶路3號(hào)。見了我們便大方地打一聲招呼,然后分道揚(yáng)鑣。我必須說,“阿拉h(huán)oney”是真漂亮,身材也惹火。無需多筆墨,想像一下香港歌星甄妮吧,區(qū)別是“阿拉h(huán)oney”的臉更圓些。
加工組的小伙伴們以及阿姨媽媽自然要他不斷地交代“戀愛過程”,他也從不拒絕,用阿姨媽媽們的話來說,徐元章是出了名的“皮厚”。但我聽得出,他多數(shù)時(shí)候是在當(dāng)場胡編,比如什么第一次“香面孔”(滬語:“接吻”)啦。
當(dāng)然有時(shí)候也有真話。
有個(gè)禮拜一,徐元章又被問到:“昨日休息,你們兩個(gè)人在一道做點(diǎn)啥啦?”“真的沒做啥呀,”徐元章不勝委屈,“早上么睡懶覺,吃好中飯,拿本書,坐在草地上,我一句一句讀給她聽。”
阿姨媽媽們哄笑起來,都說他倆有“神經(jīng)病”。
“哪能不帶她出去蕩蕩馬路啦?”
“哪能不請她去吃吃生煎饅頭牛肉湯啦?你怎么這么‘刮皮,像只‘鐵公雞喏。”
“電影么總歸要看一場的呀,電影院里黑洞洞,一開場么你們又好‘香面孔 ?。”
“哈哈哈哈——”
但我和幾位他的同齡人聽得無比艷羨,我甚至當(dāng)即暗暗發(fā)誓,今生今世一定要談一回“花園讀書”這樣的戀愛。
那一年,我十八歲,徐元章他們也不過二十五六歲。
可惜好花不常開。
認(rèn)得徐元章兩年后我去外地插隊(duì),再三年我大哥病故,程氏姐弟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于是,我回滬探親,也只是與程氏姐弟見幾面聊聊天,間接聽到一些關(guān)于徐元章的消息,比如他生了一個(gè)女兒,像她媽媽,如此而已。
我最后一次見到徐元章也已經(jīng)是三十年前的事了。1984年,我考進(jìn)電臺(tái)當(dāng)新聞?dòng)浾摺.?dāng)時(shí)我們新聞部和文藝部都在北京東路2號(hào)的三樓。有一次我去找文藝部的同事聊天,沒想到徐元章正好也在那間辦公室。后來我知道,他與《立體聲之友》節(jié)目有聯(lián)系,經(jīng)常給節(jié)目組推薦一些外國最新的曲目和卡帶之類的。
我當(dāng)然要跟他打招呼的了。
“哎,這不是徐元章嘛,你怎么也到電臺(tái)來了。”
沒想到他很矜持,只是欠了欠身,說了聲,“哎,你好呀。”
我看得出他眼睛里的意思是別張揚(yáng)我們之間的關(guān)系。當(dāng)年我跟他那么熟,我當(dāng)然是不會(huì)看錯(cuò)的。于是我就很識(shí)相地借故走開了。
大家都稱徐元章為畫家,在我看來,他更像一個(gè)文學(xué)鑒賞家和音樂鑒賞家。他對文學(xué)和音樂的感覺和看法都是一流的。至于繪畫,這是他從小習(xí)得并終生練習(xí)的。在我的記憶里,他的繪畫才藝好像只出過一次風(fēng)頭。那好像是1967年初吧,那時(shí)的淮海中路汾陽路口,有三四塊寬四五米高十來米的特大廣告牌。音樂學(xué)院圍墻外有一塊,面朝東北;教育學(xué)院的墻外好像有三塊,面朝西北,它們的對面就是那家著名的意大利餐館天鵝閣。
“文革”來了,廣告牌上當(dāng)然要畫宣傳畫,時(shí)稱“紅海洋”,而且必須是領(lǐng)袖畫像。為此,當(dāng)年徐匯區(qū)會(huì)畫畫的幾乎都被找來挑選,哈定來了,認(rèn)得出哈定是因?yàn)楣ǖ漠嬍耶?dāng)年就開在我們中學(xué)的圍墻外,幾乎每天放學(xué)都會(huì)經(jīng)過。徐元章也被挑中,他負(fù)責(zé)畫音樂學(xué)院墻外的那塊,是個(gè)著名的“八一八”側(cè)面招手像。我記得我還在長長的竹梯下為他遞過顏料板等家什呢。
前些年,陳丹青的哪本書里好像也提到過這件事,他說他和陳逸飛都參加了當(dāng)年汾陽路口的作畫。但當(dāng)時(shí)我只認(rèn)得哈定和徐元章。我至今還記得的一個(gè)細(xì)節(jié)是,在畫快要完工的時(shí)候,他對我說:“這顴骨上的一點(diǎn)是最后一筆,也最難,因?yàn)樗侨嬜盍恋牡胤剑瑤缀跻冒咨伭稀5c(diǎn)在哪里要精準(zhǔn),如果是在地面上,我一定會(huì)得站在離畫一米多的地方,端詳良久,然后‘啪一記點(diǎn)上去。可惜這里太高了,竹梯子離畫面又那么近,站在梯子上眼睛離畫只有一尺多,只好憑感覺了。”
當(dāng)年圈內(nèi)是怎么評(píng)價(jià)這幾幅畫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當(dāng)年汾陽路口作畫也算是個(gè)大事件,每天都有很多人圍觀。三四個(gè)人同時(shí)作畫,也確實(shí)有當(dāng)場比拚的氣氛和味道。
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他對文學(xué)和音樂的感覺比對繪畫的感覺還要好。我大哥告訴過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們幾個(gè)一起偷偷地聽老唱片,好像是貝多芬的交響樂。放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yùn)》的時(shí)候,只見徐元章突然站了起來,跟音樂一起律動(dòng),并對他們說:“你們哪能坐得住的啦,聽這種音樂么要站著聽的呀。”眾人愧甚。改革開放了,他來電臺(tái)為音樂節(jié)目幫忙,我覺得是綽綽有余的。
因此,我們在北京路大樓里好像又見到過幾回,相互就點(diǎn)點(diǎn)頭。我了解他的苦衷,他多少有點(diǎn)擔(dān)心我的口風(fēng)不夠緊,我畢竟知道他太多。其實(shí),直到今天之前,我都沒怎么說起過他。
本世紀(jì)初,懷舊風(fēng)最甚,因而寶慶路3號(hào)也貌似最紅火的時(shí)候,我也沒講什么。我只是對少數(shù)摯友提起過,徐元章無論如何算個(gè)人物。寫寫他拍拍他對你們自己有好處。而且,徐元章畢竟是有恩于我的,他教會(huì)我讀書,我會(huì)一直記得他,但我再也不會(huì)去打擾他了。
我一直希望他的日子能過得好,尤其是聽說“阿拉h(huán)oney”帶著女兒去了美國之后。
背地里默默關(guān)注著徐元章和那座花園洋房的人很多。我妹妹其實(shí)跟他沒有過任何交集,只是當(dāng)年聽我和大哥老是說起他,竟也一直關(guān)注著他。前不久,我又接到她的短信:“徐元章走了。”
現(xiàn)在大家都說徐元章是上海灘上的“老克勒”。我想,徐元章內(nèi)心深處恐怕是不會(huì)認(rèn)同的,我也覺得他還不能算是。他們這一代,目睹了上海灘大戶人家被逐步地趕盡滅絕,上流社會(huì)的垮塌,貴族氣息的消亡,徐元章心里是很清楚的,早在他認(rèn)識(shí)我之前,上海的“老克勒”已經(jīng)日薄西山,復(fù)興無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