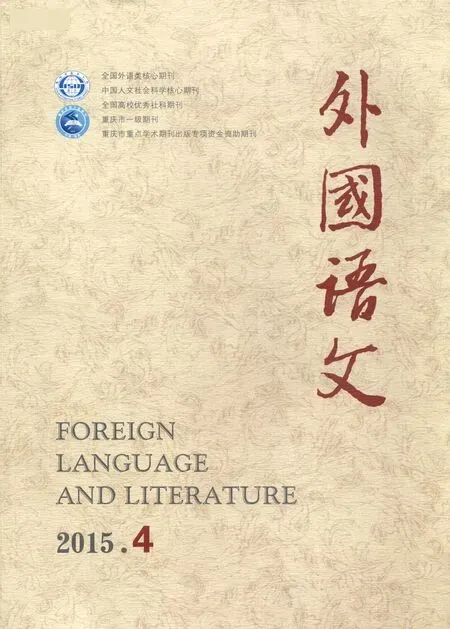論后殖民文學中的“跨國轉向”
王麗亞
(北京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北京 100089)
1.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英美文化研究領域有關“跨國”(transnational)或“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討論持續影響后殖民文學作品研究。以“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為議題,當代后殖民文學研究聚焦英語移民文學作品(以小說為主)中的跨國、跨文化主題,反思前期后殖民文學研究以“逆寫帝國”為模式的闡釋方法。據此認為這一轉向意味著有關民族/國家身份的文學主題已淡出批評視野。
本文提出,當代英語移民文學的“跨國”現象主要涉及作家身份以及通過故事內容展現的移民生活,影響并挑戰先前文學闡釋中的殖民/反殖民二元對立模式,但是,以文學主題顯現的這一“轉向”并不表示“跨國主義”替代“逆寫帝國”,更不意味著當代后殖民文學批評已經告別以“差異”為策略的知識與權力話語批判。文章認為,移民文學中的跨國現象既包含歷史范疇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又包含作為寫作和閱讀立場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前者指作家創作主體層面的跨國跨文化身份,以及以移民群體為描寫對象的跨文化體驗;后者指作品通過敘述移民之歸依感所表述的歷史反思,箭指后殖民與殖民歷史之間的延續性。
文章將以杰伊(Paul Jay)提出的“跨國轉向”和阿什克洛夫特(Ashcroft et al)的“逆寫帝國”為兩個基本閱讀模式,梳理、辨析兩個閱讀模式之間的差異與相交點,揭示移民文學中的“跨國”現象實為學界所指的“跨國后殖民”文學。
2.跨國轉向
在《全球事務:文學研究中的跨國轉向》(Jay,2010:4-11)一書中,保羅·杰伊提出,自20世紀70年代,文學與文化研究開始淡化有關國別身份問題的討論,轉向全球化條件下的跨國現象;至90年代,這一態勢成為文學研究熱點,集中體現在英國移民小說對跨國主題的書寫,在后殖民文學研究領域形成了“跨國轉向”。作者提出,就創作領域而言,這一主題轉向源于經濟和文化全球化,通過移民文學進入文學領域,以多樣化文學敘事手法表現文化多元主義,繼而滲入邊界研究、離散文化研究等,極大地拓展了英語文學中的全球化維度,改變當代后殖民文學走向。據此,杰伊認為,以“跨國”為核心主題的當代后殖民文學不同于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后殖民”文學,因此,在闡述這類作品時,原先的后殖民立場就會導致闡釋困難。
需要指出,以“跨國”主題為標識,將移民文學及其闡釋挪出高度政治化的“后殖民”文學批評,繼而探究新的閱讀與批評方法,這一認識在新世紀的文學史著作中已有所顯現。2004年,牛津大學出版了13卷本《牛津英國文學史》。其中的第13卷名為《英語文學的國際化》,該卷主編布魯斯·金(Bruce King)專辟一章,以“英國新英語文學”為題,詳述20世紀最后10年英國移民作家在文壇的主導地位。他特別提到,自1983年戈爾丁(Wiliam Golding)獲得文學獎項以后,英國國內重大文學獎項都被移民作家包攬;金認為獎項本身可能不足以證明英國文學界發生了巨變,不過,作為“文學場”運作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一事實至少說明英國文學原先的“英國性”已經風光不再。回望這一態勢的歷史進程,金認為,這一變化與戰后大量涌入英國的移民密切相關。的確,1956年當“帝國風馳號”(Empire Windrush)滿載來自加勒比地區的英國移民抵達英國蒂爾伯雷海岸時,英國文學國際化的種子悄然落地。此后劇增的移民人口與不斷產生的移民作家為英國文學增添了主題與風格的多樣化。至80、90年代,出自移民作家的文學作品成為英國文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King,2004:1-11)。毫無疑問,顯然,金把移民作家身份的“跨國性”視為英語文學國際化的標識,并將這一變化看作與“英國衰落”形成對照的英語文學國際化。早在80年代,金就提出應該用“國際化”或“跨國主義”替代“后殖民”。在他看來,“后殖民文學”這一提法過于政治化,難以概括英國移民文學中的國際化“新維度”,也難以概述作品對不同民族文化共生狀態的敘述。(King,1980:x-xi)
無論是布魯斯·金對英語文學國際化的描述,還是杰伊從理論上對“國際轉向”的概述,兩者均代表了學界對當前英語文學多樣性的關注。透過文學國際化與全球化關系這面多棱鏡,杰伊用“跨國轉向”形容當下“英語文學國際化態勢”(globalizing literary study)(Jay,2010:9),并以此強調這一轉向對先前文學闡釋的挑戰。比較之下,金則側重于移民作家故事世界的“跨國”主題和形式層面的“雜糅”;至于主題演變和寫作風格多樣性問題,在他的描述中屬于“后殖民文學批評的延續與發展”,而不是與前期形成根本差異的新時期(Jay,2010:323)。可見,金的關注點在于作家身份跨國性對英國文學傳統“英國性”的沖擊,而杰伊則認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同步發生、互為影響,由此探究文學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的可能性。
與上述動態相對應,后殖民文學批評同樣關注“跨國”問題。專攻后殖民文學闡釋的學者吉康迪(Simon Gikandi)發文,認為文化全球化對后殖民文學及其批評產生了深刻影響,文學作品從主題到風格發生的變化已經遠遠超越以往后殖民文學批評對民族/國家身份的關注,因此,必須在文化全球化視閾下關注國際化主題,同時檢視以往批評模式(Gikandi,2001:627)。不過,這一提法并未得到熱烈相應。2008年,克里沙斯瓦密(Revathi Krishnaswamy)和哈利(John C.Hawley)推出論文集《后殖民與全球化》,從理論上探究“跨國”主題在殖民與后殖民以及全球化之間的交互關系,并將這一特征形容為身份政治老套話語從經濟與文化全球化時代汲取的思想活力。與此立場截然不同,薩義德(Edward Said)以“文學研究全球化”一文回應,批評這種認識過于樂觀。在他看來,全球化屬于資本主義經濟與文化的內在邏輯,老牌帝國在經濟領域的掠奪行徑和文化領域的霸權立場幾乎消解了非西方民族國家文化身份,這種帝國意識在當代西方國家并未減弱,而是憑借經濟與文化策略變得更加隱蔽而已;以全球化為障眼法,強調某種普遍的批評話語,只會導致后殖民文學與文化研究脫離歷史語境,而這恰恰是文化帝國主義在于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領域實施的一種策略(Said,2001:67)。由此,薩義德堅持認為,新世紀文學領域的“跨國”現象并不代表歷史的轉向或斷裂;相反,民族主義、身份、敘事,以及族裔文學,依然是移民文學跨國主題的研究重點(Said,2001:68)。
不難看出,上述圍繞“跨國”現象的討論與學者們對全球化的不同認識有關。將全球化視為始于16世紀、此后日益推進的一個歷史進程,以杰伊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經濟與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當代移民文學集中書寫的“跨國”主題則是這一力量的象征展現。用杰伊的話來說,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與由此產生的文化雜糅構成文化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移民文學作品對跨國和跨文化體驗的敘述正是這種態勢的反映(Jay,2010:3)。與此不同,立足于經濟范疇的全球化,薩義德認為正是通過經濟全球化,殖民意識與文化帝國主義以文化全球化消解民族文化與國家意識,文學、文化領域有關“跨國主義”的樂觀描述正好說明全球化條件下民族文化陷入的進一步危機(Said,2001:67)。以“跨國”主題作為一種新的文學表征,杰伊倡導后殖民文學批評走出舊有的“逆寫帝國”批評模式,關注全球化時代移民生活中的“接觸地帶”(Pratt 6)。將“跨國性”看作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以移民、跨國公司等方式實施的“新殖民主義”策略,薩義德堅守民族解放運動以來對經濟與文化領域“東方主義”采取的抵抗姿態。
就這一對峙局面與文學闡釋關系而言,這里涉及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看待當代移民文學作家身份跨國性與作品題旨的關系?在英語移民文學領域,作家身份的雙重性以及作品內容對移民生活的描寫是否意味著文學闡釋立場從根本上有別于“逆寫帝國”強調的抵抗姿態?
3.逆寫帝國
作為后殖民文學批評中的一個術語(也是一個流行語),“逆寫帝國”一詞最早出現于阿什克洛夫特等合著的《逆寫帝國》(1989)中。在該書中作者提出,聚焦于英聯邦英語文學,以殖民和被殖民作為一個對立關系,后殖民作家的寫作目的在于抵抗帝國文化;由于被剝奪了自己的語言或言說方式,后殖民作家只得以“棄用”(abroga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為兩個基本策略,“逆寫”帝國文化,采用修訂甚至顛覆殖民視角對被殖民民族文化予以展現(Ashcroft el.,1989:37-38)。所謂“棄用”是指對帝國文化各種樣式的拒絕,包括其美學、規范用法,而“挪用”則是把別人的語言拿過來加以改變,使之在與民族方言或土語融合后成為作者表達心聲的新語言(Ashcroft et al.,1989:38-39)。顯然,“逆寫帝國”強調的是一種根本對立于殖民文化的寫作立場;換言之,其寫作方法僅僅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Ibid,116)。
需要說明的是,“逆寫帝國”一語并非阿什克洛夫特首創。1982年,印度裔英國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一篇刊登于《泰晤士報》上的文章中提出,80年代英國文壇,尤其是在小說界,一批移民作家將帶有鮮明民族文化特色的神話、歷史用作創作素材,使得作品從語言到風格呈現一種富有活力的混搭特點;他將這種創作風格稱作“逆寫帝國”,形容它像一股強大的“離心力”沖擊著英國文學傳統,為英國文學注入新鮮活力(Rushdie,1982:8)。很明顯,拉什迪的“逆寫”主要指移民作家的創作風格,并將這種風格歸因于創作主體的雙重身份。比較之下,阿什克洛夫特的“逆寫”強調的是原殖民地作家通過寫作表述的文化象征和政治意義。例如,《逆寫帝國》作者提出,原殖民地作家,或有過殖民歷史的作家,其創作必然是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Ibid,38-39)。與創作層面凸顯的“本土”內容和“抵抗”姿態形成呼應,阿什克洛夫特認為,關于后殖民文學的闡釋也應關注從內容與形式表述兩方面對“中心”的抵抗(Ibid,115-116)。將注意力從敘事風格上的“逆寫”移至寫作和閱讀立場上的“抵抗”,“逆寫帝國”這一提法的寓意移位對后來評論家過度闡釋“逆寫帝國”的政治意義產生重要影響:甚至使他們將“逆寫帝國”視為政治抵抗的同義詞,同時,使得他們關注移民文學作品其他問題(Mukherjee,19906)。此外,《逆寫帝國》還因將殖民抵抗進行總體化描述遭到批評。例如,麥克克林托克(McClintock,1995:12)指出,阿什克洛夫特對抵抗的強調意味著把殖民歷史看作一個連續發生的歷史,又把其視為殖民國家的“共同過去”。
不可否認,阿什克洛夫特的“逆寫帝國”具有明顯的同一化傾向。不過,從思想淵源看,這一傾向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批評立場具有密切關系。
薩義德以“東方主義”這一總體化的批評視角為核心關注,揭示歐洲殖民統治下殖民國家對殖民地民族文化身份的他者化過程,即,帝國時期地理范疇的非西方民族及其文化被一切與展現有關的話語描述為一個低劣的他者,進而遭受文化控制,并服務于帝國以世界中心自居的統治地位(Said,1978:3)。關于這一觀點,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有過更為詳細的闡述。以19、20世紀歐洲小說作為觀察對象,薩義德以他著名的“對位閱讀法”(contrapuntal reading)對文本展現與歷史事實關系進行雙向解讀。在他看來,“小說與帝國主義互為構筑,互為強化……因此,閱讀小說,就意味著以某種方法認識帝國主義”(Said,1993:70-71)。因此,有關小說的研究應該關注與小說文本之間的“觀念和參照結構”(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揭示那些被文本排除在外的某些歷史事實(Said,1993:76)。就19世紀英國小說情況而言,薩義德指出,小說常常最大限度地將殖民歷史置于文本和故事之外,將殖民地虛化為帝國邊緣“想象的地理”,由此誘導讀者以理所當然的態度接受小說家對帝國及其霸權文化的描寫與解釋(Said,1993:70)。為了揭示文本背后的事實以及敘事方式隱含的帝國意識,薩義德認為,對于帝國文化文本的閱讀必然是抵抗性的。
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到阿什克洛夫特的“逆寫帝國”,圍繞后殖民文學闡釋立場的理論思考持續關注作家和評論家的“抵抗”姿態,并且將不同國家的英語移民文學視為一個對立于“中心”的統一體(McClintock,1992:87)。隱含在這一認識背后的邏輯十分簡單:殖民文學都是維護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學話語,而一切后殖民文學均有顛覆力量(Gandhi,1998:154)。從這個角度看,提出“跨國轉向”有利于突破文學闡釋活動的簡單化傾向。與“抵抗”姿態形成差異,研究者質疑抵抗模式中的二元對立思維,揭示后殖民文學包含的雜糅性,充分關注移民文學作家身份混雜性以及作品關于離散裔身份多樣性、跨文化體驗(Jacobs,1996:13)。
依照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觀點,當代移民文學顯然不同于60-70年代的后殖民文學,其中一個明顯的差異表現在移民文學作品關于地理空間的心理描述。以英國文學為例,80年代以后的移民作家以自己移民生活為素材進行文學創作,集中講述移民在移居國生活,作品以“此地”為背景敘述當前生活,然而,人物因文化沖突時常回望故鄉,作品對于這一題旨的描寫常常使得現實空間與心理空間呈現巨大的文化張力與心理矛盾。斯蒂文森(Stevenson)在概述當代英國移民文學總體特征時,將這一特點形容為表現歷史與心理斷裂的“地理與空間維度”,用于作家表述在移居國揮之不去的“此地他鄉感”,而這種“無根性”導致的時間與空間錯置感絲毫不亞于后殖民文學反復敘述的無家可歸感(2004:479)。正如金在概述20世紀70年代后英語移民文學總體趨勢時所說,移民文學以移居地為故事空間,同時在描寫人物意識時強調對故土的深刻記憶,這一特點代表了移民作家對于族裔身份的深刻關切(King,2004:11-12;72-73)。實際上,這種關切同樣反映了移民群體對身處此地心系他鄉的漂泊感,延續了后殖民文學批評對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危機的核心主題。不過,與《逆寫帝國》以“棄用”和“挪用”為策略的“抵抗”姿態構成明顯差別,當代移民作家已經不再把英語視作帝國的語言,而是一種世界語言,便于大多數讀者理解,并且在全球使用的交流工具(Stevenson,2004:494)。但是,這并不表示移民作家不再關注語言與身份關系。代之以前期后殖民作家通過作者敘述呈現對英語語言的改造與挪用,移民作家有意使用正統英語進行創作,將語言的差異使用體現在故事世界里,通過不同人物使用的非標準英語,突出移民在移居國的生活差異。從閱讀效果來看,作品以全知敘述和標準英語敘述移民故事,使得作品在英語讀者群體中最大限度地被閱讀,被理解;同時,以故事人物語言特殊性體現的身份差異使得故事擁有理想的讀者,與故事中人物的此地他鄉感發生認同,使得這部分讀者感受到,作品是關于“你們的生活”,但是,故事發生在這些人離開故土進入了“他們的地方”(Amis,2000:176)之時。移民文學以移民在移居國生活為核心素材,以標準英語和全知模式講述的此地他鄉的故事,這一特征的確表明移民作家從邊緣來到曾經的帝國中心,將曾經屬于帝國文化的語言進行了“移植”,用于講述移民作家親歷的跨國或跨文化生活(Burgess,1977:165)。但是,故事層面以移民與移住地文化沖突為主題的敘述恰恰折射出作家對身份認同問題(包括不被認同或拒絕認同)這一現象的歷史追蹤,并將移民文化心理上的無根性作為敘述的重點,以此揭示移民在移居國的邊緣生活。
4.跨國后殖民
移民文學以移民生活為核心關注,將歷史與現實融為一體,這一特點使得移居者“migrant”成為一個核心比喻:形容后殖民文學原先以“抵抗”為姿態的寫作與閱讀行為。這一特點集中體現在一批以國際大都市為故事背景的移民小說中。這一特點在英國移民作家的小說中尤為明顯。以倫敦為故事地點,作家們持續書寫對母國與異國兩個空間的跨國生活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沖突。奈保爾的《抵達之謎》(1987)、毛翔青的《酸甜》(1982)、萊利(Joan Riley)的《無所歸依》(1985)、斯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2000)、阿里(Monica Ali)的《磚巷》(2003),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在這些作品中,倫敦既是故事人物生活空間,同時又是回望與想象故國的參照,更是作家揭示移民在“兩種空間想象”中構建文化身份的核心象征(Wisker,2007:30)。就人物置身于曾經的中心這一事實而言,移民小說與薩義德在解讀19世紀英國小說時提出的“想象的地理”形成歷史的反轉:不同于帝國小說從帝國視角和中心將殖民地虛化為遙遠邊緣之地(或者括除在文本展現之外),移民小說以生活在中心的移民為核心人物,并從他們的視角觀察自己與中心的關系;與這一空間轉換形成對應,母國成為人物想象的對象。《抵達之謎》中的主人公、《酸甜》中陳氏一家、《無所歸依》中的黑人女孩雅辛斯分別從特立尼達、香港、牙買加來到倫敦,主人公從邊緣移入“中心”。這一空間轉換無疑突出了移民文學與前期后殖民寫作以邊緣抵抗中心的歷史差異。正如斯皮瓦克所說,移民文學對于人物在不同地理空間之間流動性的強調使得“移民”一詞本身成為當代后殖民文學范式變化的重要特點。從故事人物空間位置的變化來看,移民小說依附的闡釋框架——“后殖民文學”的確指向民族國家獨立后的文學,揭示了移民文學與前期后殖民文學發生的變化。
借鑒《逆寫帝國》在寫作和閱讀兩個層面對“抵抗”的強調,移民文學作家以棄用和挪用為基本策略,將英語語言作為國際語言,根據來到“中心”的移民視角敘述自己視野中的世界,這一轉變與開篇提到的“跨國轉向”表述的時間意義相吻合。所不同的是,移民文學聚焦于移民在“中心”的生活,這一核心關注使得作品的空間意義大于歷史意義,說明后殖民文學從先前對歷史的關注轉向對“空間—地理”的強調(Ball,2004:17)。然而,稍稍留意移民文學關于“空間—地理”的描寫,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關于移民移住地的描寫,還是對故鄉的回憶,“空間—地理”都是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彼此照觀、互為界定的想象。例如,在《抵達之謎》中,主人公回憶自己在英國20年來的無所歸依感,以細膩的筆法描繪自己在特立尼達、英國和印度之間的旅程,與此同時,反復強調自己關于英國的一切前理解均來自在英屬殖民地特立尼達接受的英國教育;作品關于不同“空間—地理”的用心描寫都在強調對于歷史的深刻感知(Ibid,55)。再如,毛翔青的《酸甜》以陳氏一家從香港來到英國的移民生活為素材。小說開篇明示:“陳氏一家移居英國已有四年,足以讓他們在移民前的社群中被人遺忘,但卻沒有讓他們在新環境中感到舒服”。正是這種“像是有家又沒有家”的“無根感”使得陳氏將重返中國作為最大的心愿。《抵達之謎》圍繞主人公在三個不同地理空間里的旅行與寫作作為情節結構,與此不同,《酸甜》自始至終以倫敦附近的唐人街為故事地點,然而,小說關于這個極其狹小的空間的描寫明顯指向特定歷史條件。如敘述者概述,陳氏一家來到英國全是因為形勢所迫。60年代,泰國大米出口躍居世界第一,受此影響,廣東地區原以種稻米為生的農民只得改行;與此同時,英國為了緩解國內勞動力緊張,開放移民政策,促使原殖民地國家民眾移民英國。在陳氏眼中,這是歷史的嘲諷,意味著“一個野蠻國征服了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換言之,與《抵達之謎》的主人公一樣,陳氏將自己進入“中心”視為歷史對個體的裹挾,全然身不由己。所不同的是,通過描寫成為英國作家為主人公畢生追求的夢想,奈保爾揭示了“中心”與邊緣殖民地之間的歷史淵源;以普通人的生存作為主題,毛翔青揭示了經濟全球化與文化本土化之間的沖突關系。
上述兩個例子遠不足以說明移民作家和作品具體對象之間的差異,但是,正如評論界注意到的,移民文學對所在地空間的關注常常被賦予歷史反思意義,期間產生的文本差異取決于作家對殖民前后兩個時期關系的思考與理解(Ball,2004:17)。將“后殖民”視為民族國家獨立后新型歷史階段,有的作家主張以雜糅文化身份自居,通過文學多樣性擺脫先前以民族國家身份為立場的“抵抗”模式(Rushdie,1992:124)。與此不同,有的作家將“后殖民”視為經濟全球化對本土文化的侵蝕,甚至消解力量,提倡將當代移民文學置于“跨國后殖民”階段。在這一點上,莫拉羅(Christian Moraru)的觀點值得借鑒。在論及后殖民文學發展過程時,她提出,“后殖民文學”包括60年代“民族主義后殖民”和70年代以后的“跨國后殖民”;前者與民族解放運動密切相關,在寫作立場上表現為明確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后者雖然同樣帶有歷史回顧和文化“抵抗”之意,重點卻在于通過反思現實與歷史關系揭示移民身份雜糅性的歷史緣由。
事實上,移民文學關于移民身份與所在地空間關系的敘述常常帶有明顯的歷史反思。如,里斯(Jean Rhys)的《黑暗中的旅行》(1934)和萊利(Joan Riley)的《黃昏時等待》(1987)以主人公在英國的生活為敘述對象,然而,以主人公對加勒比島國的回憶作為襯托,展示英國生活現實的種種艱難與挫折,這種夾雜在回憶與對照中呈現的移民生活使得作品對“中心”的敘述成為一個象征結構,揭示了主人公在移居國遭受的歧視與殖民歷史密切關聯。如果說作品對主人公在移居國生活的描寫展示了移民進入“中心”的當代現實,依照主人公旅行和回憶揭示的故鄉及其歷史無疑將讀者的注意力重新帶到殖民時期原住民遭受的“錯置”(displacement)。換言之,無論是從描述在原住地淪為英屬殖民地奴隸方面,還是從呈現戰后作為英聯邦國家自由人進入“中心”方面,移民故事關于歷史與地理空間的展現仍然契合吉羅伊(Gilroy,1993:122-133)用“根與徑”(roots and routes)強調的歷史性。或者說,移民文學看似以移居地空間性凸顯的時空錯置實質上強調的是“根/徑”背后的歷史維度,而要解釋其中的歷史要義,不可能回避后殖民文學批評對民族/國家身份已有的理論立場。
5.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體現在當代英語移民文學中的“跨國”現象實際上包含了后殖民文學前后兩個時期對文化身份的不同展現。較之前期以“抵抗”為立場的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當代移民文學(以小說為主)以移住地生活現實和關于故國的想象為寫作對象,將移民生活現實的“跨國性”和文化心理層面的無身份感進行并置,以揭示當代“跨國”現象與過往歷史之間的復雜關系。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們有必要看到:集中體現在移民文學中的跨國主題固然揭示了“東方主義”、“逆寫帝國”批評模式中的同質化傾向,但是,以“跨國”主題顯現的身份認同危機和文化沖突并不意味著后殖民批評的終結,而是以“轉向”顯現的新階段:“跨國后殖民”文學。
[1]Amis,Martin.Experience[M].Jonathan Cape,2000.
[2]Ashcroft,Bill,Gareth Griffiths,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89.
[3]Ball,John Clement.Imagining London:Postcolonial Fi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Metropolis[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
[4]Burgess,Anthony.The Novel Now[M].Faber and Faber,1971.
[5]Gikandi,Simon.Globalization and the Claim of Postcoloniality[J].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01,100(3):627-658.
[6]Gandhi,Leela.Postcolonial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M].New York:Columbia UP,1998.
[7]Gilroy,Paul.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Jane M.Jacobs.Edge of Empire: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M].London:Routledge,1996.
[9]Jay,Paul.Global Matters:Transnation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10]King,Bruc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1]King,Bruce.The New English Literatures[M].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80.
[12]Krishnaswamy,Revathi and John C.Hawley.The Postcolonial and the Global[G].Minneapolis:Minnesota,Minnesota UP,2008.
[13]McClintock,Anne.The Angel of Progress:Pitfalls of the Term‘Post- Colonialism’[J].Social Text,1992(31/32):84-98.
[14]McClintock,Anne.Imperial Leather:Race,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15]Mo,Timothy.Sour Sweet[M].New York:Vintage Books,1985.
[16]Moraru,Christian.Refiguring the Postcolonial:The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J].ARIEL,1997,28(4):171 -85
[17]Mukherjee,Arun.Whose Post- Colonialism and Whose Postmodernism?[J].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1990,30(2):1 -9.
[18]Naipaul,V.S.The Enigma of Arrival[M].London:Picador,2011.
[19]Needham,Anuradha Dingwaney.Using the Master’s Tools:Resistance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African and South-AsianDiasporas[M].New York:St.Martin’s,2000.
[20]Pratt,Mary Louise.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21]Rushdie,Salam.The Empire Strikes Back with a Vengeneance[N].The Times(UK),1982-07-03.
[22]Pratt,Mary Louise.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M].London:Penguin,1992.
[23]Simon Gikandi.Globalization and the Claim of Postcoloniality[J].South Atlantic Quarterly,2001,100(3):627-58.
[24]Said,Edward.Globalizing Literary Study[J].PMLA,2001(116):64-68.
[25]Said,Edward.Orientalism[M].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1978.
[26]Said,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
[27]Spivak,Gayatri Chakravorty.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New York:Routledge,1993.
[28]Stevenson,Randall.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vol.12,1960 -2000[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9]Wisker,Gina.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Palgrave:Macmillan,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