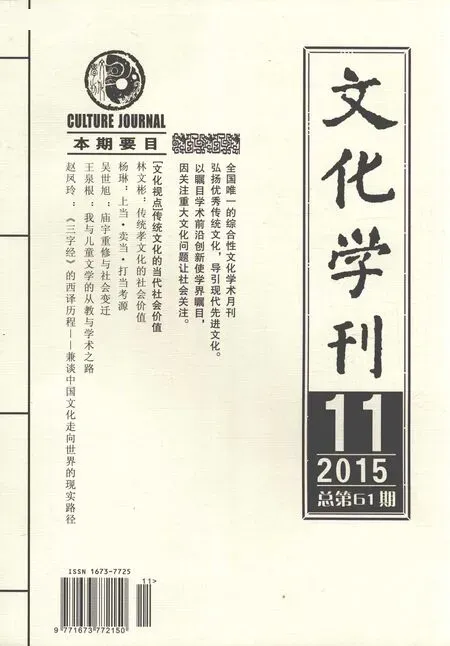法家思想的演變及對秦興亡的影響
柯瓊鶯
(福建衛生職業技術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1)
法家作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對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歷史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經過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爭霸的洗禮和幾代法家學派人物的知行構筑,法家思想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的一整套理論體系。商鞅變法后,秦國國富兵強,法家學說便成為秦國歷代君主治國的主導思想,兩者相輔相成,直至六國統一建立秦王朝,但當法家思想中固有的“重刑主義”和“君本主義”被統治者利用發揮至極致時,便為帝國的覆滅埋下伏筆,同時也為后世者提供了治亂興衰的寶貴歷史經驗。
一、法家思想的形成
法家,即謂之以法為主體,特別強調法的社會作用,認為法是治國的重要手段,法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評價:“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即不分貧富貴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根據《漢書》記載“法家者流,蓋出自理官”,法家思想的源頭可上溯至夏商時期的理官。西周時期統治者治國基本依靠兩個原則:禮和刑。“禮”針對貴族,“刑”針對普通百姓,整個社會嚴格保持著等級森嚴的統治秩序。從東周到春秋戰國,王室逐漸衰微,“禮”再也無力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社會發生了“禮崩樂壞”的巨變。[1]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加速封建化過程,成為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到了弱肉強食競爭殘酷的戰國,各國為保存自己或蠶食他人而紛紛尋求有效的治國謀略,一時間“百家爭鳴”,百家中的法家學派提出法治,倡導耕戰,反對“法先王”,不僅主張建立和鞏固新的等級制度,將“刑”提升到規范社會成員行為的主導地位,稱之為“法”。這一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韓非。他們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側面將變法運動由理論變為實際行動,尤其是韓非,吸取精華棄其糟粕,構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法家學說體系,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2]
二、法家思想的內容體系
(一)提倡變法革新,反對因循守舊
韓非指出“法與世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時代不同,統治方法也要改變,前世那種“親親”“尊尊”的仁義已行不通,一切法律制度都必須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相應變化,必須依據時勢來制定獎勵耕的法令以強國富兵。
(二)切合世情,務實于民
法家思想認為,人具有趨利避害的天性。管子說商人日夜趕路不辭辛苦,漁夫出海不懼風險,都是因為這是“凡人之情也”。商鞅也認為“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而韓非更是將人們趨利避害的人性發展為自私自利的“自為心”,并舉溺嬰例說明:“父母之為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3]所以,韓非認為,如果要使臣民服從,必須“因人之情”“令順民心”,即便要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階級意志,也必須切合實際情況,務實于民,否則人們做不到,法令終會無效。
(三)立法要遵循平等、透明的原則
首先,法應當平等。商鞅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他主張君主要慎法制,刑法不能有等級之分,上至卿相將軍,下到到大夫庶人,“有不從土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其次,法應當“布之于百姓”,立法之后就必須將法公之于眾,公開透明才能使人們依法行事。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可以讓民眾監督,防止官吏知法違法。
(四)行法要具有絕對的權威性
首先,法的實施要有強有力的保障。[4]《商君書·賞刑》載:“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如果違法就要受到嚴厲的刑罰制裁,法律才能有保障。其次,實行話語專制。法家認為,法律一旦制定,就絕不容許百姓肆意評價、議論,如有犯者“須盡誅”,只有這樣才能統一百姓的思想,仁義道德詩書禮樂才會因法而規范。
可以說,法家以其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依法治國論,為建立統一的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奠定了基礎。自商鞅變法后,法家思想由最初“德刑并用”到后來“以國為本”,再到“以君為本”,逐漸發展壯大,不斷推動秦國快速強大起來,并因歷代秦君主的推崇而迎來第一個歷史性高潮。
三、法家思想與秦君主的雙向選擇
春秋戰國,諸侯紛爭,齊魯文化、楚文化、三晉文化三足鼎立。其中三晉地處中原,無論是農業還是商業都較為發達,務實功利的社會群體心理為法家思想的繁衍及法的產生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背景。[5]但魏國的李悝,其依法治國的政改措施一度使國家強大,卻陷入后繼無力的困境,“少好刑名之學”的商鞅,也不為魏惠王所用,于是商鞅棄衛投秦,向秦孝公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最終得到秦孝公的支持;韓非著書立說屢次上書韓國變法革新,卻未被采納,輾轉流落到秦國后,他的學說尤受推崇;而李斯在呂不韋的引薦下為秦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體系,最終幫助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壯舉。
為什么自秦孝公開始,歷代的秦國統治者都如此青睞法家學說?首先,這與其地域文化特征緊密相聯。秦國地理位置版圖偏遠,建國時間晚,國土面積小,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較之其他諸侯國相對落后,加之周邊多戎狄異族,要在西部野蠻民族和東部中原大國的夾縫中求生存實屬不易,于是秦國很自然地就選擇了尚武功、講實用以便能快速富國強兵的法家理論。其次,這與歷代秦國君主主觀上對霸業的執著追求分不開。秦國本是周王室東遷時留下來抵擋戎狄東侵的一個盾牌,但由于地處西南邊陲,故傳統的周朝宗法文化對秦國的影響微乎其微,中原富庶的土地和巨大的財富無時無刻不刺激著這個西戎小國。早在春秋時代,秦穆公就屬意東進,戰國中葉秦孝公更是不甘落后,毅然頒詔求賢,奮起變法強秦。及至秦王政,立志掃平六國,統一宇內。正是這些有為君主對外積極開拓疆土,對內遵循法家思想,強君權清君側,在成就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基礎上,向創立帝王業不斷邁進。
從結果上看,商鞅變法后,秦國迅速國富兵強,兼并壯大。各國諸侯也不得不一改往日對其的鄙夷態度,連周天子也給予特殊禮遇。從而又更加促使歷代秦君主成為堅定的“法治主義”的實行者和擁護者,所以,法家思想與秦君主之間的雙向選擇就其獨立個體來說,看似偶然,實則是時勢使然的雙贏之舉。
四、秦王朝所推行的依法治國
在秦朝,秦始皇在治下的各個領域全面將“法治主義”思想推至極致。
(一)依法治國,體系完備
“依法治國”最早由商鞅在秦國付諸實踐,歷經秦幾代君主沿襲,至秦朝時,更發展為“事皆決于法”的原則。秦制定法的內容非常豐富,從考古出土的云夢睡虎地秦簡可以發現,就經濟法規一項,就有《秦律十八種》,內容涉及農、牧、工、商等各個領域。從政治、經濟,到司律、軍事,從生產到生活,一切均有法式規范,分毫不可逾越。
(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
秦始皇將自己視為“法”的化身,不斷提高君主的法律地位,集立法、司法、執政于一身,軍權牢握在手,最終“事皆決于上”。
(三)專任刑罰,輕罪重刑
秦自商鞅變法就一直奉行“法治主義”原則,這一原則在秦王宏圖霸業的統一戰爭中確實很奏效,所以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便把“法治主義”當做萬能的守業之具策。韓非曾極力鼓吹“重罰少賞”,但強調賞罰要有合理的限度。可惜,“重刑主義”到了秦始皇手中,既非“重刑厚賞”,也非“重刑少賞”,而是“重刑不賞”。如秦律規定:采幾片桑葉,“不盈一”也要“貲徭三旬”;“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趾,又黯以為城旦”。不僅刑罰嚴酷,且種類繁多,單死刑就有車裂、剖腹、棄市、腰斬、裊首、體解、鑿顛、抽肋、囊撲、鑊烹、滅族、夷三族等,[6]其殘忍、血腥程度可見一斑。
(四)文化專制,愚民政策
首先,書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思想,但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力政,不遵從周天子,于是禮樂典籍受到破壞,天下分為七國,各自特征都不同。尤其是戰國時期,分裂形勢更為顯著,因而書同文一直是一種空想,直到秦朝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通用秦文。其次,從各地保留的秦始皇出巡時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實現統一的內容。如對各地民間家庭婚姻習俗的強制性改造方針,表現出新政權文化統制的空前嚴厲。再次,由于儒者遵行古制,利用儒學經典以古非今,秦始皇為統一思想,下令將除法家以外諸子百家的著作予以銷毀,并禁止私學,形成“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局面。
五、法家思想的缺陷與秦朝覆滅
《過秦論》說:“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卻只有短短的十五年,馬上就“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賈誼認為原因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章中,賈誼提到了秦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陳勝吳廣起義,而根本原因是不施仁義。應該說史學界大部分人也都認可“秦亡于暴政”,但其暴政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源自個人主觀上的性格缺陷,但目前并沒有任何一種史據考證秦始皇是極端殘暴之人,所以這一點暫且不究。
第二,其治國指導思想的缺陷。任何一種思想或制度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作為其施政核心價值觀的法家思想也必然存在它的缺陷及消極面。早期法家思想是主張“德刑并用”。如子產雖然在施政上主張嚴刑,卻也承認“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但隨著周王朝的分崩離析,在五霸七雄的兼并戰爭中取勝的籌碼天平已漸漸遠離“仁德主義”而加速趨向實用的“刑法主義”,商鞅變法后,“令行禁止”的法治主義及“愚民不知”的文化專制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國家的戰爭潛能,使秦國迅速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中期法家的主張以國為本,君次之,強調尊君的目的是強國,但到了后期,尤其秦王政時期,為適應形勢的需要,法家思想意識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后期法家代表者韓非倡導鞏固君權,臣子要無條件的服從君主的命令,臣子不僅要被動地服從君主,還要主動地為君主盡忠獻身。當韓非直言“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時,國家和臣民都是君主個人的工具和奴仆,君主對國家和臣民有至高無上的肆意支配權力,[7]于是“立君立國”“立君為民”的觀念被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君本至上”的思想。
當秦國用法治主義來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時,嚴刑峻法確實迫使百姓不遺余力地耕戰以富國強兵,并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但秦王朝建立后,久經戰亂渴望和平的百姓希望有一個修養生息的環境,[8]統治者本應省刑罰、輕搖役,將重心轉移到發展社會生產上,然而秦始皇沒有這樣做。相反,他變本加厲地推行嚴刑峻法,強制全國上下臣服于他的個人意志,沒有節制地修筑奢華的宮殿和陵墓,于累累白骨上堆起萬里長城,征兵遠戰,巡游全國,焚書坑士,追尋長生不老藥,這一切將秦王朝一步步拖進深淵。秦朝兩代君主沒有清醒地認識到“攻守之勢異也”,沒有意識到國家已從“戰時”轉變為“和平”狀態,沒有及時對“法治”進行調整,反而繼續無限放大法家學說的理論缺陷,心安理得將“以君為本”作為自己“私天下之利”的圣旨,[9]以致民不聊生,大廈轟然傾覆。
所以,我們不能武斷否定法家思想的積極性,認為是法家思想直接導致了秦朝的覆滅,而應看到是因法家思想自身固有的缺陷被統治者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暴政,促使秦朝滅亡。正因為漢朝的統治者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戰后初期以儒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廣施仁德還民以休養生息,直至漢武帝采取“外儒內法”的治國方略,漢代由此進入了歷史的強盛時期。
[1][2][3][4]郭艷婷. 淺論法家思想及其現實意義[J]. 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4,(2):71-72.
[5][6]鄭穎慧.關于法家學說與秦代法制關系探討[J].河北法學,2007,(11):129-134.
[7][9]吳圣正. 法家思想的演變與秦王朝的興亡[J].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9,(4):66-70.
[8]李慧娟,趙曉晨.法家思想與秦朝興亡關系淺論[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4,(1):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