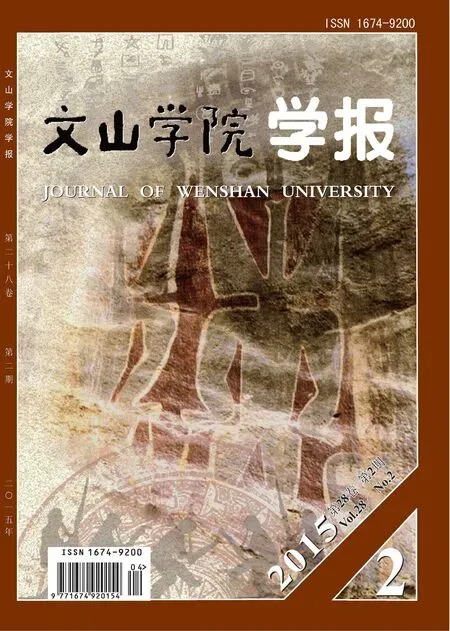情結與指向:郁達夫小說的現代性內蘊
鄧在艷,聶和平
(文山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情結與指向:郁達夫小說的現代性內蘊
鄧在艷,聶和平
(文山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文山 663099)
孤獨的漂泊是郁達夫的行者姿態,同時也將這種姿態賦予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沉論》中“他”“伊人”“丫君”的東洋之行正與這種郁式特有的行者姿態緊密相連。在其作品的情緒基調中,郁達夫式的民族夢想和衡量女性的尺度作為引子綴起了其作品主人公的生存之境——飄零與孤獨共生、游移與渴望并存。文章將以郁達夫的部分作品來探視郁達式的飄零與歸宿、寄情與游移,從而分析、探討并彰顯其現代性內蘊。
飄零;歸宿;寄情;游移
郁達夫是“五四”浪潮中的作家,“郁達夫熱”一直在影響著后世,就如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問世后的“維特熱”一樣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郁達夫的作品探討的不僅是那個時代的問題,也是整個人類的生存問題,所以他的影響遠遠超越了那個時代。筆者主要以《沉淪》《南遷》和《銀灰色的死》等作品為例,探查郁達夫小說主人公的現代性情緒基調:飄零與歸宿、寄情與游移。可以說,郁達夫式的不滿涵括了現代人最為普遍的在世狀態;其作品主人公的不滿,說穿了是一種對現實的恐懼,他們無時無刻地感覺到,煩悶的現在正通過不斷的重復將其青春的軀體不斷地吞噬,而他們試圖借助未來逃離現在的希望每每落空,于是生命變成了“當下”的機械空轉。[1] 224
一、飄零與歸宿
郁達夫作品中的男性心理情結:對希冀祖國的強大和對女人的渴求就從來沒有遮蔽過,郁達夫本人也從來不回避這個問題,足見“五四”的時代之聲一直影響著郁達夫。回首“五四”文學思潮,我們對于“人的解放”和“為藝術而藝術”是無法越過的,郁達夫也本著這兩個原則來塑造他作品中的人物,不偏不倚,真實得光怪陸離,正是這樣的新意賦予了郁達夫光環。
而筆者在《沉淪》和《南遷》中所觸及的男性,他們雖遠在日本,心卻永遠跟隨著支離破碎的祖國而律動。《沉淪》中的“他”在日記中的復仇火焰“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下去了”[2] 7筆間所露;《南遷》的“伊人”支支吾吾終于還是吐出了府上是“東京”這樣的字眼。不管是“他”,還是“伊人”均不敢承認自己是中華留學生,同樣深刻地表現了郁達夫內心深處的苦悶,祖國不強大,自己就是大海中的一片飄零的孤帆,永遠沒歸宿,唯有孤寂。
郁達夫有別于同時期的魯迅以知識分子的身份深刻挖掘國民靈魂的劣根性,筆觸也不如魯迅那樣犀利,表現方式也大相徑庭。郁達夫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其并不回避時代的主題,而是以細膩的畫筆呈現了人物的心之所向,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零距離接觸,并不像魯迅那樣將自己同胞的丑陋暴露出來。同時,郁達夫并不歧視他作品中的人物,而是予以深刻的同情,同情他們的遭際,感同身受。小說《沉淪》中寫到“他”無路可走,將要自殺之時說了幾句話:“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可我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種地步。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吧。”[2] 27作家以極其凄苦的心境關懷著他筆下的人物,與主人公共同呼吸著死亡前的空氣,舒張著自己渴望祖國富強的呼喊和悲天憫人的情懷,也儼然有別于張愛玲揭露丑惡的大悲憫情懷。郁達夫作品的美,美在凄苦和飄零中久久不能排遣的郁悶。
同樣,郁達夫作品也有別于蕭紅《生死場》的文本斷裂,蕭紅以生老病死去揭示時代之悲、國家之殤,而郁達夫卻借縈繞在青年留學生之心頭愁苦來表達揮之不去的祖國情。“蕭紅很自然地參加到了抗戰時代氛圍、時代潮流之中,轉變寫作觀念,扭轉寫作思路,導致她對自己的作品的扭曲、歪曲和誤解。”[3]但是郁達夫卻沒有像蕭紅那樣犧牲自己文本的三分之一去寫抗戰的大環境,依然選擇以側面去反映時代情懷。如以青年學生那種不敢承認自己是“中華留學生”的心理,將時代主題表現得真切萬分——“白天倒還可以支吾過去,一到了晚上……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2] 13,《沉淪》中的這一句話就將時代之思緊緊凸顯。
自從普希金刻畫了“葉甫蓋尼·奧涅金”之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記》廣為流傳,以及萊蒙托夫的“畢巧林”等多余人形象依次出現。這些“多余人”形象,在社會中遭受失敗,不管是愛情還是社會地位,而郁達夫的創作與之恰有異曲同工之妙。《沉淪》中的“他”欲與同學交流,卻覺得同學們會嘲笑他,至于愛情,他只能奢想而不敢去觸碰,因為他害怕——最后被這個世界遺棄,走向黃泉成了他唯一的歸去之地。祖國,他再也回不去 。《南遷》中的“伊人”開始覺得“money, love and fame”[2] 49全都有了,被M夫人拋棄之后,只得扼腕哭喊“名譽,金錢,婦女,我如今還有一點什么?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我……我只有我這一個將死的身體”[2] 52。凄涼的哀號里流露出了作家“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零落之情,“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還該來救救我”[2] 53這樣渴望救贖的心也落空了,因為“O”得了熱病活不久了。他的希望最后也化為泡影,一無所有的伊人也生病了,就如我們的民族一般垂危。郁達夫正是以“多余人”形象深刻地勾勒出我們的民族正和這些留日的青年學生一樣,還沒有尋找到出路,他們依舊像“畢巧林”那樣只有死亡這一種歸途,將民族情抒得一覽無余,以細微之處洞悉民族問題的時代特質。
文學的“無用而用”之美,在郁達夫作品中的民族心理也無意間流露出來,郁達夫正是運用文學來表達了他的民族情結。其作品在有些方面盡管流于情色,可也像《紅樓夢》一樣有著鞭撻社會的功用。《沉淪》中的“他”高唱“‘醉拍闌干酒意寒’,‘劇中鸚鵡中州骨’”[2] 25,正是借著辛棄疾的“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和契丹詩人元好問“中州萬古英雄氣”的豪氣來表達渴望國家和民族富強以及祖國擺脫內外交困局面的強烈愿望。可見郁達夫苦于自己的心意沒有人明白才唱出這樣的凄涼之聲,期望有人能夠意會自己的“登臨意”和一身豪邁的“英雄氣”。郁達夫正是用這樣的話語來表達自身的渴求,痛陳社會之弊,蘊藉企望改造社會的豪氣。
郁達夫作品中的人物總是以孤獨者的形象存在,《沉淪》的“他”、《南遷》的“伊人”、《銀灰色的死》的“Y君”,總是一個人在路上品嘗著孤獨、歧視、死亡的氣息。而郁達夫的這種一個人在路上的孤獨者形象就如一入佛門就用終身守住清規戒律的李叔同一般,總是活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之中直到死亡,即使是死也死得異常孤寂,就如《銀灰色的死》中Y君“‘橫倒在地上了’……‘四邊寂靜得很。銀灰色的月光,灑滿了那一塊空地,把世界的物體都凈化了”[2] 73。與此同時,郁達夫的生存境界又與蘇曼殊這個飄零四海的孤獨僧人有著細微的差別,郁達夫只把自己控制在自身的心理世界之內,而蘇曼殊卻總是想要去突破那個獨立的空間卻沒有成功,貪戀生死,死后民國主席汪精衛還為其出殯。廈門大學的周寧教授說了這樣一句話:“蘇曼殊作了一生的參與者與局外人,是不折不扣的感性天才、短命天才。”這恰與郁達夫作品中的“他”“伊人”“Y君”等人物形象存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又為郁達夫的孤獨飄零人生觀做了一種生存體驗的注譯。《沉淪》中“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后,對了那幾個中國同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心”[2] 15。“他”以這種孤獨的姿態游離于人世間,處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狀態。郁達夫正是以這種玩世不恭、敏感、郁悶的方式將人物赤裸裸地展現于讀者的眼前,與讀者零距離地交流。
此外,郁達夫筆下的每一個男人都是需要女人來照顧的,他們是一個需要母性關懷的團體,沒有了母性的愛他們最終都是走向死亡和毀滅。透過郁達夫的作品,我們不難看出郁達夫的女性需求觀,甚至也可以探視到他也屬于這個需要母性關懷的團體,與此同時,他還將多年漂泊不定、四海為家的深切體驗根植于作品之中。作品中的主人公幾乎均以死亡而告終,《春風沉醉的晚上》的“我”、《沉淪》的“他”、《銀灰色的死》的“Y君”等等均沒有好的結局。郁達夫以墮落、毀滅和死亡來反襯自己的希翼,足以表跡他的無奈和憤怒,同時也傳達出了郁達夫的民族觀——祖國不獨立便無處棲身。郁達夫以赤裸裸的墮落、毀滅和死亡無情地揭露出祖國沒有獨立尊嚴,人便沒有尊嚴、沒有“詩意的棲居地”。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生前支支吾吾不敢說是中華留學生,而郁達夫卻要他們都脫下偽裝,就如廈門大學周寧教授所說的“人的一生唯在死亡面前不存在表演”,在死亡面前人才是最真實的自己,郁達夫在其作品中通過主人公的死亡,意外地將自己的生死觀從中表現出來。人為何而生,為何而死,在郁達夫的作品中得以深刻挖掘。
二、寄情與游移
一談到女人,我們幾乎都會想到“紅顏禍水、柔美、愛情”等詞匯,女人好似天然具有這些特質似的。楊玉環、王昭君、趙飛燕等女性亦是古之女人,可她們依舊具有這些或好或壞的特點。郁達夫作品的女性亦是如此。郁達夫作品中女性大致分為三類:天真爛漫如《遲桂花》中的“蓮”、《銀灰色的死》中的“靜兒”,不帶任何功利性、任勞任怨,打破了郁達夫慣有的情感頹廢表現方式,這一類女人是郁達夫心中的完美女人;溫順如《南遷》里的“M夫人”這一類婦女形象,對這類女人充滿欲念,并且能夠獲得她們的青睞,但最終卻又被拋棄,對她們既愛又恨,這類女人是郁達夫心目中的次完美女人;《沉淪》中的侍女似的妓女形象,這類女人在郁達夫的筆下屬于女性的妖化抒寫,渴望與她們有著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但又覺得她們玷污了自己。
《遲桂花》的“蓮”這一類女性形象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女性形象,代表著自然之美 :天真爛漫,在郁達夫心目中是最完美的女性形象。“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蓮的高貴沖淡了郁先生的情欲,純潔了他的心靈,他們最終“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2] 321。正是由于蓮的純潔高貴,男主人公最后選擇了離去并留給蓮美好的祝愿“蓮!再見,再見!但愿得我們都是遲桂花”[2] 326,蓮這樣的女人永遠活在了郁達夫的心中。這一類女性雖然也具有自然之美,但卻完全有別于世界文學史上的“吉普賽少女”的野性美,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愛斯梅拉達那種天真原始、不受約束的野性美,“那蜻蜓變成了黃蜂,她不想別的,只想螫人”[4] 88,就是西方文學史上的原始美的女性形象的完美展現。而郁達夫寫的《遲桂花》中的“她”只能是中國傳統的女性形象,這類女人是五千年中國文明的催生物,郁達夫的筆下自然不可能發生基因突變。再者就是郁達夫《銀灰色的死》中的“靜兒”,“容貌也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知是什么理由,使得見過她一面的人,總忘不了她”[2] 68。盡管靜兒擁有某種氣質讓人難以忘懷,最終也只能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嫁人,螫傷了對她有好感的“伊人”。伊人被拋棄之后,死亡成了他最終的歸宿。靜兒在扮演傳統女性“乖乖女”的同時也扮演著“紅顏禍水”的角色將伊人送往萬劫不復之境,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伊人死亡。靜兒這樣的女人也只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自由戀愛之間游離,在郁達夫的筆下并沒有讓她沖出傳統女性的藩籬。《遲桂花》中的蓮和《銀灰色的死》中的靜兒這兩個女人都兼具傳統的自然美,在戀愛婚姻上不具有沖破現實的魄力,在郁達夫的筆下都是可愛又可恨的女人。
郁達夫筆下的第二類女人是《南遷》中的“M夫人”這一類形象,這類女人凸顯著郁達夫式愛憎觀,較之于前一類女人,郁達夫有更加明確的態度,對她們既愛又恨,帶有一種男性的復雜心理。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瑪、巴爾扎克《高老頭》中的鮑賽昂夫人等女性形象,無疑都是愛慕虛榮、金錢、名譽而最后自食惡果的女人,但是在郁達夫的作品中卻沒有揭示這類玩弄別人情感的婦人會有不理想的結局,作家正是以這樣的女性形象來鞭撻社會的黑暗,指出生存的幻滅感不是源于肉體的死亡而是人情冷暖所致。即使最后伊人呼喊著“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還該來救救我”[2] 53,但“O”已經處于垂死的狀態根本無暇顧及他,他只能想象“O”唱著《迷娘的歌》“你這可憐的孩子呀,他們欺負你了么?唉”這般的可憐他,將他從萬丈深淵解救出來。但是,最終伊人加諸在“O”這個女人身上的幻想破滅了,毀滅將他帶上了無望的歸途。
郁達夫筆下的第三類女人是《沉淪》中侍女似的妓女,只要有錢,她們的原則無下限。對這類女人郁達夫的心理是頗為矛盾的,作品中的“他”既渴望與她們有肉體上的交歡,但激情退卻之后又覺得這類女人欺辱了“他”的身體。侍女“口里的頭上的面上的和身體的那一種香味,怎么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別的東西”[2] 23,但當侍女去為別的客人說笑的時候,他就發怒起來“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辱我么?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你們的仇。世間哪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負心東西,你竟敢把我丟了么”[2] 24,此時在“他”的眼里侍女的美全被拋諸腦后,剩下的只有內心深處的仇恨和遺棄。終于“他”也與侍女有了肉體的茍合,把身上的最后一塊錢也給了侍女,“他摸摸身邊看,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2] 27,說是自己的身子“被人家欺辱”,把自己莫名地變為最下等人。這一類女人直接導致了《沉淪》中的“他”死亡,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顏禍水”。郁達夫對她們的態度如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既愛又恨,其實質同樣是指向民族的“零余者”尋找不到出路,反映了這類人的死亡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郁達夫作品的女性形象是具有恒定性的,他正是以這種不變應萬變的姿態將他作品中的女性與民族命運緊緊地關聯在一起,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敘述了與作家血肉相連的民族魂靈。家國同構的理想在郁達夫的作品之中自然流露,沒有國這種大環境的獨立自強,個體的存在是毫無意義的。
三、結語
郁達夫的作品就如一首主題的變奏曲。主題就是希望民族富強、追問個體存在的意義,律動的音符與這兩個主題共同建構于一體,和諧而具有張力,將郁達夫強烈的存在感蘊藏于每一部作品之中。郁達夫緊緊抓住愛和死這兩個永恒的主題,將時代之思、民族存在躍然紙上,構筑成了那個時代所有人的民族夢。現今,民族的呼聲、民族崛起依然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夢。過去,在日本不敢說出“我是中華留學生”,這時我們可堅定地道出“我是中國人”,今天的景狀些許就是郁達夫多年前的預想。
[1] 李茂增. 現代性與小說形式[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2] 郁達夫.著. 樂齊.主編.伍思.選編. 郁達夫經典[M].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0.
[3] 摩羅. 《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J]. 社會科學論壇,2003(10):41-50.
[4] [法]雨果.著. 巴黎圣母院[M]. 陳敬榮.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 田景春)
Complex and Intention: Modern Connotations of Yu Dafu's Novels
DENG Zai-yan, NIE He-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99, China)
Lonely wandering is Yu Dafu's wanderer attitude and he also gives the same attitude to the heroes in his works. The journey of “He”, “She” and “Y man” to Japan in The Fall is ju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onely wandering. In the emotion tone of his works, his national dream and yardstick of females as leads weave an existence land: co-living between wandering and loneliness, coexistence between soothing and vacillation. The paper studies Yu Dafu's wandering and end-result, soothing and vacillation through analyzing parts of his works to profi le their modern connotations.
wandering; end-result; soothing; vacillation
I207.42
A
1674-9200(2015)02-0083-04
2014 - 05 - 27
鄧在艷,文山學院人文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