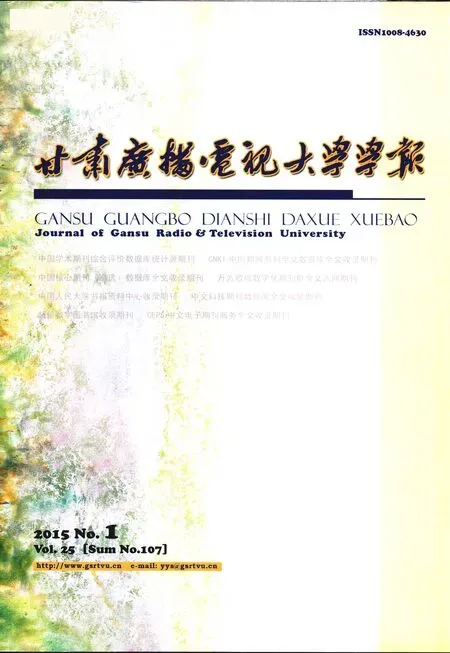地方性審美經驗的性別差異
——以影片《賽德克·巴萊》的審美人類學解讀為例
劉潔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730000)
地方性審美經驗的性別差異
——以影片《賽德克·巴萊》的審美人類學解讀為例
劉潔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730000)
少數族群文化與民間文化作為活態文化,具有其作為小傳統自身的特殊性及審美情感獨特性。在審美人類學的研究中必須重視地方性審美經驗的個體及性別差異。以電影《賽德克·巴萊》為分析文本,從審美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賽德克人基于共同信仰之上審美經驗的性別差異,在地方性審美經驗的研究中引入個體與性別研究,無疑是對吉爾茲“深描”法的新的實踐,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意義。
審美人類學;地方性審美經驗;性別研究;《賽德克·巴萊》
審美人類學提倡對少數民族/族群文化的調查研究,目的在于從中尋找被主流文化與美學所忽視的但仍以鮮活的生命力存在于民間的審美文化加以發掘與考察。然而審美經驗作為一種感性因素,蘊含了直接性、瞬時性、個體性、復雜性、流動性、模糊性等特征,區別于一般概念性的、抽象的、可被清晰闡釋的那種經驗,不能籠統加以概括。因此,正如王杰指出的,審美人類學在方法論上必須堅持多元化的方法論原則,“把人類學、精神分析、經驗美學、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等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在某種基礎上統一起來、協調起來”[1]110。因此,審美人類學研究重視并努力發展西方學者提出的“弱小者話語”理論,深入挖掘少數族群內部在審美經驗及其地方性知識上的獨特性,探索更復雜、更辯證的研究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審美和藝術的政治性尤其值得關注,由此去闡釋審美與權力的關系、審美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審美活動的族群性和階層性、藝術活動中的性別不平等、西方霸權思想等問題就構成了審美人類學的一些重要問題”[2]。但在具體的實踐研究中,審美人類學的相關案例分析對于地方性審美經驗的“深描”都顯示出對“總體研究”方法的貫徹與強調,默認少數族群為統一整體,忽視或者說刻意避開了其族群內部的審美差異,尤其是對同一種族內部性別間的審美差異的忽視,使得相關研究對少數族群的“地方性知識”及審美經驗的考察仍然停留在民族志寫作式的臆想表述中。不得不說,過分強調所謂“結構的整體”和這種整體的決定性作用,犧牲了“過程”和身體經驗的復雜性,犧牲了性別建構中的文化決定性以及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了社會結構、族群階層與性別導致的差異性。
一
審美經驗具有差異性,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地域與種族、群體與個體上,還表現在性別上。“人類學非常關注母系文化,進入男權社會后,母系文化被壓入文化邊緣和無意識狀態,但仍以藝術變形的方式加以表達”[1]109。在藝術和美學中政治屬性研究的繁多樣態中,出現一個明顯的、令人奇怪的疏漏——藝術與性別不平等關系。從當下研究來看,只有少數研究者提及了在藝術內容上反映出的性別差異問題,而大部分研究仍然以想象力形式運作,性別個體認同的問題、藝術中的性別差異問題目前仍未得到普遍重視。在審美人類學研究中只關注到了少數邊緣群體整體中帶有某種崇高意味的、脫離日常生活趣味的審美,而女性審美經驗的獨特性與異質性被沉沒于歷史地表之下。
審美人類學理應借鑒當代性別研究的一些成果。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瓊·W·斯科特所說:“社會性別是基于可見的性別差異之上的社會關系的構成要素,是表示權力關系的一種基本方式”[3]。社會性別強調男女身份特有的社會文化起源,“性別研究者普遍堅持一種觀點,即文化建構觀念”[4]。也就是說,性別是文化的產物,是話語權的結果。因此,在審美經驗的具體研究中,應該重視并揭露出偽裝于中立或所謂超性別的文本和話語中潛隱的性別因素,以性別的社會形成分析取代生理決定論,并且在具體學科領域中引進兩性的比較研究,反對抹平性別差異的審美經驗,必須認識到“任何對社會制度的研究都應該包括對社會制度所塑造并蘊藏于社會制度之中的兩性關系”[5]。審美人類學在探索地方性審美經驗的過程中,應該時刻有性別差異意識,不可抹平性別差異偽裝統一,不可囫圇吞棗式全盤加以概括,這才是格爾茲“深描”法的精要所在。
二
審美人類學應該關注具體的人。審美是情感的,它的情感性需要以身體和身體的延伸即行動來表達。少數/邊緣部落族群中固定的生活方式與儀式以及藝術行為(例如舞蹈)都是身體的延伸,是身體的一種表達形態。因此,任何對審美及其相關項(如審美經驗)的研究都應該把關注重點放在具體的人的行為——尤其是群體性的習俗、儀禮等公共行為的考察上。電影《賽德克·巴萊》重現了臺灣歷史上著名的“霧社”事件,影片中的賽德克族是典型的地方性邊緣群體,有著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獨特的文化傳統,堅定的信仰表現在他們各種行為中,并構建起了賽德克人的性別意識與自我認同,顯現出獨特的審美趣味。
一般而言,在性別認同中其實包含著人性、類性和個體自我性等三個層面,但三個層面實則交雜糅合、難分難解。基于此,性別形象的自我認同不可能脫離民族審美文化的影響,自我性的建構離不開他性的塑造。賽德克族群的性別氣質與認同差異以及伴隨此形成的審美差異可以從他們共同的信仰之中顯現出來。因此,對影片《賽德克·巴萊》的審美人類學分析將以信仰為切入點,以身體參與的儀式性行為為解讀對象,以性別理論為支撐,探討賽德克族群地方性審美經驗的性別認同差異。
(一)神木信仰
在影片中,德賽克族認為自己的祖先由巖山與神木合二為一而生,因此其族群集體記憶中天然地保存有神木信仰的維度。更重要的是,樹木叢生的獵場作為賽德克族群的生活環境背景與基本物資來源,其重要性與不可剝離性不言而喻,因此,神木信仰作為一個模糊卻又普遍的基本信仰深入而內在地浸潤著每一個賽德克人的心靈。神木信仰不僅僅是一種族群內的類似宗教的神秘文化,更是建構族群性別差異與認同的文化背景。
具體行為1:狩獵——“類”的認同
對于賽德克族群來講,狩獵是男人的事業。它不僅僅是族群基本食物供給的渠道,更是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的必須途徑。族群中成年男子必須走出部落去打獵,帶獵物回來跟族人分享。狩獵作為賽德克男性的一個共有的、帶有某種象征意味的儀式化行為,在神木信仰的大背景下,獲得了其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狩獵這個行為的過程中,男性獲得了自身主體身份的證明與認同(包括自我認同與他人認同兩方面),其男性氣質由此而得到了彰顯,由此建構起了男性主體自身的整體性與獨特性。
顯然,從狩獵行為的文化意義方面來講,一方面它是男性生命周期的文化界定中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又是賽德克人性別差異界定的方式。青年男子們的社會知識與經驗最早是由父親帶著去一起狩獵時獲得的。通過狩獵行為,父親讓兒子們了解到一定范圍的地理知識和實踐經驗,“他的獵場就是他的國”。但是,獵場只是“他”的國,這是一個分界線,這種實踐性的學習將婦女隔離在外,完全隔絕了兩性間任何的對話與交流。性別差異把經驗神秘化為一種自覺的問題,并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固化為一種族群內毫無異議的性別分工,并參與了性別的建構。正是由于這種行為介入到了性別建構的內部,每次的具體狩獵行為才獲得了其意圖與存在理由,也在某種程度上一遍又一遍地推動了這一分工模式的圣化,阻止了任何個體負面的爭議。女性自身的主體性與差異性就在這種分工模式之下被嚴格排除在獵場之外得以形構的。
這種地域(或者說空間)的區隔在賽德克人死后的祖靈之家中更是得到了鮮明的顯現。影片《賽德克·巴萊》有這樣一段唱詞:
生活在這大地上的人呀,祖靈為我們編織了有限的生命,……可我們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戰場上,他們走向祖靈之家,祖靈之家有一座肥美的獵場唷,只有真正的男人才有資格守護那個獵場。……而真正的女人……你的靈魂可以到達祖靈之家!……
可以看出,對于男性來說,走過彩虹橋,到達祖靈之家,“祖靈之家有一座肥美的獵場”,并且只有真正的“男人”“才有資格守護那個獵場”,這是“永遠的榮譽獵場”;而對于女性來說,真正的女人“你的靈魂可以到達祖靈之家”。也就是說,不論是在現世生活中,還是天堂祖靈之家中,獵場都是純然的男性空間。其對于女性的禁忌,其實就是對男性地位的肯定與維護。在一定場合中女性的缺席或被迫缺席,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達成了男性主體身份與性別氣質的建構。
因此,獵場所具有的形構男女兩性性別差異的標志性意義,也可以解釋影片中賽德克族群最終揭竿而起的反抗之舉。賽德克族人在日本的偽善文明統治奴役之下,男人不僅不能狩獵,還要砍伐搬運他們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樹木森林,“那些看過我們祖先的樹,都變成這樣的木頭了”。就信仰層面而言,神木信仰被撕裂、被毀滅,就自身主體建構而言,沒有了狩獵,男性無法建構起自我性別認同,男性氣質開始殘缺甚至消隕,自我作為男性的主體無法形構,這無疑是一種“閹割焦慮”。所以,“將來樹沒了,就什么都沒有了”。為了成為真正的賽德克人,成為真正的“男人”,賽德克男性用生命選擇了反抗。
(二)彩虹橋信仰
在《賽德克·巴萊》中,彩虹橋是賽德克人死后到達祖靈之鄉的必經之路,也是希望的象征。彩虹橋信仰是賽德克族群的最堅實的也是最重要的信仰,形成了賽德克人獨特的審美經驗,同時也是族群性別差異形構中的重要力量。
具體行為2:男性出草,女性編織——“類”的認同
要成為“真正的男人”并且獲得進入祖靈之家的資格,男性必須勇敢,必須通過出草與狩獵得以證明。在賽德克族群中,男人對獵頭活動懷抱著熱切的興趣。這種干勁,不僅源于對十分必要的自我防衛手段的堅持(野獸與外族人都時刻威脅著自己的生命),還源于他們對成人身份、男人身份的認同與追求。獵頭活動具有強有力的情感共鳴,它發生于男性個體成長過程的關鍵時刻,通過釋放個體心中的壓迫感和重負來界定男性的身份(masculinity)。在影片開始時,馬赫坡的莫那·魯道從第一次“出草”,在敵對部落眼前搶下肥美的獵物、砍下敵人首級的那一刻,他就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這奠定了他獲得族群的尊敬與欣賞、接替父親成為族群頭目的必然性。
要成為“真正的女人”并且獲得進入祖靈之家的資格,女人必須勤勞,“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繭”,這種品質的證明必須通過織布的行為得到彰顯,“真正的女人,必須要善于編織紅色戰衣”。這是賽德克族群中關于典型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的指認標準,也是一種女性的“完型鏡像”,這種標準具有某種性別類屬的穩定性、秩序性和審美性。女性主體性的形成,因而呈現為一個女性自我感知不斷向完型鏡像凝結同時又不斷沖突與克服沖突的過程。
編織行為僅為女性所有,這種行為具有持久的沿襲性與不可反抗的強制性,在滿足族群(或者家庭)眾人基本穿著衣物及其他布料需求以外,女性主體建構與身份認同在此得以完成。只有在成功具備這種能力的境況下,女性個體才較容易在他者認同和自我認同之間取得一致性。并且,編織是一種具體的行為,它的發生場合是在室內。這是女性的合法活動場所。正如家庭一樣,這種場所對于女性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強制系統,男女的性別差異及審美差異都依賴于此逐步建構起來。日常生活場所是女性被派定的歸屬,同時也是牢籠,將她隔離于男性文化(例如狩獵、反抗起義)之外。影片中反抗起義之前,巴索對妻子說的“你盡管守好火盆,別讓火熄了”。這句話無疑是具有深刻寓意的。
具體表現3:紋面——人性、類性和個體自我性三種認同的合一
正如列維·斯特勞斯對巴西卡都衛奧印第安人面部繪畫、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宗教面具、毛利人雕刻、中國商代青銅器中的圖案加以比較,發現盡管這些藝術形式存在著時代、地域和歷史文化背景中的差異,但都是對個人的生物存在與社會身份加以調和與聯系的體現[6]一樣,紋面也是賽德克族人在世時的榮耀與成年禮,更是賽德克族人自我認同的族群標記,也是男女性別審美的差異與性別氣質的認同機制,即“紋面男子表示已具有捍衛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維護家庭生計及冷暖的織布技能”[7]。紋面被視為對成年人的考驗,在整個族群的壓力下,賽德克族群個人沒有任何權利選擇是否要紋面,只能完全接受紋面的習俗。
紋面是一個賽德克男人之為男人的標志,是成為一個真正的“賽德克巴萊”的標志,也是其自我性別認同與集體認同的標志,一個男人只有成功“獵頭”之后才具備紋面的資格。狩獵成功者手掌必留有血痕(呈血紅色),手掌的血痕是辭世后靈魂要回到祖靈身邊無可取代的烙印。正如影片中所說的:
莫那,你已經血祭了祖靈,我在你臉上刺上男人的記號,從今以后,遵守祖律的約束,守護部落,守護獵場,在彩虹橋上,祖靈將守候你英勇的靈魂。
然而,在日本統治時期,歷來靠強悍的征服來表達自我的族人,“在文明的召喚下只落得一張張白凈的臉頰,曾經代表‘勇猛’的頭顱只得被獸骨所取代,雙手染血是皈依祖靈的必然途徑,現在卻在‘文明’的洗禮下漸漸被拋棄”[8]。因此,與其說,賽德克人的反抗是一次抗擊日本人暴虐統治的行為,不如說,他們的反抗是一次追認自己靈魂,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真正的男人的行為。
相對于男性而言,當賽德克少女的織藝精進、能熟練地掌握織布技術,而且在保有處女之身的情況下,得到長輩的認可后,方可進行紋面。善于織布而取得紋面資格的女子,其手掌上會因勤于織布而留有血痕,便獲得了進入祖靈之家的資格。此外紋面的成功與否還是對女性貞操的一項確認和考驗。紋面是女性善織與貞操的證明,也是一座牢籠。善織是賽德克女性被指定的、被動接受的規訓,善織與貞潔都是男性審美理想的體現。賽德克婦女都是“家中的天使”——內斂、順從并且無私。她們的審美經驗建立在自身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缺失自由意志的基礎上。
三
賽德克巴萊族群中兩性形象的認同與建構所寄寓的民族審美文化表意傳統及兩性審美經驗的形構機制,是一個少數民族歷經長時間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變遷后沉淀下來的審美文化以及特定價值向度的選擇擔當,是少數民族立足于自身日常生活習俗所采取的一種美學策略。相較于精英化、景觀化的審美文化表意方式與政治化、陌生化的西方女性主義文學表意方式,賽德克族群生活中的審美文化意蘊及其表達選擇,恰恰維護了自身的存在本質。
不可忽視的是,共同信仰之下的不同行為與儀式不僅具有意識形態的力量,是一種審美經驗的強化,它同時參與了性別間的審美經驗與審美認同機制的形構。從性別形象的身體、行為到角色氣質的認同建構,其實是一個從生理性別到社會性別逐步統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間的審美經驗被削割、被形構,性別間審美經驗差異被塑造、被認同。因此并不存在一種具有統一本質的少數族群審美經驗,也不存在鐵板一塊的族群審美意識。對少數族群任何關乎審美的研究就必須強調“得其環中”、“超以象外”,在某種直觀的、整體性的觀照狀態下,從整體社會生活中發現其內部審美差異。另外,審美經驗中性別差異的凸顯也使得婦女得以浮出歷史地表,其特有的“房間內”的獨特審美經驗可以與男性并駕齊驅,在兩性的相互交流中,產生無限的活力。
[1]王杰,海力波.審美人類學:研究方法與學科意義[J].民族藝術,2000(9).
[2]托尼·傅雷利斯.審美人類學的問題閾[J].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12(7):218.
[3]譚兢嫦,信春鷹.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匯釋義[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146-147.
[4]梁慶標.性別研究與主體訴求[J].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22.
[5]瓊·凱利—加多.性別的社會關系—婦女史在方法論上的含義[C]//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研究選擇.北京:三聯書店,1998:91.
[6]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257-258.
[7]郭明正.德賽克辭典:《德賽克·巴萊》背后的歷史真實[J].看歷史,2012(3):50.
[8]張之薇.信仰的切入-魏德圣與賽德克·巴萊的靈魂對話[J].藝術評論,2012(6):83.
[責任編輯 龔 勛]
B83-0
A
1008-4630(2015)01-0048-04
2014-12-19
劉潔(1990-),女,甘肅張掖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理論及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