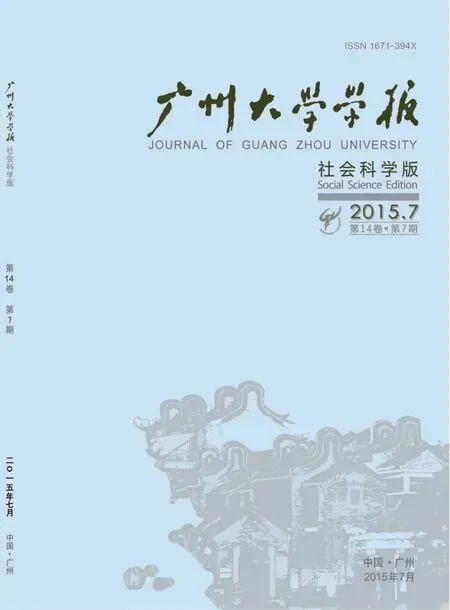《龍會蘭池錄》與王士骕《拜月亭》詞曲案考——兼與周鞏平先生商榷
石 超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一
《戲劇藝術》2009年第3期刊發了周鞏平先生的《王士骕〈拜月亭〉詞曲案考》(以下簡稱周文),周先生通過查閱大量史料,仔細分析了此案的來龍去脈,認為釀成此案的原因大致如下:(1)市井無賴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以抗倭之名借機敲詐,造成了極壞的民間輿論,也影響了官府的態度;(2)辦案主官朱鑒塘(鴻謨)不識劇本,不知“季布”“朱家”這聯曲詞的出處,又急于立案,貿然將其推定為王士骕原創之“反詩”,并寫入奏本向朝廷報告;(3)當地一些官府胥吏與王士骕等曾有私怨,借機打擊報復,落井下石;(4)把王士骕仆人胡忠的平話表演和政治動機與行為聯系起來,當成了王士骕真實的“天子自為”。[1](此四點系筆者根據周文總結,原文并無羅列)。這四點將王士骕詞曲案的個中原委和來龍去脈分析得非常透徹,筆者深表贊同,但周文第三部分根據沈徳符《萬歷野獲編》記載得出的結論則值得商榷。為了論述方便,茲錄如下:
按沈氏的說法,就是在他閱讀《拜月亭》的萬歷末年,劇中已經沒有了這聯對句。可見,在劇中刪去或改掉這聯曲詞的情況在萬歷末年就發生了。因為王士骕使用《拜月亭》詞語而獲謀叛罪,因為他的仆人說平話模仿了帝王口吻而被視為“彼天子自為”,導致下獄受刑,差點全家受誅,同案者多瘐死獄中。使人們感到非常恐懼,趕緊在劇中刪去或改掉了,于是趕緊在劇中刪去或改掉了句子,造成名劇的詞語被刪、被篡改。一樁文化冤案,就使文化活動的參與者戰戰兢兢,人人自危、惶恐不安,表演時要處處小心、時刻提心吊膽。這對文化的發展,對文化傳承的影響是多么陰森與可怕!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看到這個著名劇本的歷史原貌了。推而廣之,在這種陰森恐怖的環境氛圍里,又會有多少其他著名的劇本被刪改,有多少特色表演技藝因此而失傳了呢?思之念之,能不令人扼腕![1]
因“反詩”牽連入獄的在古代文學史上并不乏見,《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詩禍”條就有不少記載,但周先生根據王士骕詞曲案的影響,認為現今流傳的《拜月亭》缺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兩句曲詞,是因為人們害怕惹禍上身,在劇中刪除或改掉了則有待商榷。古人可能確系有類似的改動案例,但《拜月亭》并非如此。
根據沈徳符的記載,在此案中,有代為解者出示坊間刻本《拜月亭》,認定兩句反詩是“《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即反詩非王士骕自創,因此“諸公子獄始漸解”。筆者查閱相關史料發現,事實并非如此,《拜月亭》的全本和選本中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過這兩句曲詞,也不存在因此案牽連而進行改動、刪減的可能性,由此可以認定,這兩句反詩并不是出自《拜月亭》。迄今所知,兩句反詩最早的出處,是明人傳奇小說《龍會蘭池錄》。由于《龍會蘭池錄》和《拜月亭》的主人公都是蔣世隆,情節亦大體相同,所以很有可能是沈徳符混淆了,以致記載失誤。筆者認為,伍袁萃當時為解救王士骕而出示的坊本可能是《龍會蘭池錄》,而非《拜月亭》,之所以流傳成《拜月亭》中的詞曲,是受了沈徳符《萬歷野獲編》記載的影響,后人才依了此說。更確切地說,是沈徳符的記載失誤,才導致了王士骕《拜月亭》詞曲案的說法,稱為王士骕《龍會蘭池錄》詞曲案或許更準確。
二
作為古代戲曲史上的公案,明清兩代的曲論及史料筆記中多有關于此案的記載。沈徳符《萬歷野獲編》“詞曲·拜月亭”條云:
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為江南撫臣朱鑒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為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朱已去任,有代為解者曰:“《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為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2]
根據沈氏的說法,新舊《拜月亭》刻本中俱無此一聯,是因為人們害怕連累,將其削去,或云《拜月亭》中初無此詩,解紛者救人心切而進行了編造。伍袁萃是指出這兩句“反詩”出處的人,他的記載最真實可信,也最能說明問題,《林居漫錄》中云:
史譏霍子孟不學無術,以致滅宗,故肩巨任重者學術尚矣。往吳中諸貴游子相聚為兒戲,而二三惡少乘機簸弄其間,一獄吏治之足矣,而朱鑒塘處以謀反,聞當國者議用兵章下兵部,適予差竣回京,本兵石公問故,予具言其狀,公駭曰:“奈何言若是朱鑒塘疏,載有反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非確證耶?”予曰:“此詩見傳奇中,乃蔣世隆因屠瞞興福投己而作耳。”公曰:“有刻本乎?”予取以示之,公嘆曰:“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幾誤大事。”因問:“作何處置?”予曰:“廟堂自有石畫,但愚意不若行撫按再勘。”公從之,反,卒無驗,江南獲安。然則學術豈獨在經史哉?即稗官小說,亦不可廢也。[3]
伍氏是此案的目擊者和解紛者,他認為此案是“不學無術”導致的,性質并沒有嚴重到要因此而人人自危、刪改詞曲的地步。主管官員石公的態度亦是如此,即“反詩”一事的主要責任方不在王士骕,而是朱鑒塘“不學無術”導致的誤會,性質并不惡劣,只要指明出處,便可消除誤會。
從上述記載中,我們不難發現,沈徳符和伍袁萃對此案的定性截然不同。清人褚人獲《堅瓠集》八集卷二中的“豪放賈禍”條也有關于此案的記載,可能是時間相距較遠的關系,清人不用諱飾,所以對此案的來龍去脈、個中原委都記載得比較詳細,茲錄如下:
萬歷乙未,吳人以關白未靖,在位者皆謹備之。王鳳洲仲子士骕,延陵秦方伯耀,弟燈,云間喬憲長敬懋子相,俱自負貴介。士骕能文章;燈善談;相善書翰。各有時各,互相往來,出入狹邪。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立無前功者。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引以自重,每佩劍游酒樓博場,皆與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乃泛泛投刺富人曰:“吾曹欲首事,靖海島寇,貸君家千金為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或數十金,不則輒目懾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剿汝矣!”蓋意在得金,姑為大言恐之。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為必且率其黨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為亂,巡撫朱鑒塘(洪謨)檄有司擒治之,以事聞于朝。疏載反詩,有“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句。下兵部議,伍寧方(萃)言于本兵石星,此二句乃《幽閨記》中語,何得為證?下撫按,勘問,鞫之無實。其后論州平及燈死,士骕戍,相配,人咸以為冤。成疑獄,久系。鳳洲有奴胡忠者,善說平話,酒酣,輒命說列傳,解客頤。每說唐明皇、宋藝祖、明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自古已然。士骕攜忠至酒樓說書侑酒而閭閻乍聞者,輒曰“彼且天子自為”,以是并為士骕罪,目之為叛,不亦過乎?然亦由士骕等自恃高門大閥,交游非類,以至于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柳玭所云“毋恃門第”,兢兢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有殺身之禍,以貽父母之憂哉。[4]
除了時間上與沈徳符的記載誤差兩年外,①關于此案發生的時間,有兩種說法,沈徳符記載是萬歷癸巳(萬歷二十一年),王永寬主編《中國戲曲通鑒》、丁淑梅《中國古代禁毀戲劇史論》持此說;徐復祚《花當閣叢談》、許自昌《樗齋漫錄》、褚人獲《堅瓠集》記載是萬歷乙未(萬歷二十三年);周文認為海警爆發于萬歷二十一年,王士骕下獄發生在萬歷二十三年,現依周說。褚氏分析的原因與周文完全一致。根據筆者的統計,后世著作中記載過此案的有如下十種(不包括王士骕《中弇山人稿》):沈徳符《萬歷野獲編》、江盈科《雪濤小說》、徐復祚《花當閣叢談》、伍袁萃《林居漫錄》、許自昌《樗齋漫錄》、談遷《棗林雜俎》、褚人獲《堅瓠集》、嘉慶《直隸太倉州志》、程穆衡《婁東耆舊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遠壬文一卷》。這些記載基本上都與褚人獲相同,仔細比對發現,王士骕下獄的最初起因并不是“反詩”,而是“交游非類”,胡忠的平話表演和“反詩”都只是后面才附會出的謀反證據。也就是說,在周文分析的四個因素中,根本起因是王士骕“交游非類”,其次才是胡忠的平話表演和“反詩”證據。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僅提及“交游非類”,《雪濤小說》《樗齋漫錄》《花當閣叢談》和《直隸太倉州志》中都未提及“反詩”出自《拜月亭》(或幽閨記)詞曲之事,并不是江盈科、徐復祚、許自昌等害怕惹禍上身而故意不記載(同時期的伍袁萃、沈徳符都詳細記載過),而是很有可能“反詩”一事在當時更像是一場鬧劇,只要指明出處,便可消除誤會,并未在當時造成極大的影響,在此案中也不太重要,所以就都沒有記載。如若嚴重至極,主管此案的石星看了伍袁萃出示的坊本后,也不會發出“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幾誤大事”的感慨。再者,如果真是反詩,憑伍袁萃、王稚登幾人之力恐怕根本不可能解救。可見,“反詩”并不像沈徳符記載的那樣,有如此大的影響,更多的是當成了因無知上演的一出鬧劇,還沒有嚴重到需要人人自危的地步,以致要去刪改詞曲。
三
沈氏言“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筆者認為,此說法并不成立。
首先,根據上文種種記載對此案的定性,我們可以推斷,反詩之事的性質并不嚴重,這種近乎鬧劇式的表演還不至于要人人自危,刪改詞曲。
其次,查閱現存《拜月亭》全本、選本及地方戲改本,均未發現這兩句反詩。如果說案發后的出版物可能會被刪改,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案發之前的出版物自然是不可能受到影響的。此案發生于萬歷二十三年,現存有兩個版本的《拜月亭》在案發前就已出版,嘉靖三十二年的《新刊摘匯奇妙戲式全家錦囊拜月亭五卷》(簡稱《風月錦囊》)和萬歷十七年金陵世德堂的《新刊重訂附釋標注月亭記》(以下簡稱世本),兩本均未發現這兩句反詩。如果說《風月錦囊》是選本,可能沒有選錄的話,世本是全本,則不至如此。當然,現存的世本《拜月亭》沒有這兩句反詩,也不是案發后人們改動所致。因為世本是雕版印刷,而且是一版一印,全書干凈整潔,沒有大小字錯誤挖刻的地方,亦找不到挖改和涂抹這兩句詩的痕跡,可知世本中初無這兩句曲詞。通觀南戲《拜月亭》流傳至今的十一種全本、三十多種選本以及各種地方戲,②綜合車錫倫、俞為民、王湘瓊、徐宏圖、王良成、朱崇志等人的統計,全本有11 種,選本有30 種。均未發現有“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兩句曲詞。
再次,《拜月亭》中也沒有與這兩句詩風格一致的唱詞或曲白,上、下場詩亦是如此,將其插入任何地方都與全書的風格不一致。
另外,以四大南戲在明代的普及情況,朱鑒塘等人不太可能沒有接觸過,如果“反詩”真是出自《拜月亭》,應該是可以察覺的,不至于鬧出如此大的“誤會”。由此可以推斷,《拜月亭》中自始至終就沒有這兩句詩,也不存在因此案而進行改動、刪減的可能性,疑是沈氏記載失誤。兩句反詩可能并非出自《拜月亭》,而是另有出處。
四
雖然《拜月亭》中沒有這兩句反詩,但也不是如沈氏所言,伍袁萃等為了解救王士骕進行了編造。因為兩句反詩可以找到明確的出處,且在案發前就已存在,應非案發時刻意捏造。迄今所知,兩句反詩最早的出處,是明人傳奇小說《龍會蘭池錄》。《龍會蘭池錄》收錄在《國色天香》和《繡谷春容》(全名《繡谷春容騷壇摭碎嚼麝譚苑》,收錄的是《龍會蘭池全錄》,與《龍會蘭池錄》只有個別字的差異)中。《國色天香》是一部日用類書,共選錄了二十二篇文言小說,分為十卷,卷一題“新刻京臺公余勝覽國色天香”,其余九卷都題“新鍥幽閑玩味奪趣群芳”。《龍會蘭池錄》中開篇即是蔣世隆與蒲祿興福的贈和詩,詩云:
水萍相遇自天涯,文武崢嶸興莫賒。仇國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膽作朱家。
蛟龍豈是池中物,珠翠終成錦上花。此去從伊攜手處,相聯奎璧耀江華。[5]
“仇國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膽作朱家”與“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僅有數字之差。從表達上看,并無二致;從內容上講,均可列入“反詩”行列。由此可以推斷,此案所指的兩句反詩可能與此有關,而《龍會蘭池錄》也可能就是兩句“反詩”的真正出處,①嚴敦易《〈拜月亭〉和〈龍會蘭池錄〉》和王永寬、王剛《中國戲曲史編年(元明卷)》也認為兩句“反詩”出自《龍會蘭池錄》。亦可進一步認定伍袁萃等人出示的坊本可能就是《龍會蘭池錄》。
首先,就時間而言,《國色天香》初版于萬歷十五年,萬歷二十五年周曰校再次出版,《繡谷春容》也于同年出版,后又再版。此案發生時,《國色天香》已出版數年了,《繡谷春容》是案發后二年才出版的。根據日用類書在明代受歡迎的程度,以及《國色天香》的再版情況,可知《龍會蘭池錄》在當年是有相當受眾面的,伍氏完全有可能看到,并以此點明反詩的出處。
其次,就內容而言,《國色天香》在案發之前就已流行,初版的《龍會蘭池錄》中就有“仇國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膽作朱家”兩句詩,說明反詩確系有出處。萬歷二十五年再版時,離案發后僅二年時間,但兩句“反詩”并未刪除,說明此案中反詩的影響并不嚴重,根本無需刪削詞曲。如果說《國色天香》刊行時用的是舊有刻板,再版印行時沒有改動,不能證明沒受到案件影響的話,那么完全可以從《繡谷春容》的出版中得到印證。《國色天香》和《繡谷春容》的版式是完全不同的,《國色天香》中的《龍會蘭池錄》有插圖,《繡谷春容》中沒有,字體也不一樣,可知不是同一套雕版的再印之本,《繡谷春容》應是重新開刻的,并不是用《國色天香》的舊有刻板。《繡谷春容》初版于萬歷二十五年,考慮當時刻工的速度,刊刻時應該離案發時間比較接近,但是出版時并未受到此案的影響,兩句“反詩”依然赫然在列,可見因害怕惹禍上身而刪改詞曲的說法不成立。
再次,《國色天香》和《繡谷春容》都屬于日用類書,因為適應民情,所以在當時銷售很好,流傳較廣,伍袁萃等人閱讀過《龍會蘭池錄》并用來作證亦屬常理。謝友可《刻公余勝覽國色天香序》中云:
今夫辭,寫幽思,寄離情,毋論江湖散逸,需之笑譚,即縉紳家輒藉為悅耳目。具劂氏揭其本,懸諸五都之市,日不給應,用是作者鮮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計哉![6]
序中言及《國色天香》的銷售情況極其火爆,以致“日不給應”,雖不免夸張,亦可窺一斑。萬歷十五年的初版售馨后,二十五年周曰校再次出版,《繡谷春容》也于同年出版,后又再版。兩次出版說明《國色天香》在當時的傳播較廣,但畢竟流傳時間不長,所以影響力遠不及《拜月亭》,朱鑒塘等人并未閱讀到,一直產生了“誤會”。
五
依上文所言,則又涉及到一個問題,既然伍氏是示書之人,何以他的記載又不直接點明書名呢?根據伍氏記載,言“此詩見傳奇中,乃蔣世隆因屠瞞興福投己而作耳,公曰有刻本乎?予取以示之,公嘆曰: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幾誤大事,因問作何處置?”伍氏既已出示坊本,不可能不知道所示之書的名字。筆者推測,伍氏沒有直接言明出自哪部傳奇,很有可能就是依據的本子是《龍會蘭池錄》的原因。
首先,伍氏所言“蔣世隆”“屠瞞興福”與《拜月亭》中的“蔣世隆”“陀滿興福”和《龍會蘭池錄》中的“蔣世隆”“蒲祿興福”都是有出入的。以四大南戲在明代中后期的流傳情況,伍氏不太可能沒讀過,如果依據的是《拜月亭》,那么深入人心的故事的主人公應該不會記錯,可能是受了《龍會蘭池錄》中“蒲祿興福”的影響,才記成了“屠瞞興福”,以致于與兩本書都不一致。《龍會蘭池錄》這種文言小說伍氏看看就過了,記憶可能并不深刻,所以記載時名字出現了差錯,但他肯定知道這與《拜月亭》的人物名字是不一樣的,這才記成了“屠瞞興福”,不記具體書名大概亦由于此。
其次,《國色天香》共選錄了二十二篇文言小說,分為十卷,卷一題“新刻京臺公余勝覽國色天香”,其余九卷都題“新鍥幽閑玩味奪趣群芳”,題名上的不統一也可能使伍氏記憶模糊,以致沒記。
再次,小說的格調不高,一般士大夫不便染指,所以沒記具體名字。翻閱全書,我們不難發現,此書近乎是一部淫書。(《國色天香》被列為中國十大禁書)如書中云:“瑞蘭將堅晉鄙,但玉符既竊,鐵錐又至,一夜花城,兵將折沖,似不能支。時有口占詩詞甚多,聊記一二,以表龍會蘭池之行實云”,此段幾乎是性交場景的實錄。以伍袁萃士大夫的身份而言,是不太可能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及此類著作的。
伍氏記載的朦朧態度,讓我們更加有理由相信其所出示的坊本可能就是《龍會蘭池錄》。如果是《拜月亭》的話,不至于會有記憶不清或混亂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禁忌,也就不會出現欲言又止、云山霧罩的情況了。而且,也只有這種不入流的小道之言,官方才不會仔細推敲書中文字的含義,如果格調較高,則又另當別論了。
正是由于伍氏的欲言又止,才使關于此案的記載從《林居漫錄》流傳到《萬歷野獲編》時,被沈徳符將反詩的出處坐實了。從現存記載看,首次明確認定此案反詩出自《拜月亭》的是沈徳符的《萬歷野獲編》。在伍氏的記載中,只言“此詩見傳奇中”,并未具體言明出自哪部傳奇。同時期的《雪濤小說》《樗齋漫錄》和《花當閣叢談》也都有關于此案的記載,但連“反詩”一事都未提及,《萬歷野獲編》初次指明“反詩”出于《拜月亭》,此后的記載才都依了此說。《萬歷野獲編》中有關于《林居漫錄》的比較詳細的說明,可知沈氏是讀過此書的,很有可能就是通過伍氏所言推斷此傳奇為《拜月亭》。因為《龍會蘭池錄》和《拜月亭》都是寫蔣世隆的故事,且故事原型都非常接近,沈徳符將兩者相混淆,誤認為是《拜月亭》,以致記載錯誤。而《拜月亭》也因沈徳符的記載而與此案發生聯系,并因四大南戲在民間的廣泛傳播和接受,在明清禁毀戲曲史上成了顯著案例。
綜上所述,在王士骕《拜月亭》詞曲案中,“交游非類”是根本原因,反詩是因朱鑒塘“不學無術”而導致的一場鬧劇,性質并未惡劣到要刪削詞曲。《拜月亭》的全本、選本中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過那兩句反詩,亦無刪削之說。迄今所知,兩句反詩最早的出處是《龍會蘭池錄》。種種細節的一致性,表明伍袁萃所出示的坊本很有可能就是此書。之所以會演化成《拜月亭》詞曲案的說法,是由于伍袁萃的欲言又止,使得沈徳符在記載此案時,根據自己的推斷將反詩的出處坐實了,并加重了反詩的嚴重程度,以致放大了此案在禁毀戲曲史上的影響。
[1]周鞏平.王士骕《拜月亭》詞曲案考[J].戲劇藝術,2009(3):85-90.
[2]沈徳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59:646.
[3]伍袁萃.林居漫錄:別集一卷[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子部第242 冊.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濟南:齊魯書社,1995:476.
[4]褚人獲.堅瓠集:八集卷二[M]∥《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第1261 冊.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88-289.
[5]吳敬.新刻京臺公余勝覽國色天香:龍會蘭池錄[M]∥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6.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8.
[6]謝友可.刻公余勝覽國色天香序[M]∥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6.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