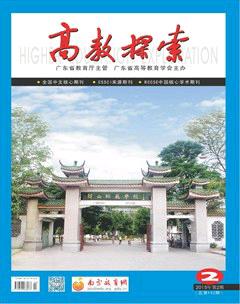美國高校服務學習模式述評
黃孔雀
摘要:近20年來,服務學習成為美國高等教育體制中重要的新教學模式,是美國高校改善教育教學的有效策略,在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受到重視。本文就美國高校服務學習的歷史發展作簡要概述,圍繞服務學習的模式展開分析與評價,以了解美國服務學習的現狀并獲得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服務學習;高校;美國
20世紀60年代美國高校掀起社區服務和公共服務的熱潮,強調知識學習與社區真實需要相結合的“服務學習”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模式誕生了。80年代,校園聯盟(Campus Compact)等服務學習研究機構的成立為高校把有效的服務與學習聯接起來提供保障,推動服務學習的相關研究和發展。90年代,在美國政府頒布的《國家和社區服務法案》和《國家服務信任法案》支持下,服務學習獲得了蓬勃發展,大量的研究成果被發表,證實了服務學習對高校、學生、教師以及社區產生的積極影響。近年來,服務學習在當今教育體制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展,高校在課程計劃中引入服務學習模式已成為趨勢,高校不同的學科融入服務學習以實現教學目標這一趨勢已經被廣泛接納并付諸實施。自此,服務學習成為美國高等教育體制中重要的新教學模式。此外,服務學習從美國擴展到澳大利亞、南非、北美、西歐以及中國香港、臺灣等地區,發展成為國際性的高等教育改革運動。對美國高校服務學習的研究和梳理,有利于我們了解美國服務學習的現狀,希望我國高校的教育教學改革能借鑒吸收服務學習的經驗并有所啟示。
一、服務學習的歷史發展
服務學習是培養社會責任感、公民意識和社交能力的一種教學模式,通過社區服務,把掌握的知識和技能與社區實際相聯系,反思服務過程并獲得成長的機會。服務學習是經驗教育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的形成與發展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需求。分析概括近半個世紀服務學習的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萌芽階段(20世紀60年代)。服務學習的實踐探索始于20世紀60年代。60年代的公民權利運動、1961年志愿服務組織“和平團隊”(Peace Corps)和1965年“美國志愿者服務計劃”(VISTA)的成立都積極號召青少年參與服務活動,并為青少年提供在真實世界中發揮自身作用的機會。1967年,羅伯特·西格蒙(Robert Sigmon)和威廉·拉姆斯(William Ramsey)在南部地區教育委員會的報告中首先使用了“服務學習”這一詞語。這標志著服務學習這種溝通課程學習和社區服務的教育現象正式誕生。[1]1969年由南部地區教育委員會、亞特蘭大市政府、亞特蘭大城市聯盟、和平協會等聯合發起組織的服務學習會議討論了服務學習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重要性,并達成了三點共識:高校必須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確保課程學習是服務的必要組成部分,并對服務中的學習給予認可;高校、團體組織、聯邦和州政府必須為學生提供參與服務學習的機會和專項資金;學生、教師必須參與服務學習的規劃和實施過程。[2]這次會議所倡導的理念一直延續至今。
第二,興起階段(20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為鼓勵大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各高校成立了不同類型的校園組織。70年代早期的“大學行動組織”(University Year for Action)、1984年校園擴展機會聯盟(Campus Outreach Opportunity League)、1985年由大學校長組成的校園聯盟的成立有力地推動大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對服務學習的推廣和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1986年,青少年服務美國協會(Youth Service America)成立,青少年從中獲得了服務的機會。1989年服務學習的實施原則公布,促進了服務學習運動的蓬勃發展。
第三,學科化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大力支持推廣服務學習。1990年布什總統簽署《國家和社區服務法案》,推動各高校支持開展服務學習。1992年,馬里蘭州成為第一個要求高校學生必須參加服務學習才能畢業的美國州政府,馬里蘭州教育委員會采取強制性措施實施服務學習初見成效。1993年,克林頓總統簽署《國家服務信任法案》,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服務學習的地位并為服務學習提供資金支持。服務學習教學模式在提高學生學業成績、培養學生公民責任感、有效溝通專業學習與社區服務等方面效果顯著,得到了各高校的廣泛推崇。2001年10月,首屆服務學習國際研討會在柏克萊召開,相關研究者和實踐人員展示了服務學習在中小學教育、教師教育、高等教育等領域的突破性進展,把研究焦點從融合在課程中的學生服務活動逐漸轉移到服務與學科學習相結合。各高校成立服務學習辦公室,制定服務學習的實施原則與步驟,并對各高校實施服務學習的模式進行了探索與研究。服務學習融入高校課程即學科化,并逐漸成為聯接學生事務與教學事務的橋梁,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一項重要策略。
二、服務學習的模式
政府高度重視學生公民意識的養成,民眾希望高校為學生提供更豐富的生活經驗,這兩大潮流推動著服務學習在美國的發展。近年來,服務學習不斷融入高等教育環境,作為有效的教學模式在不同的學科中得到推廣和應用。為了保證服務學習的有效性,服務學習研究人員和相關機構對服務學習的實施步驟、實施過程中應遵守的基本原則、服務學習的實施模式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加深了對服務學習的理解。
由于學者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教育哲學觀以及高校各異的學術文化特征,對服務學習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各高校在服務學習運作中也形成了多種模式。從實施類型來看,服務學習主要有課外型和學科型;從課程要求來看,服務學習有必修課和選修課兩種類型;從培養目標與側重點不同來看,服務學習可以分為慈善模式、公民參與模式和社群模式;[3]從服務學習與課程的關系來看,服務學習可以分為一次性和短期的服務學習、連續的課外服務學習、課程中的服務學習、集中的服務學習四種模式。[4]從服務學習融入課程的方式來看,服務學習可以分為輔修模式(add-on model)、關聯模式(linked model)、靈活學分制模式(variable credit model)、完全整合模式(total integration model)。[5]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布朗大學的學者凱瑞薩·赫弗蘭(Kerrissa Heffernan)的劃分模式,她將服務學習視為課程,并把服務學習劃分為六大模式,眾多的服務學習模式都可以囊括在這六大模式中。[6]
(一)“純”服務學習模式
“純”服務學習(“Pure”Service-Learning)把服務作為課程的主要內容,要求學生走入社區從事服務活動,以培養學生為社區服務的意識為核心,有效地貫通課程學習與社區體驗。但是,“純”服務學習受到教師的質疑。第一,該課程的內容是服務學習、志愿服務與公民承諾等,這些內容無法通過純理論的方式講授。第二,給予學生學分太容易。教師認為服務學習中的反思并不是真正的探究,只是一些簡單的對話,而這些只是給予學生學分的借口。第三,這一模式可能導致服務學習的邊緣化。教師由于時間、精力、學科教學任務等各種要素的影響,在規劃服務學習課程的內容和方式等方面難免有所紕漏。
(二)學科本位服務學習課程模式
學科本位服務學習課程(Discipline-Based Service-Learning Courses)規定學生整個學期在社區從事服務活動,并定期對他們的服務學習體驗進行反思。反思貫穿于整個學期,以課程內容為基礎,在反思中深化對服務學習體驗的分析與理解。這一模式要求課程內容與社區體驗的聯接要明確具體。但是,要求越具體明確,可供選擇的社區類型就越受限制,這就導致教師在選擇服務學習場所時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在交通、后勤以及服務學習的管理方面增加了難度。
(三)問題本位服務學習課程模式
問題本位服務學習課程(Problem-Based Service-Learning Courses)以特定的社區問題和社區需求為出發點,學生與社區成員共同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案。學生利用已掌握的知識為社區提供建議或解決問題的策略。學生或學生團隊服務于社區就像“咨詢人員”服務于“客戶”。比如建筑系的學生可以為社區設計一個公園;電子商務系的學生可以為社區制作專門的網站;植物學家可以辨認非本土的植物,并向社區提供根除這種植物的方法。學生需要一定的時間考察社區,才能發現社區存在的問題,同時學生要協調自己的時間安排來制定應對策略。但是,這一模式試圖限制學生進入社區的次數以解決面臨的后勤問題。限制學生進入社區的時間與次數會導致兩大問題:一是限制學生了解真實的工作環境和社區現狀,降低了學生制定的應對策略在解決社區問題方面的效用;二是導致學生是“專家”、社區是“救濟對象”觀念的形成,進而造成“高校是用與世隔絕的方法來了解和認識世界”的不良印象。
(四)高峰體驗課程模式
高峰體驗課程(Capstone Courses)通常分為主修課程與輔修課程兩種形式,是專門為高年級學生或優秀的低年級學生設計的。學生要將課程中習得的知識與社區的服務工作相結合,以達到探索新研究話題和加深對學科知識理解的目標。高峰體驗課程為學生提供了溝通理論世界和實踐世界的獨特方式,幫助學生更多地接觸專業知識并積累個人經驗。高峰體驗課程面臨著學生的人員配置問題。大四這一學年是實施高峰體驗課程的較好時機,學生能運用他們的知識技能來解決社區的問題,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又獲得新的知識。參與高峰體驗課程的學生,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用于研究與實踐,在參與過程中習得具體的技能。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學生往往是帶著寶貴的知識以及對社區的深刻見解畢業或離開社區的,而這些知識和見解是無法簡單復制的,造成了服務學習的間歇性斷層。
(五)服務實習模式
服務實習(Service Internships)與傳統的實習相似,但服務實習比傳統實習更密集,要求學生在社區一周工作10~20小時。服務實習與傳統實習的共同點是學生對社區或實習場所重視的工作本身充滿激情;不同的是服務實習課程通過定期、持續的反思幫助學生運用學科理論知識分析他們獲得的新經驗。反思可以是小組朋輩共同反思、與教師一對一的交談或與提供反饋信息的教師進行網絡交流。此外,服務實習更強調社區與學生從服務經歷中平等受益,即互惠。
(六)大學生社區本位行動研究模式
大學生社區本位行動研究(Undergraduate Community-based Action Research)是一種較新穎且受大眾歡迎的新模式,參與者主要是少數具備豐富社區工作經驗的學生。這些學生具備時間管理能力,能進行自我指導學習,并具備與不同的社區進行談判交涉的溝通能力。該模式作為學生獨立的研究方向,學生在實施過程中立足社區的重大問題,作為社區擁護者與教師密切合作,該模式重視學生對研究方法的學習。
三、簡要評價
近年來,服務學習作為教學模式在全球范圍內不同層次的院校和學科領域廣泛推廣與實施。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德國、印度、愛爾蘭、意大利、南非、西班牙、泰國等國家通過召開服務學習的論壇、峰會等形式,掀起了服務學習的研究與實踐熱潮,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校園聯盟就羅列出人類學、城市規劃等48個不同學科的300多項示范性服務學習的操作綱要。服務學習在不同的教育環境、不同的學科領域開展,要適應如此復雜多變的環境,服務學習必須具備成功的條件和一些共同特征。特別要強調的是,高校與社區的伙伴合作關系的構建是服務學習順利開展和取得成效的重要影響因素。
(一)服務學習成功的三要素
服務學習是聯接課程學習與社區實踐的橋梁,有效的服務學習對學生、教師、高校以及社區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追求優質、高效的服務學習是各研究人員與實踐者的目標。實踐證明,成功的服務學習必須具備3R,即真實性(Reality)、反思性(Reflection)與互惠性(Reciprocity)。[7]
1.真實性。在對現代高等教育的批評中,呼聲最高的是認為學生缺乏真實的生活經驗,習得的知識技能難以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而服務學習將學生放置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通過運用知識技能來解決社區的真實需要。學生的經驗來源于真實的服務活動,面臨的問題解決方案是沒有定論的,而是建立在深入觀察與分析社區的實際狀況基礎之上的。學生個人的能力與見識是牢牢建立在真實的學習任務與環境基礎上的,成為最可預見的服務學習成果。
2.反思性。反思性是服務學習的核心原則,也是服務學習區別于志愿活動、社區服務和慈善活動的標志。反思貫穿于服務學習的全過程,是學生的應用技能轉化為知識的工具。反思是整合新舊知識的一種方法,通過反思學生不斷地產生“為什么”的疑問,有助于學生提高自我效能感,促進個人發展和公民責任感的養成。學校和社區必須為學生提供一個固定的時間進行反思,反思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如討論、撰寫心得、學術報告等。
3.互惠性。互惠是服務學習最本質的特征。互惠是服務學習關系網絡中提供者與接受者之間供給與需求的相互關系,這種互惠關系避免了如慈善活動只是傳統的單向給予的傾向。學校與社區相互協調,實施豐富多彩的服務活動,以滿足學校和社區的需要,學校和社區間互相協作,教師、管理者、學生和社區之間形成良好的伙伴關系。被服務的社區與提供服務的學校、學生一起制定目標,共同決定服務活動的方式。服務學習承認學校與社區雙方需求的重要性,雙方相互交換資訊,分享服務學習的成果,共享資源,建立平等互惠的關系,有利于雙方的共同發展。
服務學習對學生、教師、學校、社區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如果在制度、規劃等方面處理不當,服務學習也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負面影響。近幾年來,不少學者發現多種因素導致服務學習產生了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服務學習隱藏了復雜的動機;服務學習建立在簡單理解服務涵義的基礎上;服務學習誤解了社區的真實需要;服務學習對社區真實的需要做出了錯誤的回應;服務學習把注意力轉向了志愿者行動;服務學習分散了社區的工作精力。[8]據目前的研究成果顯示,一些因素限制了服務學習的效果。第一是服務學習受到其本質要求的制約,學生必須按照高校制定的計劃進行服務。第二是服務學習還受到學習課程、交通、個人承諾等問題的制約。第三是安全和責任問題縮小了學生可供選擇進行服務的主題。第四是教師的時間分配問題,除了正常的教學任務外,教師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服務學習課程的開發和研究;很多教授是學科領域的專家,但是在社區服務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就顯得力不從心。此外,當服務學習與課程結合進行時,服務學習活動必須與課程目標相互適應,但是多數學生缺少與他人協作的經驗,服務活動中遇到的問題也是學生在生活中較少遇見的。甚至,服務學習會對個體產生一些傷害,特別是在活動中的合作伙伴。學生到社區進行服務學習,一段時間后服務學習結束,合作伙伴之間的關系也就隨之停止。對于學生來說,服務學習中的合作伙伴關系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短期的關系會給學生帶來創傷,進而造成學生不恰當地批判社區的實踐和政策,容易形成學生、學校、社區三者之間的惡性循環。
(二)“高校—社區”伙伴合作關系的重要性
建立在堅實的伙伴合作關系基礎上的優質服務學習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益。可以說,“服務學習和伙伴合作關系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作為一種新的教學模式,服務學習不能局限于課堂、學科或校園內,應建立在真實、民主、互惠的伙伴合作關系基礎之上,合作伙伴可以是其他高校、中小學、社區、政府部門或非政府組織。[9]高校要在滿足社區真實需要基礎上開展服務學習,社區與高校之間應是平等、互惠的關系。因此,高校與社區的伙伴合作關系是高校應首要處理的關系。高校與社區建立有效的伙伴合作關系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選擇合作方(學校、青少年服務組織、非營利性組織、企業、個人)并確定合作目標、服務目標和學習期待;了解服務者的類型、興趣、才能和掌握的資源;了解合作方的計劃、活動及使命;評估雙方共同關心的需求、確定主要聯絡人、選定學生協調人、提前參觀社區;建立由學生、青少年志愿者、非營利性組織、高校及其他成員組成的咨詢委員會;根據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情景重新規劃高校與社區的關系。[10]高校與社區建立伙伴合作關系應遵守以下原則:雙方協商伙伴合作的目標、任務與成果;雙方的關系強調互信、尊重、真誠;雙方關系突出各自優勢,同時關注需改進的領域;伙伴關系權衡合作方的權利以確保資源共享;雙方開放、明確地交流,及時了解對方的需求;合作方共同確定伙伴合作關系中的角色、規范與過程;合作方共同推進伙伴合作關系成效的實現;伙伴合作關系須不斷發展與改進。[11]伙伴合作雙方在互信基礎上,共同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實現共同愿景,以達到雙方共贏。
(三)高校政策的強有力支持
服務學習并非志愿服務,不是附加于現存的高校課程,也不是為畢業而設定的硬性指標,更不是作為處罰的手段。服務學習的獨特之處在于通過提供服務促進社區發展,同時也對參與者的學習、社交能力、公民責任意識等產生影響。服務學習的成效離不開高校在政策、資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研究表明,優質的服務學習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特點:第一,服務學習在高校重大戰略規劃與培養目標等文件的制定中起顯著的導向作用。同時服務學習的經費必須充足、穩定,不僅僅是依靠贊助或其它一些彈性資金,而應占高校經費預算的一部分。第二,高校制定明確的政策支持服務學習。如參與服務學習成為教師職位晉升或職稱評審的要求,參與服務學習成為學生畢業的必要條件。第三,院校領導層對服務學習的大力支持。如校長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強調服務學習,職能部門高層管理者與不同學科的專業教師的參與,對學生領導者的支持。第四,認可并獎勵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與教師。如校園媒體定期報道服務學習;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成效應在成績單中有所體現;優秀的學生可以獲得服務學習獎學金、獎狀以及畢業榮譽徽章;合格的服務學習指導教師可以獲得崗位津貼,減少工作量讓教師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服務學習課程開發,優秀教師還可以獲得教學與研究優秀獎。第五,擁有牢固的外部關系網。高校實施服務學習過程中,與其它組織如社區、中小學、非營利性組織、企業、政府部門都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合作關系,形成了持續性的互信共贏的關系。[12]相反,組織不力的服務學習也有一些共同特點:服務學習處在高校政策、規劃與實踐的邊緣;服務學習資金不足;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與教師感到被邊緣化,從院校的主體中被孤立;服務學習課程與它的影響并未被廣泛理解與采納;外部關系單一不協調。
參考文獻:
[1]游柱然.論美國高校服務學習的起源與發展[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9,8(3):61-64.
[2]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learing house.History of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EB/OL].http://www.fsu.edu/~flserve/resources/resource%20files/History_of_SL_in_HE_FINAL_May08.pdf,2013-10-16.
[3]郝運,饒從滿.美國高校服務學習理論模式初探[J],比較教育研究,2009(11),59-63.
[4]劉寶存,王維,馬存根.美國高等學校的服務學習[J],比較教育研究,2005(11),45-46.
[5]Oates,Karen K.Integr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ervice Learning into the Curriculum[EB/OL].http://eric.ed.gov/?id=ED403855,2013-10-26.
[6]Heffernan K.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at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2011,119(1):2.
[7]Kenworthy-Uren A.L.A decade of service-learning:A review of the field ten years after JOBEs seminal special issu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81(4):811-822.
[8]Eby J.W.Why service-learning is bad[J].Retrieved January,1998(26):2006.
[9][11]Jacoby,Barbara,and Associates.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service-learning[M].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3:6-14.
[10]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learinghouse.Building Effective Partnerships in Service-Learning[EB/OL].http://www.servicelearning.org/instant_info/fact_sheets/tribal_facts/partnerships,2013-11-26.
[12]Jacoby B.Partnerships for service learning[J].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1999(87):19-35.
(責任編輯陳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