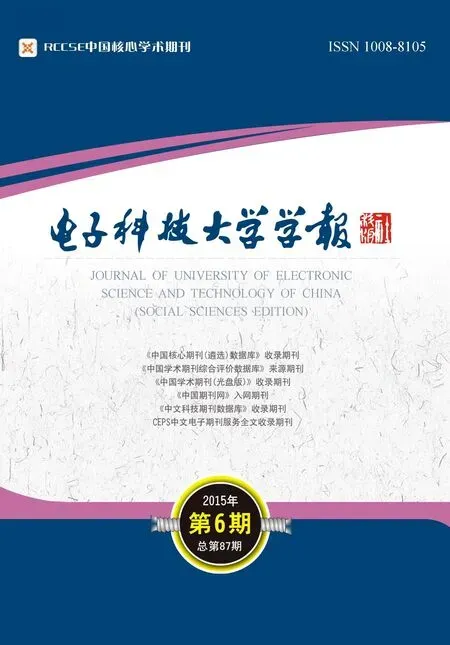貧困女性化內涵、成因及其政策思考
□寧滿秀 荊彩龍
[福州大學 福州 350108]
貧困女性化內涵、成因及其政策思考
□寧滿秀 荊彩龍
[福州大學 福州 350108]
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的提高并沒有減緩女性貧困化的程度,反而使得女性不得不承擔市場勞動和家務勞動的雙重責任。基于對家庭的照顧責任、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以及職業隔離、在經濟上對男性的依賴三個層面分析貧困女性化的原因,通過研究女性貧困化的內在作用機理,探討在社會運行過程中貧困女性與社會相互建構的機制, 以期構建適當的社會保障體制,以便緩解女性貧困化,改善貧困女性與社會的關系, 促進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貧困女性化;照顧責任;性別歧視;經濟依賴
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貧困人口極大減少,貧困率也大幅度下降。但在總體貧困減緩的背后,貧困越發呈現女性化的趨勢。到2012年,按照新的國家扶貧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總數為9899萬人,其中超過50%是貧困婦女。《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報告2011》顯示,2010年在國家扶貧重點縣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中,女性人口貧困發生率為9.8%,比男性高出0.4個百分點。眾所周知,貧困人口并非均質的而是存在著性別上的不平等,女性常常是貧困群體中的最貧困者。雖然現代社會中女性在某些領域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家庭結構和家庭規模的轉變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市場參與率的提升增強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經濟地位,但制度排斥、社會習俗等障礙卻使女性仍然處于財產結構和權力結構的邊緣。與此同時,離婚率的逐漸攀升也使得女性在家庭乃至社會中的境況并沒有多大程度地改善,反之,女性陷入貧困的概率遠遠大于男性,特別是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以及老年婦女。
據世界銀行調查數據顯示,極端貧困家庭中女性(或女童)是家庭資源分配中最終的“犧牲者”或“受害者”——世界貧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貧困者是女性(包括女童)。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貧困女性化現象越來越突出,但由于大多數學者僅關注貧困人口的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忽略貧困人口的性別差異,貧困女性化并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重視,某種程度上講,這與傳統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在傳統的研究方法里面,貧困是指家庭內所有成員共同擁有的資源總數不足以維持家庭內全體成員共同需要的一種狀態。換言之,研究者在討論貧困問題時,實際上是探討一個家庭的貧困而不是家庭內部成員的貧困。在家庭內部資源平均分配的假設下,通常我們認為家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經濟單位,家庭內部的成員彼此分享共有的資源,個別成員所擁有的資源被認為是用來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因此即便是毫無生產能力的孩子,或者是年邁的老人,也能在資源共享的原則下得到滿足。與此同時,家庭內部用來維持個人生活水準的支出,事實上也是屬于共同消費的項目,個人實際上的支出難以從家庭中抽離出來單獨計算,盡管有些消費項目如飲食穿著,勉強可以分辨每個人所花費的比例,但是其他更多的消費,特別是家庭內部的設施根本不可能區分家庭成員使用的數量。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一旦將研究焦點放置在個人身上,也就是根據家庭內部每個成員所得的多少來決定社會貧窮的狀況時,勢必將使整個社會的貧困人口數膨脹。因為社會上總有許多人沒有完全屬于自己的所得,就像沒有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殘,他們都是藉由分享家庭內部其他成員所得來滿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可見,傳統的研究方法掩蓋了家庭內部個體成員貧困的事實,對于家庭內部成員與貧困間的關系難以有清楚的輪廓,往往忽視家庭內部成員的不平等地位,一旦家庭解體或者因其他原因失去對丈夫的經濟依賴,女性照料者就會陷入嚴重的經濟貧困,成為新的貧困群體,特別是一直屬于從屬和依賴地位的老年婦女。
隨著女性主義的發展,女性主義經濟學者開始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研究貧困女性化的原因。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家庭一旦陷入貧窮,首當其沖的并非那些被認為是家庭經濟主要負責人的男性,反而是那些被視為在經濟上依賴男性的女性。與此同時,女性主義者認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未能從社會性別的角度進一步深入地分析貧困女性化的深層次原因,而女性貧困人口因其特殊性確實需要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關注。本文以貧困女性為研究對象,試圖從家庭照顧、勞動力市場、經濟依賴三個角度分析為何女性更易陷入貧困?通過研究女性貧困化的內在作用機理,探討在社會運行過程中貧困女性與社會相互建構的機制, 以期構建適當的社會保障體制,緩解女性貧困化,進而重構女性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角色, 改善貧困女性與社會的關系, 促進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一、為何女性易陷入貧困?
Jane Millar and Caroline Glendinning[1~3]指出,女性貧困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第一,女性所從事的無酬勞動得不到有效重視。許多女性為家庭所付出的貢獻(生育、照顧、家務勞動等)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無酬的“愛的勞動”。女性為家庭所耗費的精力、智慧、時間與機會成本從未轉換成實質的反饋。就算女性能夠進入勞動市場,賺取甚至和男性一樣多的薪資協助養家活口,其重要性也常被譏為家庭經濟的“零用錢”而已[4],難以換取女性在家庭中應得的尊重和決策權力。更為重要的是,女性缺乏參與家庭資源分配決策的公平機會且在資源分享上持續表現弱勢。第二,由于女性將更多的時間用在無酬勞動上,所以女性往往只能從事一些短暫性、無一定雇主的,或者是部分工時的工作,以便于女性隨時離職。女性作為非正規就業者在社會保障制度中處于劣勢[5],因為非正規就業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險覆蓋而且工資收入遠低于男性。第三,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不當。雖然女性承擔的家務勞動以及生產勞動通常在家內進行,不與市場發生聯系,但實際上無酬經濟可以為有酬經濟提供勞動力以及勞動力所需的服務,是社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簡而言之,女性的無酬勞動具有正外部性,倘若政府的社會保障制度僅對擁有勞動身份的公民給予優厚的福利待遇,從而忽視了女性的無酬勞動,無形中將會拉大男、女兩性社會與經濟條件從而使女性擁有較高的貧困風險。
誠然,女性落入貧窮的原因有遠因有近因,有顯性有隱性,絕非單因所導致。本文認為,女性在家庭中承擔的照顧責任、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利地位,包括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和職業隔離以及在經濟上對男性的依賴都是致貧風險的來源,而三者所產生的影響效果,將視其與女性作為家庭(或婚姻)“依賴者”以及經濟依賴程度互為作用而定。
(一)家庭中的照顧責任
近年來,隨著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離婚率的攀升以及經濟低迷引致的家庭內勞動力不足以賺取生活資本,更多的女性在人力資本及家庭經濟的考慮之下積極投入到勞動力市場中,但從張輝等學者針對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中發現,家庭照顧責任的牽絆仍是阻礙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重要因素。眾所周知,婦女不僅會因生育離開職場,也會因照顧家庭中的老、病、殘不得不選擇工作彈性與工資水平低的工作,或者階段性退出勞動力市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照料需求與日俱增,長期照顧體系的建構難以滿足人口老化的迫切需求,家庭照料仍然是主要的照料模式。一旦家中有老年人需要照料時,女性將成為首要的照料者。可以說,長時期的家庭照料對于女性而言難免會形成一種非自愿性的壓力源,她們被迫遠離職場與社會活動,終至成為經濟上的依賴者,與她們所照顧的對象一起成為被剝奪公民身份的弱勢中的弱勢。由此,女性被視為“無權”的群體,無法與男性一樣控制資源,缺少資源的女性無力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實現互惠。換言之,女性獲得社會資本的可能性必然小于男性,其獲得的社會支持也就必然弱于男性,更易陷入貧困[7]。誠然,兒童照顧的壓力或將隨著兒童長大而消失,老年照顧的問題也將隨著受照顧者的死亡或下一代的照顧替代而減緩,但照料過程中女性為此付出的照料成本和代價難以估量,不僅影響到女性生理、情緒和社交的健全發展,也會影響到女性老年生活的經濟收入與資產累積,增加女性暴露于貧窮的風險。無怪乎女性主義者疾呼“選擇照顧就等于選擇了貧窮”!
(二)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和職業隔離
隨著經濟轉型與經濟結構調整,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女性勞動參與率有所提升,但女性所從事的行業大多還是工資低下且具有明顯的“女性化特征”,例如美容美發、成衣、皮革、餐飲業等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相較于女性,男性多集中在石油、鋼鐵、房屋建筑、鐵路運輸等資本密集型行業。根據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顯示,18~64歲女性在業者的勞動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組。在城鄉低收入組中,女性分別占59.8%和65.7%,比男性高19.6 和31.4 個百分點;在城鄉高收入組中,女性僅占30.9%和24.4%,均明顯低于男性[8]。數據同時揭示,城鄉在業女性的年均勞動收入僅為男性的67.3%和56.0%,且不同發展水平的京津滬、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城鄉在業女性的年均勞動收入均低于男性[8]。基于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性別歧視和職業隔離,女性只能選擇兼顧照料和有酬勞動的非正式工作,通常這些工作流動性強、工資低下且沒有相應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與此同時,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會映射到女性的養老金受益水平上,一般而言,越是與繳費和就業年限聯系緊密的養老保險設計,越不利于養老金受益上的性別平等[9~10]。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也表明,在非農業戶口女性中,能夠享有社會養老保障的達73.3%,享有社會醫療保障的達到87.6%[8]。總之,以就業為基礎的社會保障程度與個人收入、生產技能、談判能力呈正相關,當以無酬照料勞動為主的婦女步入老年人行列時,社會公共政策可能難以對她們提供足夠的經濟保障,從而造成社會保障體制中的性別分層。除了勞動市場分工,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女性在家庭內的性別勞務分工。傳統性別意識型態與高度性別分工的交互作用不僅強化男性外出務工承擔家庭經濟責任,也強化了女性執行家庭照顧角色的責任。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持續影響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與發展,包括薪資水平、培訓教育、晉用、升遷、考核等措施,最后延伸到退休規定、退休后的所得替代與福利等差別待遇。總而言之,低收入的女性并不一定是無工作能力或無工作動機的福利依賴者,而更可能是后現代貧窮觀點下的、被社會排除的“風險承擔者”與“底層階級”[11~14]。
(三)經濟上依賴男性
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已為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寫定了劇本,婦女在勞動市場中必然深受社會結構與機會所陷難以持續維持其勞動身份。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以及就業隔離不知不覺中合理化“男外女內”的性別分工行為。當家庭內部有老年人需要專職照顧者時,女性在“理性”的經濟考量下,自然會選擇回到家庭中擔任照顧角色,如此,更持續加強勞動力市場中對女性的性別歧視。身為“家長和贍養者”的男性掌控了家庭的資源,自然比作為“附屬者和被贍養者”的女性擁有大得多的家庭權力,家庭自然成為男性使用和支配女性勞動力的場所[15]。國家統計局2013年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占失業總人數的59%,高出男性18個百分點,而女性的再就業率只有男性的62.2%。根據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顯示,18~64歲女性在業率為71.1%,城鎮為60.8% ,農村為82.0%;男性的在業率為87.2%,城鄉分別為80.5%和93.6%。城鎮不在業婦女中,料理家務者占69.3%,失業者占13.3%,在校學習者占6.4%。在業婦女在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45.3%、14.5%和40.2%[8]。在收入遠低于正規就業的非正規就業中,女性的勞動力的非正規就業下降幅度大于男性,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說照料工作已經阻礙女性參與有酬勞動力市場,迫使女性完全或部分依賴丈夫,一旦家庭解體或者因其他原因失去對丈夫的經濟依賴,女性照料者就會陷入嚴重的經濟貧困,成為新的貧困群體,特別是一直屬于從屬和依賴地位的老年婦女。與此同時,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保障政策預設家庭內部收入共享,然而,家庭內部獲取資源和談判能力的不平等使得家庭資源不是必然共享。總之,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進一步加深了女性照料者在經濟上對于男性的依賴,且難以揭示女性在家庭這一黑箱中真正經濟地位。
在勞動力市場職業隔離、性別歧視以及傳統文化意識型態的規范約束下,婦女想要持續個人就業力就必須對抗傳統的性別分工制度。就家庭經濟的理性選擇而言,即便夫妻雙方擁有平等的決策權力,當任何一方必須為了家庭因素(例如育兒、照顧老人或家中殘障成員等)離開職場時,一般而言自愿或自由選擇離開工作職位的往往是婦女。因為在家庭經濟收入的理性思考下以及性別角色分工與傳統家庭意識形態壓力等多重壓迫下,都會讓女性在家庭與工作間陷入兩難的抉擇,大部分女性最終還是選擇回歸家庭,所謂“自愿選擇”其實只是個假象。所以,離婚并不一定讓婦女變成經濟弱勢者,它也存有重新開始,甚至比以前更好的契機。女性貧困絕然不是個單因問題,從人力資本累積到勞動市場參與,再到社會保障政策,然后又回到人力資本累積(職業訓練和工作福利等就業策略),再到婦女勞動參與,這其實是一個動態的連續體,貧困女性徘徊于就業歧視、照顧責任與經濟依賴的狀態之間,進出來回,一生中實難與之分離。
Sainsbury[16]認為,傳統福利國家的社會供給往往具有性別階層化的效果:福利體系的設計使得男女分別落入不同的福利軌道,亦即,雙軌式的福利——男性因其具有工作能力與身分大多落入社會保險系統;而女性大多落入社會救助系統,因其大多是沒有工作身份的依賴者。然而兩個福利軌道間的差別待遇致使女性更加依賴于男性,并且加速了女性的貧困。對于那些擁有工作動機與能力,但缺乏照顧替代措施而無法就業的女性,雙軌制福利體系是否是一種懲罰與歧視?無法進入就業市場與失去福利,公民權是否就此形成一個禁錮咒,強鎖婦女于兩個選擇間:選擇低薪、低技術、臨時工時的工作,在貧困邊緣忍受勉強糊口的生活水平;或是選擇承擔照顧責任卑微地與貧困共存,并忍受依賴男性的標簽與歧視?總之,不論是保障女性基本需求,還是以擺脫女性貧困風險為政策目標,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缺乏對性別差異的思考,即存在性別盲視,也缺乏有效彌補性別差異的政策安排。
二、緩解貧困女性化的政策思考與選擇
思考如何緩解女性貧困化,轉化女性的照顧責任,增加其滿足社會照顧需求的效能,已經成為女性擺脫貧困、打破社會孤立的依據。解開女性的照顧職責與女性貧困化之間的聯結,需要將脫貧和女性福利共同置于公共政策制定的框架中,建立社會性別敏感和家庭友善型的公共政策,推動女性平等參與勞動力市場,平等享受社會保障制度的福利待遇。
第一,政府提出“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與“營利性照顧服務產業”二元分立的制度架構,促進家庭照料、社區照料與機構照料三維一體的發展,將“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列為婦女福利與脫貧的首要措施,將女性的照顧轉化為協助女性經濟自立的利器。具體來講,提升照顧服務的專業品質、可近性以及可及性,加強機構和社區對老年人的有酬照料,減輕中老年婦女的照料負擔。此外,在滿足照料需求以及減少和均衡照料負擔的同時制定有效的監督制衡政策,以便監控照料的投入以及其增進福祉和減貧的效果[17]。
第二,盡量排除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與就業隔離,提高婦女就業動機與能力,著力培育女性的人力資本,增加婦女在家庭所得中獨立與資源分配能力,在滿足家庭基本照顧需求的同時,提高農村婦女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率。與此同時,體恤女性照顧者負擔的老年經濟安全制度,建立高齡女性與社會保障制度的互利關系,一方面使得老年女性得到充分的經濟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使得養老保險制度永續發展,針對于參加過勞動力市場的女性而言,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應考慮女性的工作狀態,既保證最大量的勞動參與率,又充分計算女性的勞動貢獻。
第三,加強公共經濟資源轉移的性別敏感度。基于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依附地位,以及在勞動力市場所受到的就業歧視和性別隔離,政府應該培育女性的人力資本能力,提高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占有率,緩解女性勞動力市場和家務市場的雙重責任。在保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及企業職工社會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按時足額發放的基礎上加發貧困女性專項補貼,尤其是貧困老年女性的專項補貼。對于在家庭中承擔照料責任的女性而言,政府可以適當降低國家基本養老金所需的有限繳費年限。總而言之,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合理設計和施行保證經濟資源的有效轉移,實現女性與男性在獲得經濟資源和有效服務方面平等的地位。
第四,構建貧困女性化的監測機制與評價方法。我們除了要承認女性在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制度中所處不利地位是導致女性貧窮的主要原因之外,還必須發展一套足以使我們清楚觀察家庭內部資源分配的測量方法。家庭內部并非只由夫妻二人組成,父母與子女兩代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往往也是決定家庭內部資源分配的一種因素。因此,在考慮家庭內部資源分配時應該以個人為基礎,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這樣便于更清晰地測度家庭內部資源占有率。同時,打破勞動力市場和家庭照顧勞動之間的性別界限,承認婦女在家務勞動和照料活動中的貢獻,將婦女無酬勞動時間折算進個人養老金賬戶中,或者依靠夫妻共有養老金,由丈夫補償女性因為無酬照料所損失的養老金。也可以說,如果將無酬勞動時間也并入計算貧窮的話,那么女性相對于男性的貧窮將不成比例的增加。此外,政府要在普惠性政策之外加強針對貧困女性的性別敏感政策,提高貧困女性化監測標準的瞄準性,使得政府扶貧政策支持更加精準地到達女性貧困人口。
[1] MILLAR J, GLENDINNING C. It all really starts in the fmily: Gender divisions and poverty[C] // Women & Poverty in Britain the 1990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2] MILLAR J, GLENINNING C. Invisible women,lnvisible poverty[C]//Women & Poverty in Britain.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9.
[3] MILLAR J. Poverty and the lone-parent: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policy[M]. Aldershot: Avebury, 1989: 1-204 .
[4] HARKNESS S, MACHIN S, WALDFOGEL J. Evaluating the pin money hypothe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labour market activity, family income and poverty in Britai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7(10): 137-158.
[5] 程靜, 蔣文慧. 老年化,貧困化與社會保障——基于社會排斥的視角[J]. 湖北工程學院學報, 2014(9): 93-97.
[6] 劉曉昀, 李小云, 葉敬忠. 性別視角下的貧困問題[J]. 農業經濟問題, 2014(10): 13-17.
[7] 盧倩云. 社會資本視角下的貧困女性化解讀[J]. 桂海論叢, 2007(11): 81-83.
[8] 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課題組. 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J]. 婦女研究論叢, 2011(11): 5-15.
[9] AEBERB G. Women,work and pension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王震. 養老保險中的性別政策評述[J]. 經濟學動態, 2009(7): 123-128.
[11] WILSON W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 class, and public polic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2] STERN M J. Poverty and postmodernity, in Reisch and Gambrill 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M]. CA: Pine Forge Press,1997.
[13] NOVAK T.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in Lavalette and Pratt social policy: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introduction [M]. London: Sage, 1997.
[14] KRONAUER M. Social exclusion and “underclass”-new concepts for the analysis of poverty, in Hans- Jurgen Andre empirical poverty research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England: Ashgate,1998.
[15] 張輝. 中國老年婦女經濟與生活狀況的社會性別分析[J]. 蘭州學刊, 2006(12): 88-91.
[16] SAINSBURY D. Gender, equity, and welfare stat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郭爍. 反對貧困與不平等[J]. 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4): 5-23.
Connotation, Factor and Policy Thinking of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NING Man-xiu JING Cai-long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While the female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rate has been improved, it does not slow down the impoverishment of women; instead, it compels the women to bear the dual responsibility of labor market and housework. Based on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of labor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on men, this paper analyzes causes of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intrinsic mechanism of women’s pover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or women and social mutu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uild prope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alleviate women impoverishment. In conclusion, it will propel the relations of poor women and society, thus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care responsibility; gender discrimination; economic dependence
D601
A
10.14071/j.1008-8105(2015)06-0005-05
編輯 劉 波
2015 ? 03 ? 0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71303050);福建省高等學校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效果評價與政策選擇研究”(JAS14039).
寧滿秀(1979? )女,博士,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荊彩龍(1989? )女,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