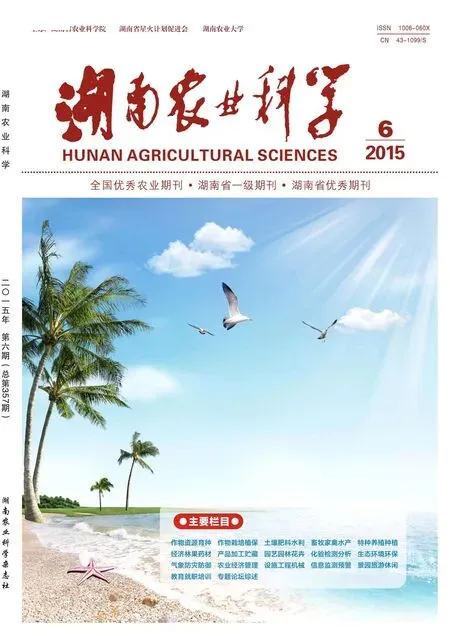基于土地流轉下的閑置農用地問題分析
肖 莉
(湖南省國土資源規劃院,湖南 長沙 410007)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保持現有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鼓勵政策。這充分表明政府已意識到土地流轉是促使當前農村土地高效利用和盤活閑置農用地的重要手段,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2014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的聯合調查數據,在土地流轉程度不活躍的地方土地閑置率接近20%,而在土地流轉非常活躍的地方土地閑置率為13.5%,土地流轉活躍地方相對土地流轉不活躍的地方農村土地的閑置率明顯降低,這表明土地的流轉對降低區域的土地閑置率具有促進作用[1]。同時,土地流轉活躍的地區農業產值明顯較高,土地的流轉能為農民帶來更多的紅利,凈增值可達10%。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表示,開放有序的土地市場可以促進土地的流轉,如果土地流轉的客觀條件和機制更加完善,耕地撂荒的現象將會減少。大規模耕地的流轉可能會伴有市場風險,但是不開放土地市場、不促進耕地流轉會造成耕地這一稀缺資源的大量浪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增產增收。當前土地流轉已成為解決閑置農用地問題的有效手段,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市場,切實保證農民的增產增收已成為盤活閑置農用地的問題核心。
1 農用地閑置的成因和難點分析
根據《湖南農村土地隱性拋荒調查報告》,2007年湖南省耕地撂荒數量已超過總量的10%,其中“雙改單”造成的隱形撂荒使湖南益陽市每年少產糧食達18萬t。根據2011年《國際先驅導報》的報道,隨著種子、化肥等務農成本的不斷增加,而糧價不見漲,農民務農還要擔負氣候、市場等因素帶來的風險,導致我國每年達200 萬hm2耕地的閑置[3]。
1.1 農用地閑置的成因分析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農村務農人員開始逐步進入其他行業,加上務農的經濟收入低,還要承擔市場風險,所以造成耕地撂荒、雙季種植改為單季種植的現象日益普遍。農用地閑置的成因主要有自然、社會和經濟三方面的因素。
1.1.1 自然因素 由于受氣候條件和耕作條件等自然因素的限制,造成耕地的季節性閑置嚴重,冬閑田大量存在。例如,部分地區的陰坡田在冬季因長期積水陰冷,形成爛泥田,使得每年只能種一季水稻。一些南方地區因秋冬季的陰雨天氣多,田間積水嚴重,農民無法翻耕土地和進行播種,使部分農田出現閑置。
1.1.2 社會因素 我國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6.22%迅速增長到2012年的52.57%,增幅達45.14%。隨著城鎮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凈流出也不斷增加,而土地對農民而言具有重要的社會保障意義,許多農民都是“離鄉不離土”,所以剩下來想種田的農民需要在原土地使用者的同意下才能租種這些“多余的耕地”,因此造成越來越多的農用地開始荒廢。
1.1.3 經濟因素 我國農產品價格長期處于較低水平,使得農民務農收入往往要低于從事其他行業。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各行各業的不斷發展,農民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收益也日益可觀,種糧已在大部分地區不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而且種糧的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小農耕作的收入微薄,導致農民耕種積極性大大下降。
1.2 農用地閑置的難點分析
目前我國對于閑置農用地還沒有明確的定義。1999年國土資源部頒布的《閑置土地處置辦法》也只是涉及了對閑置土地的定義,但其側重點是針對城市閑置建設用地而言的,對于農村土地的閑置,特別是對于農村宅基地和耕地的閑置缺乏明確概念。閑置農用地是指在農村由于各種人為原因未得到充分利用乃至荒廢的、具有生產力或者生產潛力的土地。農村土地閑置包括非農用地的閑置和農用地的閑置,同時它具有包含多種土地類型的特點[4]。
閑置農用地的概念不明確可直接帶來基層執法管理的困境。當前政府國土管理部門在針對農村耕地撂荒中的“無作為”,主要源于當前閑置農用地的概念模糊、閑置情況的界定難以把握、收回耕地或停止耕地耕種補貼的發放等處罰方式難以施行且效果不佳。
2 閑置農用地流轉的現狀和困境分析
土地流轉是實現農村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途徑,是我國農村體制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也是完善農村土地產權的良好契機,現已得到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土地承包期由“長期不變”變為“長久不變”,由此穩定了農民承包經營權。但目前農村土地流轉尚存在以下問題。
2.1 農用地的產權模糊
在我國的法律框架內,農民享有農村集體土地的權利是不完全的。農民對于集體土地只享有使用權、占用權、收益權等,卻不能對其通過轉讓、買賣等方式進行流轉處分,其所有權歸屬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且只有村民代表大會、村民自治組織有權處置。同時,附著于土地上的租賃、抵押、轉讓、入股等權利雖在發達的沿海地區有所實行,但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還沒有明確。由于農民享有的土地權屬模糊,以往的私下流轉被認為是“非法行為”。而且土地流轉行為有時僅有口頭協議,即便有簽訂的雙方協議也不受法律保護[5]。因此,明確農村土地產權已成為土地流轉推廣的前提條件。
2.2 地塊碎小難以集中連片
由于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人均農用地面積小,小規模分散經營廣泛存在,土地經營規模小,并隨農村人口的增加有進一步細分的趨勢[6]。而承包者的經營必須達到一定規模才能保證其經濟利益[7]。因此,往往要好幾家一起連片租、且需征得旁邊田主的同意,這就限制了土地流轉,導致想租地的租不到、想出租的又租不出去。
2.3 農用地的流轉市場信息閉塞且不規范
當前土地流轉的信息平臺還不完善。根據焦國棟[8]的研究發現,從整體上看,全國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土地流轉服務平臺和服務機構,導致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流轉還只局限于本村、村小組狹小范圍內。同時,集體土地的無序流轉也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鄉村建設規劃的落實帶來了制約[9]。因此,進行跨區域、統一標準的土地流轉市場信息平臺的建設,實現農用地集中連片和大規模的流轉,對優化農用地資源配置具有重要意義。
2.4 農民獲取的土地流轉收益低
由于農用地轉出戶保留了對土地長期不變的承包經營權,所以通常只能以較低租金流轉給使用者。同時,由于政府規定了流轉土地不能改變土地用途,在糧食價格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流轉后的土地收益也并不高。根據新疆農業大學的趙俊對和田地區的調查結果,和田地區的土地流轉收益依據流轉土地的區位、肥力不同,平均年收益為200 元/667m2,部分農戶為防止土壤肥力退化,常采取“零費用”的方式將自己的承包地交由親戚、朋友或鄰居代為管理[10]。然而,更多的地區由于受到經濟落后和規模經營條件不足的限制,棄種者往往難以找到尋租者,導致農用地的大量撂荒。
3 盤活閑置農用地的對策與建議
3.1 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平臺和市場
要建立縣級、鄉鎮級、村級三級土地流轉平臺和服務網絡,鼓勵跨區域土地集中連片的規模化經營。根據土地生產力的不同,要對土地流轉價值進行科學評估,分等定級。為穩定市場價格,減少土地流轉中的投機行為,還要建立流轉土地基準底價和價格公示制度。
3.2 保證流轉土地的規模經營和高效利用
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轉移和生產條件的改善,適時發展適度規模的經營已成為我國這一人多地少國家的必然選擇。為保證農用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產出,應當發展一批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帶動力的企業。政府應當重點扶持承包規模大、農業產出高的承包戶,鼓勵通過合作、聯合等方式提高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水平。
3.3 落實土地利用動態巡查和土地考核制度
要建立與城市建設用地動態巡查制度相對應的農村農用地動態巡查制度,加強基層國土資源所的建設,增加人員配置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培訓。由基層國土所擔負定期或不定期的現場巡查工作,獲取不同時間的全景照片并定期對比,將發現的核查問題及時上傳動態監測監管系統。對確認的閑置土地及作出的處置結果,應利用政府信息平臺向社會發布,并告知相關鄉鎮政府、國土等部門。防止農用地閑置應當作為基層領導干部目標考核的重要內容,應由行政一把手負總責。國土、農業、水利等管理部門要積極配合鄉鎮,完善共同責任體系的構建,形成預防農用地閑置的合力,并建立責任到組制度,及時統計匯總相關信息。對故意閑置土地的情況要進行整改,情況嚴重的應作出相應處罰。
4 結 論
農用地的閑置關系到農民的增產增收和國家的糧食安全。要解決閑置農用地的問題,關鍵是要提高農民耕種的積極性,使其在種地中得到理想的效益。由于農村人均耕地面積有限,農民增收的空間也有限,這就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進入其他行業,所以土地流轉就成了既能讓農民繼續享受土地實惠又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兩全辦法。
隨著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在我國的全面開展,勢必使農民對于承包地塊的面積、甚至歸屬等土地權屬更加明確,這也為農村土地的流轉帶來了新的契機。土地流轉是根治當前閑置農用地的有效方法,但需切實保護流轉過程中農民的權益,防止鄉、村兩級操縱流轉合同的簽訂,應賦予農民更多的決定權、知情權和談判權,建立跟隨糧價和物價變化的租金增長機制,以最大限度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應當意識到,解決閑置農用地問題的最終目的是要保障國家的糧食生產和安全,對于承包土地的使用者為追求經濟利益而改變糧食種植用途的行為,要加強監管并要求使用者簽署相應的承諾書。
[1]土地流轉將降低土地閑置率促進農民權利形成抵押物[N].中國經濟時報,2010-04-21.
[2]張 麗.中國需要“發展貧困線”——訪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J].中國社會保障,2007,(12):13-15.
[3]農民棄種拉響糧食安全警鐘撂荒耕地或達近3000萬畝[N].國際先驅導報,2010-05-23.
[4]王 滔,段建南,楊 君.基于“三個最嚴格”的農村閑置土地問題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2,40(8):396-400.
[5]成素英,張秀蘭.山東省城鄉——體化進程中的土地流轉問題與對策[J].山東農業科學,2011,(4):115-118.
[6]王世杰,原東方.新時期農村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山東農業科學,2010,(8):117-119.
[7]劉小霞,周 軍.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當代經濟研究,2009,(10):64-66.
[8]焦國棟.農村土地流轉應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作用[N].光明日報,2014-09-20(5).
[9]周紅升.我國欠發達地區農村可耕土地閑置原因及解決對策[J].經濟師,2005,(3):177-178.
[10]趙 俊,周長江.和田地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影響因素探討[J].山東農業科學,2013,45(7):15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