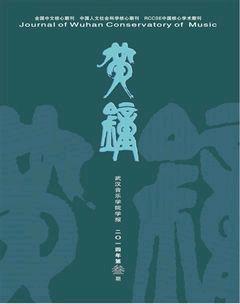琴聲笛韻話“流浪”
章濱



摘要:文章基于《流浪者之歌》原版和長笛改編版的比較,對后者如何在保證原作基本風貌不變的情況下,兼及長笛演奏特點,以致聽眾認可作了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薩拉薩蒂;《流浪者之歌》;長笛改編版
中圖分類號:J621.1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4.03.022
前記
1982年下半年,我步入廣西藝術學院的大門,正式成為了一名廣藝附中長笛專業的學生。某個秋天,我正在練琴,耳邊突然傳來一段蒼涼的小提琴旋律,循聲而去,只見一名廣藝音樂系本科生正在埋頭苦練。此段音樂正是薩拉薩蒂《流浪者之歌》的開頭部分,曲調撼動人心,聽后難忘。這首樂曲若用長笛演奏會是怎樣的效果?
21世紀初,我國著名長笛演奏家陳三慶先生到家里清談,與他說起當時的感覺,他也深有同感。當說到無譜的遺憾時,他卻堅定地告訴我譜子肯定有。果不其然,2008年12月,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王永新老師編的《長笛經典曲選》中,薩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赫然位列其中。看著那熟悉的旋律,不禁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拿起樂器,嘗試演奏,當年的旋律再一次回蕩耳邊,心中激蕩。
它,除了被用于演奏及教學常用曲目外,我應該為這首長笛改編曲寫點什么,遂有此文。
一
薩拉薩蒂(Pablo Sarasate,1844-1908),19世紀最杰出的小提琴手之一,“十歲時即表現出非凡的琴藝,連羅西尼也不禁感嘆地稱贊說‘了不起,他曾在馬德里宮廷演奏,伊莎貝拉皇后深受感動,當場賜予名貴的史塔第發利小提琴,傳為佳話。此后,他被人稱為‘帕格尼尼再世”野宮勳:《名曲鑒賞入門》,張淑懿譯,中9-6/A2524.,第328頁。 。他的精湛技藝引起了作曲家的注意,許多作曲家專門為他創作作品,如維尼亞夫斯基《d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布魯赫《第二小提琴協奏曲》、《蘇格蘭幻想曲》、圣-桑《第三小提琴協奏曲》、《引子與回旋隨想曲》等樂曲都是為他而作的。而且正是由于薩拉薩蒂的成功演奏與推廣,使上述作品成為深受聽眾喜愛的經典樂曲。
薩拉薩蒂不僅是一位成功的演奏大師,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流浪者之歌》“Zigeunerweisen”Op.20,又名《吉普賽之歌》,正是薩拉薩蒂小提琴獨奏作品中不朽的篇章。眾所周知,吉普賽民族雖然在世界上分布廣泛,但都是居無定所,并且世世代代過著清苦而又飽受歧視的生活。即使是這樣,這個民族依然保持著活潑、樂觀的生活態度。其能歌善舞的習性,我們在電影《葉塞尼亞》、《大篷車》中盡可一睹風采。在樂曲中,薩拉薩蒂運用十分恰當的手筆描寫了這一民族性格的幾個側面,并使小提琴的旋律性與技巧性得到相當完美的結合,它那回腸蕩氣的傷感色彩與天外飛仙般的小提琴技巧所交織出來的絢爛效果,任何人聽后都會心蕩神馳不已。
長笛改編版的《流浪者之歌》,如何在保證原作基本風貌不變的情況下,加入長笛本身的優勢,使聽眾能夠認可并喜歡,這是改編曲的關鍵,同時也是本文的研究重點。本文選用的小提琴版本為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010年7月第3次印刷,由鄭石生鄭石生教授(1936~2014),男,原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先后在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是我國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大名鼎鼎的薛偉、左軍等人均出自他的門下,他的教學效果可謂豐厚,因此,選用他的版本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教授編訂的《薩拉薩蒂小提琴名曲選》,鋼琴協奏。
1.兩種版本的初印象
從曲式結構看出,此曲由四個部分組成,前三部分篇幅較小,第四部分較長,占全曲的1/2強,且一改之前的風格與速度,可見最后一段在全曲中所占地位之重。
第一部分:中板,c小調,4/4拍子。由鋼琴強而有力的右手八度以及左手和弦顫音織體作為開始,然后主奏樂器奏出充滿憂傷的旋律。這一部分很短,只是全曲的引子。
第二部分:緩板,由獨奏者奏出新的旋律,是一種美麗的憂郁,以短小樂句變奏和反復作為技巧性極強的發展,輕巧的泛音和華麗的滑音顯示出這一主題的豐富內涵。在這部分,鋼琴聲部并不太明顯,始終是以獨奏樂器的輕柔旋律為主。
第三部分:稍為緩慢的緩板,2/4拍子。小提琴裝上弱音器,長笛則是使用弱奏,“molto espr.”作為本段的唯一一個表情記號,要求奏出充滿感傷情調的旋律,使悲傷的情緒達到極點。
第四部分:2/4拍子,速度驟變為極快的快板。本段與之前部分形成明顯對比,反映出吉普賽民族性格能歌善舞的另一面。樂段開頭仍然以鋼琴強奏為先導,獨奏樂器演奏出歡快的旋律,充滿舞蹈氣氛。然后以更具技巧性的旋律再現本段的最初部分,逐漸前行到樂曲高潮,最后閃電般結束全曲。
二
根據改編手法的難易程度,以及考慮到在長笛上應用的數量及質量,筆者將本曲改編者的手法分為常用手法改編以及非常用手法改編兩種分述。
(一)常用手法改編
所謂常用手法改編,是指沒有或較少改變原有版本音符、節奏、音響效果,適合長笛演奏而對原作不產生顛覆性的改編方法,現歸結如下:
1.改變音域
(1)提高音域
通過對比,可看到在獨奏開始,原作的g音提升變成了g1音(見譜例1),提高了一個八度。g音是小提琴的最低音,因長笛音域中不含此音,故改為g1音。此后,這一樂句整體上調一個八度。同樣在第32小節,同樣的g音改為g1音。
譜例1譜例中,第一行為原作譜,第二行為改編譜,下同。
(2)降低音域
由于小提琴音域比長笛寬,小提琴的高音區音符在長笛上無法演奏,因此通過降低音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整個樂曲中,采用降低音域來進行改編可以說比比皆是,較為突出的是第24-27小節,如下例。
譜例2
譜例中有很多小字四組上的音,這些音在長笛上演奏極其不便,特別是#f4、g4音,是無法演奏的,而其他音則音響尖利,音準難以控制,與小提琴極高音纏綿悱惻的如泣音響南轅北轍。因此除了音域因素外,音響的特殊性也是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之一。
2.增/減音改編
(1)增音改編
增/減音是指在改編過程中,為了讓改編版旋律更加流暢,了無痕跡,在不違背原作音響效果的前提下,增/減某些音,這些音一般是本和弦的和弦內音。本改編曲中,有多處使用了增音改編技術,現選第34小節加以說明。
譜例3
從上例可以看出,原作在長段的裝飾音之后緊接著是一個八度跳躍,但在改編版中,加進了幾個音,鑲嵌在八度上行跳進中,它們是本和弦的和弦內音。增加的音,雖然失去了原有的大跳音程所造成的不穩定氣氛,使音樂的張力減弱,但卻使裝飾音和弦更加豐滿,對于演奏員來說,如果用大跳的方式來演奏幾乎達到了常用音域頂點的bB3音,是有一定困難的,除了氣息不好控制,音質、音準也差強人意,但如果通過和弦分解來演奏,飛躍這座跨度很大的“橋”則要容易許多,這些和弦內音正是方便的“橋墩”,讓演奏者很順利地到達終點,并穿越在兩者之間。
(2)減音改編
在本曲中,減音改編分為減低音和減高音兩種情況。
1)減低音
兩個版本中的第4小節是一個典型例子。第4小節需要演奏一個長距離的多音裝飾音,雖然都是從本樂器的最低音開始,但長笛版比小提琴版少了起始的兩個低音,省略的g音是長笛音域無法演奏的;b音,在有B尾管的長笛中,可順利演奏此音,因此建議從此音開始演奏,最大程度地保持原作風貌,同時,作為c小調音階,從導音開始到主音的解決,無論從張力、還是期待感和聽覺需要來說,都是順理成章的,而對于無B尾管的長笛來說,無法演奏此音,則完全屬于無奈之舉。
譜例4
2)減高音
如果原作的高音超出了長笛音域,長笛無法演奏原有音符,那么就會使用減高音的改編手法,如在原作的第11小節,此處為G大調,原作的分解和弦落音于g4音,非常穩定的一個主和弦。雖然長笛無法演奏此音,卻可以演奏d4音,但如果演奏到此音,很容易造成調性的模糊,而如果到b3,穩定的大三度結構正是G大調主和弦骨干構成,因此,減去d4和g4音為最佳選擇(譜例5)。
譜例5
3.以上兩種方法的結合
由于小提琴比長笛的音域要寬得多,所以在改編中也會用兩種方法相結合來達到最終目的,如第23-24小節(見譜例6)。
從譜例的對比中我們可看到,改編者在樂句開始減少了一個c2音,而在下行的和弦分解中增加了3個音,分別是e2-c2-g1,這三個都是和弦內音,整個和弦因此從高音經中音順利下行到低音,順理成章地使原作原本在中音區的旋律可以從長笛的低音區開始,這樣的改編手法,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曲裝飾音的長度與效果,而且,由于增加的是和弦內音,也沒有改變本和弦的色彩,這樣就達到了一個“雙贏”的結果。
在譜例7中,原譜是c小調主和弦以及c旋律小調上行音階,在低音區早早出現的升Ⅵ、升Ⅶ音,加速并加強了c自然小調到c旋律小調的轉換。而改編譜把原譜的和弦和大段音階分割成一小段下行音階和兩小段上行音階,雖然音符數量相同,但延遲出現的升Ⅵ、升Ⅶ音,則延長了c小調音階轉換的時間,降低了聽眾聽覺的期待感。
而在譜例8中,改編譜把原譜的下行滑音半音階改為雙吐下行半音階,增加了演奏者的演奏難度。試想改編譜如果只是簡單的重復原譜的下行半音階,不但絲毫沒有原譜滑音的泣訴效果,而且改編手法過于簡單,照搬原譜材料,對于吹奏滑音異常困難的長笛來說,則不可能演奏,因此,用雙吐改編,從演奏效果上說,筆者認為是一個非常貼切的選擇。
5.連線改編
連線改編是很常用的改編手法,除了此曲的主奏樂器不同外,發音原理、音域音量、表現風格、演奏習慣等,都會引起改編者對連線的不同用法。在樂曲中,由于小提琴上下弓以及力度對比的需要,同一個和弦的上下行分解,很可能需要上下兩弓才能演奏完,如第43小節,長笛卻可以一氣呵成地演奏。這樣的片段非常常見,但所引譜例是特殊的。
譜例9
原譜41小節以弓尖起音,到第二個連線自然轉為弓根起音,倒數第二個音是弓尖,接著又是弓根演奏最后一個音。這一小節的連線改變較大,首先第一弓的四個音變成了兩個二連音,而處于第二個連線末尾的E顫音,由于是上弓末音,音響較強,長笛版則用吐音對應。而接下來的弓尖起音D,音響較弱,長笛則用連線末音對應,使其音響較一致。最后一個音為弓根起音,長笛則用單獨吐音來對應突出。所以說,原譜上每一個特殊的音點,改編譜都會考慮主奏樂器的性能與演奏習慣,通過對連線的改編,力求重合原點,達到與原作相同的效果。
(二)非常用手法改編
本文中所涉的非常用手法,是指在長笛上很少或幾乎不可能使用的演奏技術,而這些技術在小提琴上則較為常用,這些技術其實就是管樂器與弦樂器在演奏技術上特有的區別。長笛改編曲中使用的非常用改編手法很多,但在本曲中涉及以下幾種。
1.泛音改編
在《流浪者》小提琴版本中,運用了大量的,甚至是密集的泛音演奏技術,這種演奏技術對于長笛來說較難,在多普勒的《匈牙利田園幻想曲》中,長笛的泛音演奏僅限一句,且具有重復音多、音程之間跨度小、用低音指法來演奏高八度的同音旋律的特點,可見作曲家對于長笛演奏泛音技術的運用比較謹慎。作為長笛改編版,《流浪者》想要真實還原原作音響,只有通過對泛音音響的實際考慮,加以技術性的處理,才會使作品不至于走樣。
(1)利用泛音聽覺音高改編
在小提琴上,利用泛音的指法可演奏出記譜泛音上方五度音,因此,改編版中也利用此法,使得其更加貼近原作。
譜例10
改編者在譜例10中充分考慮原作泛音的聽覺音高,但并沒有套用,而是通過升高或降低音高的寫法,既忠實了原作音響,音程之間跨度增大,又增加了長笛演奏的難度。
(2)不規則的泛音改編
譜例11
改編版并沒有完全按照泛音的聽覺音高進行改編,而是把泛音的聽覺音高稍微降低,使之變成主音的一個小二度裝飾音形式,來模仿原譜的實音與泛音相結合的效果。和聲音程變成了小二度裝飾音連接,增加了樂曲的動感與活躍,使舞蹈的場面一下子躍于眼前。
2.滑音改編
在小提琴上,滑音被定義為“在一根弦上用一個手指,從一個音到另一個音的全部過程的滑動”。《牛津簡明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頁。 滑音技術在許多樂器上都有應用,如鋼琴,豎琴等。在鋼琴上,滑音是奏出音階上的固定全音或半音的音高,而在弦樂上,所奏出的音高數量是無數的。管樂器上,長號使用滑音技巧最多,效果也與弦樂最為相似。長笛作品中也有使用滑音的,一般是采用復雜的指法,通過微分音來實現,或者是通過向里/外轉動笛管,使氣息輸入角度發生改變,從而降低/升高音高。但是,小提琴版的《流浪者之歌》,對滑音卻有著兩種不同的演奏要求。
(1)同指異音滑音
譜例12
同指異音滑音,在此版本中大量運用,演奏者用一根手指,在一根弦上完成了若干音的連續演奏,在音響效果上體現出一種蒼涼、如泣如訴的感覺。
(2)異指同音滑音
譜例13
異指同音滑音,是指連續演奏同一個音,卻使用不同的指法。而在上述的兩個長笛改編版譜例中,卻發現改編者沒有作出任何的變動,可見改編者深諳長笛演奏滑音的不易與不宜,但卻削弱了原作的神韻。
3.撥弦改編
撥弦也是弦樂演奏中的特色技巧,通過手指在琴弦上的撥動,發出與弓弦摩擦迥異的聲音,其音短促,有彈性,代表作無疑是斯特勞斯的《撥弦波爾卡》。原作中,撥弦演奏的是和弦,實際效果為掃弦;改編版中,截取原作和弦的高音,加上重音與頓音的雙重記號來模仿小提琴右手的演奏技巧,重現作者意圖。
譜例14
4.和音/和弦改編
和音/和弦演奏是弦樂器獨有的演奏技巧,偶見于現代長笛作品中,但需要使用復雜的指法,才能演奏。在此種情形下,和音/和弦的改編有以下兩種。
(1)改編成帶有琶音性質的裝飾音結構
譜例15
在改編版中,原作的和弦低音改為裝飾音,過低音由于長笛音域緣故,舍棄不用。原譜中連續弓根演奏,在改編時無法體現,因此較原音響略遜一籌,建議演奏時強調裝飾音低音,以最大程度呈現原作音響。
(2)和音一般取上方音作為旋律音
譜例16
在原作中,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可以說,但凡是和音旋律,一般都會采用此法。
5.超高音域/最大音程的運用
長笛的常用音域范圍為c1/b-c4,超越此范圍的音稱為超吹音,由于這些音發音困難,音質粗糲,指法復雜,因此長笛傳統作品中鮮用,在20世紀中葉以后的現代派作品中才逐漸少量應用。長笛版《流浪者之歌》,極高、極低音大量運用,連接方式一般為音階或琶音式連接,但也有幅度大的跳進連接,甚至超過雙八度。極致高音在第4小節提前出現。由于此譜例與譜例4相同,并在譜例4中已附帶標出,在此不再贅述。
在譜例16中,第一次連接是以音階上行連接,到達最高音be4,緊接著是音程大跨度下行跳進到c1,其幅度為三個八度多,音程跨度達到二十四度,這在長笛作品中極為罕見。正是由于它的出現,也揭示了作曲家向往自由生活,向往放蕩不羈、天馬行空性格的精神世界,使聽者馬上感受到音符、節奏、律動和演奏者相互作用,從而也演化出生動的吉普賽音樂景象。
三
在目前的長笛作品中,深刻描寫吉普賽音樂的作品可謂是鳳毛麟角。《流浪者之歌》長笛改編版無疑給長笛文獻蘊藏作出了巨大貢獻。由于是改編于小提琴版本,所以,就長笛而言,除了常用的改編手法以外,大量的弦樂演奏技術被借用于管樂器。由于管樂器不同的發音模式,不同的處理手法,不同的音色變化,也使《流浪者之歌》在另一種背景下熠熠發光。吉普賽音樂文化與長笛傳統文化的深度融合,使改編版有了不同于傳統小提琴版本的血性基圍,煅造了整個音響的氣質,并滲透至肌理。
超技運用、大幅跳躍、超吹高音等,對演奏者是個嚴峻的考驗。作品的演奏過程,猶如和歷史老人穿越時空進行深度對談。其中的技術難點,則是讓演奏者更加深刻領悟作者意圖,體會吉普賽音樂的踏腳石,歷經“試煉—升華—質變—成器”,最終煅造絕世美妙的音樂瓷瓶。
長笛與小提琴,一個管樂,一個弦樂,卻因為《流浪者之歌》有了交集。而作為一部音樂形象鮮明無比的小提琴作品,加入了長笛元素后,不但沒有削弱原有風采,而且還因為不同材質樂器所發出的音響,不同音域、技巧的運用,再次煥發出奪目的光輝。對于演奏者來說,豐富其演奏風格與經歷,增加音樂會曲目的多樣選擇,擴大音樂視野,《流浪者之歌》都是一個較好的選項,因為對演奏者的技巧考驗與個性張揚,對音樂會曲目的風格選擇,對現場音響的對比,都是一個極具個性、極具挑戰的經典曲目。
(責任編輯: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