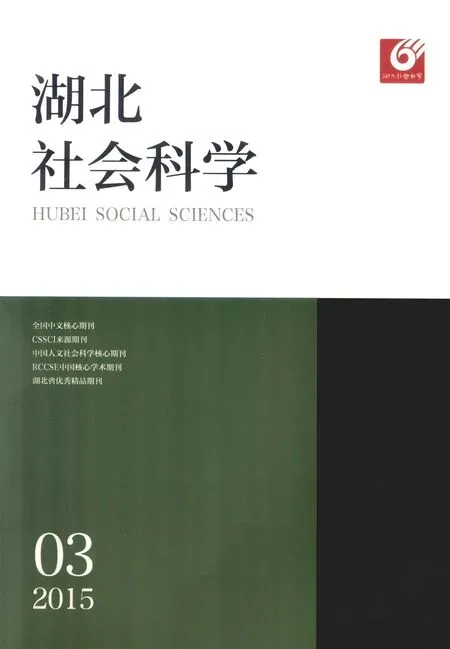從關聯期待看拒絕言語行為的解譯
蘆麗婷
(華中師范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
一、引言
關聯理論是由Sperber和Wilson在《關聯性:交際與認知》(1986)[1]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來的,用來闡述人類交際的“內在機制”(Sperber&Wilson,1986/95:32)。[2]從此,關聯理論在西方語言學和語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和持續的關注。Sperber和Wilson認為,語言交際的過程應該是:一個負責接受語言刺激信號的單位首先接收了語言信號,然后把它們傳遞到中心系統,再由中心系統進行運算和破譯。所以,語言交際并非簡單的“編碼—解碼”過程,而是一個尋找關聯的“明示—推理”過程。意義的理解也不僅僅是對語言符號的解碼,而是對發話人的明示意圖和交際意圖進行辨認。[3]
本文所觀察和描寫的客體是拒絕言語行為(Refusal Speech Act),是一種強語境下的言語行為。它是指說話者對交際對象的邀請、請求、建議、給予等表達拒絕意圖的言語行為。它是交際中威脅面子的一種言語行為,為了使拒絕達到讓雙方都滿意的效果,除了語言的交涉,還可以恰當使用緩和氣氛和調節拒絕行為的各種輔助策略。人們使用的拒絕策略往往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策略的綜合,“拒絕”這種威脅面子的行為由于其表達的復雜性,使得受話人在解譯這些迂回曲折的“拒絕”時必然要下一番功夫。本文試從關聯理論中“關聯期待”的始發、改變、取消、重生以至最終“期待”得到滿足或被放棄的整個過程,結合漢英語料,來描寫“拒絕”話語如何得解,語用推理如何完結,拒絕策略為何多樣。
本研究所采集到的語料分為兩組,第一組來自漢英兩個版本“語篇補全測試”的問卷調查,第二組則來源于漢英各5部職場劇目,其出品年份均為2010年以后,這樣的選擇既保證了語料的新鮮度,也保證了某些語用習慣和社會習慣符合現代人特點。收集到的樣本,根據統計學“分組比例抽樣”的原則進行抽樣。最后兩組數據合計,本研究中“職業交往中的拒絕”語料,漢語共780份,英文共780份。
二、關聯期待在拒絕語用推理中的作用
交際關聯理論中最關鍵的概念就是最佳關聯性,聽話人所有的推理都在假設話語具有最佳關聯性的基礎上展開,它是聽話人推理的主要依據,對它展開的一系列的理解過程是關聯運作機制的關鍵。[2](p607-632)認為在話語解讀過程中,需要按可及性的順序檢驗解讀假設,且當“關聯期待”得到滿足時,停止推理。
關聯期待是關聯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明示意圖與交際意圖在關聯期待的制約下相互調節。[3](p719-22)關聯期待產生于所有話語處理的最初階段,它包括對于說話人有信息傳遞的意圖的期待、對說話人意圖傳遞的信息與某話題相關的期待和對說話人意圖傳遞信息的具體內容的期待。[4]
其中,最宏觀的是第一種期待,它不涉及任何方向性,僅僅是對接下來的話語的一種不具有任何實質內容的期待;比如,在辦公室里,老板突然叫了一聲小張的名字“張百勝!”,此時小張便會對其老板接下來的話語產生關聯期待,但此時的期待僅僅是小張對老板接下來有意圖傳遞的一種期待,不涉及內容。
第二種期待比第一種具體一些,聽話人對說話人的話題有預先的信息期待,所以聽話人的大腦中已經激活了某些關于這個話題的相關語境信息,這些語境信息會使話語的推理變得省力;如,最近部門為了接下一個大單子,一直忙于各種公關工作,此時員工A對員工B說:“對了,那個單子的負責人是誰?”這里,A說的“那個單子”,B能夠在不費努力的前提下很輕松地從高可及的語境范圍內找出“那個單子”的指稱。
最后一種期待是最具體的一種關聯期待,它不但對說話人的語境信息有所期待,而且對具體的話題也有預先期待,此處的關聯期待已經滿足了量的需求,融入了關聯內容和關聯方向的期待。本研究中的拒絕語料,如果未使用迂回手段而是直接拒絕的話,大多數是這種關聯期待的體現。比如,老板要員工加班、同事請求幫忙或員工要求加工資等等,在聽話人回答之前,提出要求的一方就已經將語用推理的方向鎖定在“同意還是拒絕”的選擇上了。
其實,關聯期待并非僅僅產生在語用解讀之前,也不是在整個話語釋義過程中一成不變,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產生期待到滿足期待,它在整個過程中都可能產生變化,且這些變化相互關聯,上述三種類型的期待可能出現在話語釋義過程的任何階段,并且可以互相轉化。這些期待內部的內容調整或類型轉化都能影響到認知效果和對話語的處理、理解。如:
[1]總編:只要你從現在起,決定不要孩子了,……,我調你去法國總部工作一年,行不行?(《辣媽正傳》)
李木子:可我還是更想要孩子。
[2]李木子:我得趕緊回家一趟,那個選題策劃會,你先幫我管一下,我,我一個小時就回來。(《辣媽正傳》)
夏冰:策劃會還有半個小時就開始了,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3]李斯特:裝修方案和報價,搬家時間表和流程,這些東西你什么時候能給我啊?(《杜拉拉升職記》)
玫瑰:其實我最近身體不太好。要動個小手術。
首先,最初的關聯期待應該產生于拒絕者說話之前,被拒絕者在以上三例中,都期待“同意或不同意”的答案,這會使得被拒絕者提前為話語推理預設一定的認知語境范圍,當接受到對方的信息之后,預設范圍內的語境假設具有較高的語境可及度,接著便會在預設的認知語境內進行一系列的充實命題、分配指稱、消解歧義等顯義生成過程及推導隱含結論所需的隱含前提的確定,從而指向對方是否同意的方向。
在例[1]中,“我”和“孩子”這兩個詞的指稱在預先設定的認知語境范圍內很容易得解,“還是更想要孩子”也很容易被“決定不要孩子了……調你去法國……”的語境補足,其命題充實后,得出的話語顯義是“選擇孩子,放棄法國工作”,這直接滿足了被拒絕者對拒絕者所傳遞信息的具體內容的期待,期待得到滿足后,語用推理結束,且在這個答語中,關聯期待單純而未經改變。
例[2]很好的闡明了關聯期待的動態性。這一例中答語里“策劃會”“我”等的指稱分配也依然很明確,其命題上的充實也可以在預知的語境范圍內得以進行,然而,預先設定的“同不同意”的推導方向卻無法獲得明示,于是最初的關聯期待被擱淺,推理由最初的具體內容期待轉換成對說話人意圖傳遞的信息與另一個話題相關聯的期待。話語的顯義激活了如下的語境假設:
“第一天上班,不可能熟悉新會議的流程和內容”
“不熟悉就會需要時間學習和了解”+“離會議開始還有半個小時”
結論:“時間不夠,無法學習”
最后根據推導,得出認知效果“夏冰無法擔此大任”,滿足了對話題相關性期待的解讀,并且上述推理直接否定了“夏冰是否同意”的先決條件,成為初始關聯期待被取消的原因,也滿足了被調整以后的期待,推理結束。
例[3]的解讀更為復雜,李斯特在聽到玫瑰的答語之后將話語放在預設語境范圍內,準備生成顯義的過程中就遇到了麻煩,在“裝修工作”的語境中,并不存在“身體”和“手術”的指稱,要理解玫瑰的話語,初始期待必須被暫時擱置,需要在話題相關期待的預設語境中找到關聯,然而,玫瑰的答案里沒有跟“裝修工作”相關的任何信息,該重期待再次被擱置,此時對說話人意圖或傳達信息的大致方向都必須進行調整,這時只剩下對最寬泛的交際意圖的期待。其實,劇中玫瑰在話語表述的同時,遞上了一份體檢報告,此時環境起到了作用,該信息在“遞報告”“面色蠟黃”等非言語交際的語境中更具有優先權,玫瑰的意圖是傳達這個新信息而非討論上述舊信息,所以無法對李斯特的話題給出反饋,這就是兩重上級期待被取消的原因,此時,推理也終止了。玫瑰更為關注的是個人健康,而非工作,從而也表達了委婉的拒絕。
以上三例可以表明,解譯拒絕時,大多數情況下,關聯期待并不是一開始就被滿足,滿足調整后的期待是關聯期待動態性的體現,拒絕話語無論間接與否,信息傳遞和對方在理解的過程中,隨著被滿足的關聯期待與初始期待間的差距越大,推理方向和初始期待方向的偏差也會越大,聽話人所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如果產生于語言處理前的關聯期待較為具體,語用解讀就只限于對該具體期待的滿足;在推理的過程中受到解碼順序和受話人顯性認知語境交互的影響,當最初的關聯期待產生的顯義或被解碼出來的顯義能滿足該期待時,拒絕話語得解,推理結束;當關聯期待在其生成的語境中無法被滿足時,為了使得推理正常進行,原期待只能被暫時擱置,等待后續話語中來帶的新語境和新信息,或者是通過對期待的調整引起受話人顯性認知語境的改變,經過調整以后的期待需要在重新調整后的語境中去尋求滿足的契機,若在此處能生成滿足該期待的顯義,又能解釋上級期待為何取消,則話語得到了解讀,推理工作完畢,若仍無法滿足,則重復上述過程,直至滿足。
三、語用解讀的終止與關聯期待
在表達“拒絕”的初始階段,被拒絕一方的語用推理就開始進行了。隨著語用推理的繼續,關聯期待的性質會轉換或發生內容增生,最終,關聯期待被滿足或是被放棄,推理結束。
(一)語用推理終止于關聯期待的滿足。
改變受話人的認知語境是交際的目的之一,人的大腦中儲存的語境假設數量龐大、結構復雜,如果不加限制,通過話語本身與語境假設結合產生的認知效果有可能會過于膨脹和無法控制,在實際話語解碼的過程中,關聯理論認為語用推理的目標是用最小的認知努力來獲取最足夠的認知效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只要關聯期待獲得了滿足,語用推理就必須終止。然而,理想的模式不是總有發生,在表達拒絕的話語中,如果拒絕的直接性高,比如說話人直接說出“不行”“不可以”“No”這樣帶有否定含義的詞匯或相應的表達,期待的滿足就變得順理成章,而在很多情況下,語用推理結束時所得的認知效果都并沒有完全滿足或根本不滿足最初的期待。關注語用推理在拒絕言語行為中的應用,必須以關聯期待的動態變化為理論基礎。要獲得這種動態性的期待滿足,受話人必然要下一番功夫。
[4]Gaby:up?
Job agency lady:No,…(《絕望的主婦》)
[5]Job agency lady: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children.I have a job at a day care center.
Gaby:And deal with other people’s kids?I don’t even like my own.(《絕望的主婦》)
[6](調查問卷第十題“接替工作Taking over other’s job”)
Your reply:I have been working for like 14 days without any break at all!
以上三例,是關聯期待被滿足導致推理結束的三種情況:
第一種,靜態滿足。例[4]中,Gaby提出自己的薪酬應該上漲,在工作人員給出回答之前,Gaby已然已經預設好了關聯期待,而且該期待固定而明確,在整個話語理解過程中也并未出現性質和層級上的改變,由于工作人員的正面直接拒絕正符合其期待,所以該例子體現的是最簡單的語用推理過程。
第二種,單向動態滿足。例[5]中,Gaby的拒絕話語無法通過直接的語用推理得出解答。這是由于受話人在提出建議以后,最初的期待是Gaby的答語限定在“做或不做這份工作,或者至少給出與“這份工作”相關的信息。然而當Gaby一開口,受話人就不得不將關聯期待沿著某單一方向做調整,此處,關聯期待被調整為跟“deal with other people’s kids”這樣的具體信息相關,具體化的期待疊加到原有期待之上,稱之為期待的內容增生,這種額外的期待隨著強語境的植入“I don’t even like my own”,讓受話者的認知語境控制在關于孩子的解讀上,了解到Gaby連自己的孩子都不喜歡,“even”在這里是一個有標的用詞,可以推導“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人,更不會愛其他人的孩子”這一結論,從而豐富了受話者對于Gaby給出的關于孩子的新信息的認知,最終得出的話語解讀是“不希望從事和孩子有關的工作”,這個解讀既滿足了最初的期待,也滿足了被具體化以后的期待,推理終止。
第三種,曲折動態滿足。這種情況是比較復雜的話語解讀過程。職業交往中,無論是漢語還是英文,人們往往對上下級的敏感程度都略高于日常生活,在發生拒絕這樣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時會分外小心而采取更為曲折的方式,這對于解讀話語的人而言,語用推理的過程會變得比較復雜,此時在語用推理過程中期待會發生層級調整,推理結束時得出的認知效果是一種滿足綜合變化后的關聯期待。如例[6]中的受試,當被要求接手他人工作時,受試表明自己已連續工作多日。當受話人接收到這個信息時,發現該信息并不滿足他最初的具體期待,即回答與“工作”、“生病員工”和“是否同意”有關。然而,受試的回答生成的顯義無法與語境匹配,也就是說受試“連續工作”和預設的推理方向“生病員工”等無法產生聯系,受到語境的限制,原期待不得不取消,連帶其推理方向也被阻止繼續。進而,受話人根據省力原則,在話語產生的場合、非言語交際行為(如對方表情和手勢等)和個人認知體系中尋找足夠相關的解釋,發現當“連續工作14天”和“忙、累”這一語境假設的可及度比較高,作為隱含前提被臨時調用,所以該受試的話語能夠找到具有關聯的解釋。其實,推理并未終止,因為,想要滿足該關聯期待,受試本可以說“不”來表達拒絕,既然舍易取難,必然有其原因,于是,受話人的期待又動態演變到下一層級,并使得其期待增加了新的內容:找出不直接拒絕的原因。即,用表述自己對公司的貢獻作為理由,削弱了拒絕本身的直接度和不禮貌程度,也表達了加班的辛苦和些許不滿情緒。自此,語用解讀滿足了語境和話語內容下的動態關聯期待,各層期待均被滿足,從而初始期待也不言自明,推理完成。
(二)語用推理終止于關聯期待的放棄。
關聯期待的放棄,常常被認為是話語理解失敗的結果。然而我們發現,在釋義拒絕的過程中,預設語境范圍內或與語境相關聯的推理方向上體驗不到相關的語境效果是常態,這種情況下,推理經常會被取消,但這并不是推理失敗的標志,而是為了實現對拒絕的解譯而擴大語境范圍和泛化推理方向,來生成新的期待。關聯理論本身是承認語境有大有小的,熊學亮[5](p1-6)認為在小語境內(如語句提供的信息)不相關的信息在大語境內(如百科知識介入)可以相關,在原有語境中不相關聯的信息在擴展了的語境中可以關聯。也就是說,語境的延伸和擴展是隨需要可以實現的。
在對拒絕語料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當受話人對于對方的信息傳遞意圖有了關聯期待,而話語的實際內容卻無法和受話人腦中的任何可及語境假設產生關聯從而達到足夠的認知效果時,受話人有兩種途徑解決這個問題,一是被迫放棄推理,二是可以通過將對該話語的解讀留在短期記憶內,等待接下來的交際提供合適的語境假設時,再來進行二次解讀。如:
[7]Bree:…Some Salmon en croute or perhaps some cog au vin?(《絕望的主婦》)
Vitale:Got anything I can pronounce?
[8](調查問卷第4題“送禮”)
您的回答:我的妻子是位非常嚴厲的母親,上次兒子成績沒考好,鬧著要去動物園,我偷偷給帶去了,回家就挨了批評。這東西帶回去,老婆還不把我給剮了。我有時太寵小孩了,應該檢討,老婆是對的。所以我從不會送孩子這么貴的禮物。
在例[7]中,Bree提供關于宴會餐點的建議,客戶Vitale是受話人,他對于Bree的餐點安排是有宏觀期待的,然而,出身上層社會的Bree脫口而出的法語菜名讓Vitale無所適從,他無法將該信息與腦中的舊有知識和語境假設做出關聯,雖然語境明確,上下文清楚,但該信息無法達到足夠使受話人順利推理的認知效果,Vitale只有被迫放棄推理,通過打斷Bree的話來拒絕并重新發問,要求獲取足夠關聯的新信息,寄希望于新信息能夠產生恰當的認知效果,挽救放棄推理帶來的交際失敗。
例[8]問卷中的受試,為了拒絕下屬的送禮,可謂并不輕松。首先講了一個略顯得沒頭沒尾的故事,無法為現有語境產出相關的認知效果,聽者的關聯期待僅僅在最宏觀的一個節點上等候“接受或不接受禮物”。所以,此故事一出,必然會讓受話人的期待落空,從而只能停止該期待。由于在可及性高的語境中無法產生與“妻子”“動物園”等所指相匹配的認知效果,該受話人也無法改變期待和推理方向。此時唯一能做的,便是靜候接下來的話述是否能擴大語境的可及度。接著,受試用到了“這東西帶回去,老婆還不把我給剮了”這樣半開玩笑的語用策略,使得聽者的初始期待重新得以顯現:
“帶孩子去動物園就會挨批評”
“替孩子接受貴重禮物更會挨批評”
“接受了禮物等于寵壞了孩子”
“所以,拒絕收禮”
其實,一般情況下,受話人發現期待需要被迫放棄時,往往會盡量延緩這個過程,為的是將交際損失減到最少,而在這個拖延的時間內語境可及范圍會變大,在新范圍內如果能找到與話語結合產生足夠量的認知語境假設,話語依然能得解。這里的受試并未用到明確的“不”字,而用了一則小故事,委婉地表達了拒絕的含義,對方在釋話的過程中,隨著關聯期待的產生,停頓,重新獲得,推理結束,也漸漸能明白拒絕者的良苦用心。這樣的拒絕,既不太傷害對方顏面,也給自己留下臺階和樹立了形象,是職業交往中常用的一種拒絕模式。而解讀這個拒絕的過程,看似是期待的放棄,其實只不過是期待的暫停。
四、關聯理論下的拒絕言語行為的多樣化
在不同場合下,人們可以自主選擇是使用語言還是保持沉默,又或是使用非語言,如肢體語言來達到交際的目的。實際上,語言的使用是一種交際的選擇,這種選擇包括語音、語義、句法、詞法和句子結構等、。而做出相應的語言選擇并不是隨機的,為了使得交際順利進行,語言選擇背后有著許多的因素如語境、對象、文化制約等。
根據關聯原則,話語的理解過程是在一系列的語境假設中做出選擇,語境有大有小,既能指通識和百科知識,也包括長時記憶、短時記憶、文化背景、詞匯形式等等。解譯話語的關鍵是在可及度較高的語境假設中尋找關聯信息,可及度越高,解譯所需要的努力就越小,話語就更容易理解,反之,可及度低的語境,解譯所需要的花費就更大,理解可能更費周折。
當拒絕者聽到一個請求、邀請等時,他/她將自己要表達的信息進行“明示化”給受話人,分別明示其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由于受話人是發語者,所以自然會在初始階段生成關聯期待,并使用其邏輯思維、百科知識和詞匯語法解碼知識來創造一個語境假設,或是當一個語境假設不夠足量認知效果時,創造一個系列的語境假設,接著從這一個系列的語境假設中尋找具有最佳關聯的假設,來解譯該“明示話語”,得出被拒絕的結論。其實,拒絕者的話語表達過程和受話者的語用推理過程是同時進行的,拒絕者表達拒絕含義時也受到語境假設和諸多其它因素的影響,反應出來的拒絕策略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策略的綜合使用。想要理解這個拒絕的真實含義,需要從一系列的語境假設中做出選擇,這個選擇在雙方的認知環境中既省力又是最佳關聯。在一種文化里,人們對于最佳關聯的選擇可能在另一種文化里是根本說不通的,或者說在一種文化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進行語用推理在另一種文化里需要更加費力才能搭建起關聯橋梁。
語境假設本身是多樣的,是具有個體差異的,對于個體而言,隨著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個性特征和所處環境的不同,其認知能力和語境假設的范圍體系也有所不同,特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生、成長、受教育的中國人和美國人,他們對于最佳關聯的選擇必然是不同的,思維推理的路徑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么在相同場景下表達拒絕,他們的言語選擇和策略選擇也是不同的。例如:
[9](問卷調查第6題“邀請做講座”)
您的回應:我這何德何能啊,還為你們部門的人做培訓,況且你那個部門的一些業務我也不是特別的懂,當然沒有你那么專業了。
[10] (問卷調查第6題“邀請做講座Inviting you to do a lecture”)
Your reply: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packed at the moment.I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though.Have you asked…?She may be available.
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樣的拒絕場景中,語言的選擇不僅僅限于詞匯、語法、句法等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認知背景和語境假設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策略。因而,在解譯拒絕的過程中,也會經歷不同的語用推理過程。
就本研究中的語料樣本來看,職業交往中的拒絕往往采取更為委婉的間接語用策略來實施,這也要求聽者付出額外的努力才能順利釋話。“只要言者以最佳關聯性為交際目標,就有理由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一定是為了驅使聽者去尋求更多的語境效果,以此來補償為這類話語所付出的代價。”[8](p9-16)
例[9]中,受試的回答使用了“自我嘲諷”的語用策略,該策略使得聽者無法從當下情景中尋找關聯來滿足自己的原始關聯期待“是否同意”,于是促使聽者調用上層語境里中國人傳統的“自謙”實則表示“推脫”的認知概念,從而拒絕得解。美國文化崇尚獨立和個性,例[10]中的受試希望自己的時間和自由不被束縛,因而用完全關乎自身的理由來拒絕對方,是可及性很高的強語境,受話人只要聽到這句,便可以順利推導出拒絕的含義。而接下來這位受試還使用了另一條語用策略“提供它法”來降低自己起初拒絕時的強勢語氣。試想,若是美國人聽到例[9]中的拒絕,由于無法適應“自謙”這樣的東方高權勢文化,沒有相應的認知背景和語境假設,必然會在語用推理過程中不斷推翻之前的關聯期待,關聯期待則得不到滿足,從而給理解造成困難,即使反復生成關聯之后最后拒絕得解,也由于不理解該策略使用的目的而危害了其面子,引起交際不愉快甚至是交際失敗。同樣,若是中國人聽到例[10]這樣的拒絕,雖然下一番功夫也能理解其明示的拒絕意圖,然而必定會危害交際本身的意圖,即人際關系的維護。
五、結語
拒絕,特別是職場中的拒絕,是一種極具面子侵害的言語行為,為了保證交際順利達成,拒絕者會采用各種形式的間接語用策略來完成拒絕。而對于被拒絕者來說,解譯這些紛繁復雜的間接策略,是需要預設期待、關聯期待、并隨著期待的取消重置和認知語境的改變來調整期待,動態性地過渡到另一個層次或另一個性質的期待,最終使得各層次上的期待被滿足或是為取消的期待找到相應的理據,從而完成語用推理過程。我們發現,在拒絕言語行為的解讀中,關聯期待的放棄并不一定就意味著語用推理的失敗和交際本身的失敗。因為,對于拒絕話語而言,其關聯期待的具體程度是很高的,對于推理結果的期待是很明確的,由于預設的語境是強語境,所以即使關聯期待被迫放棄,聽者也可以繼續發問來尋找建立聯系的辦法,或是暫停期待,繼續在接下來的話述中尋找隱含的前提和調用更為廣泛的預設語境,直到期待被再次激活,尋找推理繼續的理據。
正是因為話語的理解過程是在一系列的語境假設中做出選擇,語境的大小區別、記憶的長短、文化背景等都可以造成對于語境選擇的不同。所以,在一種文化里人們對于最佳關聯的選擇可能在另一種文化里是“不可理喻”的,這也給跨文化語用學和跨文化交際學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理論視角。關于這部分的漢英語料對比研究,我們會另行文論述。
[1]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
[2]Wilson,D.&D.Sperber.Relevance theory.Entry in G.Ward and L.Horn(eds.)Handbook of Pragmatics[Z].Oxford:Blackwell,2004.
[3]Wilson,D.Relevance and relevance theory.Entry in R.Wilson&F.Keil(eds.)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Z].MIT Press,Cambridge MA1999.
[4]楊子.言語交際的關聯優選模式及其應用[D].博士學位論文,2008.
[7]熊學亮.試論關聯期待的放棄[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3).
[8]張亞飛.關聯理論評述[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