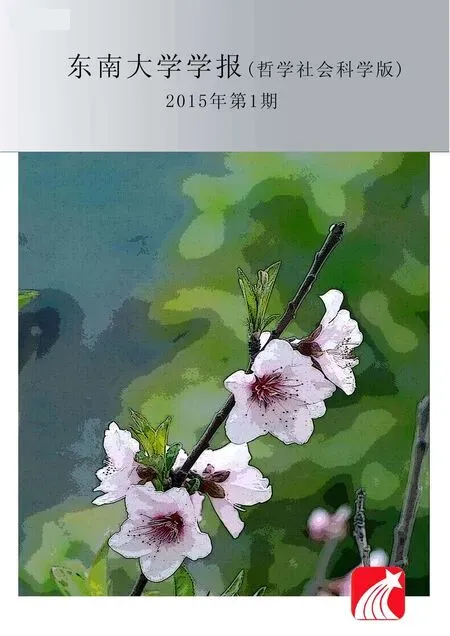淺論明朝政治制度中的困境——以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為范本
劉伶俐,吳江龍
(華東師范大學 政治學系,上海200241)
本文力圖以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為范本,明朝的政治制度進行剖析,目的是通過對明朝政治制度瓶頸的反思,對政治制度能夠有更為全面的理解,對當前我國政治制度中面臨的問題形成現(xiàn)實觀照,不斷完善和發(fā)展當前的政治制度。
一、關于文官集團
文官集團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一般是指中國古代提倡以儒家文化為標桿修身、齊家、治國的擁有官職的士大夫階層。黃先生書中人物的困惑、命運及整個帝國的結局都與文官集團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那么,文官集團是如何出現(xiàn)的呢?
中國古代自有“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也就是說,一個人書讀好了,就必須考取功名,爭取走上仕途。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非常重視儒家文化對人的教化作用。在人才的選拔上,采取了“八股取士”的考試制度,考試內容以宋朝朱熹注釋的《四書》為主。在考取功名的途中,他們不斷誦讀儒家經典,將儒家思想內化于心,通過對儒家思想的理解與把握,讓自己的行為盡量與典籍提倡的行為保持一致。但是通過讀書成為士大夫中的一員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的。中國古代是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國家,一個家族若想更好地保障家族的地位或財富,就會挑選家族中優(yōu)秀的成員,投入巨大的資源支持他們考取功名。一旦他們進入士大夫階層,就會利用自己擁有的資源為家族盡義務,如增加財富、幫助家族中的其他成員走上仕途等。如果他們沒有這么做,就違背了他們熟記于心的儒家道德,忘記了“飲水思源”。當然,中國古代的文官集團不單是有家族關系,而且還有同年、同鄉(xiāng)等各種關系。實際上,文官集團就是由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組建而成。
一個人通過仕途可以實現(xiàn)自身治國平天下的偉大抱負,也可以增強家族的實力。那么,文官集團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呢?一般認為,明朝自洪武皇帝廢除丞相制度后,就“沒有了傳續(xù)幾千年的宰相體制,而是由皇帝自己直接來負責政務的處理,直接統(tǒng)轄行政部門”[1]181。廢除丞相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更好地鞏固皇權,打破宰相與皇帝分權的格局。但是這種企圖加強皇權的制度卻將所有國家事務的重擔壓在皇帝的肩上,這種制度設計要求皇帝必須要有很強的主持朝政的自覺性以及處理政事的高效性。明朝歷史上,像朱元璋那樣具有強烈的權力欲望的皇帝并不是很多,如正德皇帝因對打仗感興趣,非得給自己封個“將軍”的頭銜;嘉靖皇帝后期癡迷于修煉丹藥,對政事不聞不理;而萬歷皇帝在“立太子”風波后,一直處于逃避的狀態(tài)。由于沒有宰相為皇帝分擔政務,明朝逐步形成內閣制度。內閣作為文官之首,在政治生活的運作中,實際上成為了宰相的“替代品”。到了萬歷年間,明朝經過兩百多年的發(fā)展,文官集團也不斷成熟,擁有龐大的勢力。
二、政治制度中的角色沖突
黃先生將書中的各個章節(jié)以人物命名,萬歷皇帝是明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申時行、張居正是內閣首輔,志在實現(xiàn)個人抱負的皇帝顧問,海瑞是重視倫理道德的模范官僚,戚繼光是有豐功偉績的一代名將,李贄是“離經叛道”的思想家。盡管他們都有身份、有地位,然而他們卻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
萬歷皇帝處在權力的頂峰,他代表著天命,即韋伯所說的“克里斯馬型”權威。然而,作為帝國最高統(tǒng)治者的萬歷卻無法選擇自己最心愛的女人所生的兒子——朱常洵作太子。祖宗的傳統(tǒng)無形中給他造成了巨大壓力,文官集團也在實際行動中不斷地告訴他:長幼有分,嫡庶有別,必須立朱常洛為太子。立儲事件僵持了將近十年,萬歷皇帝的想法遭到朝中文官的一致反對,最后迫于無奈不得不立朱常洛為太子。萬歷皇帝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擁有治理國家的權力,卻沒有選擇太子的自由,正如黃先生所言:“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摒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御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于廷臣”[2]102。萬歷心里的憤怒與苦悶沒有人能理解,他不再管理朝中繁瑣的事務,不批閱奏折,消極怠工,也許這是他唯一的反抗方式。
張居正和申時行同為內閣首輔,但兩人的行事風格完全不同。張居正在十年的任期內,主張新政,他施行一條鞭法,希望改善帝國的財政體系,增加帝國的財政收入。他整頓吏治,企求改革文官集團,提高政府行政系統(tǒng)的運作效率。然而他的一系列的改革觸動了利益,引起文官集團莫大的恐慌,以至于他死后被清算,家產籍沒,子弟流放。“為什么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jiān)視之下,并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2]81。申時行繼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后,行事風格與張居正完全不同,他是一個具有誠意的人,寬厚地處理事情,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jié),有著清晰的認識。他充當“和事佬”的角色,希望能夠調節(jié)陰陽,希望能夠求得各方的團結。但他的誠意終究沒有讓他安然地收場,在立儲事件中仍然擺脫不了文官對他的道德譴責而背負上“墻頭草”的罪名。
海瑞作為“古怪的官僚模范”,一直成為民間傳誦的“正直的清官”典范。他以正統(tǒng)的道德作為自己行事的標桿,重視民生,打壓地主,直言皇帝,嚴懲貪官污吏。正因為他的勵精圖治,與文官集團需要維持現(xiàn)狀的格局相沖突。他的一生起起落落,在樹立起他的榜樣形象的同時,也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一代名將戚繼光在軍事上有著豐功偉績,面對東南沿海的倭寇和北部的蒙古軍隊,戚繼光從技術和組織上進行軍事改革,發(fā)明了許多新的軍事技術,提升了軍隊戰(zhàn)斗力,最終消除了東南沿海倭寇的騷擾。即使有著豐厚的功績,最終也因為張居正的倒臺及重文輕武的傳統(tǒng)而成為孤獨的將領。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贄,剃發(fā)為僧,反對程朱理學,在今天看來是自由主義者,但他被世俗所垢,難溶于當時的社會最終選擇了自殺。
黃先生筆下每一個人,雖然處于不同的位置,但是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個性都非常鮮明,但他們對個性的追求都使他們身上都背負著難以卸下枷鎖,在制度內引發(fā)強烈了角色沖突。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人的命運會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個人的遭遇又反映了所處時代的特點。
三、關于政治制度的道德化
黃先生在該書的自序中直言: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明朝政治制度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導致法制在中國不能茁壯成長。在皇權制度下,禮制與道德的結合——“禮治”成為官方的主要治理手段。
禮制的形成和確立在西周時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如《禮記·曲禮》中記載:“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論,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成不莊。”[3]24可見,禮制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已經建構起基本的框架。而禮制與道德的結合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完成的。春秋戰(zhàn)國是“群雄爭霸”而“禮崩樂壞”的時期,西周時期崇尚的禮制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亟需尋找新的治國方案來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然而,諸子百家提出的眾多治國方案中,并不是在否定禮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而是從各自的思想出發(fā)對禮制進行新的辯護,如最主要的儒家提倡“克己復禮”,主張“禮治”“德治”。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主張的“禮治”成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禮治”借助權力的力量實現(xiàn)社會化,比如,“在以儒學為基準的選舉制度確立之后,教育制度完全受到科舉的影響而成為科舉之一環(huán),……由于選舉和取士的制度日益單一化,導致教育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合一化傾向,官方的知識傳播系統(tǒng)自不用說,由于權力指向的唯一性,民間的知識傳播體系日益向科舉準備轉向。到明清時代,整個教育體系包括兒童的啟蒙教育都日益以科舉為唯一取向,這樣,權力、儒家知識和政治合法性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便完整地建立起來。”[4]23除此之外,儒家文化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如朝廷禮儀、宗廟祭祀、政府組織和法律等,使統(tǒng)治者獲得合法性。明朝時期,儒學已經發(fā)展成程朱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要求人們自覺地遵守道德規(guī)范。
那么,這種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又是如何束縛著人的行為,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呢?前已述及文官集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儒家思想教導這些士大夫要成為君子。作為君子,通過對儒家經典的理解與把握,他們在處理各項事務中把圣賢語錄作為衡量是非曲直的標準。事實上,擁有強大勢力的文官集團成為儒家道德規(guī)范的發(fā)言人。皇帝對于文官來說只是一種制度的象征,他們標榜“道德倫理”,不希望皇帝通過行使權力獲得權威,而是給予皇帝太多的教化——要成為道德模范。所以,對于萬歷皇帝,他“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guī)范,但是道德規(guī)范的解釋卻分屬于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倫理道德”[2]110。對于整個帝國來說,任何企圖觸犯文官利益的改革,都難以避免失敗的命運,“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后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5]60。
四、評 價
黃先生的這本小書從序言到結論總共不超過300頁,但其中心思想也非常鮮明。《萬歷十五年》從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截取了一個小的歷史節(jié)點,從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的詳細地分析了六個人物的政治歷程,探尋這些人物背后的制度性悲劇。總的來說,黃先生對明朝的政治制度持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但是任何事物都很難十全十美。黃先生對明朝的分析只是局限于作為上層的皇帝與官僚的層面,而忽略了占有多數的普通民眾。事實上,晚明的社會可以分為兩層結構:在上是龐大的官僚集團,在下則是多數無組織的農民,例如在1578年,山東省的3000農民,由于饑荒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的白蓮教信徒也不斷增加。[5]52-53那么,對于這些不讀書、不明理、沒有在歷史上留名的普通民眾,是如何通過道德治理的規(guī)則維持其協(xié)調性的呢?
對于普通民眾的儒學教化,是由民眾所處的社會組織和環(huán)境決定的。杜贊奇認為,文化網絡由鄉(xiāng)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guī)范構成,這些組織既有以地域為基礎的有強制義務團體,也有自愿組合而成聯(lián)合體,文化網絡還包括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絡,比如血緣關系。[6]13-14明朝時期,處在這一權力的文化網絡中的農民也會時刻受到儒家道德教化。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民,他是某一家族的成員,從小就會受到家族規(guī)法的規(guī)訓。除此之外,他還可能要經常參加宣講活動,在生活中會遇到許多儀式和象征,向他傳達儒家道德倫理的信號,這些活動都是通過生活化的儀式將儒家道德內化于心。[7]50也就是鄉(xiāng)紳通過“間接管制”將各項“民規(guī)習俗”延續(xù)下去。
將明朝的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來看,16世紀的歐洲已經開始逐步走向工業(yè)化的道路,而中國卻處在保守的帝制時代而停滯不前。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也許我們應該理解那個時代。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他們只能從傳統(tǒng)文化中去尋找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方案。而對于現(xiàn)時代的我們,需要通過歷史的失敗,從中獲得經驗與教訓,反思過去,直面未來。
[1] 張鳴.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
[3] 武樹臣.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辭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5] 李贄.焚書(第二卷)[M].北京:藍天出版社,1998.
[6][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7] 劉靜.走向民間生活的明代儒學教化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