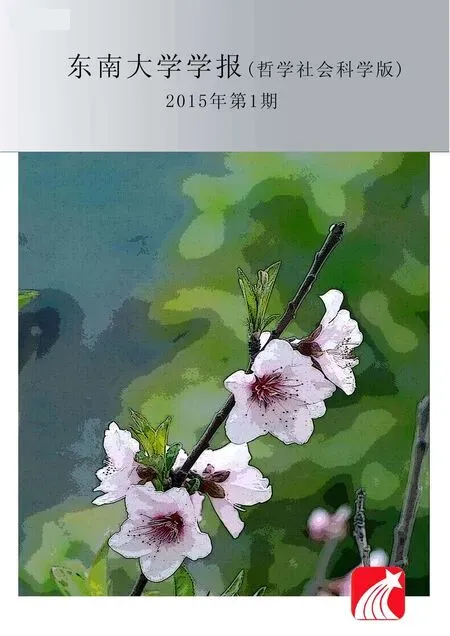法律的規范性解析
李曉飛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法學院,北京100070)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成為黨和政府治國理政新的突破點。法律規范性問題作為法哲學的基本問題,對該問題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對實現全面推進我國依法治國的宏偉目標具有積極的實踐意義。目前學界對于法律規范性問題的探討,基于其性質,主要集中于法律規范性的來源探究。在20世紀開啟實證法的規范性研究,同時做出了有關法律規范性論述的學者中最具分量的是凱爾森,而另一位對法律規范性理論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是著名法哲學家哈特。
一、實證主義法律規范性學說
作為實證主義法學兩位重要的開拓者,他們都將對實證主義前輩奧斯丁法律命令主義的分析與批判作為切入點,恪守法實證主義的基本原則,堅持法律規范性的獨特性,并且反對將法律的規范性與道德的規范性混為一談,反對將法律簡化成一系列相關聯的事實的現實主義傾向,也就是法律不可還原的規范性品質,反對將法律的規范性立基于道德考量的任何企圖。在現代實證主義法律學看來,對于法律規范性的理解主要在于探討法律正當性效力的來源,法律如果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也就具備了規范性。所不同的是,他們對法律規范性的來源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因而構成不同的法律規范性理論。
(一)凱爾森“基礎規范”理論下的法律規范性
凱爾森認為:“一個規范效力的理由始終是一個規范,而不是一個事實。探求一個規范效力的理由并不導致回到現實去,而是導致回到由此可以引出第一個規范的另一個規范”,按照他的理解,一部法律的效力來源于另一部法律,現實中就是所有法律效力最終來源于第一部憲法法律,而憲法作為法律效力的根源,它的效力來源也必須有一個合理解釋。對于這個問題,凱爾森提出了著名的“基礎規范”理論。基礎規范做為整個法律體系的效力源頭,它本身給予了法律正當性。但這種基礎規范不是一項事實存在,而是一種虛構,它不是某種實際規范,之所以必須虛構這種基礎規范,是“因為沒有它,整個歷史事件的規范性也就不能建立”。當人們虛構出一個應當被遵守的基礎規范時,尋求一個規范的主觀意愿,為了實現在現實中客觀遵守的要求,在由主觀向客觀轉換的過程中,這個虛構是必不可少的。在哲學層面解釋,這種存在于主觀向客觀轉變之時必不可少的假設,它的必不可少就是其有效性,這個假設就是基礎規范。試想一個本無政府的社會,在尋求一個法律治下的政府,則必然會假設一部憲法作為各法律的效力根源,也許這個憲法的效力是虛構的,但是對它正當性的這種虛構卻是必不可少的。對于堅持要構建一個純粹的法理論體系的凱爾森而言,虛構一個基礎規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可以看出,他對法律規范性問題的分析局限于形式層面,這是與他秉持的法是一種“應然”范疇而不是某種“實然”范疇的理念密切相關的。他從形式上強調了法律具有規范性,但實際上并沒有回答該問題,即具備何種現實性條件,法律才會具有規范性。任何規范性都應該源自現實生活,只有現實條件才能給予法律不同于其它規范的獨特規范性,從而區分法律與其它社會規范。
(二)哈特“承認規則”下的法律規范性
另一位對法律規范性問題提出重要論斷的是法學家哈特。哈特認為,法律是具有規范性的,法律的規范性來源于人們對其有效性的承認。哈特的創造性工作,來源于他對如下社會事實的精準把握:當一個人嚴肅地主張某一規則有效時,事實上他已經在使用自認為妥當的效力規則來鑒別法律,而且該效力規則不僅是個人運用的判斷標準,也是被社群成員普遍接受的,這種規則在該法律體系的運作中被普遍采用。哈特將這種公民對法律效力的最終判斷標準稱作承認規則,將法律是否具有規范性與其是否符合這種承認規則聯系起來。應當指出的是,該理論中承認與承認規則是不同的:承認規則是一套復雜的理論體系,承認是公民個人的一種行為狀態。哈特是反對凱爾森基礎規范理論的,他認為法律效力的來源不在于一個邏輯預設,而在于人們于社會實踐中的承認規則。由此可見,哈特與凱爾森眼中的法律規范性問題是不同的,凱爾森把法的效力和法的規范性等同了,法律規范性構成了法律規則,是它的邏輯屬性,一個法律只要有效,就具有規范性;而哈特在法的規范性問題上退了一步:法是否具有效力取決于它是否符合承認規則的要求。換言之,有效的法律可能具有規范性,但不是必然具備。哈特指出了法律是具有規范性的,這種規范性來自于法律在人們的承認規則中有效與否。但是,他并沒有進一步指出這種承認規則的來源是什么,它究竟來源于人內心的道德觀念或是具備其它理由。
二、客觀“秩序”視野中的法律規范性解析
(一)法律規范性的概念
某事物具有規范性即意味著它能夠為人們從事它提供正當理由。法律具有規范性就意味著它能夠為人們遵守它提供正當理由,能夠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正當標準。倫理規范、道德規范與宗教規范都具有規范性性質,它們都提供了“應然”標準,社會照此標準行事,便得到了道德上、宗教上等等的行為依據。
(二)法律規范性與法律規范性作用互為邏輯屬性
法律能夠為人們遵守它提供正當性支持,這種作為人們行為依據的性質,就是法律的規范性性質。規范性性質具有的作用,也就是引導人們行為的作用,稱為規范性作用。法律的規范性作用與法律的規范性性質概念是不同的。筆者認為,分析法律的規范性,可以從法律規范性與法律規范作用的關系入手,因為法律的規范性作用是其規范性的現實體現。
關于規范性作用與法律規范性的關系,應當指出的是:法律規范性是其規范性作用的前提條件,具有規范性則必然具有規范性作用。反之,具有規范性作用,也正說明了法律具有規范性。外在的規范性作用與內在的規范性是不可分割的。
每一種法律秩序都或多或少與道德秩序相一致,如果統治階級信奉某種道德或受某種道德制約,并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考慮這種道德,那么該法律秩序從道德的角度看就是正義的,人們這時可以說,法律對人符合它的行為以正當性支撐,并能引導人的行為,這種情況下法律具有規范性,它指引了人們的行為,起到規范性作用;假設一個社會不存在道德時,這個社會要想維持下去,會比當下處于道德規范中的社會更需要法律使社會避免解體。
法律在社會中的作用不在于它符合道德來指引人們,使生活更美好;而在于它起著維持秩序的作用,在這種秩序中人們迫于周圍人的壓力才遵守法律,或為了行事方便,或懼怕權威的制裁而受這種規范指引。久而久之,在社會成員眼中,不是法律在指引自己的行為,而是周圍人在指引每個人的行為,這種行為慣性的結果,會導致一個本來沒有這種道德的社會,因為人們長期行為一致,而產生新的道德。可以看出,法律與道德是不同的,毋寧說法律與道德只是偶然混雜在一起發生作用,而沒有必然聯系。
歷史上,具有規范模式法律的誕生晚于道德,但群體社會中對秩序的維持,周圍人帶來的壓力,卻早于道德的產生。得益于智力狀態的進步,道德與法律才被區分開來,可以說法律真正來源于秩序本身,而非道德。法律的正當性與道德是相分離的,它的正當性就是秩序的存在自身。法律的正當性不來源于道德,而起源于秩序本身。法律作為維持秩序的工具,其正當性在被制定出來的那一刻便因起著規范性作用而被賦予,法律指引人的行為這種規范性作用的體現與規范性性質是緊密結合的。一種社會規則,它的規范性作用也正說明了其具有規范性。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則,其規范性和其規范性作用兩者互為對方的邏輯屬性,不能割裂開來。
法律是具有規范性的,其規范性出于有效性,但是有效性必然來源于法律之外,決不能靠后天誕生的法律自身來解釋。同時,法律的規范性也不能以符合承認規則加以解釋,法律沒有先天范本,它歸根結底來源于群體意志,只是表現方式在不同社會形式不一。從法律目的的角度看,它是為了維持秩序的存在而存在的,在“秩序”的視野中,群體意志相對于個人意志而言,其實已經上升到客觀現象的層面,此時個人意志不再是影響群體意志的根源,只能視作對群體意志的影響因素,法律規范性的根源也只能落腳在秩序的存在本身,而非個人意志。
[1] Sylvie Delacroix, Hart ’s and Kelsen ’s Concepts of Normativity Contrasted[J]. Ratio Juris,2004. 17(4):501-502.
[2][奧]漢斯·凱爾森. 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 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3] 范立波. 論法律規范性的概念與來源[J]. 法律科學,2010(4).
[4] 苗炎. 哈特法律規范性理論研究[J].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