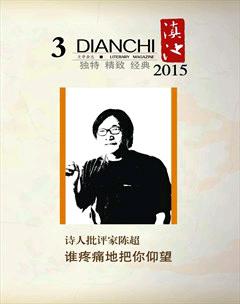靈韻消失的世界
一
70后作家俞勝一直以來把自己當(dāng)作城市中的“異鄉(xiāng)人”,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打量自己生活的都市,關(guān)注農(nóng)民工和外來者在都市生存中的身份焦灼與城里人“小市民”式的狹隘、功利與文化偏見。這種關(guān)注,糅合了作家的個人經(jīng)驗和對當(dāng)下中國現(xiàn)實進(jìn)程的思考,使其作品呈現(xiàn)出純正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色彩。在他引起較好反響的作品中,《當(dāng)來到霞村的時候》書寫底層青年希望通過考研躋身大城市的磨難與苦痛,也寫出了在考研族身上漁利的種種人群的可憎面目;《我在學(xué)報當(dāng)編輯》寫出了文化機構(gòu)內(nèi)當(dāng)代“文化人”的“儒林外史”;《城里的月亮》寫出了都市月光下生活在城里的異鄉(xiāng)人的陰冷和遭受的各種歧視與冷暴力。這些都說明了俞勝一直以一種“問題意識”牽引自己的寫作,將目光對準(zhǔn)現(xiàn)實中的各種痼疾與頑癥,而不作無謂的無病呻吟。但在現(xiàn)實問題面前,俞勝并不悲觀,他的筆調(diào)悲涼中仍有暖色,筆觸輕松幽默中又不失凝重,這與他本人平和的個性以及對人性的寬容理解應(yīng)該不無關(guān)系。著名作家范小青認(rèn)為,俞勝的小說創(chuàng)作“有不落俗套處,有一種內(nèi)在的韻味,文字也很漂亮”;評論家肖鷹則認(rèn)為俞勝的作品“不僅在敘事結(jié)構(gòu)和語言駕馭兩方面均展示了非常好的張力,舒展自如,引人入勝;而且將農(nóng)民工和城里人的傳統(tǒng)隔閡展示在底層生活的糾結(jié)中,既向讀者揭示了‘類群偏見的愚昧,又使讀者感受到底層生活不可泯滅的人性美麗。”這些評價都是非常切中肯綮的,從其新作中篇小說《田螺姑娘》和短篇小說《田婄的苦旅》中也可以看出俞勝一以貫之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題材關(guān)注。
二
中篇小說《田螺姑娘》講述了一個城市底層青年與高官情人之間的意外邂逅與情感交往。這種情節(jié)設(shè)置本來是有很大風(fēng)險的,很容易淪入網(wǎng)絡(luò)言情劇中的種種“屌絲逆襲”之類的橋段。但正如同樣的食材在水平懸殊的廚師手里加工出來味道絕然不同,高明的作家也能“化腐朽為神奇”,將平常的素材加工成不同凡響的藝術(shù)品。
《田螺姑娘》在文本中設(shè)置了“復(fù)式結(jié)構(gòu)”,使神話傳說和當(dāng)代生活成為小說中兩個互相應(yīng)證、互相辯駁的部分。小說一開頭就先講述了70后耳熟能詳?shù)纳裨拏髡f“田螺姑娘”的故事。在這個傳統(tǒng)的神話文本里,一個農(nóng)村青年意外邂逅了一個美麗、善良、勤勞的田螺姑娘,但又因窺破她的秘密而導(dǎo)致后者離開。講完這個故事,作者接下來用十九節(jié)的內(nèi)容分別從下崗工人吳大軍和高官情人申小莉的視角敘述兩人的交往始末,從而再現(xiàn)了一個當(dāng)代底層青年邂逅當(dāng)代“田螺姑娘”的故事。兩個故事的結(jié)局都是男主人公因為窺破對方的秘密而導(dǎo)致后者離開,不同在于此“田螺姑娘”非彼“田螺姑娘”,那個傳說中的美麗、善良、勤勞的田螺姑娘對應(yīng)的是當(dāng)代的同樣美麗卻輕浮、甘當(dāng)寄生蟲的“田螺姑娘”。這一小說結(jié)構(gòu)令我想起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在這部世界名著中,喬伊斯也用神話故事與當(dāng)代生活的雙線結(jié)構(gòu)對作品進(jìn)行總體構(gòu)思。小說的題目來源于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拉丁名為尤利西斯),而《尤利西斯》的章節(jié)和內(nèi)容也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和荷馬史詩《奧德賽》內(nèi)容的平行對應(yīng)關(guān)系。利奧波德·布盧姆是奧德修斯現(xiàn)代的反英雄的翻版,他淫蕩多欲的妻子摩莉·布盧姆則對應(yīng)了奧德修斯堅貞不屈的妻子帕涅羅佩。與《尤利西斯》一樣,《田螺姑娘》的題目來源于神話傳說,神話傳說人物的美好形象與當(dāng)代人物的丑行形成了對比,小說所寄寓的反諷意味油然而生。
德國哲學(xué)家本雅明曾經(jīng)在其著作中用“靈韻的消失”來形容機械復(fù)制時代與商品經(jīng)濟時代審美體驗的瓦解和崩潰。其實,推而廣之,“靈韻的消失”不僅僅可以形容商品經(jīng)濟時代的文化產(chǎn)品,也可以描述以功利為邏輯的時代中的人際關(guān)系。可以說,俞勝在《田螺姑娘》中所描述的就是這樣一個功利至上的靈韻消失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不再是一個能夠誕生神話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中的底層青年再也找不到那種神話傳說中僅僅為感恩就愿意以身相許的美麗善良的“田螺姑娘”。申小莉與市長之間固然有感情,但更多的是利益交換。申小莉在吳大軍身上尋求的也只是寂寞時的肉體安慰。一旦這種關(guān)系可能危機她的現(xiàn)實利益的時候,她就果斷地將吳大軍的手機號屏蔽,從吳大軍的生活里消失。
正如肖鷹先生所評論的,俞勝對人性并不悲觀,所以即便是對他所批判的對象,他也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盡力去發(fā)掘他們身上人性的閃光。吳大軍和申小莉之所以認(rèn)識是通過他們各自的寵物。這樣一個情節(jié)設(shè)置本身也是意味深長的。它意味著在今日都市社會的層級化結(jié)構(gòu)中,不同階層之間已經(jīng)很難建立起正常的人際聯(lián)系,而只能通過人與動物的關(guān)系曲折地建立起聯(lián)系。從小說的結(jié)尾可以看出申小莉?qū)櫸镅喷饕约皩谴筌娺€是有點感情的;當(dāng)然,這點感情不足以超越階層隔閡和現(xiàn)實的利益計算。
三
與《田螺姑娘》相對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設(shè)計不同,短篇小說《田婄的苦旅》在結(jié)構(gòu)上要單純得多,但作品的內(nèi)在含量并不簡單。作品聚焦于都市大齡未婚女青年的現(xiàn)實苦惱。田婄之所以急著要在35歲前將自己嫁出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周圍人給予的巨大精神壓力。她唯一的閨蜜(可見單身大齡女青年在現(xiàn)實中往往被當(dāng)成難以相處的另類)牛芳華開她玩笑讓她給自己十歲的兒子當(dāng)伴娘,給她介紹的也都是各種“奇葩”。在她眼里,田婄能夠有男人愿意要就應(yīng)該感謝上蒼了。最后,田婄終于找到自己相對滿意的對象,她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從此,牛芳華會淡出自己的閨蜜圈了”。這并不是說明田婄的忘恩負(fù)義,而恰恰是說明田婄作為一個大齡未婚女青年長期以來受到的精神折磨。田婄之所以成為一個大齡未婚女青年,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dāng)年田婄的母親不同意田婄與來自鄉(xiāng)村的男朋友張振海結(jié)婚。最后,繞了一大圈,田婄找到的未婚夫還是來自農(nóng)村的張和平。這無疑是對田婄母親那種都市小市民的狹隘城鄉(xiāng)觀念的諷刺。這一主題在俞勝的《城市的月亮》、《水乳交融》等其他作品中都有表現(xiàn),使得這些作品構(gòu)成了一種內(nèi)在的互文關(guān)系。
四
俞勝曾如是說,“以后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我打算堅持兩種風(fēng)格的路子,一個就是像《當(dāng)我來到霞村的時候》這類的,以一種幽默、略帶調(diào)侃的筆法表達(dá)自己對生活和人生的理解,也希圖給讀者以某種啟示,文章中的人物盡量具有鮮活性和獨特的個性。另一個就是像《人、狗、狼》這樣的寓言筆法,概括地表達(dá)對現(xiàn)實和人生的看法,文章中的人物盡量具有某類人的特征,當(dāng)然也不想把人物寫得平面化。”從他的這兩篇新作也可以看出,俞勝一直在堅持以都市中的“異鄉(xiāng)人”身份觀照都市的各種痼疾、小人物的悲歡;始終帶著他對現(xiàn)實問題的敏感和對人性的寬厚理解帶領(lǐng)讀者一起參與這個時代的進(jìn)程。這種帶著“問題意識”的寫作無疑是能夠給人帶來啟示的,也是大有希望的!
鄭潤良:廈門大學(xué)文學(xué)博士后,《中篇小說選刊》、《人民文學(xué)》醒客APP專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