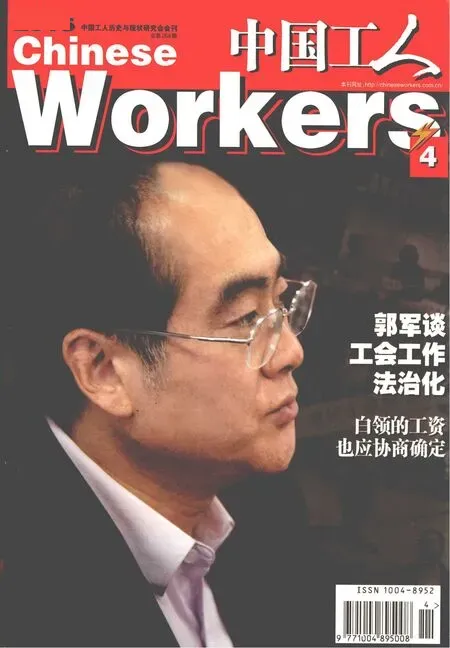三問職工工傷賠償問題
楊召奎
編者按:上一期我們就張為江等建筑業農民工遭遇的工傷拒賠問題進行了討論。在剛剛結束的今年全國“兩會”上,工傷保險、農民工權益等職工關心的話題再次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重要話題,人們期待這些問題一旦經過兩會的討論和人大代表的提案,就能夠早日得到落實。但期待離現實顯然還有一定的距離,仍然還需要一定時間的等待,比如說工傷認定48小時時限問題,去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卓長立曾提交建議,希望調整工傷認定時限。但時至今日,依然沒有明確的答案。
本期“論壇”中,我們重點就“工傷認定48小時時限能否調整?”、“工傷先行支付‘落地’為何這么難?”、“ 超齡農民工能否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三大問題再次進行探討,希望能夠引起社會關注。
職工利益無小事。筆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工傷認定48小時時限能否調整?工傷先行支付“落地”為何這么難?超齡工人因工作原因傷亡能否算工傷?是與職工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亟待解決的三大問題,要找到其答案,期待社會的共同努力。
一問:工傷認定48小時時限能否調整?
2013年3月,山東司機宋洋在高速路上突發腦干出血,他強忍疼痛踩下剎車以生命盡頭的一次安全停靠挽救了33條生命,被譽為“最美司機”。但因接受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宋洋未獲工傷認定。
2014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卓長立提交建議,希望調整工傷認定時限。卓長立在建議中提出,《工傷保險條例》第15條存在爭議,建議完善對這一條款的司法解讀,不應以數字劃分工傷認定的結果,避免產生更大的不公平。但遺憾的是,因兩會議程十分緊湊,這一建議沒有在大會上討論。
問題沒有解決,但同樣的事件仍在發生。
2014年10月24日,北京阜外醫院麻醉科副主任醫師昌克勤在手術室內暈倒。12月2日,醫治無效死亡。因死亡距離發病超過48小時,未能認定為工傷。此事經媒體報道后,再次將“工傷48小時”問題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甚至社交網站有網友稱,上班要在兜里揣聲明:一旦在工作中倒下,搶救不要超過“48小時”。這一“生命戲謔”的背后,是人們對法律在實踐中的機械化,以及對職工合法權益保障的不公存在的質疑。
工傷認定“48小時”的規定如何出臺?是否確有失偏頗?在實踐中存在哪些問題?記者就職工關心的問題采訪了多位專家。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李娟告訴記者,針對工作中因疾病導致傷亡的情形能否被認定為工傷,我國立法經歷了從狹窄到寬泛、再由寬泛到狹窄的轉變過程。
1996年10月1日,我國頒布實施《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正式將工作中的突發疾病納入工傷范疇。該《辦法》第八條第四款規定:“在生產工作的時間和區域內,由于不安全因素造成意外傷害的,或者由于工作緊張突發疾病造成死亡或經第一次搶救治療后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為工傷。”
然而,2003年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對工傷認定的規定又變為嚴格,還在條文中加入了“48小時”的認定時間限制。
2004年11月1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實施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寫道:“突發疾病”中的疾病包括各種類型的疾病,“48小時”起算時間,以醫療機構初次診斷的時間為突發疾病的起算時間。將《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中的“第一次搶救治療”縮短為“第一次診斷后的48小時”。
自此,工傷認定“48小時”的規定正式建立并沿用至今。那么,為何《工傷保險條例》要限定48小時,又為何不是72小時、96小時?
記者檢索發現,我國《工傷保險條例》將工傷分為典型工傷、視同工傷和不得認定為工傷三種情況,其中第十五條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可以“視同”工傷。
為什么要強調突發疾病呢?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講師劉曉倩告訴記者,“這里主要想強調與工作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時,也就是勞動者個人身體健康突然出現問題而導致的疾病不能‘視同’工傷。”
“從情理來看,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上因疾病造成的死亡,本不屬于工傷范圍,但畢竟可能是工作勞累、精神緊張等種種因素導致病發,所以,條例把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視同工傷處理,已經考慮到維護工傷職工的救治權與經濟補償權。” 上海中夏旭波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曉茂說。
至于為何要限定48小時呢?李娟說,如果工傷保險認定的范圍過寬,對用人單位不利,認定的范圍過窄,則對勞動者不利。在立法時,48小時是整個搶救過程的黃金時間,為了便于操作,就規定48小時作為工傷認定的時間限制。
李娟告訴記者,這條認定標準因其過分偏重死亡時間、縮小了工傷認定的范圍、缺乏人道主義法律的導向作用等原因,自2004年實施起就存在極大爭議。
“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王勝利律師對記者表示,他在代理案件中發現,“工傷認定48小時”常常導致“用人單位利用現代醫學技術將病人的死亡時間拖至48小時以后”和“患者家屬在近48小時時不再給予搶救”的情況。
備受媒體關注的“民工尹廣安之死”事件就是一例。據媒體報道,51歲的建筑工人尹廣安在工作期間突發腦溢血被送往醫院,經過30個小時搶救后,尹廣安的家人決定撤下呼吸機。尹廣安的兒子說,在搶救期間,勞務公司有人來到醫院,讓醫生用呼吸機維持父親的生命,說一定要堅持48小時,當時他不清楚是為什么,咨詢律師后才知道“48小時之內死亡才能算工傷”。于是,為了拿到16萬元的“高額”賠償,兒子決定撤下呼吸機,讓父親“自然”死亡。
“受傷害職工家屬和用人單位都可能惡意利用該條款造成人為悲劇。背后的原因是工傷與非工傷,賠償金額存在巨大差別。”王律師說。
據記者了解,對于因工作死亡職工待遇,根據2010年《工傷保險條例》,包括供養親屬撫恤金、搶救產生相關醫療費用、喪葬補助金以及上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倍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
而非工傷死亡的相關待遇,包括供養直系親屬生活困難補助、搶救產生醫療費用(全部由死者醫療保險承擔)、喪葬費(2個月企業職工月均工資)以及一次性救濟金(按照其最高標準,供養三人以上則為12個月死者工資)。
王勝利律師認為,“突發疾病搶救超過48小時死亡或者沒有死亡,工傷認定部門理直氣壯‘不予認定’,也不論案情、誘發因素、法律原則的適用、各種原因的結合程度、社會的發展和法律的滯后等等,這種‘一刀切’的方式顯然不利于職工合法權益的保護。”
“《工傷保險條例》的初衷,是保障因工致傷、致病、致殘、致死的職工獲得醫療保障和經濟補償,倒逼企事業單位更好地落實職工休息權。”王勝利律師說,“那么就應該采取更為科學有效的手段來界定何為工傷。”
他認為,應擴大工傷認定的范圍,將職工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后死亡或者在搶救超過48小時后死亡都納入視同工傷范疇。
劉曉倩對此表示認同。她說,一條“善意”之舉卻被惡意使用,應當及時、科學地予以修訂以補其缺,回歸到立法本意和最大限度保護職工利益出發點上來。“我們試想如果不是48小時,是96小時,是15天、30天,或者更長,那就不會有人在標準外了嗎?錯不應在48小時。”
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也認為,“只要他的死亡或傷殘是由于超強度勞動造成的,我建議都可以認定為工傷。但是這個依據可以在司法解釋當中加以完善”。
實際上,這些不乏先例。2008年4月,廈門建安集團有限公司工程師肖文旭開會發言時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3天后死亡。廈門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為,出于人性化,利用呼吸機延續病人生命超過48小時后死亡的,也應給予辦理工傷賠付手續。
二問:工傷先行支付“落地”為何這么難?
2011年7月1日實施的社會保險法,首次確立了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根據這一制度設計,在工傷事故發生后,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不支付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該保險待遇應由用人單位償還;用人單位不償還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以追償。
在法律界人士看來,這一制度主要是為了避免職工在發生工傷事故后,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而得不到有效救治,從而落下殘疾甚至失去生命的現象發生,體現了我國工傷保險的保障功能和救濟功能。
但這一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制度,卻在實施過程中遭遇“落地”難,甚至有人稱其為“僵尸條文”。2014年10月30日,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在北京理工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舉辦“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立法研討會”,并在會上與到會專家分享《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實施三周年調研報告》。《報告》指出,目前我國大多數省份仍然不受理工傷先行支付相關申請。
義聯研究員以研究人員的身份,向17個城市的人社部門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公開該地區受理的工傷先行支付申請數、已支付的工傷先行支付金額等事項。此后,上海市答復已申請工傷先行支付9例,北京市要求延長答復期限,暫未做出答復。
近年來,各地陸續出現的“工傷先行支付”第一案,也凸顯了該制度“落地”之難。
2013年7月26日,“重慶工傷先行支付第一案”在重慶忠縣人民法院開庭。本案原告王棟梁是重慶忠縣卓越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卓越公司)的駕駛員,卓越公司沒有與王棟梁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為其交納社會保險。
2011年7月16日,王棟梁工作外出時發生交通事故,被認定為工傷,并被鑒定為三級傷殘。由于卓越公司不具備償還能力,2013年6月,王棟梁依據《社會保險法》和《社會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暫行辦法》向忠縣醫保局申請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醫保局以王棟梁沒有參保為由拒絕了他的請求。
2013年7月10日,王棟梁將忠縣醫保局告上法庭。醫保局在法庭辯稱,工傷保險實行的是市級統籌,但重慶市沒有出臺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的實施細則,縣級醫保局沒有辦法擅自支付。更為重要的是,法院已下達了終止執行書,卓越公司沒有財產可以執行,如果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必將無法追回債務,導致保險基金缺口。醫保局認為,如果今后此類無法追回資金的案件過多,就會導致資金無法承擔甚至崩盤。
10月11日,王棟梁訴忠縣醫保局關于工傷待遇先行支付的案件第二次開庭。醫保局還是堅持原來的抗辯意見,同時補充說,《工傷保險條例》修改的時候,《社會保險法》已經向社會公布了,但《工傷保險條例》明知法律有規定,卻在條例中沒有規定先行支付,說明不能執行該制度。
最終,法院駁回了王棟梁要求先行支付工傷待遇的請求。理由是,醫保局在訴訟期間作出書面回復稱不予先行支付,法院認為該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證明醫保局已經履行了法定職責,再責令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已無實際意義。
盡管向社保機構申請工傷先行支付很難,但袁群彥案經過兩年多的維權,終于贏得了艱難的勝利。
2012年3月,新疆工傷先行支付第一案在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開庭。本案原告袁群彥2008年7月在烏魯木齊市某工地干活時,被一個倒塌的架子砸傷,后被烏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鑒定為七級傷殘,由于他未與公司簽訂勞務合同,公司拒絕工傷賠償。
2011年11月4日和30日,袁群彥先后向烏市社保局遞交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申請,一個月后,烏市社保局拒絕了他的申請。2012年年初,袁群彥將烏市社保局告上了法庭。
2012年3月,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法院判決烏市社保局60日內向原告袁群彥履行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中工傷保險金支付項目的法定職責。烏市社保局不服,上訴到市中級人民法院,中院要求水磨溝區法院重審此案。
2013年3月,水磨溝區法院重審后判決,撤銷烏市社保局關于不受理袁群彥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申請的決定,責令市社保局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市社保局不服,再次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
2013年5月,烏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烏市社保局在庭審中認為,袁群彥所屬公司已無財產可執行,如果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必將無法追償,造成基金缺口。若開先河,將給工傷保險基金的安全造成嚴重后果,甚至會有人以各種名義套取工傷保險基金,最終導致參保人員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負責此案的烏市中級法院審判長杜瓊在接受采訪時說,袁群彥在沒有獲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情況下,向烏市社保局申請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應當適用社會保險法第41條的規定,即:用人單位不支付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
10月24日,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法院駁回烏魯木齊市社保局的上訴請求。
對于上述兩案,韓世春律師分析認為,社保部門以“當事人沒有參加工傷保險”、“地方未出臺實施細則”、“事后追償難”、“基金會出現缺口”等理由拒絕工傷保險先行支付,都反映出當地政府對展開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后基金安全的擔心。
“這反映出工傷先行支付制度設計有不足,這一制度確實有可能造成基金風險,但有關部門應該完善追償方面的規定,而不是以此作為不執行的借口。”韓世春同時認為,勞動者的弱勢,也導致了人社部門在執行先行支付制度方面,壓力和動力明顯不足。因此,如果勞動者能像王棟梁、袁群彥那樣采取行政訴訟的方式,就能給不作為的行政部門一定壓力,有利于助推制度“落地”。
而針對先行支付“沒有實施細則”的問題,韓世春建議,政府部門應制定工傷先行支付的進一步細則,清理不合法的規定,推動落實先行支付制度,可以通過明確先行支付的申請人的范圍;明確“用人單位拒不支付”這一事實的舉證責任;明確先行支付規定適用的時間范圍;明確社保機構追繳失敗的審計、財政處理程序等途徑共同實現。
義聯主任黃樂平建議,首先要明確“用人單位拒不支付”誰舉證。社保機構應在一定期限內責令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并調查用人單位的財務狀況。若社保機構未履行上述義務且未證明“用人單位拒不支付”的事實不存在,則應推定“用人單位拒不支付”的事實存在。
其次,如果追償失敗如何處理?由于基金管理相當嚴格,追償難度大,這給經辦人員帶來很大的風險。因此,“降低區域性基金風險,確立先行支付款追償機制。”
最后,明確申請人條件與適用時間范圍。根據社會保險法第41條的規定,職業病也應屬于“工傷范疇”。然而,在我國職業安全和衛生法律體系中,“事故”概念多指短期性、突發性的傷害事件,故長期接觸有害物質而引發的職業病并不典型地符合“事故”的概念。實踐中,就有法官對先行支付條款是否適應于職業病職工提出了質疑。因此,應明確先行支付申請人的范圍。
三問:超齡農民工能否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60歲,本該是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的年紀,可在廣大進城務工人員中,年逾六旬的超齡打工者并不鮮見。他們中絕大多數既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又沒有參加社會保險,一旦發生工傷事故,往往很難進行維權和求償。
據《綿陽晚報》2014年8月29日報道,年過六旬的農民工黃某林受雇從事垃圾清運工作不到3個月,就因搬運裝載量過多的垃圾桶,致急性彌漫性腹膜炎致殘。
但當黃某林向工傷認定機構申請工傷認定時,該機構認為,黃某林申請工傷認定時,已超過法定勞動年齡,與用人單位勞動關系不成立,對其申請不予受理。
無獨有偶,據《大河報》2013年1月10日報道,54歲的吳女士在工作中受傷也未能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不過,記者近日了解到,經過五年多的艱難維權,66歲的河北籍在京打工者劉玉啟獲得了“工傷與第三人侵權雙份賠償”。
北京市豐臺區法律援助中心王丹律師對記者表示,此案為北京地區超齡農民工獲“雙賠”第一案,對今后類似案件具有重要參照意義。而劉玉啟的維權經歷,也見證了我國工傷保險制度不斷調整、完善的過程。
劉玉啟告訴記者,他是1948年2月生人,于2005年12月入職北京麗豪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麗豪園物業),主要負責首鋼地質勘查院的綠化保潔工。

2009年8月,劉玉啟在上班期間去市場買保潔工具,在回勘查院的路上,被一輛小轎車撞傷,導致三根肋骨骨折。事發時,他已經61歲,屬于超齡工人。而隨后的維權和求償問題,正好遇到我國工傷保險制度的兩大難題:一是超齡工人的勞動關系確認問題;二是超齡工人的工傷賠償問題。
超齡工人能否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根據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即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勞動合同終止。”但《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規定:“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終止。” 即使勞動者達到退休年齡,沒有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勞動合同也要終止。
不過,2010年9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規定,用人單位與其招用的已經依法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或領取退休金的人員發生用工爭議,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按勞務關系處理。
但上述《解釋》對于沒有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或領取退休金的人員,是否也按勞務關系處理,沒有給出明確結論。
劉玉啟的援助律師王丹認為,本案中,劉玉啟雖然超過退休年齡,但未享受退休待遇,也沒有領取退休金,因此勞動關系并不當然終止,雙方爭議可以按勞動關系處理。
2011年4月,北京市西城區仲裁委作出仲裁裁決,認定劉玉啟與麗豪園物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記者注意到,盡管本案中,仲裁機構認定劉玉啟與麗豪園物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但今年5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公布的《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二)》則規定,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在工作期間發生工傷要求認定勞動關系的,應當駁回其請求,可在裁判文書中確認屬于勞務關系。
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則認為,鑒于超齡農民工這一特殊用工形態的客觀存在,在法律未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司法實踐的處理原則應該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均衡雙方的利益,維護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秩序,引導勞動力市場的規范發展。因此,可按特殊用工關系處理,其工作時間、勞動保護、最低工資等參照適用勞動法的規定。
超齡工人能否獲得工傷認定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不少爭議。2003年頒布的《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明確規定,受傷害人員是用人單位聘用的離退休人員或者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工傷認定申請“不予受理”。
但有律師認為,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民沒有穩定收入,不少農民即使到了60歲,也選擇外出打工。而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大多又累又危險,工傷事故時有發生,如一味地強調“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農民工發生工傷,不能享受工傷待遇”,不符合國情。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在《關于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進城務工農民因工傷亡的,應否適用〈工傷保險條例〉請示的答復》中明確,用人單位聘用的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務工農民,在工作時間內、因工作原因傷亡的,應當適用《工傷保險條例》的有關規定進行工傷認定。
2011年11月10日,北京市西城區人社局最終將劉玉啟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傷情認定為工傷。
2011年11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審議通過《北京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規定》,《北京市實施 <工傷保險條例>辦法》相關規定被廢止。
我國《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用人單位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具體到本案中,劉玉啟已經被認定為工傷,其工傷保險待遇應由麗豪園物業參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支付。
根據2014年5月公布的《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二)》第49條明確規定,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因無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而主張工傷保險待遇賠償的,應予支持。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受到第三人侵權,第三人侵權賠償并不影響其向用人單位主張給予工傷保險待遇賠償。66歲的河北籍在京打工者劉玉啟獲得了“工傷與第三人侵權雙份賠償”。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全球合伙人王建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不認定工傷”、“按雇傭關系處理”是一段時期內處理超齡農民工因工受傷問題的主要處理方式。隨著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案件作出明確具體的指導后,各地方行政、司法部門也在實踐中相繼認可對超齡農民工因工受傷情形享受工傷保險待遇。本案也正是這一趨勢的體現,值得肯定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