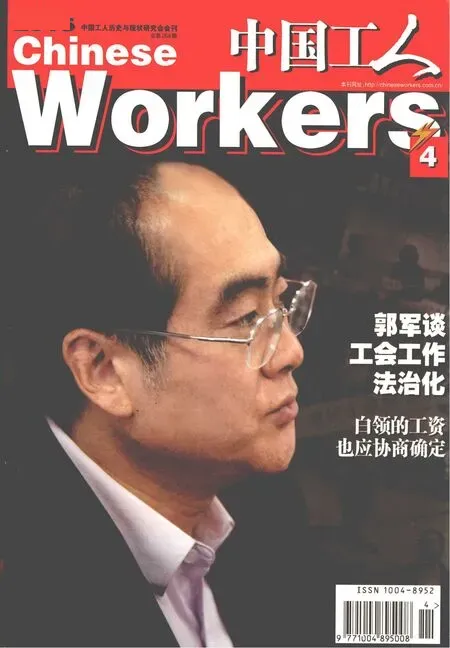新生代農(nóng)民工:媒介素養(yǎng)有多高?
吳麟

2014年“廣東東莞裕元罷工事件”中,工人以QQ群作為溝通和組織活動的信息平臺,使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話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前段時間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幾位學者談起農(nóng)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問題,普遍認為新生代農(nóng)民工在這方面與其父輩相比是有著自身獨特的特點的。
農(nóng)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社會經(jīng)濟體制和社會經(jīng)濟結構雙重轉型而出現(xiàn)的一個特殊群體。國家統(tǒng)計局的《2013年全國農(nóng)民工調(diào)查監(jiān)測報告》數(shù)據(jù)顯示:2013年全國農(nóng)民工數(shù)量為26894萬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nóng)民工為12528萬人,其規(guī)模占總量的46.6%。他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僅占6.1%;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qū)及大中城市務工;八成以上選擇外出就業(yè),外出平均年齡是21.7歲,且其中87.3%的人未從事過任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以從事制造業(yè)為主;在外務工更傾向于就地消費。農(nóng)民工的代際轉換,及其對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的潛在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已有研究顯示:與老一代農(nóng)民工相比,新生代農(nóng)民工已不滿足于實現(xiàn)基本勞動權益,更向往追求體面勞動和發(fā)展機會,他們維權意識更強,維權行為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
勞資利益的制度化表達,涵蓋立法表達、行政表達、黨群表達和社會表達四種類型。媒體表達是社會表達的關鍵構成,在應然意義上,媒體應成為勞資利益表達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們不能脫離社會權力關系認知媒體,它是嵌入具體時空政經(jīng)結構中的一種社會機制。筆者此前的研究顯示:建制內(nèi)的所有媒體,報道主題均緊密追隨和闡釋政策議題;消息來源和報道主角均呈現(xiàn)出鮮明的行政和組織傾向;話語引述方面均未對弱勢社群予以必要和足夠的空間。在整個主流媒體系統(tǒng)中,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話語權狀況可視作“主體性表達缺失”;在其間的工會媒體中呈現(xiàn)出“弱主體性表達”圖景,雖略有改善但二者不存在根本性區(qū)別。他們尋求平等公民權的真實訴求,即從滿足于實現(xiàn)基本勞動權益轉向進一步追求體面勞動和發(fā)展機會,未能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呈現(xiàn)。
在目前關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勞資關系問題的研究中,ICT技術的傳播賦權功能得到積極肯定。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學者汪建華分析珠三角地區(qū)三家代工廠罷工事件,指出: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的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為動員的中介,對代工廠工人的認知形塑和集體抗爭時的內(nèi)外溝通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具體表現(xiàn)在“認知與情感動員提升參與意愿”、“組織動員確保運動有序高效”,“動員外部力量以避免鎮(zhèn)壓”,“示范動員以供經(jīng)驗借鑒”諸方面。又如:勞動經(jīng)濟學學者李琪分析2011至2012年172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提出:新生代農(nóng)民工已成為行動主體,行動邏輯趨向“以勢維權”——通過現(xiàn)代通訊技術進行有效動員和組織,在短時間內(nèi)形成聚合之“勢”與資方進行博弈,以期實現(xiàn)在現(xiàn)行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中難以實現(xiàn)的訴求。
新媒體的確具有傳統(tǒng)媒體所不及的參與性、互動性等諸多優(yōu)勢,改善了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勞資利益表達境況;但是我們需要審慎對待技術樂觀主義觀點,對新媒體的功用應避免陳義過高。這不僅因為新媒體與傳統(tǒng)媒體一樣,是否作為及活動空間取決于國家、資本及媒介三重邏輯的共同作用;還因為新媒體能否實現(xiàn)傳播賦權,受限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群體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以下本文將結合問卷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對此進行論述。
知行皆不足: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
20世紀30年代,媒介素養(yǎng)在英國被首先提出;1994年,這個概念才被介紹到中國。目前,對媒介素養(yǎng)內(nèi)涵的認知,大致可以分為“技能模式”、“知識模式”和“綜合模式”三種。其中,“技能模式”側重于強調(diào)對媒介信息的認知過程。典型如1992年美國媒介素養(yǎng)研究中心的定義——“媒介素養(yǎng)就是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zhì)疑能力、評估能力、創(chuàng)造和生產(chǎn)的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知識模式”側重于強調(diào)媒介知識的累積。“綜合模式”則是二者并重,認為媒介素養(yǎng)是知識與技能的綜合。對此,社會學者江宇提出:“綜合模式”的概況更為全面,因為只有具備了“知識模式”所強調(diào)的“知識結構”,才能擁有“技能模式”強調(diào)的技能;而從“技能”也可以體現(xiàn)相關注視是否具備。
筆者認同這一分析,在2012年針對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的問卷調(diào)查中,即從認知與行為兩個層面,對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進行衡量。
這項調(diào)查旨在了解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勞動狀況與維權、媒介接觸與認知情況,于2012年7月在北京市進行,采取非隨機抽樣方式,發(fā)放6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540份,調(diào)查樣本的男性有327人,女性有213人,其所從事的行業(yè)分別是制造業(yè)(男性78人,女性57人)、建筑業(yè)(男性111人,女性10人)、服務業(yè)(男性138人,女性146人)。問卷的第二部分為“媒介接觸狀況與認知”,其中關于“媒介素養(yǎng)”主題,共設計了5個具體問題。
在認知維度上,可從其對“媒體表現(xiàn)”(包括真實公正地報道打工者、讓打工者表達自己的觀點與心聲、幫助打工者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提供有用的工作和招聘信息、提供打工方面的政策法規(guī)服務)、“媒體功能”(包括信息傳播、輿論監(jiān)督、宣傳教育、廣告功能、娛樂功能)和“可信度”(包括報刊、廣播、電視、網(wǎng)絡、手機)三個方面的評價(分很差、較差、一般、較好、很好5個評價等級),衡量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認知水平。調(diào)查顯示,三個維度的選項分布均呈現(xiàn)出中間評價選項比例居多而兩側選項比例較少的形態(tài)。這或許意味著兩種情況:第一種可能性是受訪者確實對各類媒介及其基本狀況評價居中;第二種可能性則是受訪者沒有對各類媒介及其基本狀況做出獨立的、符合自身實際的評價的。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則說明他們整體表現(xiàn)出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相對較低。此時,分析應主要從兩側的選項進行挖掘。如果從第二種可能性入手,則有如下判斷:在媒體表現(xiàn)上,他們認為各類媒體在“幫助打工者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提供打工方面的政策法規(guī)服務”方面做得比較好,但是在“真實公正地報道打工者”方面則做得比較差。在媒體功能上,他們認為各類媒體的“廣告功能”和“娛樂功能”履行得比較好,但是在“輿論監(jiān)督”方面表現(xiàn)則相當差。在媒體信息的可信度上,電視和廣播的可信度比較高,網(wǎng)絡和手機的可信度則比較低。
在行為維度上,可從“媒體閱讀行為”(包括提出疑問或批評、琢磨新聞的用意、拒絕接受部分內(nèi)容、通過其他途徑核實等4種行為方式)和“媒介參與意愿”(包括遇到突發(fā)事件時會向媒體爆料、自身權益受損時會向媒體投訴、會參與感興趣的媒體正文和討論、會向媒體反映自己看不慣的現(xiàn)象等4種行為方式)兩個方面,衡量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參與能力。問卷顯示,在媒體閱讀行為上,對問卷列出的四種行為方式,選擇“從不”和“偶爾”的比例之和均在60%以上,而選擇“經(jīng)常”和“頻繁”的比例之和均在10%左右。可以推斷,在閱讀媒體所發(fā)布的內(nèi)容時,絕大部分新生代農(nóng)民工缺乏獨立思考。在媒介參與意愿上,對問卷列出的四種行為方式,“從不”和“偶爾”的比例之和同樣高度集中,且均超過了75%,而選擇“經(jīng)常”和“頻繁”的比例之和均在8%以下。與閱讀行為相比,參與意愿會涉及的要素更多,因而,選擇“有時”、“經(jīng)常”、“頻繁”的比例均略低。
綜合上述關于認知維度和行為維度的分析,可以判斷——新生代農(nóng)民工既比較缺乏獨立見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又很少有參與意愿和參與行動,其媒介素養(yǎng)水平比較低。
結合田野筆記、訪談記錄,筆者發(fā)現(xiàn):整體而言,此次調(diào)查顯示出新生代農(nóng)民工因教育水平和工作環(huán)境之故,較少與傳統(tǒng)媒體接觸,手機以及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成為其主要信息來源和社交渠道;但是技術發(fā)展并未彌合知識鴻溝,在媒介素養(yǎng)上,他們認知固然有限,行動更加罕見。
何以出現(xiàn)此種狀況?“教育程度”具有重要影響,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受訪者,方有相對清楚的媒體認知、相對積極的媒體參與意向,以及曾經(jīng)有過質(zhì)疑媒體信息、利用媒體維權的經(jīng)歷。
媒介接觸與勞資關系:一個初步的判斷
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勞資關系狀況,各級工會的調(diào)查報告多有反映,諸如《關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深圳新生代農(nóng)民工生存狀況調(diào)查報告》、《新生代農(nóng)民工權益保護狀況與對策》等等。概而言之,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勞動權益受損問題突出、勞資關系中缺乏話語權、職業(yè)選擇及發(fā)展的空間逼仄、教育程度和職業(yè)技能水平待提高。此即:他們面臨生存和發(fā)展的雙重困境。農(nóng)民工(包括新生代)的媒介接觸,也有不少研究論文,諸如《農(nóng)民工媒介素養(yǎng)現(xiàn)狀調(diào)查與分析——基于河南省鄭州市的調(diào)查》(鄭素俠,2010)、《上海市新生代農(nóng)民工新媒體使用與評價的實證研究》(周葆華、呂舒華,2011)、《新媒體與中國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意見表達——以上海為例的實證研究》(周葆華,2013)等等,大致存在三點共識:新媒體的接觸頻率高于傳統(tǒng)媒體;新媒體使用主要以人際交往和休閑娛樂為主;農(nóng)民工群體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不容樂觀。
既有的研究中,有一個問題很突出——或聚焦勞資狀況,或探討媒介接觸,未能將二者進行有機的、具體的聯(lián)系與分析。只有少數(shù)例外,諸如學者李紅艷通過對北京市海淀區(qū)肖家河社區(qū)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問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由于在社會信息傳播過程中“信息洞”(InformationHoles)現(xiàn)象,此即“社會信息系統(tǒng)的傳播鏈條中,傳受雙方的交互缺位和社會角色期待的差異而造成的信息缺失”,新生代農(nóng)民工在就業(yè)信息獲取渠道中存在“斷裂現(xiàn)象”。對大眾媒體提供的就業(yè)信息的不信任,以及農(nóng)民工管理組織信息傳播的缺失和斷層,使得他們在城市的就業(yè)中仍然選擇單一而傳統(tǒng)的獲取信息方式——“依賴人際傳播的關系網(wǎng)”。

因而,媒介接觸與勞資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需要深入探究。
綜合分析本次調(diào)查的問卷數(shù)據(jù)、田野筆記、深度訪談以及其他二手資料,筆者有一個初步的判斷——“不一樣的媒介接觸,不一樣的勞資關系”。此即:媒介接觸行為越積極和能動,就越有可能獲取媒介資訊和利用媒體表達以改善勞資關系。
學者邱林川提出在中國信息社會建設中,隨著中低端信息技術的普及,出現(xiàn)“信息中下階層”(informationhave-less)。這一概念泛指在社會信息分層結構里介于“信息擁有者”(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notes)之間的各種人群。他們廣泛、自發(fā)地使用手機、QQ等中低端信息傳播技術建構草根社會網(wǎng)絡。其中,手機是新生代農(nóng)民工群體中普及率相對最高的媒體,且智能手機的比例日益增加,對其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響,在個體自主性的獲得過程中發(fā)揮出積極作用。手機的使用動機大致可分為5類——“聯(lián)系親友”、“休閑與娛樂”、“維護親情”、“新聞與資訊”、“意見分享與討論”。不過,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手機使用范疇基本停留在前三項;若他們能在后兩項上更有作為,如利用手機(含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尋求維權知識、分享勞資信息、學習談判策略、進行集體動員等,便有可能提升自己在勞資關系中的議價能力。
在2014年“廣東東莞裕元罷工事件”中,工人便以QQ群作為溝通和組織活動的信息平臺。據(jù)《鳳凰周刊》記者的觀察,“工人在現(xiàn)實中沒有自己的組織,所以他們對聯(lián)絡、協(xié)商和組織資源的渴求,使其轉戰(zhàn)網(wǎng)絡,他們建立的QQ群非常飽滿的展現(xiàn)了所思所想。”行動之初,罷工現(xiàn)場發(fā)生任何事件,消息和圖片在第一時間就會被發(fā)到群里;任何媒體對罷工做了報道,無論中文抑或外文,都有工人轉到群內(nèi),并號召大家去給門戶網(wǎng)站相關報道評論“頂帖”。對此,英國《衛(wèi)報》刊文認為:中國的農(nóng)民工積極利用QQ、微信等社交網(wǎng)絡,正從“苦役者”轉變?yōu)椤皵?shù)字時代的反叛者”。
新生代農(nóng)民工能否進行積極和能動的媒介接觸,與其媒介素養(yǎng)(MediaLiteracy)水平密切相關。媒介素養(yǎng)一般包含兩個維度:媒介信息處理,即公眾如何處理所接觸的媒體信息,尤其指向是否具有質(zhì)疑反應和批判意識;媒介參與意向,即公眾能在何種程度上介入到媒體內(nèi)容的生產(chǎn)和創(chuàng)造。周葆華、陸曄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和西安2409名市民進行隨機面訪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描述層面上,對媒介信息的批判思考和對媒介生產(chǎn)的積極介入,均處于偏弱水平;公民的政治與公共事務興趣、開放型的人際討論模式,對其媒介信息處理能力和媒介參與意向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網(wǎng)絡新聞和海外媒介的使用對媒介信息處理能力有重要貢獻;更高的媒介信息處理能力也預示著更高的媒介參與意向。相較市民群體,農(nóng)民工群體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更是偏弱。

前述積極利用QQ群的裕元工人,根據(jù)《鳳凰周刊》記者手記描述,個別工人媒介素養(yǎng)水平較高,但整體而言也不過爾爾——“‘中國的媒體有中國特色,他們討厭文革,所以使用文革時代相關的口號和方法,媒體是不會支持的。’一位被眾人認為了解媒體的工人,這樣分析罷工中應選取的策略。不僅如此,另一位同樣被認為‘見多識廣’的工人,還努力為自己的工友分析應當聯(lián)系哪里的媒體,為了減少多次重復的勞累,他把自己創(chuàng)建的群名修改為‘省內(nèi)媒體不可靠’……不過絕大多數(shù)工人還是缺乏對媒體的了解,正如他們對中國媒體政治譜系的劃分一樣,臆測多于考察。他們會把門戶網(wǎng)站轉載的新聞視為這家網(wǎng)站自有的報道;當騰訊大粵網(wǎng)將罷工新聞放到頭條時,他們欣喜若狂,誤以為騰訊把他們的事情當成全國性頭條新聞在報道。工人們搜羅了一大串媒體和中央機關的聯(lián)系方式——當然基本都是假的——還是有工友一個接一個撥了過去。”
筆者的2012年問卷調(diào)查中的540名新生代農(nóng)民工,其媒介信息處理能力和媒介參與意向皆非常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對勞動權益的維護。
提升媒介素養(yǎng):實現(xiàn)傳播賦權的可行途徑
代際轉換并未從根本上改變農(nóng)民工群體的弱勢地位。學者姚俊通過調(diào)查2009年長三角地區(qū)五市(縣)478名新生代農(nóng)民工,發(fā)現(xiàn):新生代并非更有希望、更“精英化”的一代。在多項指標中,他們的文化程度和外出動機略好,但這只是正常代際差異,而非本質(zhì)區(qū)別;同時在收入水平、務工時間、社會保障享有和工作穩(wěn)定程度上,則明顯不如“老一代”。的確,新生代農(nóng)民工仍然處于社會的下層,其命運同時受到制度和市場的影響,生活境遇不甚理想,關鍵是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很容易跌入社會的最底層。正如2014年《南風窗》的報道《城市空間迎來“新生代”》所言:“從外表和認知上觀察,這撥‘新人’,已被‘釘’到和城市主流社會群體的同一面墻上。是否會掉下來,就看他們的造化了。”
新媒體被普遍認為“有巨大的潛力能在更大程度上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賦權,并改善社會邊緣群體的日常生 活 ”(MehraB,MerkelC.&BishopA.P.,2004)。學者鄭永年曾從“技術賦權”角度探討互聯(lián)網(wǎng)對中國國家-社會的影響,認為:“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互聯(lián)網(wǎng)能夠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進行改造和賦權。”他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分權的效果”,此即“它的益處以分權的方式擴散”,因而“即使存在‘數(shù)字鴻溝’,但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不僅使中間階層和上層階層受益,也有助于中下階層努力改善自身經(jīng)濟和社會福利。”確實,新媒體的傳播賦權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顯現(xiàn),有具體的案例可資佐證,例如:四川籍在京務工民工劉建偉,自2006年被確診患塵肺病,帶病為自己及十余名工友進行了有效的維權,其總結的成功經(jīng)驗之一就是“學會運用自媒體,向社會各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他以及@張海超、@古浪趙文海、@樂山何兵、@陽和平等塵肺病維權人士,就是“不斷通過微博發(fā)聲,引起了主流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不過,媒體是一個充滿爭斗的場域,弱勢群體“報道配額不足”問題異常突出;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尤其是經(jīng)濟資本匱乏,是其“媒介弱勢”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網(wǎng)絡空間亦是如此,學者趙云澤、付冰清結合社會分層理論,曾于2009年12月16日、22日、29日,搜集“人民網(wǎng)輿情頻道”每日瀏覽數(shù)最多的500個網(wǎng)帖,剔去被刪除的,共獲得有效網(wǎng)帖總數(shù)為1374個,通過內(nèi)容分析判斷“網(wǎng)上說話人代表的階層”,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言論更多地是代表社會中間階層的“民意”。在網(wǎng)絡話語權的占有比例方面,社會中間階層以68%居首;“社會上層”以28%次之;而“產(chǎn)業(yè)工人”、“農(nóng)業(yè)勞動者”等社會“底下”階層僅有12%。網(wǎng)絡空間話語權的結構呈“不平衡”狀態(tài),并未解決社會底層話語表達問題。
媒介素養(yǎng)包括個體從認識媒介、使用媒介到參與媒介的各種批判性反思、理解和行動能力。簡言之,它不僅是指公眾建立有關媒介社會角色的認知和理解;而且強調(diào)培育民主社會所必備的質(zhì)疑和自我表達能力。學者陸曄、郭忠實的實證研究顯示:媒介素養(yǎng)具有“賦權”作用,能夠增強人際溝通能力和媒介參與意向。話語能力建設,在有效保障公民表達權的基礎上,重在提升新生代農(nóng)民工群體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以使他們有意識、有能力利用傳播媒介進行自主、能動地進行話語表達,是實現(xiàn)傳播賦權的一個可能途徑。
如何提升農(nóng)民工群體的媒介素養(yǎng)水平,便成為一個有迫切意義的問題。對此,學者鄭素俠進行了有益探索,提出:政府、高校、媒體和公益組織等多元行動主體相互協(xié)作,以開展農(nóng)民工媒介素養(yǎng)教育;并編寫《農(nóng)民工媒介素養(yǎng)教育簡明讀本》。不過,其設計的實施思路和方法失之簡單;我們需要在現(xiàn)實的政經(jīng)結構下,進一步尋求具體可行的進路,根據(jù)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媒介接觸習慣和信息需求狀況,展開富有針對性的媒介素養(yǎng)培訓,有效提升其知識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