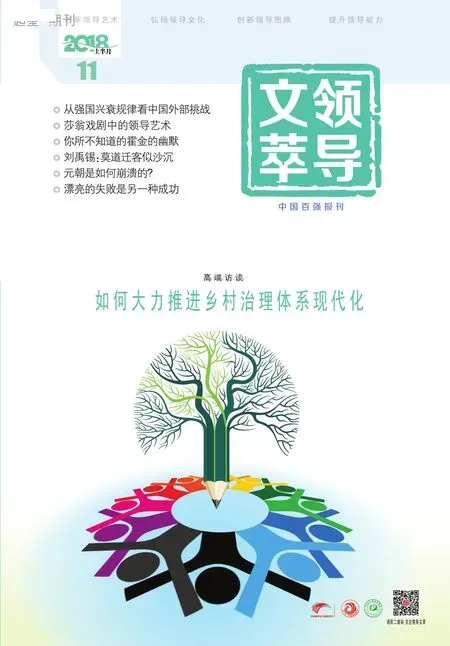希臘危機(jī)背后的地緣政治牌局
□思理
希臘危機(jī)背后的地緣政治牌局
□思理

英法德三國各懷鬼胎?
戰(zhàn)后經(jīng)歷了分裂和統(tǒng)一和經(jīng)濟(jì)振興,以如今歐洲最強(qiáng)勢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德國事實(shí)上已問鼎歐洲,現(xiàn)在還與法國結(jié)成了神圣同盟。英國當(dāng)不了歐洲的盟主,但也決不允許其他人當(dāng)盟主,如今已發(fā)出了要退出歐盟的吼聲。如此局面下,將希臘趕出歐元區(qū)的決心委實(shí)難下。
希臘太小了,若出局,只要不演變?yōu)闅W元危機(jī),德國依然可以高枕無憂,歐元區(qū)也可高枕無憂。但怕就怕希臘出局引發(fā)后續(xù)連串效應(yīng),動(dòng)搖世人對歐元的信心。歐元區(qū)成立之初,說好棒打不散,有福同享,有難同當(dāng),現(xiàn)在卻要把小兄弟希臘推出門外。這樣做的后果如何,誰也無法預(yù)料。
而從另一方面看,債務(wù)達(dá)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約180%的希臘確實(shí)沉疴纏身,難以救治。在今天的希臘就業(yè)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少報(bào)或不報(bào)稅。希臘地下經(jīng)濟(jì)占到經(jīng)濟(jì)總量的24%,而該比例在歐洲國家平均為19%。雅典政府所征收的各種費(fèi)用,占到希臘勞動(dòng)成本的43%。
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希臘在未來三年需要?dú)W洲伙伴提供360億歐元資助,方能免于破產(chǎn)。其實(shí),當(dāng)初歐元區(qū)接納希臘時(shí),對希臘的經(jīng)濟(jì)實(shí)情,各方其實(shí)心知肚明。既然如此,當(dāng)初為什么還要拉希臘入伙呢?這既有盲目樂觀的情緒,而更重要的是德國有想當(dāng)歐洲霸主的算盤,至少是想當(dāng)歐盟的盟主。
所以,對希臘危機(jī),德國的態(tài)度是最強(qiáng)硬的。法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托馬斯·皮克迪認(rèn)為德國是“最沒有資格教訓(xùn)他國的國家”。皮克迪的依據(jù)是,根據(jù)1953年簽署的倫敦債務(wù)協(xié)議,英國、美國等20個(gè)簽字國同意勾銷德國半數(shù)以上的債務(wù),他據(jù)此認(rèn)為,這份協(xié)議應(yīng)該能作為希臘和其他歐元區(qū)負(fù)債國家的藍(lán)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時(shí),德國的負(fù)債額達(dá)到其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200%以上,在之后的十年里,由于通貨膨脹,加上對私人財(cái)富征稅和債務(wù)減免,這個(gè)比率降低至不到20%。德國隨后得以發(fā)展為歐洲經(jīng)濟(jì)大國。
除德國和法國之外,歷史上英國也想當(dāng)歐洲的霸主。這回英國人似乎是有先見之明,沒有加入歐元區(qū),所以置身希臘危機(jī)之外。但即便沒有希臘債務(wù)危機(jī),即便英國當(dāng)初知道希臘不會(huì)有危機(jī),英國也不會(huì)加入歐元區(qū)。英國的既定國策是,歐洲哪個(gè)國家強(qiáng)大,英國便與之為敵:拿破侖意欲稱霸歐洲時(shí),英國便組織反法聯(lián)邦;德皇威廉意欲稱雄歐洲時(shí),英國拉上法國和俄羅斯組織反德聯(lián)盟。總之,英國當(dāng)不了歐洲的盟主,也決不允許其他人當(dāng)盟主。今天德國和法國執(zhí)歐盟牛耳,英國就要攪局:倫敦已發(fā)出了要退出歐盟的吼聲。
希臘與俄羅斯“眉來眼去”
歐洲的大國博弈中,俄羅斯舉足輕重。俄羅斯打敗過拿破侖,蘇聯(lián)打敗過希特勒。這次希臘也與俄羅斯“眉來眼去”,盡管還不至于“另尋新歡”,也要嚇嚇歐盟。從另一方面說,希臘也必須與俄羅斯周旋。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不久前參加完金磚領(lǐng)導(dǎo)人峰會(huì)后表示:“俄羅斯和希臘有一種基于精神血緣、宗教和歷史關(guān)聯(lián)的特殊關(guān)系。”
希臘在歐盟內(nèi)是小兄弟,但在巴爾干半島也想當(dāng)霸主。在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國的一些銀行中,希臘持股可達(dá)到15%至20%。巴爾干島居民大多是斯拉夫民族,俄羅斯也是斯拉夫民族,而且歷史上就以斯拉夫國家的保護(hù)神自居。如果說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后院,那么巴爾干半島就是俄羅斯的后院。希臘想在巴爾干半島稱大,不能不與莫斯科搞好關(guān)系。
歐盟知道希臘退歐的后果之一就是俄羅斯將會(huì)在希臘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隨著俄羅斯與西方的關(guān)系惡化,希臘倒向俄羅斯能夠有效幫助其在歐洲站穩(wěn)腳跟。
對中國的警示意義
到目前為止,希臘債務(wù)危機(jī)引發(fā)的“蝴蝶效應(yīng)”基本是在歐洲內(nèi)部顯現(xiàn),但并不是說與中國毫無關(guān)聯(lián)。除了經(jīng)濟(jì)影響,希臘債務(wù)危機(jī)對中國還不無警示意義。
其一,對于債務(wù)問題可能引發(fā)的系統(tǒng)性危機(jī)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中國也局部存在較為嚴(yán)重的地方債務(wù)問題。不同的是,希臘是以國家信用為擔(dān)保的對外欠債,中國則是對內(nèi)欠債,而且國家主權(quán)信用足以保證債務(wù)問題不致失控。希臘危機(jī)提醒我們,金融體系建立健全嚴(yán)密的風(fēng)控體系、對地方債務(wù)及時(shí)跟蹤監(jiān)管是涉及宏觀經(jīng)濟(jì)健康發(fā)展的大問題。
其二,希臘債務(wù)危機(jī)從一個(gè)側(cè)面告訴我們,在推動(dòng)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進(jìn)程中,必須把風(fēng)險(xiǎn)控制放到突出位置。“一帶一路”、互聯(lián)互通、亞投行等戰(zhàn)略的推進(jìn),除了強(qiáng)調(diào)互利共贏的前景,也需要在風(fēng)險(xiǎn)控制方面作出縝密設(shè)計(jì)。
同時(shí)也要看到,希臘債務(wù)危機(jī)固然給中國帶來了直接或間接的負(fù)面影響,但客觀上也改善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jìn)環(huán)境。出于對中國資本的需要,近來英國等國放寬中國資本的準(zhǔn)入條件,積極與中國開展貨幣互換,加入亞投行為代表的國際金融體系建設(shè)等,表明中國與歐洲的戰(zhàn)略合作關(guān)系正在升級。
有危即有機(jī)。不管希臘債務(wù)危機(jī)今后如何演變,控制其風(fēng)險(xiǎn)因素,抓住其中蘊(yùn)含的機(jī)會(huì),中國就能保證經(jīng)濟(jì)繼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
(摘自《思想理論動(dòng)態(tài)參閱》)
- 領(lǐng)導(dǎo)文萃的其它文章
- 天津港是另一個(g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殘余
- 制度化反腐從廉潔政治到廉能政治
- 舉措
- 未定稿
- 趨勢
-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