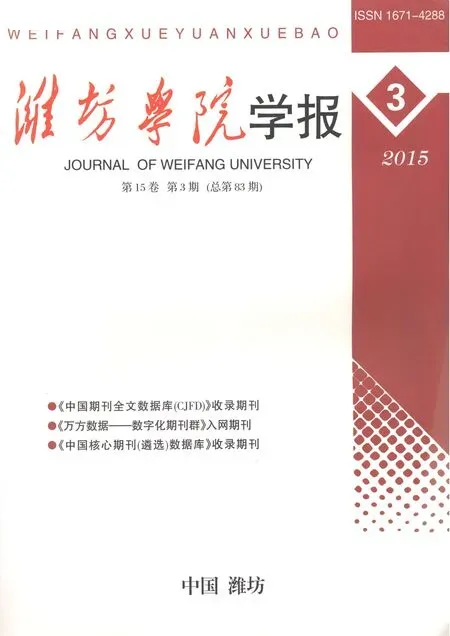論蘇軾密州詩詞中的“狂”
王曉磊
(諸城市超然臺管理處,山東 諸城 262200)
論蘇軾密州詩詞中的“狂”
王曉磊
(諸城市超然臺管理處,山東 諸城 262200)
宋神宗熙寧七年秋,蘇軾由杭州移知密州,開始了為期兩年多的密州從政歲月,知密期間目前可見詩文共235篇。這些密州作品中多次出現(xiàn)“狂”字,用“狂”字之多、之密,為蘇軾宦居各地之最。蘇軾密州詩詞之狂含義廣泛,寓意深刻。或展現(xiàn)了對自身學識的自信,或留露出宦居京外的一種復雜心態(tài),還有部分狂字或暗含對新法之不滿。而蘇文中的狂,并非狂妄,這種狂實際是對先秦至宋一種儒家積極思想的承襲,是一種摒棄當時世俗的觀念,疏離當時社會的主流和庸俗,而歸根結底就是一種追求真理的人生態(tài)度。
蘇軾;密州詩詞;狂;真理
學術界目前有數(shù)篇論及蘇軾狂之論文,最早的是日本學者橫山伊勢雄在《詩人的狂——蘇軾》(《漢文學會會報》34號,1975年)一文中提出來的。日本學者保苅佳昭《蘇軾詞里所詠的“狂”》(《新興與傳統(tǒng):蘇軾詞論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也談到了蘇軾詞中的狂。此外大陸學者張海鷗《蘇軾外任或謫居時期的疏狂心態(tài)》(《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也探討了蘇軾謫居時期的疏狂心態(tài)。王啟鵬的《疏狂:蘇軾“野性”的任真表現(xiàn)》(《惠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也提到了蘇軾之狂,認為蘇軾的疏狂實際是蘇軾一種“野性”的表現(xiàn)。
雖然關于蘇軾詩詞中的狂最早由日本學者提出,大陸學者張海鷗隨后也對蘇軾之狂進行了拓展性的研究,進而提出了蘇軾的疏狂心態(tài)。但是以上學者并未探討蘇軾狂之發(fā)源地,以及蘇軾之狂對后代文人影響。筆者認為,蘇軾真正意義上的狂應是從密州開始的,當時蘇軾由斜風細雨的杭州來到民風彪悍的密州,受到當時政治環(huán)境與當?shù)貧v史地理環(huán)境影響,蘇軾在此地不僅產生了豪放詞,而且還激發(fā)了內心潛在的狂之心態(tài),這就是本文的創(chuàng)新點。下面筆者分三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
一、積極意義的狂
漢語中的狂,大體有四種含義:病態(tài)的狂,本指狗的瘋狂狀態(tài)(參《說文》),引申于人,則指人喪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狀態(tài);自然現(xiàn)象的失常狀態(tài),如狂風暴雨;正常人無知狀態(tài)的躁動和妄想,即通常所謂狂妄;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一種高級的精神形態(tài)的狂,表現(xiàn)為恃才傲物,自信,放縱個性,執(zhí)著追求,本文所謂文人之狂即取此義。
關于文人之狂,張海鷗《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中曾做過詳細的梳理。[1]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上文人的狂有一個發(fā)展的流變,最早稱正常人為狂是貶義的,自孔子始,狂獲得了積極的含義:“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2]孔子認為如果交不上中行之人做朋友,則寧可與狂狷之人為伍,因為狂者志向高遠,進取心強而狷者則能保持獨立的價值觀念,不肯隨波逐流。在孔子的理念里,理想的人格是圣人君子,而不是狂狷。他之所以贊賞狂狷,一則出于對鄉(xiāng)愿④的厭惡,二則是因為狂狷人格距成圣的境界不遠,可以籍此而達到圣人的境界。由此可見孔子不拒斥狂狷人格,這是一種不違背儒學本旨的道德人格,符合一般士人成才的基本規(guī)律。[3]
此后儒生大都認為狂具有執(zhí)著進取、正直無悔的積極意義。由此可見儒家思想中的狂源于孔子。其后孟、莊、屈,還有縱橫家蘇秦、張儀等,皆崇尚文人之狂。而發(fā)展到魏晉,文人的狂似乎發(fā)展到一種病態(tài)。由于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加之司馬政權政治高壓,引起了當時文人對權勢的恐懼和厭惡。初期他們佯狂以避禍,放誕以求真,清談玄虛,潛心藝術,而到后期則發(fā)展到一種病態(tài)之狂。到了李唐王朝,相對開明的政治和開放的文化環(huán)境,大大激發(fā)了文人士子們進取的狂想。他們無須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頹廢自毀。進則指點江山、致君堯舜,退則在山水中流連、癡迷。不論進退,他們都喜歡詩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從中享受審美的愉悅。
到了宋代,雖然承襲唐風,但是宋朝和唐朝相比,士人的狂者精神似乎已經收斂了許多。還有部分學者甚至開始抵制這種狂氣,如與蘇軾同時代的宋儒大家程顥、程頤,便不能容忍學者有狂的氣息。
蘇軾之狂,既不像魏晉名士那樣自毀形骸、佯狂避世,也不像屈原那樣固執(zhí)一端。蘇軾的狂,有盛唐遺風的率性之狂,他心儀于唐代才子風流倜儻、瀟灑率真的審美精神,用審美的追求去沖淡仕途功名的得失。但是蘇軾的狂,也并非完全與盛唐之狂一致,他的特點就是比前人更多了幾分超然。蘇軾一生屢遭貶謫,于是融儒、釋、道等諸家學說以自救,故對儒家思想中積極意義的狂,深有體會。他常常稱許前人、同時人以及自己為狂,從中可見他對狂的理解與認同。
二、蘇軾密州詩詞中的狂
蘇軾之狂雖承襲傳統(tǒng),卻又個性鮮明。而體現(xiàn)在密州詩詞中,主要表現(xiàn)為對世俗的叛逆、狂直(大膽講真話)、醉里狂言、狂歌與狂獵,其中部分詩詞或暗含對新法之不滿。
前文已述,蘇軾之狂實際是疏離社會主流和庸俗,是一種對世俗的叛逆,是一種“野性”的表現(xiàn),是一種追求真理的人生態(tài)度。蘇軾于熙寧八年(1075)冬季創(chuàng)作的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老夫聊發(fā)少年狂”,[4]P347這首詞起句用一“狂”字,貫穿全篇,統(tǒng)攝全文。從儒家積極狂狷思想的角度來分析,則是用少年之狂來表現(xiàn)自己的返璞歸真。
熙寧九年(1076)八月作《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婦惡嘲謗”[5]P693以及《坐上賦戴花得天字》中的“老狂聊作坐中先”[5]P806、《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中的“誰知海上詩狂客”[5]通過描繪友人,以及自況等,表達了作者對世俗的叛逆。從用詞上來分析,前面的“老父聊發(fā)少年狂”,少年與狂字還比較貼合,而后面頻頻用到的老狂,卻給人不少疑問,通俗來說狂好像只適用于少年,而蘇軾這里偏用老狂一詞,更能體現(xiàn)出作者內心的心態(tài),以及所要表達含義的深刻意義。其實老狂并不是蘇軾獨創(chuàng),根據(jù)《吳越春秋》記載,伍子胥就曾自稱自己為老狂。[6]
密州詩詞中,蘇軾不少狂都是伴隨著酒興而來。其實蘇軾的酒量是很小的,而且常飲常醉。他曾說:“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書《東皋子傳》后)又說“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飲酒、唱曲”[7]但他的酒興卻極高,以酒為生活伴侶,他曾說“殆不可一日無此君”[8]P2369
蘇軾的狂,大體與酒狂無關,但借酒壯膽、增加豪氣的想法,也未必沒有。“無多酌我君須聽,醉后飆狂膽滿軀”[5]P550(《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孤村野店亦何有,欲發(fā)狂言須斗酒”[5]P601(《鐵溝行贈喬太博》)蘇軾醉里狂言不同于一般人的酒后失態(tài),這是他鮮明而又獨特的個性使然。他天性率真坦誠,為人處世無城府,對朝政時事既關心又有敏銳的見識,只是不會把話藏在心里。他在仕途屢遭坎坷,多是直言所致。而當時北宋中后期的社會風氣是,不能容下直言,部分官員阿諛奉承,諂媚上司,空話連篇,而蘇軾的這種性格自然受到同時代其它官員的疏離,“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5]P645(《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他對自己狂言惹禍十分清楚,并時常告誡自己“狂言各須慎”[5]P626(《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5]P740(《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一)然而秉性難移,他總是醉后狂言“醉后狂歌不自知”[5]P649(《劉貢父見余歌詞數(shù)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西齋》)不過他也很矛盾,乘酒興而放言固然痛快,過后想起來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詩中坦承“飲中真味老更濃,醉里狂言醒可怕”[5](《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以上部分詩詞亦為“烏臺詩案”所據(jù),可見蘇軾為“醉后狂歌”險些付出生命代價。其實蘇軾“醉后狂歌”并非失去理智,他只是天性喜歡坦率直言。
蘇軾的醉后還喜歡狂歌和恣游山水,他一旦疏離了朝政事務,就進入超凡脫俗的文化藝術創(chuàng)造境界。醉酒狂歌和恣游山水正是醞釀創(chuàng)作靈感和激情的良好情境。每遇這種情境,他便放縱性情,痛飲狂歌,清賞自然與天籟,既享受自由,又創(chuàng)作詩文。
熙寧九年(1076)知密州,與僚友登常山,作《登常山絕頂廣麗亭》:“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5]P686熙寧十年(1077)知徐州,還念念不忘密州,贈密州太守孔周翰《和孔周翰二絕》:“小園香霧曉蒙朧,醉守狂詞未必工。”[5]P753又《登云龍山》:“醉中走上黃茅岡,……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5]P877
蘇軾密州詩詞中所詠的狂,并非狂妄,也不完全是詞風中的豪放狂邁,而是一種從古至宋傳承下來的一種特殊的文人心態(tài)。發(fā)展到蘇軾這,變成了一種獨立的人格意識、自由的人生觀念、正直的人品素養(yǎng),追求的是一種疏離社會主流和中庸,達到人生真諦的目標。
三、蘇軾之狂緣何始于密州及對密州文人之影響
蘇軾移知密州之前,由于自身天生率性的性格以及周邊的生活環(huán)境,或許內心已埋下狂的種子。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種狂卻沒有一份合適的沃土來滋養(yǎng),使之生根發(fā)芽。當蘇軾由煙雨江南來到這座民風彪悍的北方“寂寞山城”,受到當時政治環(huán)境以及當?shù)貧v史地理環(huán)境影響,加之自己處于青壯年時期,以及邊疆戰(zhàn)事、新法橫行不得人心,內心又沒有受到“烏臺詩案”影響,在外在與內在等一系列因素的促使下,終于激發(fā)了蘇軾內心狂之心態(tài),蘇軾的感情也得到了完全的迸發(fā)與釋放,在密州發(fā)出了諸如“老父聊發(fā)少年狂”之類的怒吼,具有積極意義的蘇軾之狂也正式誕生于密州大地。
(一)密州當?shù)靥赜械拿耧L與文化
蘇軾與生俱來的叛逆,與其狂之心態(tài),許久之前,或許已深深根植心底,但是需要一種環(huán)境來滋潤,密州這片沃土,正好滋養(yǎng)了蘇軾這種心態(tài)。
蘇軾在密州文風產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豪放詞,作有被稱之為密州三曲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江城子·密州出獵》、《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等千古名篇,除此之外,《超然臺記》標志著超然思想的誕生。蘇軾在密州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成就,除自身的因素之外,與密州文化對其陶冶和影響分不開的。
密州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帶山負海,號為持節(jié)之邦”,風雅靡境,人文淵藪。尤其作為密州治所的諸城,“彬彬文獻足以征往而俟來,使人有所觀且有所興起;禮樂足以殿邦,山川因而增重”。[9]
早在春秋儒學初興之時,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的公冶長,即在境內致力于傳播儒學,從者如云,從此尚學崇禮蔚然成風。至漢代,儒學大興,兩漢經學集大成者鄭玄,著名經學家貢禹、師丹,《易》學開創(chuàng)者梁丘賀,經學世家伏湛、伏無忌等,均為密州人,他們的治學活動,將儒學推向新的高峰,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后,境內儒宗名臣,文獻著作,代不絕書。“民物日以熙攘,風俗日以樸茂,野無啙窳之民,市有輕實之賈,禮教信義之風,迄今猶未泯哉。”蘇軾知密州時,就是處于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之中,對他的影響是深遠的。他一生篤信儒教,而密州正是崇尚儒學的禮義之邦。超然臺、瑯琊臺、盧敖洞、韓信壩等許許多多的古文化遺跡,馬耳山、盧山、常山、障日山、九仙山、濰水等山川名勝,鐘靈毓秀,攬物慨發(fā),使他的思想境界和文學造詣有了新的升華。[4]張崇琛也有過著名論斷“以儒為主、兼融各家的學術氛圍對蘇軾以綜合性為特征的思想的形成有‘聚合效應’;古樸、淳厚、豪壯的民俗對生活于其中的蘇軾的精神升華具潛移默化之功;而格調樸野的‘東州樂府’文化則是蘇軾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詞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轉折、飛躍的觸媒。”[10]
(二)暗含對新法不滿
蘇軾之狂,除了受到當?shù)丨h(huán)境的影響外,筆者認為蘇軾之狂,還有一種暗含對新法不滿之意味。當時北宋中后期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激烈的政治斗爭把許多進取的“狂者”送上了遷謫的旅程。蘇軾就是由此自請外放,先去杭州后至密州。當時面對密州大地的旱蝗相虐的情況,而此時新法又橫行不斷,天災人禍連連。由此蘇軾密州詩詞中的許多狂字,也暗含了對新法不滿的傾向。
王水照在《評蘇軾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詩》一文中指出:“現(xiàn)存蘇軾詩約二千七百多首,社會政治詩比重并不大,但仍是蘇詩的一個重要內容,表達了詩人對于政治和社會重大生活的態(tài)度和觀點。”[11]蘇軾入職密州前后所作詩詞,不排除帶有一些政治色彩。當時蘇軾在密州所作的《超然集》①散佚。,是集中了密州部分作品,很多就是后來烏臺詩案的證據(jù)。“見為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為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為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為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4]P75其中知密詩文編為《超然集》,以膠西古跡超然臺而得名。書所刪“不合道理者”,顯然是涉及王安石變法與直刺朝政的詩文。“得罪日皆為家人婦女輩焚毀”者,足見烏臺詩案對蘇軾詩文的損毀何其慘重。
在當時對蘇軾審訊的過程中蘇軾也承認了部分詩詞確有譏諷之意味。如《后杞菊賦并序》、《超然臺記》、《寄劉孝叔》、《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其二)》等。
而他的主要目的則是通過友人間的詩詞往來,使新法的反對派更加堅定,使那種對新法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而又可能被變法派拉攏,內心開始出現(xiàn)猶豫的人清醒起來,不忘與自己的交誼。在遣詞造句中,表現(xiàn)出對于新黨的不屑,讓朝廷能夠看到新法之不足。
(三)邊疆戰(zhàn)事與密州匪患
蘇軾詩詞中之狂,除了以上兩個原因外,還有就是對于邊疆戰(zhàn)事的不利所表現(xiàn)出的一種忠君愛國、上陣殺敵的赤子之心。北宋以降,由于太祖趙匡胤堅持文人治國、重文抑武的方針,華夏士子自宋代以后變得文弱了許多。但是蘇軾面對內憂外患的境況,面對國家遭受外敵入侵的危險時刻,毅然發(fā)出了內心狂的怒吼。這是一個普通的宋代士子想要馳騁疆場,驅逐韃虜,報效國家的狂邁。
蘇軾少有報國壯志,喜佩劍出游。他在詩中說:“少年帶刀劍,但識從軍樂。”[5](《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二,詩集卷二十一)蘇軾喜讀兵書,蘇轍說他:“舊讀兵書氣已振,近傳能射喜征鼖。”[12](《聞子瞻習射》,《欒城集》卷二)又說:“子瞻每欲為國守邊,顧不敢請耳。”[12](《次韻子瞻感舊詩》自注,《欒城后集》卷一)
蘇軾在密州時,有一位太常博士喬敘(字禹功),尚武,蘇軾引為同道,寫了一首《鐵溝行》:“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歸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5](《詩集》卷十二)以漢朝名將李廣比之。
熙寧八年(1075),在密州知州任上,在常山求雨得雨后,他高興地先是舉行了一次小獵,又在鐵溝舉行了一次會獵。作《祭常山回小獵》、《和梅戶曹會獵鐵溝》二詩,(《詩集》卷十三),還作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詞,描繪了會獵的宏大場面:“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又說:“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4]P347洋溢著報國熱情、一片沙場立功之意。當時,密州境內有一伙強盜,安撫使、轉運使都拿他們沒有辦法。蘇軾派了緝捕使臣帶數(shù)千名悍卒去圍捕。但悍吏兇殘,竟誣殺無辜良民,恐致民變,這些悍卒畏罪四散,欲為亂。民上書州衙告變,蘇軾故意投書于地,不看書,說:“必不至此。”[4]悍卒乃安。蘇軾徐徐派人把殺人悍卒招來,立刻降服。(蘇轍:《亡兄墓志銘》)
(四)對密州文人之影響
由于當時蘇軾在北宋文壇的地位,他的這種狂也影響了許多密州士子。熙寧九年雖然蘇軾離開密州,但是密州士子“崇蘇熱”不減。許多文人也受到了其狂之影響,如明末清初詩人劉翼明在密州游覽完盧山后,在《鐵園觀雪放歌行》發(fā)出了“有天莫須舟問天,天生狂客豈徒然”[4]P755的狂言。無獨有偶,安丘文人商琥也仿效蘇公發(fā)出了“對菊始知佳節(jié)在,開尊忽憶少年狂”[4]P734的呼聲,還有如竇汝珽的“山意濃歸狂客眼”[4]P816等。而蘇軾的弟弟蘇轍在寫關于密州的詩詞中亦受到了其兄長的影響,寫下了“老大未須驚節(jié)物,醉狂兼得避危機”[4]P787以及“眼看狂瀾倒百川,孤根漂蕩水無邊”[4]P789的詩句。這些或許都間接表明了蘇軾的狂之詩詞對密州文人們的影響。
小結
狂放不羈,直言直語這或許是蘇軾與生俱來的性格,但是時代與周邊環(huán)境卻與他的這份狂格格不入。自己內心的這狂一直沒有一份沃土來滋養(yǎng),及至密州,周邊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以及文化氛圍,加之新法造成的窘態(tài)與邊患的不斷加深,蘇軾真正意義上繼承儒家思想中積極的“狂”也因此誕生,而蘇軾在密州期間的這些詩詞中大量出現(xiàn)狂字便說明了這一點。
[1]張海鷗.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3]劉建瓊,王蘋.淺論孔子的狂狷思想及其對后世文人之影響[J].湖南第一師范學報,2007.
[4]李增坡.蘇軾在密州[M].濟南:齊魯書社,1995.
[5](宋)蘇軾.蘇軾詩集[M].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6](漢)趙曄.吳越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宋)彭乘.墨客揮犀[M].北京:中華書局,2011.
[8](宋)蘇軾.蘇軾文集[M].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9](明)王之臣修,陳燁篡.諸城縣志[A].
[10]張崇琛.密州的文化氛圍與蘇軾知密州時期思想與創(chuàng)作的轉變[J].齊魯學刊,1999,(1).
[11]王水照.評蘇軾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詩[J].文學評論,1978,(3).
[12](宋)蘇轍.欒坡集[M].棗莊,馬德富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陳冬梅
F299.2
A
1671-4288(2015)03-0018-04
2015-04-05
王曉磊(1984—),男,山東平度人,諸城市超然臺管理處(蘇東坡紀念館)《超然臺》編輯部編輯,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三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