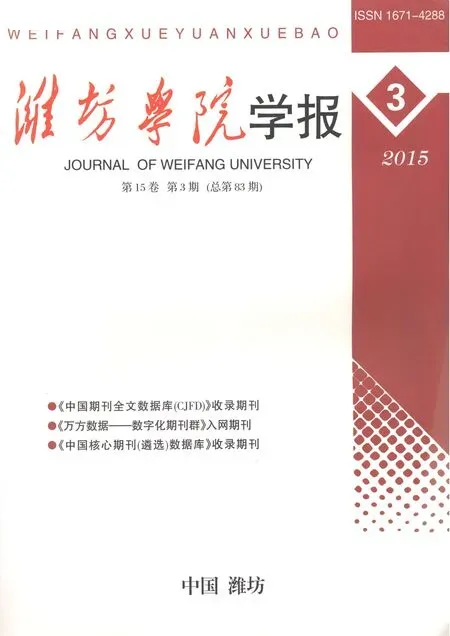巴拉丁斯基哀詩詩思淺探
——兼論十九世紀俄羅斯哀詩的流變
盧文雅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巴拉丁斯基哀詩詩思淺探
——兼論十九世紀俄羅斯哀詩的流變
盧文雅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巴拉丁斯基突破了浪漫主義哀詩的局限,為了確定哀之緣由,達到文之真實,他將“環境與個人”、“具體與普遍”等現實主義思考與浪漫主義筆法結合在一起,從而開拓了一種新的哀詩詩思。作為俄羅斯詩壇上最卓越的哀詩詩人之一,他的哀詩創作對十九世紀俄羅斯哀詩的流變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巴拉丁斯基;哀詩;真實;浪漫主義;現實主義
葉甫蓋尼·阿勃拉莫維奇·巴拉丁斯基(1800—1844),這位“普希金時代詩人群”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占據著重要的一席。他的詩優美清晰,哲意豐富,感情與心理刻畫真切動人,其詩才連普希金本人都稱賞不已,普希金甚至給他指定了一個“在茹科夫斯基的旁邊,在家神和塔夫里達的歌手(指著名詩人巴丘什科夫)的上面”[1]的詩壇位置。他的哀詩尤為繆斯女神所青睞,那種無奈和愁苦徹心徹骨,句句似嗟,字字如淚。這些美妙的詩篇不僅為俄羅斯文學畫卷涂上了一抹亮麗的色彩,還有形無形地影響了后代詩人的創作甚至彼時文壇的整體走向。將巴拉丁斯基的哀詩放置于整個俄羅斯哀詩流變的歷史語境中去考查,更能理解他的哀詩創作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的轉折性作用,以及他作為詩國傳統的延續者兼創造者的歷史價值。
一
哀詩(элегия)是浪漫主義文學中最為盛行的一種抒情詩體裁,顧名思義,其思必憂,其情必哀。別林斯基將哀詩定義為“內容憂傷的詩歌”[2],但哀詩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和不同的民族文學傳統中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俄羅斯文學受西方影響頗深,其哀詩體裁的興起與西方哀詩的演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西方,哀詩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跌宕起伏的過程:它起源于公元前七世紀的古希臘,最初以表達道德政治內容為主,在希臘化時代和羅馬時代,愛情主題漸占上風。[3]由于不見容于揚“理性”而抑“抒情”的古典主義,在17世紀日漸衰落。但是到了18世紀,由于前浪漫主義思潮的勃興,哀詩再度成為西方文人寄興寓情的重要表達形式之一。在資本主義文化的沖擊下,詩人們紛紛用哀詩來抒發對個人生活和命運的憂思,對沉重現實的哀訴,以及對田園理想的向往……
在俄羅斯古典主義文學繁盛時期,特列季亞科夫和蘇馬羅科夫最先為哀詩這一體裁賦予了較高的藝術價值。但俄羅斯哀詩真正的黃金時代還應始于茹科夫斯基,始于他那首“為俄羅斯前浪漫主義開辟了一個新時期”的《鄉村墓地》(1802),以及那首被譽為“俄羅斯第一首浪漫主義哀詩”的《黃昏》(1805)。[4]茹科夫斯基一改前人重外部刻繪而輕內心描摹的作詩傳統,將更多筆墨傾注于個人所思所感,再加上自然風景的巧妙渲染,使一腔幽思回腸九轉,分外哀婉動人。他也因此被別林斯基稱為“俄羅斯大地上第一個悲傷的歌手”[5]。與茹科夫斯基同時代的詩人巴丘什科夫也是一位吟唱哀詩的大師,他克服了前者的詩題局限,將歷史題材和公民題材納入自己的哀詩之中,憂郁之余更顯壯麗。如果說茹科夫斯基的憂郁哀詩是俄羅斯文學踏入浪漫主義大門的一把鑰匙,那么巴丘什科夫的歷史哀詩便是這扇大門中一道別樣的風景。
然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上半期,當文學發展進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之時,哀詩卻遭遇了嚴酷的危機。В.К.丘赫爾別凱的《關于近十年我們的詩歌——尤其抒情詩——之動向》(1824)一文一發表便激起了一股關于哀詩體裁的爭議之潮。盡管這篇文章遭到了諸如布爾加林、沃耶伊科夫、雅科夫列夫、別斯土舍夫、維亞澤姆斯基等各個派別文人的不同程度的反對[6],作者對哀詩的一些見解卻不可謂不深刻。丘赫爾別凱認為,哀詩發展的瓶頸不僅在于這一體裁本身的封閉性,還在于眾多哀詩作者才情的匱乏,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效仿者們的拙劣伎倆:“效仿者毫無靈感:他說的不是發自內心之言,而是強令自己復述他人的觀念和感受…我們這兒盡是些‘夢想’和‘幻影’,盡是些‘似乎’、‘好像’、‘仿佛’,盡是些‘宛若’、‘猶如’、‘某種’、‘某個’……感覺在我們這兒久已不存:憂郁感吞沒了其他一切…我們所有人都一窩蜂地懷念著自己逝去的青春……畫面處處雷同:月亮自然是憂郁的、蒼白的,山巖上其實從不曾有櫟樹叢,森林中成百次升起旭日和晚霞……”[7]在他看來,毫無來由的憂傷使哀詩變成了無病呻吟的囈語,似乎到了該將這一抒情體裁打入冷宮的時候了。
不過哀詩并沒有就此退出詩人們的視野。當哀詩體裁同浪漫主義文學一道陷入困境時,正是普希金力挽狂瀾,為哀詩寫作尋得了新的出路,也為浪漫主義物色了新的替代者——現實主義。他所開創的政治哀詩表達了進步人士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和憂憤,對自由理想的謳歌和神往,將時代精神融入字里行間。普希金挖掘出了哀詩之“哀”的社會性原因,在他和巴拉丁斯基的筆下,哀詩成了早期現實主義的“試驗田”,而那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哀詩則隨著浪漫主義的式微越發黯淡無光。
與此同時,巴拉丁斯基也以另一種方式改變著哀詩體裁的面貌。
二
1827年是巴拉丁斯基第一部詩集面世之年,也是他的詩歌生涯的轉折點,這一年將巴拉丁斯基的創作歷程截然劃為兩個階段。在巴拉丁斯基的早期創作階段即1819至1827年這段時間的詩作中,哀詩占據了極大的比重。這一時期,俄羅斯哀詩早已樹立了浪漫主義代言者的名望,并漸漸走向兩難之境:是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而積極尋求改變,還是茍且生存在蹩腳詩人自我陶醉的詩行里、然后自行告別俄羅斯文學的歷史舞臺?
面對哀詩危機的到來,巴拉丁斯基卻依然執著于他所鐘愛的體裁。不同于開創政治哀詩的普希金,他決定以傳統的形式向傳統發起挑戰,在文學發展的新條件下重寫愛情哀詩。
如果說,茹科夫斯基還相信塵世之外存在永恒的幸福,巴丘什科夫還試圖從宗教中尋求拯救,那么,巴拉丁斯基則對一切都絕望了:包括世界的制度,包括人被挾至的處所,包括愛情和友誼。他不信塵世的和諧,也不信天堂的和諧;他懷疑“此岸”的幸福,也懷疑“彼岸”的幸福。在他看來,人從一開始就支離破碎,而壓在人肩上的沉甸甸的生活則是陪伴他一生的不可規避的痛苦。[8]這種無所不在的失望感貫穿于巴拉丁斯基幾乎所有的哀詩之中,而他的愛情哀詩則無一不以“愛的失卻”來展示這種失望,因此或許也可稱其為“沒有愛情的愛情詩”。
巴拉丁斯基早期愛情哀詩的基本母題在他的《愛情》(1824)一詩中得到了表述,詩中所描寫的情感被抒情主人公看作是“危險的毒藥”,它毀滅人的心靈,使人對未來的快樂失去希望[9]:
我們在愛情里啜飲甜蜜的毒藥;
但我們依然在其中啜飲著,
我們為短暫的快樂而付出了
長久的不快樂。
愛情的焰火,生機勃勃的焰火!
所有人都說:可是我們會看到什么?
充滿破壞力的焰火
將他的心靈包圍、毀滅!就像詩人在哀詩《失望》(1821)中發出的感慨一樣,“我”不相信眼下的愛情,也不相信人類的所有愛情,甚至幸福本身也不可能存在:
我已經沒有信心再相信,
我已經不再相信愛情,
我不能再一次、
再一次沉湎于那變幻多端的夢景!在巴拉丁斯基最負盛名的愛情哀詩《自白》(1923)中,人們看到了一場痛入骨髓的無望的愛情。詩人運用真實而細膩的心理描繪手段,將抒情主人公復雜的內心活動刻畫得淋漓盡致。“我”對舊愛曾經滿懷情意:“你的嬌容和那舊日的幻想啊,我曾苦心銘記。”可是如今,生活的風波和長久的苦別早已熄滅了“我”的熱戀之火:“但今日的回憶已無生機/舊日的誓言也力不能及”,“你的影子在我心中業已淡薄,/我很少將你召喚,違背自己的心意,/熾熱的愛情逐漸冷卻,/心中的火焰已自行停息。”“我”也曾向往愛情,但初戀的幻滅使“我”再難尋覓新的愛情:“我孑然一身,仍有求愛之心,/但我要將這愛情遠遠拋棄,/不再墜入另一個情網,/只有那初戀才使我們沉迷。”愛情成為遙不可及的奢侈品,即使新婚也不能使“我”重溫愛情:“也許,我會選得一個不愛的伴侶,/在精心安排的婚禮上我會向她伸手表愛。”但是,“我們不會互傾心中的秘密,/也不會縱情歡樂與狂喜,/我們結婚未結同心,/是命運將我們牽到一起。”[10]
在詩人筆下,抒情主人公的內心感受是動態的、變化的,準確的選詞和精到的分析使那種欲愛而不能的矛盾心理格外具體可感。這種分析式的心理描寫作為巴拉丁斯基哀詩的重要特點,在《失望》(1821)、《吻》、(1822)《辯解》(1824)等其他愛情哀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自白》的最后四句道出了愛情破滅、幸福無望的根本原因:
諸事難從人愿,你我身不由己,
在那青年的時代
我們曾匆忙發過誓言
但在全知的命運看來可能會是荒誕滑稽。[11]
是什么造成了昔日女友的悲傷、未來嬌妻的不幸?不是“我”的負情與無情,而是環境使然,命運使然。人無力抵抗命運,客觀現實不會因人的意志而改變。這正是巴拉丁斯基在早期哀詩中竭力試圖表達的思想,也是他在哀詩危機來臨時作出的體裁改革的探索,即將“個人與環境”這個現實主義命題植入浪漫主義氣息濃厚的哀詩體裁中去。
1821年,初露鋒芒的巴拉丁斯基寫下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關于謬誤和真實》,詩人對自己的審美信念進行了論述,對自己詩中所描繪的生活現象進行了哲理性的闡釋。在巴拉丁斯基的行文中滲透著這樣一種思想:我們的感覺機體所感知的客觀現實是外在于我們的,它并不取決于我們怎樣理解它。我們在造就了我們的意志與觀念的現實的影響下發生著改變,用不同的方式去評價同樣的事物,而事物本身卻依然故我,不以我們的評價為轉移。經驗“為我增添一些東西,或者消除我的某一部分:在這兩種情況下我都不再是之前的我,——我變了,而客觀事物卻沒有變。”[12]巴拉丁斯基創作思想中的關鍵要素——經驗、環境、現實——非但不由人的觀念和意志而定,還對人的理智與情感、觀念和意志,對人的生活的改變、個性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
還在1819年時巴拉丁斯基就在他那首浪漫主義色彩十足的贈言哀詩《致克列尼岑》中隱隱透露出了人無法擺脫現實控制的悲劇性事實:
過去的時間在哪里,曾經的夢想在哪里?
那童心的活力和希望的甜蜜!
冷酷的經驗銷毀了所有。
朋友你知道嗎?——病痛和哀愁,
使他在青春華年里便老去;
你熟悉的許多弱點已消失,
他的許多夢想變得陌生不已!
理智更可靠、更堅固,
言談舉止更謙虛;
或許,他變得更謹慎、更聰明,
不過,想必如今幸福也減少了百倍。我們無法駕馭時間,甚至無法駕馭我們自己。眼睜睜看著時間將萬物改換得面目全非,自己卻無計可施,那是怎樣一種悲哀。前文提及的《自白》一詩就是對這種悲劇意識的最完美的印證。
多年以后,現實主義聲勢漸起,客觀事物與外界環境對人的思想行為影響之大已成為人所共識。當屠格涅夫、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一批現實主義大師將客觀環境納入自己的研究對象之列時,巴拉丁斯基早已在詩歌實踐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索。盡管他的作品與真正的現實主義還相去甚遠,他的哀詩中還充斥著浪漫主義特有的詞匯手段和形象體系,但是從這些哀詩中已經可以看到未來文學發展趨勢的端倪。“人與環境”問題的提出使巴拉丁斯基的哀詩創作成為俄羅斯文學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轉換的復雜進程的一個環節。
三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拉丁斯基的哀詩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失敗,三十年代反動統治的加劇,這一切都促成了巴拉丁斯基詩歌的轉變。少年時節最愛吟弄的愛情悲歌逐漸讓位于而立之際深沉的哲理思索,只是那種無可救藥的失望感和悲劇感卻有增無減。生命與死亡、歷史與永恒、詩的繁盛與衰落,這些困擾著所有哲理詩人的存在性問題同樣也困擾著巴拉丁斯基。詩歌的命運、詩人的命運,終究都是悲劇性的存在。他憂傷地審視著因無人關心而漸趨沒落的詩歌:
時代沿著鋼鐵之路邁進,
人心貪財,欲壑難填,
幻想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無恥地
專注于迫切需要的、有利可圖的東西。
詩歌的幼稚幻夢
在教育的光照下消逝了,
人們不再吟風弄月,卻操心辦工業。[13]創作主題的嬗變、悲哀情緒的加重意味著巴拉丁斯基哀詩的思想基礎的蛻變。詩人曾在其頗具綱領性的《關于謬誤和真實》一文中表達了自己力圖在詩中描繪真實的愿望,而他前期的哀詩的確也在努力踐行著這一目標,方法便是將客觀環境對人的巨大影響當作悲劇不可逃避的緣由寫入詩中。在巴拉丁斯基的后期創作中,“真實”依然是一個關鍵性的詞匯,不過此時的真實已經不再是先前那種具體可感的真實,而是另一種抽象的、普遍的真實,抒情主人公的個性也不再那樣清晰、鮮明,而變得更加寬泛、更加難以捉摸。我們可以在巴拉丁斯基為自己的長詩《姘婦》(1831)所作的序言以及隨后發表的文章《反批評》(1831)中看到詩人思想變化的軌跡。此時的詩人看到的并不是無窮無盡的真實,而是一個真實的范疇,以及與其相反的非真實的范疇。真實乃是關于事物和現象的所有真相。在藝術作品中真實的尺度只有一個,即生活和現實。文學應是“類似于其他科學”的學科,作家應“像科學家一樣”能夠“展現真實”。巴拉丁斯基不僅在藝術中看到了現實的反映,還解釋了藝術是如何完成反映現實這一功能的。他在若干文章中都提出了——盡管沒有使用這一術語——藝術典型化的問題。為了達到真實,思想應當“從總體中獲取,而非從個別中獲取”,而“總體”指的是那些最普遍、最典型、最常見之物。[14]正是這種對真實的理解成為了巴拉丁斯基后期哲理詩創作的思想基礎。
在巴拉丁斯基的詩歌世界里,對現實的深刻把握同對哲學的深切關注是不可分割的。現實蘊藏于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在詩人筆下卻都被賦予了哲學的涵義。物理學家牛頓從墜落的蘋果中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詩人巴拉丁斯基則從同樣的果實中發現了“上天的律令”:
蘋果果實從樹上落下:
人類便理解了上天的律令!普遍的規律取代了具體的現象,整體的存在取代了個別的人與物,這就是巴拉丁斯基后期哲理哀詩最重要的一個特點。《秋天》(1836)是這類哀詩的典型代表,詩中那“步入秋日”的“生命田野的耕者”并不是某個具體的形象,那“懷著希望播種”、“做著關于遙遠的獎賞之日的美夢”的“農夫”展現給我們的也不是某個特定之人的命運。巴拉丁斯基臨終前寫下的另一首哀詩《何時你的聲音,噢,詩人……》(1843)則將“沒有主人公”的哀詩藝術發揮到了極致:
何時你的聲音,噢,詩人,
會在高呼中被死神終止,
何時正當盛年的你
會被迫不及待的劫數捉住,——
誰會被繁華時光的夕照,
觸動內心深處?
誰會為你的死,
哀嘆著心扉緊縛,
拜謁你靜靜的棺木,
為沉默了的繆斯號哭,
向你的骨灰致敬,
真誠地祭奠亡靈?
不會有一個人!——但是不久前的佐伊爾
會為歌者編寫一支贊美曲,
他已為死去的人搖爐散香,
也要讓活著的人沾沾香爐。
顯然這是一首獻給死者的哀詩。但這位“被死神終止聲音”的詩人到底是何許人也,巴拉丁斯基并沒有交代,研究者們也是眾說紛紜。不過這首詩的主角是誰似乎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詩中體現的存在性意義。全詩有七個完成體動詞表示將來時態,分別是“終止”(остановит)、“捉住”(уловит)、“觸動”(тронет)、“哀嘆”(восстонет)、“拜謁”(посетит)、“致敬”(почтит)、“編寫”(сложится),筆者以表達未來意義的“會”字置于其前用以標記時態。這七個動詞支撐起了整首詩的意義框架,詩人的死不僅僅發生在過去,還發生在現在,甚至未來。不僅僅是已成之事,也是將成之事。死,是已逝者的命運,也是在世者、甚至未生者的必然歸宿。這首哀詩看似講的是某位詩人死時的冷清之境,但實際上巴拉丁斯基是將“死”作為一種普遍的存在來書寫的,身后的凄涼或許是每個人都難以逃避的宿命,存在的悲劇使這首詩更添了幾分苦楚。
同早期哀詩相比,巴拉丁斯基的后期創作對“真實”的孜孜追求絲毫未減。他將藝術與科學相提并論,他把個別的真實與總體的真實區分開來,他以從具體事實中抽象出來的一般性規律作為詩歌寫作的對象。這一切都使他的詩思十分接近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但他并沒有像涅克拉佐夫一樣成為一位現實主義詩人,他的哀詩哀嘆的不是社會的現實,而是存在的現實。詩人站在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十字路口,無處可歸的孤獨身影就像他筆下的哀詩詩句一樣,既哀傷,又無畏。
四
縱觀巴拉丁斯基的整個詩歌創作生涯,哀詩這一版塊尤其醒目,其情之哀、其語之美、其繪之真、其思之深,共同構成了他的哀詩特色。他的哀詩藝術對同時代和后代詩人的創作具有無法忽視的影響,在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哀詩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巴拉丁斯基的一絲影子。
在巴拉丁斯基之后,萊蒙托夫的哀詩開啟了俄羅斯哀詩體裁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其中也不乏對前人創作經驗的承繼。他的愛情哀詩里有靜靜的眼淚,朦朧的愿景,以及夢似的回憶,使人想起多情善感的茹科夫斯基。他的歷史哀詩則繼承了巴丘什科夫的詩歌傳統,借史抒懷,哀而不傷。但是萊蒙托夫的哀詩卻有一套不同于浪漫主義哀詩的哲學:他不去來世、不去身外憧憬那種神賜的幸福,而是一頭扎進混沌的現實,激烈地控訴,決絕地反抗。這與巴拉丁斯基不無相似,后者盡管承認人在現實面前的無能為力,卻從不曾向虛無的未來或宗教乞求幸福的可能。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巴拉丁斯基最先意識到,對現實的確證也包括對反抗現實的確證,這種反抗正是現實的一部分,叛逆的夢想有其存在的權利。[15]
萊蒙托夫進一步發展了巴拉丁斯基的“叛逆”哀詩,他對世界的悲觀態度與對虛偽的人世、冷酷的上流圈的不肯妥協是緊緊相連的。
涅克拉索夫大概是十九世紀俄羅斯哀詩發展史上最后一個特色獨具的詩人了。他的時代已同浪漫主義揮手作別,哀詩體裁的風頭也不似以往,詩歌發展趨勢如此,他的哀詩創作便顯得尤為不同尋常。在涅克拉索夫的現實主義哀詩中,我們不僅能夠體察到以普希金為代表的民主政治詩詩風,也感受到了巴拉丁斯基早期愛情哀詩中那種對“真實”的不倦追求。Г.А.古科夫斯基這樣描述涅克拉索夫的抒情主人公:“愛情詩的主人公不是作為一種規范,不是作為一個道德審美的理想模型或者合乎道德的愛情形象——最純潔、最自由、最崇高的愛情之形象被描繪的,而是作為一個擁有具體又普通特點的活生生的人被描繪出來,這是個好人,但卻為‘丑陋’的時代所毒害,他將這個病態時代的精神通病帶到了自己身上、帶入了人自己的愛情中。”[16]這一曾似相識的愛情主角,不正是我們在巴拉丁斯基的哀詩《自白》中所看到的那個再不肯相信愛情的主人公嗎?
[1](俄)亞歷山大·普希金.普希金散文選[M].謝天振,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45.
[2]В.Г.Белинский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13-ти т.,Т.5 [M].М.:Наука,1954,стр.50
[3]Литературн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ерминовипонятий [M].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А.Н.Николюкин.М.:НПК《Интелвак》,2003,стр. 1227.
[4]王立業.《黃昏》:俄羅斯文學的清晨——解讀茹科夫斯基的風景哀詩《黃昏》[J].國外文學,2006,(2).
[5]В.Г.Белинский.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трехтомах[M].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Ф.М.ГоловенченкоМ.:ОГИЗ,ГИХЛ,1948 ТомIII.стр.32.
[6]см.Л.Г.Фризман.Жизньлирическогожанра:Русскаяэлегияот СумароковадоНекрасова[M].М.:Наука,1973,стр.60.
[7]В.К.Кюхельбекер.Онаправлениенашейпоэзий[DB/OL],http: //az.lib.ru/k/kjuhelxbeker_w_k/text_0180.shtml,2009-1-27
[8]см.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XI-XIXвв[M].Подредакцией В.И.Коровина,Н.И.Якушина.М.?Русскоеслово?2001,стр.235.
[9]С.В.Рудакова.Своеобразиежанраэлегиивраннемтворче ствеЕ.А.Баратынского[J]/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фил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2008,(20):102.
[10][11][13]譯詩選自徐稚芳.俄羅斯詩歌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7-169,172.
[12]Л.Г.Фризман.Жизньлирическогожанра:Русскаяэлегияот СумароковадоНекрасова[M].М.:Наука,1973,стр.104
[14][15][16]см.Л.Г.Фризман.Жизньлирическогожанра:Русская элегияотСумароковадоНекрасова[M].М.:Наука,1973,стр. 110-111,123,111.
Research on Poetic Thoughts of Baratynsky’s Elegy——Also on and the Chang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ussian Elegy in the 19 Century
LU Wen—ya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Baratynsky overcame the limitations of Romantic elegy, and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reason of sadness and obtain the reality of poems he combined the questions of Realism such a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dividual”the specific and the general”with the Romantic style, thus opened up a new poetic thought of elegy. Baratynsky i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Russian poets, and his elegy writt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ssian Elegy in the 19 Century.
Baratynsky;elegy;real;romanticism;realism
I106.2
A
1671-4288(2015)03-0035-05
責任編輯:陳冬梅
2015-03-21
盧文雅(1988-),女,山東濰坊人,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羅斯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