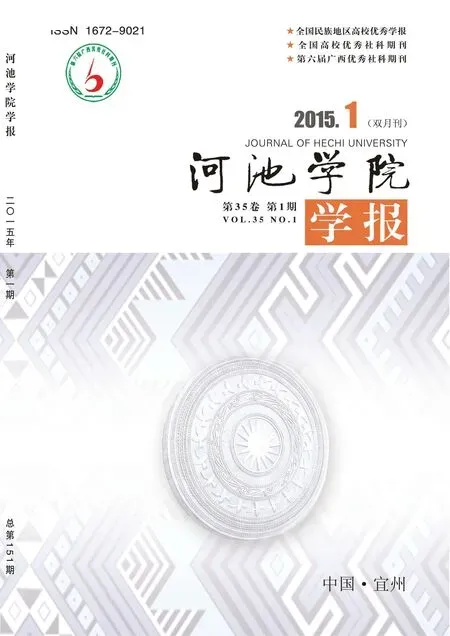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視野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戴燕玲,黃璜
(廣西衛生職業技術學院 社會科學和衛生事業管理系,廣西 南寧 53002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視野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戴燕玲,黃璜
(廣西衛生職業技術學院 社會科學和衛生事業管理系,廣西 南寧 530023)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司法制度,是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進程中的重要一環。人民陪審員制度當前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現實困境可以總結為制度、操作和觀念三個層面的形式主義。將現行的共職共權模式改為分職分權模式、遴選機制,并回歸大眾化路線,才能體現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公民權利屬性,有可能改變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和不力狀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人民陪審員;監督權;司法權
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1]這一重要論斷,讓人民陪審員這一充滿爭議的司法制度,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
一、人民陪審員制度基于公民監督權而合理存在
自20世紀50年代制度化以來,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在不斷的爭議聲中經歷了“法律初步肯定、恢復和淡化兩個階段”[2]后,國家投入巨大的公共資源進行建設和完善,2004年專門訂立實施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人民陪審員制度已然成為我國一項基本的司法制度。
然而,在實踐中不管是實務界還是學界,對這項司法制度都存在巨大的認識分歧。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缺陷和現實困境、急需改革已成為基本共識,甚至主張廢除這一制度的聲音也不罕見。由于立法規制上的某些不完善和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學界對人民陪審員制度有各種否定性的評價,如認為這一制度直接違反我國憲法的“違憲說”[3]、認為1982年憲法取消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表述是將其“降格”[4]為普通法律制度的“降格說”,等等。在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法律地位是否下降,這一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弄清這一問題是解讀其命運前途的關鍵。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基本性質是公權力還是私權利?即人民陪審員參與司法審判,行使的是國家司法權還是公民監督權,是這一問題的關鍵。《決定》第一條:“人民陪審員依照本決定產生,依法參加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同法官有同等權利。”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一文件的表述來看,人民陪審員擁有與法官同等的權力;而對我國法官的定義,根據《法官法》第二條,“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由此似乎得出結論:人民陪審員行使的是國家審判權,即國家司法權。而當我們試圖在規定公民基本權利和國家權力的憲法中尋找支持這一結論的論述時,卻發現行不通。我國現行1982年憲法刪除了1954年、1975年和1978年憲法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規定,對司法權的行使主體則有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也就是說,我國憲法在第二章規定了公民享有的是包括平等權、生命健康權、宗教信仰自由、監督權等在內的一系列基本權利(Right),并未授權公民作為個體可以行使國家司法權(Power)。針對作為下位法的《決定》與作為最高位階法的《憲法》存在沖突的問題,《關于<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說明》作出了說明:“第一,立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司法工作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的重要體現,是落實憲法關于公民依法參與管理國家事務權力的重要保障;第二,立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弘揚司法民主、維護司法公正的現實需要;第三,立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增強司法活動透明度,強化人民群眾對司法活動監督的現實需要,對于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加強訴訟調解,說服當事人息訴服判,也具有良好效果;第四,立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的必要措施。”由此可見,《決定》的立法意圖在于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這一載體,使公民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從而達到推進司法民主、公正、廉潔和權威的效果,其立法依據,就是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的公民監督權。試問,如果人民陪審員行使的是司法權,根據“不能當自己裁判員”基本的法理,如何“強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因此結論就是,人民審判員行使的是公民監督權,而非司法權。
我國最高司法部門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性質及作用的認識,也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歷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一般將人民陪審員制度放在“司法改革”這一部分,表述各有不同:2012年之前的工作報告沒有直接說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目的,僅列舉基本情況;2012年和2013年在列舉基本情況之前,加入了“推進司法民主”的表述;2014年報告在保留了上述內容的同時,首次加入了“暢通人民群眾依法參與、監督審判工作渠道”的表述 。[5]可見,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性質及作用已經逐漸清晰、成型,那就是保障公民通過參與司法過程、監督審判權。
綜上所述,將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公民監督權的體現,不僅符合公民基本權利廣泛性、平等性、真實性和權利與義務一致性的特點,也更加與權力機關的立法意圖完美契合。由此,“違憲說”與“降格說”的疑問亦可以迎刃而解:監督權是我國現行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權利,這一點并沒有因為其取消了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表述而改變,公民作為人民陪審員參與具體案件的審理,正是在行使公民監督權,何來違憲一說?其次,憲法性制度必須通過下位法得以實施,所謂“普通司法制度”也得有憲法制度作為前提;《決定》作為下位法確定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憲法依據,正是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的公民監督權,完全符合憲法至上的法治原則,又何來“降格”?
這一結論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解釋為何人民陪審員制度會在爭議中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也能證明為何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建設中國特色法治體系的重要一環。這一制度體現、保護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更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完全吻合。
行使公民監督權這一基本屬性,在微觀上表明人民陪審員的陪審行為與審判員的審判行為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是對后者的監督,以保證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得到落實;從宏觀上表明隨著我國依法治國工作的推進、公民維權意識的提高,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公民行使權利的具體保障制度必將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加強。人民陪審員的監督,與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并不沖突。在當前我國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影響法院獨立審判的因素往往來自公權力的非公益性使用、媒體的不當報道和社會輿論的過分關注,作為個體的人民陪審員既無必要也無能力干涉審判員正常履行職責,相反其非“體制內”的身份可以對外部力量起到制衡作用。因此,隨著我國社會轉型進入關鍵節點、司法改革進入攻堅期,進一步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維護人民權益、推進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制度、操作和觀念三個方面的“形式主義”表現與原因分析
形式主義即應然與實然不相吻合,事物的形式和實際相互脫節,是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特征之一 。[6]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幾乎所有的制度都或多或少存在制定意愿與實踐效果的不一致,即形式主義。如公務員應該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職業群體,當出現權力尋租、貪腐等現象,相關的制度規定就是停留在紙面的規定,這就是形式主義。在當前我國司法領域,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理由與狀態的表述混亂、“陪而不審”、“可有可無”[7]等現象也可以總結為制度、操作和觀念三個層面的形式主義。
首先,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制度層面上呈現出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特點。從立法淵源的角度來看,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移植于西方的陪審制度,但不管是制度目的還是運行模式上都與后者有所區別,可總結為脫胎于英美法系陪審制、借鑒了大陸法系參審制,希望畢其功于一役的特殊制度。英美法系如美國的陪審制是根據美國憲法第六和第七修正案確立的一項憲法權利,本質是公民權;大陸法系如法、德兩國的參審制則是作為本國司法制度內的特殊法官,用其專業知識完善審判過程,行使的是完整的國家司法權 。[8]根據我國憲法和相應的規范性文件,我國陪審員一方面具體工作包括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區別于英美陪審制;另一方面我國陪審員沒有法官身份(甚至排除了其他法律從業人員的參與),又區別于大陸法系的參審制。可以說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在立法精神上與英美陪審團制度相近,而與法官共職共權的實際工作內容又借鑒了法德的參審制。這種將兩大法系融合于一身的制度設想,造成最高指導思想的憲法、負責具體實施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與三大訴訟法之間對人民陪審員制度表述的混亂。制度性質是公民權利,在制度的實施上卻參照國家司法權,可謂“名不正言不順”。
制度制定的形式主義又必然在具體制度實踐中得到體現,這種體現首先是實施效果的形式主義。自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積極探索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到2004年《決定》的通過,再到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決定》的發布,國家權力機關始終對人民陪審員制度報以極大熱情。從宏觀數據統計來看,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工作可以說是“重煥青春、欣欣向榮”。[9]
上表表明:第一,2009年至2013年,我國人民陪審員數量逐年增加,這說明2004年《決定》的實施效果是明顯的;第二,參審案件數量在近5年都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說明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發展勢頭很猛;第三,2013年我國我國人民陪審員參加一審普通案件占比達到73.2%,說明人民陪審員已普遍參與到我國司法審判過程中。
以上我們僅從宏觀層面考察了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發展,微觀層次的操作層面表現則展現出不一樣的情形。自2004年《決定》頒布后,根據學界的諸多研究成果和媒體的報道,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諸多的實際問題:一是代表性不足,首先表現為陪審員在文化程度、職業結構等方面不具代表性。根據2008年5月《人民法院報》的一篇報道,全國陪審員大專以上學歷占87.31%;[9]而我國國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內地人口中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11963.679萬人,僅占總人口的8.73%,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為8930人。[9]同一篇報道同時指出,截止到2008年5月,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校、農民工、無業人員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比重分別占25.31%、6.41%、2.53%和2.87%,[9]即非黨政機關的僅占37.12%。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不足,最后的表現就是往往由少數固定的陪審員參加審理,隨機抽取形同虛設。二是由于陪審員缺乏專業知識,難以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提供有用信息,往往是“陪而不審”。法官是訓練有素、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職業群體,根據1995年《法官法》,我國法官必須經過嚴格的法學教育并要求具備至少一年的法律工作經歷。而我國人民陪審員一方面排除了法律職業的參與,另一方面又因為與職業法官共職共權的工作方式,要求必須擁有與職業法官相同的工作能力,結果易成為僅滿足合議庭開庭人數要求的“擺設”,或者成為法官的助手做一些輔助性工作,實踐操作中的狀況就與制度目標相距甚遠。
最后在觀念層次上,人民陪審員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司法制度,其制度目標體現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價值,而現實是不管是法官、還是社會,甚至是陪審員本人,對陪審制度的認同度都不高,輕視人民陪審員工作價值的觀念普遍存在。
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制度、操作和觀念三個層面的形式主義,可以用社會分工的理論解釋。涂爾干認為,不協調的分工是反常分工的一種,是由不適當的分工組織的出現導致社會成員行動不和諧、勞動積極性缺乏所產生的。[10]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方面,是個體社會功能從復合走向單一,即職業化、專業化。我國人民陪審員從事陪審工作是兼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還需承擔另外的分工,缺乏必要的訓練卻被要求承擔復合的社會功能,這就導致了社會功能、社會角色之間的沖突,進而效率下降、造成資源的浪費。
專業法律職業群體是我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內容,目前職業化的改革路線是符合中國社會轉型期一般規律的。反觀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制度、操作和觀念上與大趨勢存在相背離的狀況,這就要求,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必須解決好上述三個層面的形式主義。
三、完善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若干思路
對于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前途問題,即要取消還是要繼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過程中有其特殊價值、承擔著獨特任務,非但不應取消,還應得到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這一論斷已作為事實上的決定,被載入了作為下一階段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指導思想的《中央發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決定》這一重要文件。我國的法制現代化是典型的外發型模式,在這一進程中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占主導地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更可認為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實際領導者和主要推動者,不僅設計形成了若干法治目標,還可以利用包括公權力在內的政治資源來實現法治目標。因此,在接下來的一個時期,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會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不是取消,這是確立無疑的。
(一)擴充陪審員隊伍的絕對人數
目前,有限的人數制約了我國人民陪審員這項保障公民監督權的重要制度的實現,隨著推進依法治國工作的深入,人民陪審員隊伍必須得到極大的擴充。2013年我國人民陪審員為12.3萬人,僅占我國總人口的十萬分之九;與此同時,根據近期的報道,我國目前法官人數為19.6萬 ,[11]人民陪審員與法官之比例不夠一比一。人數的短缺使得人民陪審員無論是在微觀層面監督法官公正審判,還是宏觀上代表人民監督審判權,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作為對比,性質類似的美國陪審制度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美國公民理論上都有當陪審員的義務(Jury Duty),不履行陪審義務甚至會遭到逮捕;在具體的庭審中,陪審員的人數根據案件需要來決定,可以是12人的小陪審團(Petit Jury)到16至23人的大陪審團(Grand Jury)。[12]拋開美國陪審團制度消耗大量社會資源等弊端,從人數而言,美國陪審員相比中國人民陪審員顯然更具代表性,在具體庭審過程中起到的監督作用也更強。當然,必須強調美國陪審團制度是與其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配套制度,其確定的人員比例也并非我國陪審員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中美兩國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公民參與審判行使監督權,不管是美國陪審團制度還是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數的保障是重要的前提。這個結論與我國結合具體實際推進司法改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并不矛盾。
人數的擴充會引出另一個問題是人民陪審員的遴選機制是否需要改革?根據《決定》,排除了法律工作者、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和被開除公職的人員后,只要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年滿二十三周歲;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體健康;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的條件即可通過法定程序擔任人民陪審員。表面上看,獲取我國人民陪審員資格的門檻并不高,實際上我國人民陪審員的遴選機制走的是精英化路線,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已經排除了絕大多數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可能。精英化的遴選方式,結果必然是我國人民陪審員呈現出少數化和固定化的模式。這種遴選機制對于我國進一步推進司法民主、暢通人民群眾依法參與和監督審判工作,在實踐中是不利的。特別要指出,這種遴選機制還直接將我國廣大的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民(包括農民工)排除在外,使其無法享受到基于公民資格應有的權利和機會。當然,這種現狀并非司法部門有意為之,而是我國當前轉型期農民遭受較為廣泛的社會性和制度性歧視的一個體現,但對于司法部門更重要的應該是如何消除這種歧視。
(二)去除人民陪審員“精英化”要求,使其適當平民化、大眾化
體現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公民權利屬性使其具有最大代表性,要求人民陪審員在遴選機制上必須走大眾化的路線。我國廣大國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這一事實表明,“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要求既不現實也無必要。不現實指在這種標準下遴選出的人選不具代表性;無必要指隨著《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決定》精神的逐漸落實,我國人民陪審員將“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憑借“公道正派”的道德觀念判斷是非曲直,這與文化程度并無直接聯系。此外,在如農村宅基地、土地流轉、農民工勞動爭議等涉農糾紛中,還應通過普法宣傳、名額保證等制度性安排主動吸納農民群體參與人民陪審員工作,讓農民這一“典型的結構性弱勢群體”可以平等行使基本權利、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有學者指出,應建立“雙軌運行機制”,即在平民陪審之基礎上比照職業法官的標準選任專家陪審員;案件當事人在平民陪審和專家陪審中擇一選擇 。[13]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意識到了陪審制度平民化、大眾化的重要性,但本質上還是企圖將英美陪審團模式與法德專家法官參審模式合二為一的老思路;這種模式不但與我國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相悖,也不符合社會分工專業化的趨勢,更不能回應這樣的問題:當事人為何要拋棄更具權威性的專家陪審選擇平民陪審?平民陪審缺乏競爭力、吸引力的結果當然是因為無人問津而被架空,人民陪審制度的平民化、大眾化自然就無從談起。
擴大候選人群、吸納較低文化程度人群擔任人民陪審員并不會當然地損害審判工作的嚴肅性和公信度。首先,前述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主要職責為行使監督權而非行使司法權,那么就意味不需要太高的法律專業知識和素養。另一方面新任人民陪審員在參與審判工作之前要接受培訓,以了解有關工作職責、流程、法律責任等必要知識,以保證審判工作順利進行。在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的前提下,任前培訓的內容并不會過多涉及具體的法律適用問題,不存在可行性的問題。再次,人民陪審員在具體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扮演的是“保險”的角色,職責是確保案件不會受到案外因素的干預,法官做出合乎“公平”的裁判,最終的司法文書簽署者仍然是人民法院,并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公信力。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D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0/28/c_1113015330.htm.
[2]王敏遠.中國陪審制度及其完善[J].法學研究,1999(4):23-46.
[3]吳丹紅.中國式陪審的省察——主要以<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為對象[J]. 法商研究,2007(3):182-197.
[4]謝曉斌.公民參審: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探討[J]. 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4):14-19.
[5] 2009~201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DB/OL].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官網:http://www.court.gov.cn/.
[6]劉祖云.中國社會發展三論:轉型·分化·和諧[J].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33-35.
[7]丁愛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立法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J]. 人大研究,2003(4):40-42.
[8]彭小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復蘇與實踐:1998-2010[J]. 法學研究,2011(1):17-34.
[9]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DB/OL].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2-4-20),http://www.gov.cn/test/2012-04/20/content_2118413.htm.
[10]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0.
[11]歐陽開宇.中國內地法官人數已達到19.6萬人[DB/OL].中國新聞網(2013-7-25)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7-25/5085883.shtml.
[12]程翔.美國陪審團制度的晚近發展[J].司法改革論評,2007(1):239-255.
[13]廖永安.社會轉型背景下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路徑探析[J].中國法學,2012(3):149-161.
[責任編輯 韋志巧]
Review on People Assessor System: in View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DAI Yan-Ling, HUANG Hu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 Medical Management, Guangxi Medical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23, China)
As a fundamental part, people assessor system is greatly significant to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le of la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 The existing defects and realistic difficulties of this syste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rmalism on system, operation, and concept. Therefore, future reform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hange the operation mode from so-called “unseparated power” into “separated power”. Consequently, the people assessor system can be enhanced and truly embody civic rights.
socialist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 people assessor; the supervision right of citizens; jurisdiction
D925
A
1672-9021(2015)01-0100-06
戴燕玲(1966-),女,廣東五華人,廣西衛生職業技術學院社會科學和衛生事業管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法學、思想政治教育。
201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