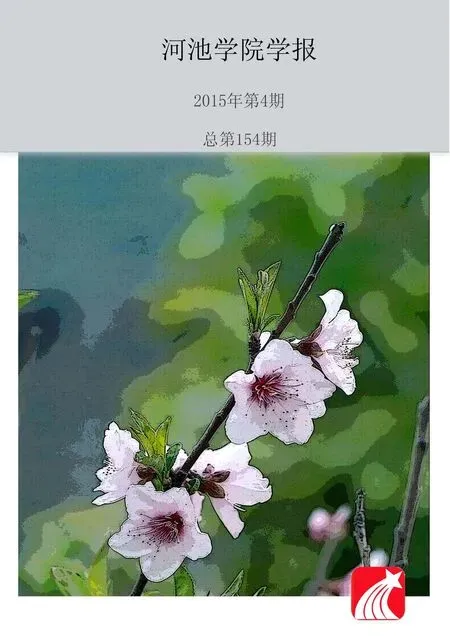略談巴赫金外位性理論的發展過程
簡圣宇
(廣西藝術學院 公共課教學部,廣西 南寧 530000)
巴赫金作為思想家,其復調理論廣為人知,但任何成熟的理論的建立都經歷過萌芽期。外位性理論作為后來復調理論的鋪墊性理論,為巴赫金從現象學走向對話理論打下了重要的哲學基礎。“外位性”這一概念,雖為巴赫金早期嘗試構建其主體性哲學的副產品,實際上到了巴赫金晚年,仍然因其作為他的主體間性美學思想的根基而具有主要理論價值。
他在《論行為哲學》中提出:“現在我身處的這唯一之點,是任何他人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時間和唯一空間所沒有置身過的。圍繞這個唯一之點,以唯一時間和唯一而不可重復的方式展開著整個唯一的存在。”[1]41在此,他試圖倡導建立一種強調“負責任”主體意識(所謂“應分”)的道德哲學,并把自我主體(“我”)存在的唯一性作為這種道德哲學的基礎,但在具體闡述時,他愈加意識到既然“我”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那么同理,他人也同樣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
“我”由于自身存在的唯一性而處于他人的外位,他人亦由于其存在的唯一性而處于我的外位,所以“任何人都處在唯一而不可重復的位置上,任何的存在都是唯一性的”。[1]41這里涉及到主體間性理論的一個關鍵基礎,即,無論是作為“我”的自我主體,還是“我”之外的作為“他者”的諸多主體,在存在的時間、空間和思想維度上都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這暗含著一個傳統主體性最簡單、直接的悖論:傳統主體性強調自我主體在思想意識結構內的崇高地位,因為自我主體是獨一無二的。然而既然你我都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那么就不可能只存在一個話語中心,而是復調和聲的諸話語中心。欲想溝通這些諸話語中心,就必須設立對話的平臺,彼此進行開放性交流。思想壟斷可以持續一時,但終無法長久維持。因為其他主體在對話平臺上,任何獨白都將被復調結構所消解。
一、作為主體存在形態的“事件”
“бытие-событие”是巴赫金在其早期提出的一個核心概念,直譯為“存在-事件”。而以構詞法觀之,“事件”(событие)一詞由“共同”(со -)和“存在”(бытие)構成,雖然在詞匯學上“事件”(событие)不能直接等同于“同在”(со - бытие),然而觀察巴赫金相關文本中的具體論述,他確實是從哲學意味上來使用(событие)一詞的,在他的概念中,這就是“共同存在”(со - бытие)。諸多主體共同存在于一個結構之中,“唯有這樣的行為才充分而不息地存在著、生成著,是事件即存在的真正活生生的參與者,因為行為就處于這種實現著的存在之中,處于這一存在的唯一的整體之中”。[1]3-4每個單一主體都應當承認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承認自身的局限性無法憑借自身而得到徹底克服,只有在彼此對話的主體間性的結構中,單個主體的視野盲點才能在對方的視野優勢中獲得澄明。故而該命題也可視為巴赫金主體間性美學思想的起點。
雖然寫作《論行為哲學》時,巴赫金還主要是從主體性的角度進行理論思考,但其已經逐漸呈現出主體間性的思想萌芽:從此文開始,巴赫金逐漸以自我主體與他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為思考的出發點闡述問題,在我與他人的辯證關系上思考主體的存在,并且意識到主體的這種存在不是已完成的現實,而是在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中不斷生成、建構而又不可替代的。巴赫金在此論文中反思到,“存在即事件”并非只是某種思辨構想之物,而是在存在的演變中逐步顯現的未完成品。從《論行為哲學》開始,在他的論著中,與“共同、相互”有關的詞匯也多了起來,以至于美國學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半開玩笑地說,巴赫金有在單詞中使用前綴“со-”(共同、相互之意)的癖好。[2]198
在《論行為哲學》里,巴赫金以外位性論點為依據,對審美移情說((Einfühlung))進行了批駁。他認為單純的移情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我”真的與他人重合、淹沒在他人之中,就會失掉自己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位置、失掉自己對世界所持的立場和“應分”的參與。“消極的移情,沉迷、淹沒自我”的被客體化狀態,是與我的“應分”的積極進取的主體精神相左的。兩個參與者因為移情而變成一個,就是一種“存在的貧困化”。[1]18-19
巴赫金的理論此時仍有非常明顯的認識論哲學美學傾向,對審美活動還沒有上升到存在論的理解層面。在認識論領域,自我主體當然斷不可能與外位于我的他人彼此重合,但在審美體驗中,卻可以虛擬、感悟式處于他人之位,摹想他人之思。況且,在審美的終極體驗中,我與他人、與世界是圓融為一的。不是客體化的被湮滅,而是共主體化的圓融為一。馬丁·布伯有一句話極好地闡述了這種終極體驗的存在狀態:盡管人具有唯一性,但當他進入生命的深層時,他就絕對找不出一個自身整全而且自身接近絕對的存在。人不是依賴與其自身的關系才變得整全,恰恰相反,整全需要依靠與另一個自我的關系。[3]231
寫作《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以后,巴赫金對“審美移情”觀有所改變,轉而認為“審美活動的第一個因素是移情:我應體驗(即看到并感知)他所體驗的東西,站到他的位置上,仿佛與他重合為一”。[1]121他還創造性地將審美移情說和他的外位性理論貫通起來,提出審美活動既應該把握移情因素(“我應該掌握這個人的具體的生活視野,就像他自己所體驗的一樣”),又不忘外位性的因素(“但在這一視野中沒有包括我從自己位置上能夠看到的許多東西”)。[1]122他從哲學美學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在我所體驗的他人內心存在中(通過他性范疇積極體驗的存在),存在和應分沒有分離,也不相互敵對,而是有機聯系在一起,同處于一個價值層面。他人在涵義中得到有機的成長”。[1]218因為這是一種美學層面的體驗,而非現實生活中的理性認識。但另一方面,我與他人也生活在現實里,同時進行著現實層面的體驗,所以“用我這個范疇不可能把我的外形作為包容我和完成我的一種價值來體驗;只有用他人這一范疇才能這樣來體驗。必須把自己納入他人這一范疇,才能看到自己是整個繪聲繪影的外部世界的一個成分”。[1]132
《論行為哲學》里提出的“存在即事件”命題,到《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里就進一步發展成“審美事件”的論述。他指出,當只有一個統一而又獨一無二的參與者時,不可能出現審美的事實,一個絕對的意識,沒有任何外位于自身的東西,是不可能加以審美化的。因為審美事件的實現,必須在諸主體之間才能逐步推進。任何人都不應也不能單憑自身做出評判。在此文中,他把審美移情中的“我他”關系區分為二,一是“我”與他人的關系,另一個是作者與主人公的關系。而作者與主人公的關系也可以區分為現實創作中的作者與主人公的關系,以及審美視野內的作者與主人公的關系。不再如同《論行為哲學》那樣籠統地談“我他”關系,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巴赫金在此關于“審美事件”的論述,實際上成為了他接下來所提出的“復調小說”理論的先聲,為他接下來進一步發展其主體間性美學思想做好了鋪墊。如,他在此文中提倡作者需要與文本中主人公彼此處于外位關系,作者應該超越自身之外,不是在通常的現實生活的層面上,而是在視主人公為他人的層面上進行自我體驗。[1]110-111作者作為積極的創造者應該處在他所創造的世界的邊緣上,因為一旦他闖入這一世界,就會破壞它的審美穩定性,因此藝術家的神奇之處就在于,他有著至高的外位性。[1]288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一書的片段》里,巴赫金還再次提及有關“事件”的命題。他在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柏拉圖時批評說“柏拉圖把思想不是作為事件(событие),而是作為存在來思考”,結果柏拉圖的對話雖然不是完全獨白化了的、教學式的對話,但其中聲音的紛雜歧異還是在思想中被消解了。[4]370人的本質,不能僅憑借自身獲得,而需要通過與他人的交往才能得到。人也必須將自己置入與他人的主體間性的交往關系中,才能深刻地返身思考自己的存在意義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巴赫金在其思想發展的中后期,越來越強調對話和交往,重視諸主體間的共在。他指出:“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個人意識之中,它如果僅僅停留在這里,就會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別的思想發生重要的對話關系之后,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發展、尋找和更新自己的語言表現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成為真正的思想,即成為思想觀點,必須是在同他人另一個思想的積極交往之中。”[4]114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思想發展的中后期對對話和交往越來越強調的同時,對單個主體自我獨一無二性的確立卻越來越淡化,有一種厚此薄彼的傾向。其實,思想是自我意識與開放交流的統一,是自我的自由自覺性與外位性的統一,而它既不是一種單純源于個人心靈的主觀精神產物,也不是單純依靠與他人的對話、交流就能產生的。
沒有交流,自我意識就會陷入自我封閉和僵化,于是思想難以向前發展,但如果沒有自由自覺的主體精神為基礎,對話和交流就難以達到引導自我發展的預期目的,“我”的思想就有可能成為他人思想的附庸。主體一詞來源于拉丁語“subjectum”,意為“基礎”“基質”,這也意味著主體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只有發揮自己的主體精神,以獨立思考為基礎來面對他人、面對世界,才能不迷失于彼此共在的思想叢林當中。存在即共在(со - бытие),是諸主體既相互對話,又互不溶合的共同存在,兩者辯證統一,缺一不可。單個主體的思想不可能自然而然的產生,而是需要一面借鑒他人,一面充實和確定自己的存在,在自我與他人的雙向敞開過程中一步步建構起來。
二、從外位性到主體間性理論
巴赫金在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時所提出的復調理論,在某個側面上看實際也可以理解為外位性立場與主體間性對話思想結合之后,在作者與主人公等關系上的延續。他提出,文本中的“人的形象”和現實的人的概念原則上是不同的,作者對待文本世界里的主人公,應當視之為另外一個主體,即,將之在文本中呈現為“人的形象”。因為文本中的“形象”在彰顯人物本身時,總是“不僅從內部(從‘自己眼中指物’)也從外部(從他人的角度也為著他人,最終是從作者的角度也為著作者),在自己的視野中也在他人統攝一切的視野中,最終是在作者的視野中”。[5]346于是形象就不是在某個單一視野中孤立構思出來的,而是在多重視野的交錯參照下形成的。作者雖然在現實領域內是主人公的創造者,但卻不能是全知全能的支配者,因為作者的立場應當是“外位的立場”。假若作者強行將自我從內部灌注入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中的話,那么主人公就只是與作者同質的傳聲筒、復制品而已,作者就無法外位于這種物化的客體,無法以“超視”來看待主人公。巴赫金對此的解釋是,“作者的超視中有對他人的珍愛、同情、憐憫以及其他純屬對人的反應,這些對純粹的物是不可能有的”。[5]346即,正如同只有在主體之間才能進行交流、對話一樣,也只有在主體之間才能樹立外位視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持的立場之所以是“全新的作者立場”,就在于他努力去發現和確立主人公身上的自我意識,即所謂“個性”或“人身上的人”。要想能夠從“人身上的人”這一主體化的角度來發現、理解主人公,就需要秉持主體對主體的特殊方法:“對話的方法”。只有當主人公不是物,不是無聲的客體,而是另一個主體,另一個平等的“我”,才能夠“自由地展現自己”。[5]345將主人公當作另一個“我”,才能使主人公在審美領域克服其客體性。主體性只能是主體間性的前奏和基石,而非其存在狀態。獨白型文本的思想和心態都被作者所壟斷著,該模式由于預設了思想前提,在討論的一開始就已經預設結論了,因此不能被視為對話。對話的共識是在彼此辯駁當中形成的,而非思想和話語的壟斷中完成的。只有在開放性的大型對話結構中,才會萌發新的思想和達成堅實的共識,而一個有著多重視點的多元世界方能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后來他在構思狂歡理論時,就發現騙子、傻瓜和小丑這三個對話性的范疇,在打破封閉性走向開放性時所具有的重要外位性因素。他們由于其所戴著的詼諧面具及其話語所具有的獨特性質,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時空體:“狂歡化的世界”。由此他們是作為不溶于、不妥協于其中的“外人”來審視現實世界的,現實的“真”卻不“美”甚至也不“善”的人生處境無法令其滿意,相反,他們在常人習以為常的世界里“看出了每一處境的反面和虛偽”。[6]355
在1959至1961年的筆記手稿《文本問題》里,巴赫金的復調、外位性理論都得到了更深的發展。在此時的論述里,包含著巴赫金力圖厘清具有對話性、外位性特征的“理解”與具有獨白性、封閉性的“解釋”之間的重要差別。同是面對作品,自然科學的觀念是視之為用以解釋、復制某種意識和聲音的客體,而人文科學則能夠視之為能以資外位于自我主體,并且反觀、反思自我主體的另外一個主體:“看到并理解作品的作者,就意味著看到并理解了他人的另一個意識及其世界,亦即另一個主體(‘du’——你)。在解釋的時候,只存在一個意識,一個主體;在理解的時候,則有兩個意識、兩個主體。對客體不可能有對話關系,所以解釋不含有對話因素。而理解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對話性的”。[5]314我們可以通過另一個主體的目光返視自身,卻不能通過冷冰冰的客體來回看自我。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巴赫金理論中的“解釋”這個概念,與伽達默爾理論中的“解釋”概念是不同的。巴赫金是在傳統解釋學意義上使用“解釋”這個概念,而非如伽達默爾那樣在現代解釋學意義上視“解釋”為生成性的概念。巴赫金的所謂“解釋”,即復制性的消極“曉諭”,只是力圖消極、被動地復現、描述作者的獨白原意,而所謂“理解”,則是讀者能夠外位于文本的獨白結構,以更加高遠、深刻的外位性視角來看待文本,及其與作者、讀者之間的積極關系。
巴赫金在其理論發展的后期,開始試圖突破自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中把獨白和對話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兩者在主體彼此言說中具有相對性,在主體間彼此理解的情境中,每一個表述因其都是來自某一個具體主體的表述,故而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獨白性,但由于對方應答因素的存在,每一個表述又需要受到其他表述的制約。“解釋”在主體間的對話中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理解”。
可見,“理解”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即便文本本身是獨白型而非復調型的,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也能夠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通過與文本對話而消解文本本身的獨白性。
“理解”是言說者與接受者之間溝通的橋梁,接受者不是純然無思的全盤接受,而是要以自身原有視野為底色來添加言說者的描繪,在這一過程中更新、重構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內容。同樣,言說者也并非純然去言說、傳遞一種絕對自我的獨白之思。恰恰相反,對話中的“理解”既包含指向他人的言說,又內在蘊含著對他人應答的期待。當獲得積極應答之后,言說者就會根據接受者的應答內容和思路來調整自己下一步的言說,進而又促使接受者的應答產生新的內容,獲得新的啟發。因此,理解的世界,是一種主體間性關系的世界,是包含著眾多豐富具體的個體世界的大世界。各個主體之間既不封閉于自我的世界,又不因過度敞開而自失于對方世界,而是相逢于“新的第三世界”,即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主體間的交際世界中。
三、結語
在《文本問題》中,巴赫金的對話和外位性理論有兩個重大拓展。首先是以闡述人文學科“理解”與自然學科“解釋”的不同為契機,躍出復調理論“作者與主人公關系”的框架,加入讀者的參與因素。他認為“任何真正創造性的文本,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個人自由的領悟,不受經驗之必然所決定的個人領悟。所以它(在自己的自由的內核中)不可能用因果關系來解釋,也不可能訴諸科學的預見。但這當然不是說文本的自由內核不具有內在的必然性、內在的邏輯(如果沒有這個,文本也不可能為人理解,被人承認,不可能有效能)”。[5]305-306
第二是對“文本”這一概念的意涵進行了延伸性的發揮,同時也使其主體間性美學思想由此及彼地得到了發展。他提出人的行為也是一種“潛在的文本”,需要置入其時代的對話語境才能真切理解。也就是說,他將“文本”所包涵的內容,從存在于小說、詩歌和散文等文學作品中的文本世界延伸到了由諸行為主體、諸文化構成的社會世界,將一切可以由諸主體相互對話交流,參與解讀的存在,統統視作一種文本。于是到了《答<新世界>編輯部問》中,巴赫金就順理成章地明確地將對話和外位性理論從文本上升到文化,完成了其第三次重大拓展。
[1](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M]//哲學美學.錢中文,主編.曉河,賈澤林,張杰,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美)凱特琳娜·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爾·巴赫金[M].語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3](德)布伯(Buber,M.).人與人[M].張健,韋海英,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 卷.[M]//詩學與訪談.錢中文,主編.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M]//文本,對話與人文.錢中文,主編.曉河,周啟超,潘月琴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小說理論.錢中文,主編.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