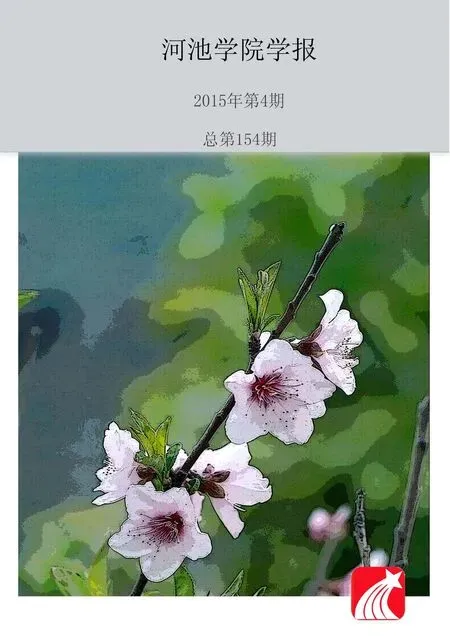論東西小說的文學思想
姚 蘭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引言
東西是當代廣西文壇上極具影響力的一位作家,對于他的作品讀者褒貶不一。褒揚者如評論家謝有順認為,“他的小說超越了現世、人倫的俗見,有著當代小說所少有的靈魂追問,是少數幾個形成了自己的敘事倫理的作家之一。”[1]批評者則多以晚生代作家的小說缺少必要的深度和厚度之類的說辭來以一概之。然而東西從不成熟的處女作《龍灘的孩子們》到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的《沒有語言的生活》,再到后來的長篇《耳光響亮》《后悔錄》一直都在探索小說是什么,文學是什么等問題。他不是在為寫小說而編織小說,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寫小說就是要挖掘人類靈魂深處的絕密文件,進而刺激人類日漸麻木的靈魂,擴大他們心靈的空間。”[2]所以盡管他的每一篇小說都各具特點,但他始終不忘通過挖掘人類內心深處的秘密,來寫一些觸及讀者心靈的東西。因此他還說了這么一句話,“只有把我們的秘密戳穿的作家,才會是真正的大師。”[3]簡言之,他的小說語言雖荒誕,故事雖簡單,但背后卻蘊藏著深邃的文學意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其文學思想的表達,他每一個精心勾勒的故事,每一句精心編排的話語都是其詮釋自己文學理念的一種方式。本文試圖通過揭露現實,剖析人心,探索心靈;主張想象,注重創新;推崇夸張,回到“漫畫”;張揚悲劇,救贖人性這四個方面對其小說思想進行闡述,旨在明確其小說思想的前提下,進一步挖掘其小說背后的深層意蘊。
一揭露現實,剖析人心,探索心靈
在政治、經濟、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慢慢地走向世俗,走向墮落。東西作為當代文壇的一枝新秀,自始至終本著文學的根本意義是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的方向前進,無論世事怎么變化,他始終堅守作為一個作家應有的品行。所以他的作品中沒有一味附和大眾的浪漫情節,更沒有為爭名逐利的媚俗故事。他的作品總是以揭露現實荒謬為先,旨在剖析人心,觸及人類心靈。就像他自己說的,“我筆下的愛情沒有那么多童話,都是一些現實的、病態的和性相關的愛情。而且還不僅僅是愛情,愛情在我的小說里就像一節拖車,它會拖出一些另外的東西。……這種做法就像是把那些正在做夢的的人叫醒,有時會讓你很不舒適。但是這是一種向前的姿勢,它和現代人的心理保持一致。”[3]33他還說,“浪漫只不過是我們的一種幻想,現實才是我們的終身伴侶。”[4]44而他的小說就是在試圖推開現實的重重阻礙,努力踐行了他的這一思想。
東西算不上一位高產的作家,然而他不多的作品里卻洋溢著豐富的思想內涵。他雖生于鄉間卻是心懷天下,所以他的每一個作品都在力爭揭露現實荒謬同時,又不忘剖析丑惡的人心,試圖通過人類靈魂深處的發現來編織一些觸及人類心靈的東西,從而喚起人們的知覺。《不要問我》講的是一位年輕教授衛國的故事,他因酒后吻了女學生而被迫辭職,又因在火車上丟失了證明自己身份的材料而在異地無法立足,最后卻因一份不需要材料證明身份的酒吧工作丟了性命。這個故事揭露了現實生活中身份大于自身的荒謬行跡,批判了我們當下這種只看材料,不重自身才干的社會現象;《我為什么沒有小蜜》顧名思義講的就是一個找小三的故事。在社會這個大染缸里,很多人都會和米金德一樣,很多時候并不是為了想出軌而找小蜜,就只是為了爭一口氣,為了所謂的面子和細小的虛榮心,去做一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所以最后的結果是小蜜沒有娶回家,原配卻丟了。作品無疑是對生活中人們變相證明自己的荒謬行為進行批判,是想通過對人物內心的剖析來警醒世人,從而使人們認清自己、認清社會。
當然,東西小說在揭露現實,剖析人心的同時,還希望通過人類靈魂“秘密地帶”的描寫,來提升作品的內涵,與讀者達成共鳴,從而探索人的心靈。他認為,誰的小說中都有人物,如果僅僅寫出一堆名字,而缺乏這一人物與我們心靈的重合,那這只是在對人物進行素描。在他看來,魯迅筆下的阿Q之所以經久不衰就是因為阿Q身上有我們每個人都與之重合的地方,看到阿Q我們會反思自己的行為,所以他主張筆下的人物要與我們的心靈重合。與前兩篇作品相比,《后悔錄》顯得更為深刻,作品通過主人公曾廣賢的故事,揭露了特殊時期曾廣賢平白無故坐了8年牢等諸多荒謬現實,塑造了一位與我們身心重合的人物。故事通過倒敘的手法來寫,一個從未有過性生活的人,竟因強奸罪坐了8年牢。事情真相大白后,他本可以擁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卻因自己延宕的性格親手將其斷送。當他步入中年后,他開始花錢請小姐聽他講自己充滿后悔的一生,后來又對著自己癱瘓了15年的父親講。這部小說的價值就像廣西著名評論家溫存超所評價的那樣:“長篇小說《后悔錄》更是一部不屈不撓地直問本心的作品,‘在歷史、政治與人物的錯綜關系中對中國人復雜的精神生活做了有力的分析和表現’,抓住人類共有的一種普遍心理現象,將‘后悔’無限地放大,‘在嚴峻的難度下推進精神敘事’,揭示‘世上沒有后悔藥’一說所包含的生活真諦與哲理,具有心靈地拓荒開墾的意義,讀來令人驚心動魄。”[5]122
二、主張想象、注重創新
在東西看來,小說的魔力就在于具有想象力。所以他說,“愈是有想象力的小說就愈具有魔力,所以我堅信小說肯定不是照搬生活,它必須有過人之處。”[4]54卡夫卡的《變形記》為什么能享譽海內外,他認為關鍵就在于卡夫卡勇敢的邁出了第一步——大膽想象。但是他在主張想象力的同時,就特別注重創新。因此他在寫作時便經常提醒自己,“要標新立異,要出人意料,要寫得與眾不同。”[4]50在文學史上,單獨寫聾子、瞎子、啞巴的文學作品多得不可勝數,而將三者組合起來寫,東西卻是第一人。這部由聾子、瞎子、啞巴組合而成的作品《沒有語言的生活》,讓我們發現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難,使我們開始關注正常人在生活中丟失的道德與品性。正是因為作品大膽的想象,別樣的創新,使東西在1996年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從此《沒有語言的生活》成了他的代表作。
《把嘴角掛在耳邊》是一部抒寫未來的作品,故事告訴我們,生活在未來社會里的人們,審美取向發生了變化,開始以裸露為時尚,失去了笑的本能,僅有久爺爺這個活了100多歲的老人還會這種表情。“笑”,一個小得幾乎讓人忽略的本能在東西的手里卻成了材料,大放光彩。這別具一格的構思不僅是主張大膽想象的表現,更重要的是,東西揭示了:生活中一些美好的東西正一點點流失,正統的、主流的道德、精神在現代商業理念的沖擊下已開始慢慢退出歷史舞臺這樣一個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東西主張的大膽想象并不等于虛構,注重的創新并不等于神游。在大膽的想象下,他始終不忘初心。生活中有比錢、比車、比房,甚至比媳婦、孩子的,就是沒有比賽痛苦的。《痛苦比賽》無疑是作者的創新,也給了我們眼前一亮的感覺,但是他這看似虛構的想象卻是為了揭示生活在畸形環境中的人們是怎樣的荒謬與可笑,從而透視我們的社會、生活、文化以及自我身份存在的問題。
三、推崇夸張、回到“漫畫”
東西在張鈞的“訪談錄”中說過,小說其實就是夸張。某個事件或是某個人物夸張到一定程度,就是漫畫的效果。那什么是漫畫?即“用簡單而夸張的手法來描繪生活或時事的圖畫。一般運用變形、比擬、象征的方法,構成幽默、詼諧的畫面,以取得諷刺或歌頌的效果。”[3]56所以在東西的作品中,我們會看到《耳光響亮》中牛青松一家通過舉手表決來判斷父親是否活著,以及楊春光為了讓牛紅梅打胎,精心設計了一場羽毛球賽及牛紅梅為流掉的孩子開追悼會等一系列極度夸張、詼諧的事件;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看到《伊拉克的炮彈》中,王長跑因為天天看電視里的美伊戰爭而瞎了眼睛,以及《商品》中,我和薇冬上車才認識,下車就有了孩子等夸張故事。可以這樣說,東西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由一個個夸張的故事拼貼而成,并最終回到“漫畫”上。但是“東西的這種所謂‘拼貼’,并非簡單的拼湊和機械的組裝,而是奇思妙想和深思熟慮的融合,是東西的小說觀在其小說創作中生長出來的奇花異果。”[5]125
通常情況下,漫畫更多的是用來譏諷時事而不是歌頌現實,所以東西利用漫畫式的寫作方式是用來諷刺時代的荒謬,而不是褒獎現實的美好。《耳光響亮》中一連串的夸張性事件既是東西對當下親情喪失的深思,是對牛紅梅悲慘人生的同情,也是對造成牛家悲劇社會現實的批判。東西極力推崇夸張,目的是要回到“漫畫”上。因為在他看來,真正的作品應該是像漫畫一樣具有針砭時弊的作用,而不是似素描簡單、無味,一味重復生活。
四、張揚悲劇、救贖人性
東西是一個具有悲劇意識的作家,所以在寫作時,他總不忘張揚悲劇的力量。但他并不是為簡單的塑造悲劇人物而寫悲劇,在悲劇的背后,他總是試圖去救贖那些被多種因素桎梏的人性。
作為一個悲劇的鼓吹者,他的悲劇意識主要源于他童年的生活環境。他說,“其實悲劇意識和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不通公路不通電,……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童年一睜開眼睛就沒有喜劇的舞臺,所以悲劇就深入骨髓無可救藥。”[4]29在他看來,只有悲劇才能揭露現實使人深省。在西方,古希臘時期就有了悲劇理論,認為它源自于酒神祭祀。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來表達,而不是采用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6]12卡塔西斯是一個宗教術語,有凈化之意,也有人把它譯為陶冶。在文學的領域里,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悲劇的地位都遠遠高于喜劇。新文化運動后,西方的悲劇理論傳入中國,即刻引起了一場關于中國是否有悲劇的論爭。筆者認為,不同的文化語境孕育不同的文化現象,中國不是沒有悲劇,而是中國把道德人倫看得比理性更為重要,所以這只不過是中國的悲劇不等同于西方的悲劇概念罷了,但這并不影響中國悲劇文學的高度。所以梁祝化蝶的愛情故事,竇娥沉冤得雪的情節安排不是因為中國缺少悲劇,而是因中國獨特的文化語境決定的。20世紀以來,不管是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新歷史主義小說、先鋒文學和新生代小說,都將悲劇看成是自己創作的主題。“晚生代作家的文學創作大多受到中西悲劇理論的影響,表現在作品里,就是他們對苦難的高度關注。”[7]5所以在東西的作品中,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父親》中,因為子女推脫責任,連父親已逝世多日都不知道的荒唐現象。當然,我們還能感受到《沒有語言的生活》中由聾子、瞎子、啞巴組成的殘缺家庭的苦楚,以及《目光愈拉愈長》中,劉井因丈夫懶惰須獨自照顧家庭,被丈夫燙傷沒錢看病,以及兒子最后因為鞋子再次離開她的痛苦。東西精心策劃的一個個悲劇不僅僅是為了通過人物來詮釋苦難,來揭示生活的艱辛,而是想救贖這些生活在苦難邊緣的人們。
《我們的父親》是親生子女親手造成的親情悲劇。東西想表達的不僅是呵斥那些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淡化親情的孩子們,更是想喚醒那些丟失親情的人們;《送我到仇人身邊》講的是張洪為了能有錢娶兵曉零為妻,把自己的好朋友趙構殺了,最后媳婦沒娶成,自己卻被槍斃了的故事。東西精心設計的這個悲劇也不僅僅是譴責張洪的非法行為,而是要人們看清楚當下為了錢財而不惜毒害好友的人隨處可見,我們要做的是喚醒他們的人性,屏蔽他們的獸性。
結語
綜上所述,東西的小說總是在努力踐行他的文學思想,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為什么寫小說,始終注意作品與讀者心靈的重合及對人性的啟迪。因為在他看來,魯迅、沈從文、福克納等大師之所以能打動讀者,就是因為他們荒草般的文字里,儲藏著人性,并常以此來俘獲我們的心靈。也正如評論家溫存超所言,“一個小說家的小說觀,實際上并非形成于一時一日,除了傳統小說觀與現代小說觀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來自于自己小說創作的切身體驗,其小說觀也會隨著其創作實踐的進行與體驗的不斷加深而不斷變化。”[5]125所以通過對東西小說的文學思想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的去理解東西的作品。
[1]謝有順.中國小說的敘事倫理:兼談東西的《后悔錄》[J].南方文壇,2005(4):34 -43.
[2]侯虹斌.東西:最厲害的寫作是寫出寬廣的內心[N].南方都市報,2006-4-10.
[3]東西.誰看透了我們[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
[4]東西.時代的孤兒[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2.
[5]溫存超.秘密地帶的解讀:東西小說論[M].北京:臺海出版社,2006.
[6]亞里斯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
[7]李志云.論東西小說的悲劇意識[D].山東:山東師范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