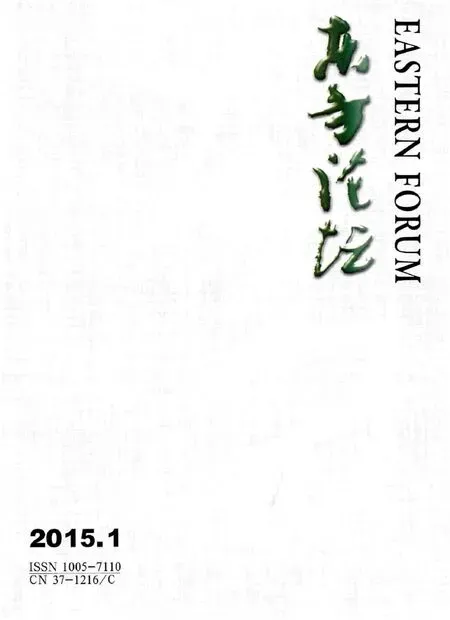創傷記憶與現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傷痕電影”
韓琛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創傷記憶與現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傷痕電影”
韓琛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在1979-1983年間,無論是關于電影語言現代化的理論爭論,還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傷痕電影”創作,抑或是學院時代的第五代導演的創傷敘事,都試圖通過重構創傷記憶來釋放被延遲的現代性渴望,當代中國電影則藉此而形成了新的現代想象與文化認同。“傷痕電影”是一個過渡時代的文化鏡像,其與同一時期出現的其他“傷痕文藝”一樣,與其說是對歷史的客觀追溯與還原,不如說是試圖在記憶歷史中遺忘歷史,進而與以發展進步為核心的現代化意識形態達成曖昧的妥協。
現代化;傷痕電影;創傷記憶;遺忘;意識形態
通過否定之前時代,“文革”成就了自己合法性敘事,而后革命中國的歷史合法性論述,也建立在否定“文革”的基礎上。新時期伊始,對處于歷史巨變中的中國電影界來說,立足于辭舊迎新的歷史批判,是需要首先完成的政治表達:“電影工作的當務之急有二:一是繼續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及其同伙的罪行,徹底肅清其流毒;二是總結過去電影工作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改進今后的工作。”[1]對“文革”的批判與否定,在1976-1979年間促成一批反“四人幫”電影的出現,《十月的風云》《藍色的海灣》《希望》《嚴峻的歷程》《失去記憶的人》《風雨里程》《并非一個人的故事》等“反映人民與‘四人幫’作斗爭的影片,在整個電影生產中占有一個很大的比重。”[2]在完成歷史批判與重建現代性項目的同時,主流意識形態也需要通過整合記憶的歷史書寫,來重構集體和個人的思想譜系,從而彌合“文革”造成的合法性危機。這就使得各種追溯歷史、控訴壓抑、感時傷懷的“傷痕文藝”風行一時,趁勢而起的“傷痕電影”,亦藉此而蔚為大觀,被不同世代的中國導演落實于電影創作實踐中,成為1979-1983年間最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之一。然而,彌合創傷、重塑記憶的歷史生產和文藝創造,并不能完全消除被延遲的現代化焦慮,當下還必須擁有事關未來世界的理論藍圖,才能真正確立其文化領導權。“現代化”因此成為此一時期的主流話語。中國電影也不例外,電影現代化作為一種歷史渴望,成為其理論探討的主要訴求,并與“傷痕電影”的創作實踐相伴而生。
一、現代性渴望與電影語言現代化
1979年,張暖忻和李陀發表《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一文。這篇文章暗示了新中國前30年電影的“非/反現代”的本質,顯示了十分激進的理論姿態。雖然作者認為論文“完全從電影藝術的表現形式這一方面著眼的”,[3]但是,對所謂現代化電影語言的推崇與重視,顯然使形式本身具有了優先于內容的本體論意味,電影語言的電影化、現代化,其實就是突出電影語言的自足性和本體性,以使之脫離意識形態的束縛。圍繞這這篇文章,電影創作和電影理論界展開了一系列討論。
關于電影語言現代化的討論不僅事關理論本身,而且更在于清算革命時代的基本電影認識,彌合“文革”給中國電影帶來的傷害。辯證理論問題是為正本清源、重構合法性。這場討論主要涉及到三個問題:一是關于電影的主題問題。其主要內容是關于人性的討論,其與此一時期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的議題是一致的,圍繞著人性的抽象性和具體性、普遍性和階級性展開的論爭,是對階級斗爭敘事的反撥。但是,討論僅僅停留在表征層面,而沒有深入到歷史潛意識的層面。二是是關于電影體制改革的問題。電影生產的政企分離是其主要內容,袁小平認為“影片是商品,制片廠是企業”,[4]因此必須遵循價值規律和市場關系,一個市場化的文化生產體系初見端倪。三是關于電影本體論的問題。這是一個核心議題,因為所謂電影語言的現代化,即是重構“電影是什么”的問題,前述兩個問題必須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建立“現代”的電影話語體系并不僅僅意味著技術革新,它同樣表明了知識精英對于現代的新認識,進步和發展的現代觀念從民族主義角度得到了知識精英的認同:我們“只想從一個角度做一點探索,這就是如何使我國電影跟上世界電影藝術的發展,實現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問題”。[3]電影的現代化是整個國家現代性想象的一部分,知識話語的現代性建構是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表意機制重建的關鍵環節。即便在今天看來,關于電影本體論的爭論是極為尖銳的,因為這涉及到了根本的認識論的問題,并與整個社會的歷史轉向聯系在一起。
首先是電影與戲劇的關系問題。以白景晟,張暖忻、李陀,鐘惦棐,陸建華,青竺,何仁為代表的一方主張“丟掉戲劇的拐杖”[5],“電影和戲劇離婚”[6],通過對于影戲傳統的摒棄與否認,進而強調電影的本體論地位,“在銀幕上以電影表現生活的逼真性代替戲劇反映生活的假定性,這才是將銀幕從舞臺框里解放出來的坦途。”[7]而以邵牧君,張駿祥,余倩等為代表的另外一方則主張:“只要電影還是一種敘事藝術,而且還是一種需要演員的敘事藝術,那么,戲劇矛盾和戲劇情節,就不但不是違反它的本性,而恰恰相反,卻正是它的本性所要求的。”[8]辯論雙方都沒有否認電影的戲劇性因素,只不過持激進立場的一派致力于“純電影”的理論建構,是一種現代主義電影觀的表述,而反對一方則堅持革命現實主義的電影觀,并指責激進派的非戲劇化主張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原則格格不入的……從而不自覺地向現代派的非戲劇化靠攏,這可是一條十分危險的錯誤道路”[9]。最終,爭論雙方陷入了意識形態對峙之中,并沒有從藝術本體性的角度思考戲劇與電影的異同。不過,邵牧君認為“電影語言現代化”就是現代派的判斷十分準確,其實踐者便是數年之后出現的第五代導演。
其次是電影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張駿祥在1980年的一個會議上提出“電影就是文學——用電影手段完成的文學”[10],引發了有關電影與文學、電影性與文學性的關系討論。王愿堅,舒曉明、文倫,陳荒煤,艾明之、李天濟、孟森輝,王煉,葉丹,汪流等人認為:“文學性是電影藝術從娘胎里帶來的一種屬性。或者可以說,電影,就是看得見的文學”。不過張衛,鐘惦棐則堅持“電影既然作為一門獨立藝術,也就必然有獨立的表現思想、創造典型的功能,有觀察、提煉、表現生活的直接性,不需要其他的藝術做它的中介和橋梁”[11]。余倩試圖調和二者之間的關系,認為電影和文學是這樣矛盾,又是這樣統一。電影和文學的矛盾統一,也可以說是電影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征[12]。圍繞電影性與文學性爭論其實就是關于電影的領導權的爭奪。在80年代初期的中國電影界,主導電影話語權的主要是文學界人士,堅持電影的文學本質其實就是堅持文學對于電影的領導。而另一方則通過對于電影性的強調或者與文學的對比,突出并分離出電影的本體性特征,“電影形象本質上未必低于出自筆端的形象,甚至完全可能勝過它,是一個新的美學實體”[13](P127)。
無論是探討電影與戲劇還是電影與文學的關系,其目的最終還是關于電影本體論的分歧,于是就出現了關于電影本體論問題的討論。在這個問題上主要是“純電影”和作為綜合藝術的“電影”之爭。邵牧君,張駿祥,李少白,張柔桑,鄭雪萊,孟森輝,于敏各自發表了不同的看法,但出發點皆是針對《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一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表明了一種影像本體論的電影觀,其基本訴求在于確立“作者電影”的觀念。雖然邵牧君在《現代化與現代派》中批判了前者的現代派傾向,但他本人在1980年發表了《略論西方電影中的現代主義》一文,批判性的論述亦隱含著別樣的意義。到1983年,隨著第五代電影的出現,有關電影語言現代化的討論告一段落,鄭雪萊在《現代電影觀念探討》中梳理現代電影的概念及歷史,將現代電影看作是一個歷史性概念,是一個生發于傳統的電影模式但又與之斷裂的前驅的電影觀,而中國電影的現代化突破則“表明我國電影正努力趕上當代世界電影藝術的發展趨勢”[14]。“電影語言現代化”最終被具體“落實”于現實的電影實踐中。
有關現代電影的討論意義重大,其一方面顯示了中國電影源于擔心自身被排除于現代化進程之外的創傷體驗,另一方面則表征了意識形態領域關于如何定義“現代”的分歧。所謂現代,意味著持續地斷裂、分離,而現代化與其說是追逐未來,不如說是不停地告別過去。實際上,這個現代意識已經充分體現在了此一時期的中國電影中,《沙鷗》《小花》《小街》等電影在探索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同時,又試圖完成一種斷裂式的歷史敘事,“傷痕電影”于是成為中國電影銀幕上的主流,后革命中國籍此完成了對于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的鏡像重塑。
二、重塑記憶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傷痕電影”
從1979年到1983年,各大電影廠每年生產的劇情片從65部增加到127部。 《啊,搖籃》 《小花》《天云山傳奇》《巴山夜雨》《沙鷗》《小街》《城南舊事》《逆光》等影片是這一時期比較出色的作品。影片體現了比較強烈的時代性和寫實性,與1930年代的左翼電影具有一定的承繼關系,還可能受到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張暖忻和李陀談及的現代電影語言,即指巴贊的現實主義電影理論,巴贊認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是在“拯救著一種革命人道主義”[13](P270),同樣也可以作為對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電影的評價。不過,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強烈的現實批判意識不同,此一時期的中國電影卻致力于重塑歷史,電影中真實的“現實”其實是關于集體記憶的虛構性重構。就像1979年發表的沙葉新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一樣,亦真亦幻的“傷痕電影”所塑造的創傷記憶,不過顯示了一種急于告別過去的倉皇,在記憶與失憶的交織中,將個體的現代想象與國家的現代化項目統籌在一起。
“絕大部分改編自‘傷痕’文學的電影都是在1983年以前攝制的,它們的焦點主要集中于愛情關系的破裂以及忠誠于國家的個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非法迫害而帶來的失望情緒。”[15]這一時期的“傷痕電影”主要有:《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 《淚痕》 《如意》 《元帥之死》 《苦難的心》《第十二個彈孔》《巴山夜雨》《帶手銬的旅客》《天云山傳奇》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 《楓》 《丹心譜》《于無聲處》等。這些電影通過構造“文革”時期的創傷記憶,表達了人道主義的立場和對于“人類生存狀態的熱烈關注”[16](P39),并從社會、文化和歷史的角度對于革命歷史進行反思。在一些“傷痕電影”獲得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認可的同時,另外一些“傷痕電影”以及電影劇本卻受到了批判,如《太陽和人》,《女賊》,《假如我是真的》,《在社會檔案里》 等。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之后,“傷痕電影”基本上退出了中國大陸銀幕。在1980年前后,雖然精英知識者與國家權力在中國現代性問題上可以達成基本共識,但是知識者和主流政治則是帶著不同歷史性和價值觀來定位他們在現代性項目中位置和關系,不同政治群體對社會信仰主題的話語建構必然產生分歧,精英知識者在集體信仰話語建構過程中往往隱含了對這些話語的批判,而國家權力則通過政治懲戒、意識形態詢喚,介入了對于“文革”記憶的塑造過程。“傷痕電影”的榮與衰,除了電影主題本身的局限外,主流政治對“文革題材”的限制也是它不能為繼的重要原因。在對電影《太陽和人》的批判中,當時的廣電局局長就認為劇本:
……沒有反映出‘四人幫’橫行前,黨對于知識分子總還是重視的……許多知識分子是受到重用,也發揮了他們的為祖國服務的才能。這個分鏡頭劇本在結尾,寫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尋找他的人們發現他時,他已經是在一個大問號的那一個點兒上冷卻了身體,他用兩手盡量向天空伸去,兩眼睜著……這樣表現是不好的……”
“這個劇本大寫雁在天空寫成人字,從開頭貫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結尾是‘一枝蘆葦在風中晃動著,堅強地挺立著……’這種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現的,更加深了對死的渲染,這種手法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17]
隨后的批判則被上升為“違反四項基本原則”[18]的政治高度,并釀成了一場涉及文化界以及中共內部分歧的“苦戀風波”。實際上,就《太陽和人》這部電影本身來說,其社會批判和歷史反思主要基于一種古典的人道主義,并沒有帶來超越性的精神反思與歷史批判。這其實也是所有“傷痕電影”的共同缺陷,記憶編織與精神重建局限在狹窄的領域內進行,創傷記憶被歸罪于一些偶然性事件——“反右”或“文革”,以及個別性群體——“林彪”或“四人幫”。當然,“傷痕電影”作為新時期電影發展過程中的起始一環,為電影領域的現代化奠定了生發的基點。可以說,新時期電影的現代想象是建立在遺忘基礎上的,只有一個“失去記憶的人”,才能充滿激情地生活在關于未來的期待中。
毫無疑問,“傷痕電影”創作中最突出的導演是謝晉。他的電影《天云山傳奇》《牧馬人》和《芙蓉鎮》,其實構成了1980年代中前期關于“文革”歷史敘事的代表性文本。謝晉電影的幾個特點,如“無深度的反思”,“溫婉的人道主義”,“歌德的主流形象”,“苦盡甘來、因果報應的傳統敘事”,“中庸的政治傾向”等等,被認為是“化解社會沖突的奇異的神話”。[19]非獨謝晉,此一時期的“傷痕電影”都可以看作是通過重新塑造“文革記憶”而獲得自我救贖和社會救贖的神話,而通過記憶重塑的意識形態編織,社會政治主題和社會話語主體得以重新確立。
“傷痕電影”的記憶編織中也隱含著質疑。在電影《小街》的結尾,創作人員設置了三個各不相同的結局,結局的不確定性使電影生發別樣的意味,表達了作者對自己所編織的敘事的懷疑,顯示了一個時代在遺忘與銘記的間徘徊的惶惑。雖然限制很多,但并未妨礙創新的出現。特別是第四代電影人,其視聽語言具有了一種特別的詩意,雖然不及之后的第五代那樣狂飚突進,但也代表了中國電影發展的別樣路徑。在1979-1983年的電影生態中,第四代即是那先鋒的一環,他們“登場于新時期大幕將啟的時代,他們的藝術是掙脫時代紛繁而痛楚的現實/政治,朝向電影藝術的純正、朝向藝術永恒的夢幻母題的一次‘突圍’”[20]。
三、第四代導演的感傷主義美學
在中國電影的“代際論”中,第四代是指成長于新中國,在1979年前后開始獨立電影創作的一些電影主創人員,以吳貽弓、謝飛、楊延晉、黃蜀芹、吳天明、鄭洞天、滕文驥、黃健中、張暖忻等為主要代表。這一代電影人是共和國一代,在1950-1960年代社會氛圍中奠定了個人的價值觀和藝術觀,其藝術創作往往因為個體意識與主流意識的同構性而缺乏先鋒精神。在1979-1983年間,第四代電影人是主要的創新群體,其理論和實踐往往處于同步的狀態。張暖忻在《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中所推崇的巴贊的“紀實美學”和“長鏡頭”,幾乎是所有第四代電影人共同的電影美學主張,當然也不乏對于西方現代主義電影手法的借鑒。《沙鷗》,《小花》,《苦惱人的笑》《小街》,《生活的顫音》,《鄰居》,《城南舊事》等,是第四代導演在此一時期代表性作品。這些電影的人道訴求和感傷美學,成就了這個階段中國電影的最高藝術成就,鄭洞天將這個成就總結為“人的解放和電影的解放”[21]。
人的解放不僅涉及電影主題,也是第四代的自我期許,他們總是強調個人在電影創作過程的主動性。張暖忻認為電影應當“成為一種創作者個人氣質的流露和情感的抒發”[22]。滕文驥“強調創作者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主觀對于客觀世界的反映”[23]。黃健中則表示導演應當成為“自己‘畫面的上帝’”[24]。強烈的個人意識使第四代的影像表現出了一種比較獨特的個人風格。此一階段的電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風格趨向和藝術創新:一是對絕對紀實的“現實主義”風格的追求,鄭洞天、徐谷明導演的《鄰居》是“紀實美學”的代表性作品,電影“在美工、道具上刻意求真。不用插曲,不采用無聲源音樂”,“把攝影機作為觀眾的眼睛,去觀察現實生活,捕捉真實而生動的現實生活,這本身就是一種探索,也能夠構成獨特的風格”[25]。《鄰居》真正實踐了巴贊的“紀實美學”。二是在電影敘事上采用了“時空交錯式”的意識流結構,通過運用閃回等藝術手段突破時空的限制,使心理時間的邏輯代替了客觀的時間流程,造成了電影敘事結構的解放。1979年的《小花》《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等都使用了這種“時空交錯”的敘事結構。在《沙鷗》和《小街》中,一種注重心理時空轉換的“復合時空”得到了表現,主創人員將這種電影手法看作是“現代電影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使電影語言不再停留在對事物(時間、環境)的客觀敘述上,而是力圖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展示人在特定環境中的心理狀態”[26]。三是注重了電影造型的個性化。張暖忻認為“現代電影語言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努力探索新的電影造型手段。”[3]《沙鷗》《小街》等都試圖通過環境造型,光影、色調、視聽手段的綜合運用獲得獨特的電影氛圍。《沙鷗》里“圓明園獨白”的鏡頭段落以及《小街》里對于“小街”場景的主觀性營造,是第四代導演在造型藝術上突破的典范。雖然寫實主義的追求使這種造型缺乏如第五代電影一樣的視覺沖擊力,但是卻更符合中國傳統的時空經驗和審美趣味,從而具有一種傳統的詩意。
寫意和抒情本就是中國傳統美學的基本特征,而“意境”的營造則是電影民族化的出路。[27]在1979-1983年的電影創作中,吳貽弓導演的《巴山夜雨》《城南舊事》就是電影民族化的代表,堪稱為具有民族美學精髓的“散文電影”或者“詩電影”。電影“以精巧的藝術構思把我國二十年代社會生活的一個側影表現的意境深邃、富于韻味,具有和諧的美,在探索電影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的美學傳統方面,獲得了可喜的成果”[28]。整部電影中所彌漫的那種“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詩意氣氛正是“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傳統感傷美學風格的體現,化繁為簡的白描手法寥寥幾筆便將人生的況味、懷鄉的哀愁盡皆道出,是所謂“黯然銷魂,唯別而已,清夢如風,鄉音漸遠”。《城南舊事》應該代表了此一時期中國電影的最高成就,就中國電影史來說,它繼承的是《小城之春》所創造的感傷詩意的美學風格。《城南舊事》是吳貽弓的代表作,他并沒有再創作出一部可與《城南舊事》相媲美的電影,而民族化的電影美學探索在大陸似乎也就終至于《城南舊事》。但與此同時,在海峽另一側出現的“臺灣新電影”,則出現了諸多電影美學中國化的典范性作品,特別是侯孝賢的電影《風柜來的人》 《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等等,真正體現了一種典型的傳統美學意蘊。如果將兩岸的電影史看作一個整體的話,“臺灣新電影”或者才是中國民族電影的真正高峰。
如果不是第五代的出現,那么第四代的感傷美學的電影探索將會繼續下去。不過,第五代橫空出世,讓一切因此而改變。第四代導演似乎很快就放棄了他們的寫實主義電影旅程,而更多了表現主義的形式感。在第五代導演中間,田壯壯是最接近第四代電影風格的導演,其作品風格內斂低調,氣度淡泊從容,奠定了田壯壯導演獨特的先鋒性。第四代導演營造的感傷美學風格在1990年代電影中或有所見,賈樟柯的《站臺》,顧長衛的《孔雀》以及王小帥的《青紅》還有個中滋味一二。在第四代導演成為這個時段的電影現代化的前驅時,第五代導演正在北京電影學院完成他們的學業,張暖忻、鄭洞天等第四代電影人作為導師,影響了他們最初的創作,使他們學院時代的作品,呈現出別樣的風格特征。
四、 創傷記憶與學院期的第五代
談及第五代電影,人們通常會認為其發端是1980年代初期《一個和八個》和《黃土地》。實際上,在這兩部標志性的作品出現之前,第五代電影人已經獨立或者合作創作了幾部電影。這些作品既包括在校學習期間的實習作業,也包括畢業之后的幾部電影實踐,這幾部電影主要以田壯壯為創作中心。與一般所公認的第五代風格并不相同,這些電影更多記錄意味與寫實精神,是以田壯壯為代表的另一種第五代風格的顯示。這些作品主要包括:田壯壯、謝小晶、崔小芹導演的電視短片《我們的角落》,田壯壯、謝小晶、崔小芹導演短片《小院》,潘淵亮、潘華、白宏導演的短片《目標》,田壯壯、謝小晶、張建亞導演的兒童故事片《紅象》。除了《紅象》,其余的短片都是他們在北京電影學院期間的實習作品。
之所以將這些實習作品作為第五代“前史”加以論述,是因為這些電影短片在題材選擇,畫面處理等方面,雖然已經具備了第五代后來的一些影像特征,但是也具有與其后來的總體風格不同的地方。其中,最為令人矚目的是這些電影對于歷史創傷重構,因為其涉及到的是這個“電影世代”真實的歷史經驗和創傷體驗,這與他們日后從個人經驗之外組織民族寓言的手法區別極大。這幾部影片一方面與那個時期社會整體的歷史反思氛圍的相契合;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第五代電影在這個整體性的記憶塑造過程中的另類思考。另外,這些電影也是解讀第五代導演的歷史基點,因為電影的主要人物多是第五代的同齡人,表達的幾乎就是他們自己在歷史和現實中的錯位與無奈。應當注意的是,從未在這些電影中出場的“文革”,其實是隱而未發的歷史背景與創傷之源,因為作為“共和國之子”的這一代人,在“后文革”文化場域中,被指認為處在“沒有太陽的角落”里的“殘疾人”。
第五代的最早作品不是《一個和八個》,而是《我們的角落》。其是根據史鐵生的短篇小說《沒有太陽的角落》改編的電視短片。這個短片有意識地嘗試了紀實風格,質樸、沉蘊的影像構成了田壯壯后來電影的美學雛形,原生態的生活和情感是他最感興趣的電影內容。《我們的角落》有三個特點令人矚目。第一、紀實風格。演員全部都是沒有經過訓練的業余演員,保持了生命的原初狀態,而充滿自抑趨向的鏡頭,則顯示了對于生活和人的尊重,整部電影“極力追求紀錄片的客觀態度,片子拍得哀而不傷、恬淡節制”[29](P126)。第二、庶民立場。普通市民是電影主要表現對象,與第五代后來的電影主題截然不同,對現實的關注似乎更多的與第四代電影相契合,鄭洞天在同一時期拍攝的電影《鄰居》具有類似傾向。第三、傷痕書寫。電影是對于“共和國一代”的內在化的創傷記憶的顯影,在1980年,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創作者沒有將主人公的身體殘疾和精神壓抑進行簡單解釋,而是從個人存在層面揭示了人生殘疾的本源性,人生荒誕的存在仿佛是太陽永遠不能照進的角落,短暫的溫暖和光明不過襯托出了永恒的缺失,人永無超越的可能,而只有沉淪的宿命。主人公的身體殘疾隱喻了一代人的精神創傷,現實中國并不能提供治療的途徑,個體只有在晦暗的生命耗盡之后才能獲得解脫。
第五代導演的畢業短片《小院》《目標》等,則延續了《我們的角落》的立意和風格。這兩部作品分別改編自王安憶的小說《小院瑣記》和《本次列車終點》,都是反映了個體在社會現代化、世俗化的過程中的困惑、無奈和不安。《小院》依然是以田壯壯為中心創作的電影,電影反映的人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掙扎,其實就是烏托邦幻滅后的一代人的生活寫真。雖然電影給出了一個光明的結尾,女主人公桑桑通過和丈夫一起通過對于往昔生活的回憶而達成和解,美好的未來在理想主義的光芒中熠熠閃光,但是,對于“創傷記憶”的美學修正卻正暴露了這一代人不能忘卻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精神,第五代雖然崛起于后革命時代,但他們終究還是“革命之子”,并宿命般地留有革命的烏托邦烙印。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精神取向在田壯壯后來的電影《獵場扎撒》《盜馬賊》,甚至《茶馬古道——德拉姆》都有體現。
短片《目標》的立意則更為明顯,返城知青不能適應城市生活,只好在回憶中獲得精神安慰。影片在現實與過去的交叉敘事中描述著個人精神困惑,“知青世代”在返城后發現自己成為一個“多余的人”,被流放的知青生涯成為他們獲得現實精神支撐的唯一來源,革命時代的“創傷記憶”成為個體的精神家園。通過這幾部短片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文革經歷”和“知青生涯”是他們電影創作最重要的精神來源,經歷“革命——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一代在世俗化的世界中,依然追尋著一個理想主義的精神家園。然而,這個革命家園——“精神之父”曾經許諾的烏托邦——已經幻滅,“后文革”時代的個體不得不告別革命夢幻,重返世俗世界。但是革命時代的成長經歷、理想主義的歷史抱負,使他們力圖賦予世俗化的現代性追求以烏托邦主義色彩。《目標》等電影對于精神生活、藝術人生以及知識價值的推重,將世俗化的現代化趨向轉換成告別傳統中國和前現代社會的理想主義景觀,其與1980年代中國自我想象相得益彰——這是一個世俗現代化過程中的烏托邦階段,其以一種吊詭的理想主義姿態迎接著一個即將到來的消費主義時代。
在1983年拍攝的《九月》中,田壯壯延續了之前的藝術追求,藝術烏托邦和人性理想國代替了革命烏托邦的拯救功能,人生在象征苦難的《小白菜》的吟唱中獲得升華,“創傷記憶”成為個體獲得存在感的唯一體驗。以田壯壯為代表的第五代早期電影“已經形成了一條貫穿始終的探索道路,這條線索的發源處,本來是第五代電影之河最早的起點。但是,《一個和八個》這條水勢洶涌的支流,突如其來,勢不可擋,改變了原來主流的河道和流向。”[29](P127)實際上,《一個和八個》并沒有改變這個時代的電影主流,這部電影所展示的表現主義風格是對略顯陰柔、感傷的最初源流的補充,而對于“創傷記憶”的影像塑造,則從一個具象、現實和個體意識的層面深入到抽象、歷史和集體無意識的層面。
結語
在1979-1983年間,無論是關于電影語言現代化的爭論,還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傷痕電影”創作,抑或學院時代的第五代導演的創傷敘事,都反映出對于現代化未來的無限期冀,以及對于過去創傷經驗的記憶編織,當代中國電影藉此而獲得了新的現代性認同。與那些在創傷記憶中營造樂觀未來的“傷痕電影”不同,作為第五代最早的電影《我們的角落》,或者才真正將歷史創傷在新時期的無奈延續給充分表達出來。電影中的殘疾主人公既是“知青一代”的自我想象,也象征了被這個致力于“遺忘”的時代所有意忽略的“沉默多數”,現代化的陽光并不能照進他們生存的角落,即便照入,也是不知所往的“殘夢”,而非浴火重生的“新篇”。這個詭異的現代化狀況及其后果,在1990年代出現第六代電影中有著更多批判性再現,而1980年代第五代更鐘情于一個“現代化神話”的塑造。即便存在著各樣異議之聲,1980年代中國還是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新的現代化進程中,包括“傷痕電影”在內的各種“傷痕文藝”的大量出現,與其說是對于過往革命歷史的追溯、控訴與批判,不如說其更傾向于在“歷史記憶中遺忘歷史”,并試圖與新意識形態達成曖昧的妥協。作為過渡時代之文化鏡像的1980年代“傷痕電影”,尚未將創傷記憶完全曝光就潦草終結,成為一個新電影時代拉開帷幕前的無關緊要的注腳。
[1] 夏衍.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祝《電影藝術》復刊并從中國電影的過去展望未來[J].電影藝術,1979,(1).
[2] 藝軍.揭示心靈的戰斗歷程——反映與“四人幫”斗爭的電影創作的一個問題[J].電影藝術,1979,(1).
[3] 張暖忻,李陀.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J].電影藝術,1979,(3).
[4] 袁小平.關于改革電影事業管理體制的我見[J].電影藝術,1980,(12).
[5] 白景晟.丟掉戲劇的拐杖[J].電影藝術參考資料,1979,(1).
[6] 鐘惦斐.電影和戲劇離婚[J].電影通訊,1980,(10).
[7] 青竺.也談電影與戲劇的“離婚”[J].電影創作,1980,(11).
[8] 余倩.電影應當反映社會矛盾——關于戲劇沖突與電影語言[J].電影藝術,1980,(12).
[9] 邵牧君.現代化與現代派[J].電影藝術,1979,(5).
[10] 張駿祥.用電影手段完成的文學(根據國慶三十周年獻禮片第二次導演總結會上的發言整理)[J].電影通訊,1980,(11).
[11] 張衛.電影的“文學價值”的質疑[J].電影文學,1982,(6).
[12] 余倩.電影的文學性和文學的電影性[J].電影新作,1983,(2).
[13] [法]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14] 鄭雪萊.現代電影觀念探討[J].電影藝術,1983,(10).
[15] [美]威廉·呂爾.中國大陸電影:1949~1985[J].楊彬譯.當代電影,1987,(8).
[16] 梅朵.歷史與現狀[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
[17] 徐慶全:《苦戀》風波前后[J].南方文壇,2005,(5).
[18] 本報特約評論員.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N].解放軍報,1981-04-20.
[19] 朱大可.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N].文匯報,1986-07-18.
[20] 戴錦華.霧中風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1] 鄭洞天.僅僅七年——1979~1986中青年導演探索回顧[J].當代電影,1987,(1).
[22] 張暖忻.我們怎樣拍沙鷗[J].電影通訊,1981,(8).
[23] 滕文驥.嘗試和探索[J].大眾電影,1981,(8).
[24] 黃健中.人·美學·電影[J].文藝研究,1983,(3).
[25] 張明堂.群星燦爛又一春——中國電影金雞獎第二屆評選活動側記[J].電影藝術,1982,(2).
[26] 吳天忍.環境節奏時空——由影片《小街》所想到的[J].電影藝術,1982,(8).
[27] 藝軍.電影的民族風格初探[J].電影藝術,1981,(11),(12).
[28] 中國電影金雞獎第三屆評選委員會對各獲獎項目的評語[J].電影藝術,1983,(5).
[29] 倪震.北京電影學院故事:第五代電影前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馮濟平
Traumatic Memory and Modern Imagination: Revaluing the Scar Films of the 1980s
HAN Che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Between 1979 and 1983, all the theoretic disputes about modernizing film language, all the work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s' films telling the trauma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s' traumatic narratives,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 traumatic narratives to release the delayed desire for modernity. From then on, the new modern im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s. As a mirror of the transitional era, the scar films or others arts telling about trauma, was a recall or reduction of history rather than an action to forget it, then reached a compromise with the modernist ideology whose core i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scar film; traumatic memory; forgetting; ideology
J951.1
A
1005-7110(2015)01-0049-07
2014-10-26
韓琛(1973-),男,山東黃縣人,青島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與華語電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