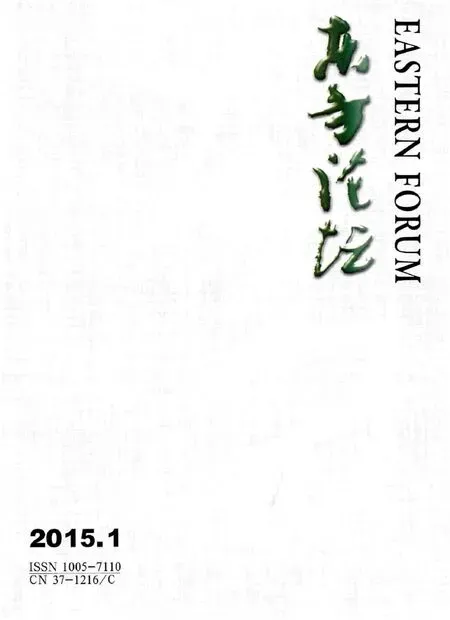荷蘭庚款“退款”與民國水利科研機構創設
李碩
(上海電機學院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40)
荷蘭庚款“退款”與民國水利科研機構創設
李碩
(上海電機學院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40)
庚款“退款”各涉案國情況不同。過去研究多集中在美、英,而且多舉清華學堂、粵漢鐵路為例說事。荷蘭庚款“退款”情況雖說與美、英類似,卻因“占比極微”“業績平平”而很少為學界所關注,研究更是幾近空白。基于此,借助現有豐富的中英文史料,把荷蘭庚款“退款”放到庚款案的整體中進行考察,并對荷蘭“退款”管理和利用情況進行具體探討就顯得很有必要,這不僅有助于豐富和擴展對庚款“退款”問題的研究,也可使學界對該論題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荷蘭;“退還庚子賠款”;檔案;翻譯;水利科研機構;創設
一、荷蘭庚款“退款”的背景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1年9月7日,清廷全權代表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個當事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個“受害國”的“損失”共4億5千萬海關兩白銀(本息合計達9億8千萬兩)。其中俄國所獲最多,其次為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美國、意大利等。荷蘭列第10位,不計息賠款78.21萬兩,占比0.17%[1](P27)。
1904年中國政府和民間組織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退款”交涉,筆者所見在美國第一次“退款”之后,中國最先由外交部向英國(1917年)、法國和意大利(1919年)提請“退款”;1921年教育部商請有關各國仿效美國將庚款的一半用于中國教育事業,并以Powers Asked to Relinquish Half of Boxer Indemnity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為題,在4月9日《英語周刊》的English Weekly Supplement中做了報道。是年8月中國政府派專使向國聯提出“退款”。1922年3月教育部設立“籌辦退款興學委員會”,《英文雜志(月刊)》第5期以Commission for Disposal of Returned Boxer Indemnity Organized為題對外宣示。同年5月財政部、稅務處、司法部先后提出要求各國豁免賠款。該月國務會議決定,交涉庚款“退款”統一由外交部辦理。隨即外交部電令有關駐外使館向駐在國提出交涉,標志著 “退還”庚款的對外交涉全面啟動[1](P337)。
各國“退還庚款”的情況不同,至少可分為6類。(1)德、奧,1917年因“一戰”時敵對而停付賠款;(2) 俄國,因1917年“十月革命”放棄賠款,以上3國少付占“退款”總數的一半,用在了政府行政開支;(3)美英荷,“退款”占比18%,用途為文化教育和實業;(4)法意比,“退款”占比19%,由于從紙法郎改為用金法郎支付而實際“退款”縮水;(5)日本,“退款”占比7%,由自己操縱使用,中國政府未予承認;(6)西、葡、挪和瑞典四國則沒有退款[1](P561)。“退款”使用本屬中國內政,某些國家卻順勢提出非分要求,有的純屬乘機挪用、勒索。后來有學者主張對此在統計中應予扣除。這種狀況直到抗日戰爭爆發6年后的1943年,中外許多條約中申明廢除《辛條約》,才得以改變[2](P83)。為此史學界常常在感嘆“弱國無外交”之余,說起交涉成效必舉英美,并以清華學堂、粵漢鐵路,以及中美、中英高層次人才培養等為例說事,卻很少有人關注荷蘭的庚款“退款”,理由是“真正退回者除俄國外,只有美英荷三國,荷蘭所占比例極微,無足輕重”[1](P563);或說退款使用的“業績平平”[2](P68)。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二、使用荷蘭“退款” 的水利項目
1925年10月作為荷蘭對“退款”的正式反應,是荷蘭照會中國愿將庚款余額作治理黃河用,由荷蘭工程師協助。但項目并未最后議定。此后,1928年9月華北水利委員會成立,早年留學德國但澤(Danzig)工業大學專修水利的前輩李儀祉倡導成立研究所開展水工模型試驗,聘任荷蘭工程師方維因為該會顧問,并爭取用荷蘭“退還”的庚子賠款進行此項工作,擬定8萬元預算,未獲批準。1929年后又有歐陽彥謨、汪胡楨、沙玉清等多人提議成立中央水工試驗所,1930年6月又有人提議用該款開辟東北兩大港口,亦未能實現。有的認為水利需款多,需要多國合辦。1933年楊汝梅在《軍需雜志》上著文說;“荷蘭大使自動向我國政府表示愿將賠款余額作為治理黃河之用,曾經我國外交部復函致謝,并經商議在案。荷款余數在民國20年可得荷金7萬余元,民國21至29年每年可得荷金11萬元。查意比荷退款用途大致相同,荷款甚微不敷治理黃河之用……故與其假定許多用途,一事不能成功,不如合辦一事,較為易致效果……再與協商劃一用途,當不難解決”[3](P155-168)。一個研究所的設立引起如此廣泛討論,可見荷蘭庚款“退款”在國人心目中并非“無足輕重”。
同年中國外交部部長羅文干與荷蘭駐華公使杜培克互換照會,確認自1926年1月1日起將應付之庚款全數交還中國政府,65%用于中國水利事業,35%供作文化用途。水利事業款項,用于南京水利測量研究所建設,其余撥充南京市水利經費。經費由董事會保管處理。董事會由中國董事二人、荷藉董事一人組織之,以上董事均由中國政府委派,并就中指定一人為董事長。為上述水利事業雇用荷蘭高級工程師,負責辦理中國政府所需要的專門事務,薪俸由水利事業經費內支付。文化事業則在海牙設立由中荷兩國組織的董事會,以1926年以來所積存款項作為文化基金,由中國駐海牙外交代表、荷蘭皇家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和萊頓大學校長組成的3人董事會管理,中荷雙方董事輪流擔任主席。并規定基金所得利息的40%,作為中國學生留學荷蘭費用[4](P923-925)。
有關水利科研項目的落實,在1934年1月《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錄》中有記載。該會秦汾秘書長報告簽呈事項中有:“外交部函知荷蘭退還庚款案內,原照會第二項載有提撥華幣40萬元在南京設立水利測量研究所一節。關于此案荷蘭大使曾向秘書長表示此項測量研究所,如由本會辦理較為妥適。最近荷使來京與水利處茅處長(茅以升,時任該會水利處處長—筆者注)晤談,彼擬于本年2月上旬返國,4月間來華,關于水利測量研究所由本會辦理一案,愿趁回國之便向荷蘭政府建議,并可代為延聘荷籍工程師一人同時來華協助云云。查該項水利測量研究所辦理各項事務,實與興辦水利有密切關系,應否告知荷蘭大使可以接受辦理”。全國經濟委員會負責人批示:由本會辦理。時間為1934年1月27日。以籌建水利測量研究所為標志,使用“退款”的水利項目大體確定了下來[5](P269)。此前李儀祉倡導的水工模型試驗機構,1933年10月成立董事會,經多方籌款,最終不得不以11萬元總經費為限起步,1935年6月1日開工建設,到1936年才得到政府第一筆2萬元撥款。以上可見庚子賠款數額巨大,荷蘭“退款”占比雖小,但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用在水利科研上也不算小數字。
三、 水利科技需求與科研機構創設
清末民初“西學東漸”,從傳統水利向近現代水利轉變,開發引進先進水利理論和技術首當其沖。科研從測量入手,在中國建立水利測量研究所主要是蒲德利·弗朗西斯(Francois Bourdrez)的提議[6](P16-27)。蒲德利 1933年來華,是國聯駐中國的特別顧問,代表國聯在水資源管理領域工作了7年多。受中國政府委托代表國聯參與審查導淮計劃、華北水利計劃、上海商埠發展計劃等,并在1931年大水后的堤防建設中建立了聲譽。[7](P18)到了中國后他意識到是在一個比荷蘭技術早1500年的國家里工作,在體驗中國勞動人民治水經驗與技能的同時,他深感在中國與水利有關的地形測量、水文測驗、氣象觀測資料缺乏,從而,利用他在中荷兩國的影響努力促成利用荷蘭 “退還庚款” 資助建立水利測量研究所。 他本人則在1939年不幸落水,犧牲在金沙江航道查勘一線崗位上[6](P16-27)。
當時,國內水利界關注的熱點是水工模型試驗而非測量技術。1898德國德累斯頓大學恩格斯教授創立世界第一個水工試驗室。1913年起,又建成規模更大的水工試驗室,模型試驗作為研究解決水利工程問題的有效手段,獲得重視,很快在歐洲以至世界各地傳播。1923年恩格斯受中國委托舉行黃河丁壩試驗,留學人員沈怡、鄭肇經參與其事;所著《制馭黃河論》一文,由鄭肇經譯為中文,刊布國內,一時朝野人士咸甚注意;1932年及1934年中國政府兩次撥款委托恩格斯作進一步治黃試驗研究,先后派李賦都、沈怡兩人參加。自此,水工模型試驗在中國的傳播已成風靡之勢。
水利科研機構的創設,實際與當時連年水災有關。民國初年全國水利行政分散,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水利更分屬不同部、會分頭管理。1931年江淮大水,全國輿論呼吁水政統一,科技界呼吁建立全國性水利科研機構的呼聲也日益高漲。1933年統一水利行政過程中新成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1934年在暫行組織條例中修訂提出“水利處為研究水利工程,得設置水工試驗所”[8](P452)。1934年9 月13日在統一改組原導淮委員會等機構的同時,全國經濟委員會決定創建中央水工試驗所(簡稱水工所),要求將其建成為全國水利科學研究中心,掌理水工試驗,研究水利改進事宜,為水利的規劃設計和工程實施提供科學依據。明確建設經費從荷蘭庚款“退款”40萬元 和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經費中支出,日常經費由全國經濟委員會負擔。該所以水工試驗為主,同時開展土工試驗、河工實驗、水文測驗、水工儀器制造、水利文獻編研、地形測量,并購置航測飛機及航測儀器,與陸地測量總局合作成立水利航空測量隊[9](P75-82)。該所的綜合性特點,既反映了中外專家的不同意見,也反映了中國水利科技發展的客觀需求,為該所日后自身建設和作用發揮創造了條件。
四、創設水利科研機構的“退款”使用
水利經費的研究所部分,主要用于中央水工試驗所南京廣州路試驗大廳建設。該大廳至1937年抗戰內遷前完成土建80%,建筑與設備費用去60萬元(使用荷蘭“退款”只是其中一部分)。該試驗大廳是當時東亞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水工試驗廳,還聘用荷蘭德爾夫特的水工試驗專家萬和佛(Heuvel)為顧問工程師。水利經費的南京市部分,用于整治下水道等市政工程,并聘用了荷蘭德爾夫特科技大學的阿爾瑪(Alma)為顧問。此項工程執行到1937年底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也沒有完工。至1939年12月庚款停付時,未動用水利款項本息合計22.34萬元。此時國際局勢突變,納粹德國侵占荷蘭,中國政府為支持荷籍人員共赴國難,將此款作為酬勞和遣散費,悉數付出,以此結清“退款”。
用于中國留學生的中荷文化基金,1935年5月,由基金董事會將第一筆用款匯至中央研究院,該院于1935年7月在南京舉行第一批次選拔考試。考試由丁文江(中英文)、秦汾(德文)、萬和佛和阿爾瑪(水利和灌溉、統計學和水力學)負責。結果,嚴愷(兩院院士,曾主政水工所10多年)和張炯(回國后在該所工作,金沙江查勘時與蒲德利一起犧牲)以考試成績前兩名入選。第二批次留荷選拔考試,1938年由中央研究院聘請羅家倫、傅斯年和葉公超分別負責黨義、國文和英文。專業考試由曾世英(測量),萬和佛、須愷(水利學與水利工程、應用力學、結構工程學),吳有訓(物理與物理儀器)負責,除物理與物理儀器一門用中文外,其他考試均用英文。1939年1月中央研究院又分別組織了以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和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長周仁為主考的水利工程、航空測量的專業選拔,陳善謨(水工所選送,美籍湍流力學專家)、劉雋快(主修測量,中國測量儀器制造奠基人之一)和王以康(主修漁業,被譽為中國魚類學先驅)入選[10](P44)。庚款留荷起點高、選拔嚴、經費有保障,以上5人都學有所成。納粹占荷后庚款停付,庚款留學派遣也隨之終結。
中央水工試驗所在解放前艱難創業、慘淡經營,直至解放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才有顯著發展。但廣大科技人員為水利的分科研究作了許多開創性工作,對一些水利學科在中國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建所初期借用中央大學建設了臨時水工試驗室。抗戰內遷后更與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西北農學院,以及國立中央工業專科職業學校合辦了磐溪、石門、昆明、武功、成都等五個水工試驗室(有的研究工作延續至今),研究所與大學互相兼職,試驗室兼作教學。目前,該所作為首批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單位,辦有中外文期刊5種,其中3種為SCI,EI收錄期刊,繼續著產學研結合的傳統。1949年4月大陸部分科技人員以中央水利實驗處(1942年更名)的名義,攜帶該處部分設備、圖書去臺,與臺灣大學、成功大學合作創辦了臺北、臺南兩個水工試驗室,至今保持著與大陸的聯系。
水工所業務寬泛,有些已超出現在“水利”范圍,但同樣不能無視它們的貢獻。如抗戰時期該所打破日軍封鎖試制成功了水準儀、平板儀、流速儀、回聲測深儀、自記雨量計等。以水準儀試制成功和批量生產為標志,結束了中國依賴進口光學測量儀器的歷史,所屬水工儀器廠也就成為國內生產光學測量儀器的第一家工廠。據解放初統計,它不但是全國生產土工、水文儀器的唯一廠家,也是生產測量儀器的最大廠家。該廠上世紀五十年代獨立建制、九十年代上市,領跑著國家水利電力自動化產業,已成為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十佳(中國)創新型杰出企業,其產品榮獲“中國名牌”稱號,創造著不平凡的業績[11]。
[1] 王樹槐.庚子賠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31號[M].臺北:精華印書館,1974.
[2] 宓汝成.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J].近代史研究.1999,(6).
[3] 楊汝梅.整理各國退還庚款余額用途的意見[J].南京:軍需雜志,1933,(19).
[4] 荷蘭駐華公使杜培克與外交部羅文干來往照會[A].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3)[Z].北京:三聯書店,1962.
[5] 秦汾.簽呈事項. 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記錄(一)[Z]. 2005.
[6] Roland van den Berg. The Role of Hendrik De Rijke and Francois Bourdrez in the history of Sino-Netherlands Water conservancy Cooperation[A].特來克與南通水利事業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C].南通市水利局,張謇研究中心,2009.
[7] 全國經濟委員會.報告匯編[Z].叢刊第30種,1937.
[8] 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 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暫行組織條例.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財政經濟第七卷[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9] 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民國二十四年水利事業進行情況報告[A].全國經濟委員會會議紀要[C],叢刊第22種,1936.
[10] 楊安吉.傅斯年有關庚款留荷的一則信函[J].沈陽:蘭臺世界,2009,(9).
[11] 國電南京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首頁[EB/OL].公司網,http:// hr.bjx.com.cn/compweb/guodiannanjing.
責任編輯:侯德彤
Establishment of Some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in 1930's-1940's Utilizing "Gengzi Peikuan" Returned by the Netherlands
LI Shuo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anghai Dian Ji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
The returning of "Gengzi Peikuan"(formerly called Boxer Indemnity) varied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n the past, there were a lot of discussions on the returning of "Gengzi Peiku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K, but few on that by the Netherlands only due to its "trifling proportion" in "Gengzi Peikuan", which is a pity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hat covers the diplomacy with the Dutch government concerning the returning of "Gengzi Peikuan", the
fund management and the
fund utilization, especially that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entral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Dutch;
"Gengzi Peikuan";
fund utilization; archives; translation;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stablishment
D693
A
1005-7110(2015)01-0106-04
2014-11-26
李碩(1969-),女,山東昌邑人,上海電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