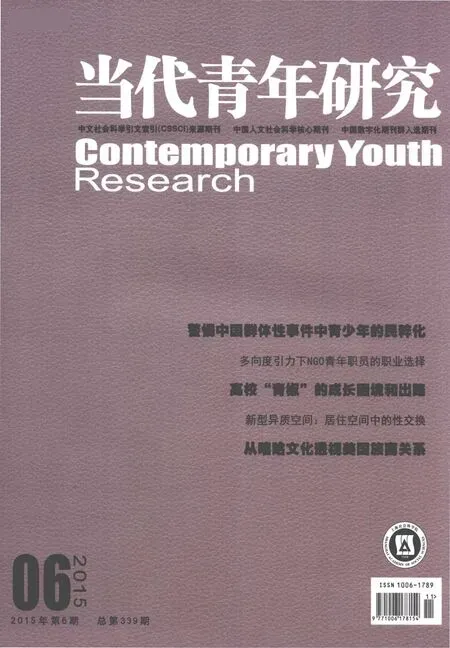美國的兒童保護體系及其啟示
何 芳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近年來,兒童受到傷害的事件頻繁發生。“南京養母虐童”、“黑龍江女嬰被父親扎鋼針”等駭人聽聞的事件一次次地沖擊人們的心理底線。盡管我國政府已不斷加強對兒童的保護力度,但案件的屢屢發生說明兒童保護仍存在諸多困難和不足。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如何及時有效地開展兒童保護服務,已成為當前我國兒童保護領域亟須研究的重點內容。本文旨在通過分析介紹美國在兒童保護領域的法律基礎、政府職能和具體工作流程,結合當前我國兒童保護工作面臨的困境與挑戰,進一步提出在我國完善兒童保護體系的對策建議。
一、美國的兒童保護體系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根據美國憲法,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作為互不相關的獨立實體并存,各自具有自己的權限范圍。因此,美國沒有全國統一的兒童保護體系。不過,聯邦政府就兒童保護設置了法律標準,各州都必須以此為基礎建立自己的兒童保護系統,只是在具體的政策、立法和實踐上有所差異。
(一)法律基礎
美國的兒童保護體系建基于一個法律概念——國家親權(Parens patriae), 即以國家公權利代替失職的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扮演父母的角色以保護未成年人。長期以來,美國社會有著濃厚的個人主義文化傳統,主張個人須為自己的人生負起最大責任,父母有權決定如何撫育自己的孩子。然而在1874 年,一名9歲女童瑪麗·埃倫(Mary Ellen)遭受其養父母長期虐待的事件被公之于眾,不但喚起了人們對處于弱勢的兒童的極大同情,也把兒童的脆弱性和依賴性鮮明地凸顯出來。 社會大眾開始逐步接受國家力量介入曾經被認為是私密不可侵犯的家庭事務,以確保兒童得到適當的支持與保護。不過,此時美國還沒有保護受虐兒童的相關法律,法庭不得不以動物保護法來解釋人是動物界的一員,才將瑪麗·艾倫從家庭中帶離,使她免于繼續受到養父母的虐待。
20 世紀60 年代,全美各州陸續建立了針對疑似受虐兒童的強制舉報制度。1962 年,《美國醫學會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受虐兒童綜合癥”的文章,揭示了受虐兒童的大量存在,并建議強制某些職業群體報告虐待兒童的事件。同年,聯邦政府兒童局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解決虐待兒童問題。會議達成決議,建議各州出臺舉報虐待兒童行為的制度。1963 年到1967 年間,全美各州先后頒布實施了受虐兒童舉報制度。最初,強制舉報制度僅規定醫務人員具有報告兒童受虐的責任,后來逐漸發展到規定所有與兒童有密切接觸的人員都有報告的義務,如醫生和護士、教師、社會工作者、警察、兒童攝影師等;而被報告的對象則是對兒童有責任的人或機構,如父母、其他家庭成員、保姆、托兒所、學校、寄養家庭等。隨著強制舉報制度的施行,原先鮮為人知的虐童事件開始大量進入公眾視野。僅1974 年,全美就約有60000 個舉報虐待兒童的報案。[2]
社會對虐童問題的關注直接推動了美國關于兒童保護的第一項聯邦立法,即1974 年通過的《兒童虐待防治法案》(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該法案授權聯邦政府為各州提供經費,用于改善和加強各州應對兒童遭受身體虐待、性虐待和忽視等問題的措施。同時,它還為兒童虐待問題的調查研究、救助受虐兒童的社工的培訓、建設地區性的受虐兒童救助中心以及開展救助受虐兒童示范項目提供經費支持。此外,該法案還要求社工定期訪問、監督和評估那些有虐待和忽視記錄的家庭,以保證虐待兒童事件不再發生。[3]《兒童虐待防治法案》中最重要的一點,還是要求各州建立兒童虐待或疑似虐待的強制舉報制度,否則不能獲得聯邦資助。
在《兒童虐待與防治法案》的關照下,每年都有大量兒童被帶離家庭,進入寄養照料體系。然而,美國政府很快發現,接受寄養照料的兒童人數始終居高不下,這說明國家強力介入的做法未能從源頭上避免虐待案件的發生,反而可能對兒童成長產生不利影響。為了改變兒童安置的現狀,自20 世紀80 年代起,美國政府開始大力提倡家庭對兒童的意義,主張以家庭的維系來彌補寄養照料的不足。1980 年《收養援助與兒童福利法》(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的出臺,體現了聯邦政府在兒童保護觀念上的轉變。最初的寄養安置旨在割斷兒童與原來家庭的聯系,而現在的寄養安置則以重組家庭為目標,寄養觀念從破壞原有家庭轉向家庭的維系,政策重心從救助轉為預防,并尋求寄養照料的替代方式。按照《收養援助與兒童福利法》的思想,兒童保護機構的主要任務不再是把兒童帶離家庭,而是對家庭需求進行評估,并為其提供深度服務,以避免兒童被帶離家庭。即使出于安全考慮必須將兒童帶離,兒童保護機構仍應積極幫助家庭解決造成孩子被帶離的根本問題,盡可能快地讓家庭重新團聚。[4]
家庭維系服務在20 世紀90 年代持續擴張,許多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因此免受寄養安置,但過分強調家庭維系卻犧牲兒童安全的事件也時有發生。[5]為此,美國國會在1997 年通過了《聯邦收養與家庭安全法案》(Federal 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與之前的《收養援助與兒童福利法案》相比,《聯邦收養與家庭安全法案》在政策取向上有明顯轉變:它減少了對家庭維系的強調,要求兒童福利的一切決策應以保護兒童安全為首要原則。雖然這一法案規定,在將兒童安排到寄養體系之前,相關機構必須做出“合理努力”,以降低將兒童從家庭轉移的必要性。但它同時也強調,如果兒童留在家里可能會受到傷害,相關機構則無須再做出維系家庭的努力。[6]這意味著,一旦父母被認定為不適合照顧自己的孩子,那么不論孩子年齡大小或親子關系的好壞,他們的監護權都會被終止。
(二)機構職能
兒童保護工作是一項公共事業,它是一系列計劃、決策、制度和行動的結合,涉及一個國家中各級政府及各種社會部門的協同合作。在美國,聯邦、州、縣的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在兒童保護工作中扮演著不同的重要角色。
美國聯邦政府的許多部門都在不同領域和不同程度上承擔了保護兒童的任務,例如住房與城市發展部有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住房補助的項目,教育部有保障兒童就學的項目,但主要承擔兒童保護工作的是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HHS 下設11 個部門,兒童保護工作集中在兒童與家庭署(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ACF)。ACF 是一個綜合性的兒童工作部門,其主要職責是增進家庭、兒童、個人和社會福利。它并不直接面向個體或家庭提供服務,而是為那些負責直接提供服務的州和地方政府及社會組織提供資助。目前,ACF 將全美劃分為10 個地區,在每個地區挑選一個城市設立地區辦公室,總部則設在華盛頓,由此構建出全國聯系網絡,確保工作流程的暢通。ACF 下轄19 個部門,其中一個是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管理局(The 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該局下設兒童處,其主要職責就是兒童安全與兒童保護。[7]
因美國各州行政相對獨立,故各州所設負責兒童保護事務的機構名稱和工作范疇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州和地方各級政府都設有兒童保護工作部門,通常稱為兒童保護服務部(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CPS)。CPS 負責受理疑似虐待兒童的舉報并做出反應,包括開展調查或評估、安置兒童、提起訴訟等。CPS 的核心任務是:對兒童的安全狀況進行評估;實施干預,使兒童免受傷害;增強家庭保護兒童的能力;幫助兒童與家庭團聚,或為兒童提供替代性的、安全的家庭環境。[8]當然,CPS 的工作還涉及與各個相關領域的機構和人士進行合作,包括司法、醫療和教育機構、宗教團體、反家庭暴力團體以及兒童的親屬等。CPS 需要發揮協調作用,促使各種社會力量協同合作,共同保護兒童免受傷害。
除了政府部門和公立機構以外,全美還遍布著大大小小的兒童服務社會組織。它們通常是非營利性質,依靠政府資助和社會捐贈,向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免費服務。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資助采取一套規劃、立項、實施、評價的項目化運作模式,即由從聯邦到地方的各級各類政府機構發布和資助特定的項目,由社會組織對這些項目提出申請,獲得批準的社會組織得到經費,按照項目要求提供服務。例如,聯邦政府的ACF 根據有關法律研究和開發出針對兒童的項目,并將其納入政府財年預算,經國會通過并撥款。發布項目公告后,符合條件的州和地方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社會組織等都可以進行申報。對于一些非競爭性項目,各州都能按照一定公式計算得到相應比例的撥款,而另一些項目則采用競爭性的差額立項。立項后,聯邦政府下撥項目經費,獲得資助的部門和機構開展項目所要求的工作。州與地方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既能以項目執行者的身份向聯邦政府提出項目申請,另一方面又要對本地所有受資助的社會組織進行監督、管理和指導。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兒童保護體系就是各種項目的組合體,各級政府的相關部門和全國的公立、私立保護機構都是依托項目發揮作用,形成一個多層次運作的綜合保護體系。[9]
(三)兒童保護服務部工作流程
CPS 是開展兒童保護工作的核心部門。它負責受理本地區的虐童舉報,評估兒童的安全和風險狀況。對那些得到證實的報告,CPS 要為兒童提供服務或安排相關的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幫助兒童獲得穩定、安全的生活環境。如果父母或監護人不具備提供安全生活環境的能力或意愿,CPS 還可以代表兒童向法院提出起訴,依據法院判決對兒童進行適當的長期安置。CPS 的工作流程大致分為六個階段:受理報告,初步調查,家庭評估,安置兒童,提供服務,評估結案。
1.受理報告
CPS 通常有專門的24 小時免費熱線電話,用于受理舉報。在這個階段,接線員要從舉報者那里獲得一些關鍵信息,包括:兒童和父母的姓名、住址等基本信息;兒童受到虐待的類型、嚴重程度、發生地;目前兒童的狀態;父母或照料者的身體和精神狀態等。總之,接線員要盡可能收集充分的信息,以便做出相應的判斷,如:該舉報的情況是否達到了虐待的標準?兒童目前是否面臨緊迫的危險?[10]一旦受理該報告,接線員還要決定對此做出反應的時間。根據兒童面臨危險的緊迫性,反應時間一般分為三種:立即反應,24 小時內反應,24 小時以外反應。
2.初步調查
受理舉報之后,CPS 會派出調查員對案件開展初步調查。調查對象包括所有與案件有關的人員和機構,如兒童本人、父母、家人、警察、社工、學校、醫院等。在調查階段,CPS 的工作人員應完成五項任務,一是判斷該舉報是否屬實,即是否有充足的證據證實這一舉報;二是評估兒童面臨的風險因素;三是評估兒童當前的安全狀況;四是評估家庭的應急需求,為有需求的家庭安排相應的醫療、食物、住所等;五是決定該案件是在CPS 的服務范疇,還是應該轉介到其他機構。[11]
3.家庭評估
開展家庭評估的目的,是幫助父母或兒童的照料者認識到問題所在并加以彌補,使兒童能繼續留在自己的家庭中生活。在家庭評估階段,CPS 的社工要盡量激發家庭參與評估過程,發掘家庭所具有的優勢、需求和資源。如果說初步調查階段的重點是辨別家庭中不利于兒童生活的消極因素,那么家庭評估階段的重點就是辨別積極的方面;初步調查的目的是發現問題,而家庭評估的目的是加深對問題的認識,理解問題形成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需要做出的改變。社工在評估過程中必須注意保持“文化敏感性”,[12]即尊重不同種族、地區、文化中的家庭結構和養育習俗。
4.安置兒童
如果調查發現兒童已不適合在原來的家庭生活,CPS 就會啟動替代家庭的安置服務。CPS 一般需要得到法院命令才能帶走兒童,但如果兒童的生命、身體受到極為緊迫的威脅時,也有權直接將兒童帶走。被帶離家庭的兒童一般有幾種臨時安置選擇,最理想的安置是和親屬居住在一起,因為它對兒童生活的干擾是最小的。其他的選擇還有寄養家庭、青少年獨立生活機構等。如果法院裁決終止原有監護人的監護權,則由CPS 暫代其監護權,并負責尋找一個最適合該兒童的長期安置途徑。[13]
5.提供服務
CPS 的工作并不僅限于將兒童移出家庭,它更重要的職責是提供服務。自家庭進入CPS 系統起,就會有專業的社工為其制定個案計劃,并幫助它們完成設定目標。全美公共兒童福利管理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blic Child Welfare Administrators)將家庭分為高、中、低三個風險等級。高風險家庭存在嚴重的兒童虐待行為,CPS 需要與司法機構合作,服務內容主要是收養、寄養以及刑事訴訟等;中等風險家庭存在的問題多是由疏忽照顧、不恰當的教育方式引起,CPS 需要與社區相關機構合作,提供一些支持家庭的服務;低風險家庭一般不存在虐待行為,CPS 會將其轉介給社區相關機構,由它們提供早期干預、家庭支持、家長教育等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服務。[14]
6.評估結案
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有必要對家庭的進展做出評估。社工與家庭的每次接觸,實質上都是一次對既定目標完成情況的評估。此外,社工每隔3 到6 個月應該做一次正式評估,其結論將成為結案依據。結案有兩種可能:一是家庭達到了CPS 制定的各項目標,重新獲得兒童的監護權,兒童回家團聚;二是家長不愿意或無法完成CPS 的要求,家庭環境被認定為不適合兒童居住,那么家長的監護權被永久剝奪。顯然,家庭團聚是CPS 最理想的結案狀態。[15]
二、當前我國兒童保護工作面臨的困境
經過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政府在兒童保護方面采取了多種多樣的積極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毋庸諱言,當前我國的兒童保護還面臨著不少困境,需要尋求進一步的解決之道。
(一)缺乏受虐兒童的強制舉報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在兒童保護方面處于“被動應對”而非“主動發現”的狀態。其原因在于,兒童保護系統中缺乏一個迅速發現舉報的機制。對于父母或其他成人侵害兒童的行為,誰有舉報義務,不舉報會承擔哪些后果,如何舉報,舉報給誰,接受舉報的人或機構應該在多長時間內做出反饋等,對于這些問題,都沒有可具體實施的規定。例如,一些民眾在發現家長虐待兒童后并不舉報,這固然與人們普遍缺乏干預家庭的意識和習慣有關,但更多的情況是,人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虐待,卻不知道應該做出什么反應。我們常常看到,許多網民在發現受虐兒童后會義憤填膺地將其拍照上傳到互聯網,但除此之外卻不知道應該采取什么行動來使兒童免受傷害,也不知道在第一時間應與哪個部門聯系。可見,沒有對受虐兒童的強制舉報制度,兒童保護就缺少必備的基礎。
(二)有關兒童監護責任及監護權的法律尚不健全
隨著近年來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現象的增加,由于父母監護失職而導致的兒童傷害案件越來越多,過去傳統的以家庭為主的監護模式已不足以應對當前的嚴峻形勢。按照我國刑法,如果因父母疏于監護而造成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或者死亡,父母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實際的司法操作中,常常要考慮到兒童受傷害或死亡對其家庭是非常沉重的打擊,以及兒童受傷需要照料、社會文化對父母的同情等因素,很少有真正剝奪父母的監護權或將父母判刑的判決。
盡管《民法通則》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都規定在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時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但遺憾的是,這一規定沒有對“有關人員”和“有關單位”進行明確界定。按照目前法律,法院只能在接到申請之后才能做出撤銷和轉移監護權的判決,但兒童基本上無法自己提起監護權撤銷申請。兒童的近親屬、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所在的單位、村(居)民委員會有權代表兒童提起撤銷監護人的申請,但現實情況是,因為擔心監護責任會落到自己的頭上,這些個人和單位并不愿意提起申請。顯然,目前法律難以回答的問題是:誰有義務提起撤銷兒童監護人的申請?不履行該義務將會承擔什么責任?監護人資格撤銷后,如何指定新的監護人?上述問題不得到解釋,那些不適合繼續養育子女的,甚至已對子女造成了嚴重傷害的父母就仍然擁有監護權,兒童受到傷害的事件就會繼續發生。
(三)兒童保護的長期安置渠道不暢
兒童監護權轉移的真正難題,在于撤銷監護權后無人“接手”,這是司法遭遇現實困境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目前只有父母雙亡的兒童或者棄嬰才能進入體現國家監護制度的兒童福利院,受虐兒童、流浪兒童和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等還無法接受國家監護,也沒有家庭以外的長期替代性安置的制度安排。同樣,家庭寄養、收養等救助保護方式目前在法律上也只針對孤殘兒童和被遺棄的兒童,且其覆蓋面也相對較窄。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即使與父母共同居住已經嚴重危害兒童的身心甚至是生命安全,國家也沒有專門的組織機構以及合法的制度來進行長期安置。
三、完善兒童保護體系的對策建議
上述種種困境表明,我國在兒童保護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一過程中,有必要學習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美國的兒童保護體系正是這樣一個參照物。
(一)在各級政府中設立兒童保護職能部門
美國的各級政府中都設有專門的兒童保護職能部門,如聯邦政府的兒童與家庭署、州與地方政府的兒童保護服務部等,這些政府部門承擔著調查、起訴、咨詢、干預等許多保護兒童權益的職能。實際上,這也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德國、日本等國家的政府也有相似的部門。因此,我國也可在各級政府中設置專司兒童保護事務的職能部門,中央主管單位可設在民政部,主要負責兒童保護的政策設計、項目發布、經費管理和成效評估。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在民政局(廳)成立地方兒童保護機構,接受民政部的領導,但在具體事務運作上享有自主權,負責監管中央關于兒童保護項目的實施和執行,以及制定本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兒童保護政策和保護服務計劃,并通過撥款、政策指導、信息服務、提供培訓和技術支持,開展項目評估等工作,幫助市(縣)地方機構履行服務職責。市(縣)級政府民政局設立兒童保護服務辦公室,負責有關的具體事務性工作,包括:當發現兒童需要家庭干預時,及時進行干預;當兒童需要緊急庇護時,將兒童帶離家庭并做出適當的安置;當兒童受到嚴重傷害時,對案件進行調查;認為需要撤銷監護人資格時,向法院提起撤銷監護人資格的訴訟。
(二)建立兒童傷害強制舉報制度
建議國務院出臺《兒童傷害強制舉報辦法》,規定公民在發現兒童受到傷害的情況時有舉報的義務。尤其是教師、醫護人員、執法人員、社工等在日常工作中容易接觸和發現兒童被忽視、虐待、遺棄等情況的個人或部門,必須向公安部門或民政部門舉報。掌握兒童受傷害的信息卻不舉報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全國應設立統一的兒童保護熱線電話,也可在110 報警系統或其他公共服務熱線中增加兒童傷害舉報服務。
建立對舉報的回應機制,以鼓勵公民參與舉報。民政部門應研究制定兒童風險分級標準。對高風險兒童,在接到舉報后應立即通知公安部門,聯合開展調查,以確保兒童能夠及時脫離危險環境,并被安置到安全、有益于其成長的環境。對中等風險兒童和低風險的兒童,可視情況緊迫性確定不同的反應時間,但原則上應在接到舉報后的72 個小時之內進行調查。
(三)建立國家臨時監護制度與長期安置辦法
建議出臺專門法規政策,明確提出國家臨時監護制度和兒童長期安置辦法。第一,所有無法獲得家庭適當照料的兒童,都應成為國家臨時監護的對象,民政部門承擔臨時監護職能,負責對兒童選擇最適當的臨時生活場所和照料者。第二,明確規定代表兒童提起撤銷監護人資格訴訟的主體為民政部門。對于不具備養育兒童能力、對兒童造成嚴重傷害的監護人,民政部門應依法對其提起訴訟,申請終止其監護權。第三,如果原監護人的監護權被終止,應立即啟動長期安置程序。民政部門應在征求兒童本人及兒童親屬意見的前提下,會同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聯、團委等其他部門和單位協商,選擇符合兒童最大利益的長期安置辦法。
(四)設立社區兒童服務中心
在兒童福利院、流浪兒童救助保護中心之外,設立社區兒童服務中心,面向受虐待或被忽視的兒童、困難家庭子女、農村留守兒童、失學輟學兒童、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等一切有需要的困境兒童。社區兒童服務中心的職責應包括臨時食宿、基本醫療、心理咨詢、法律援助等;聘用受過社工專業教育、具備社工從業資格的工作人員,確保兒童得到專業的服務。此外,在政府興辦社區兒童服務中心的同時,還應鼓勵社會組織參與保護兒童。政府可簡化從事兒童保護工作的社會組織的設立程序,并通過專項資金、政策優惠、購買服務等形式來進行扶持,從而形成政府與社會組織共同保護兒童的強大合力。
[1] Eric, S and Lazoritz, S.. Out of the darkness: The story of Mary Ellen Wilson[M]. Cape Coral, FL: Dolphin Moon Publishing,1998:36.
[2] Myers, J.. A short history of child protection in America[J]. Family Law Quarterly,2008, 42(3):449-463.
[3] Schene, P..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oles of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J]. The Future of Children: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Abuse and Neglect,1998 (1):23-38.
[4]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Z]. P. L. 96-272,1980.
[5] McGowan, B., and Walsh, E.. Policy challenges for child welfare in the new century[J]. Child Welfare,2000: 79 (1):11-27.
[6] 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Z]. P. L. 105-89,1997.
[7][9]何芳.“流浪兒在美國”:社會救助的制度、實踐與啟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71-273.
[8]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blic Child Welfare Administrators. Guidelines for a model system of protective serices for abused and neglecte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ublic Human Services Association,1999:35-42.
[10] Wells, S.. How do I decide whether to accept a report for a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investigation? In H. Dubowitz & D. Depanfilis (Eds.), Handbook for child protection practice[C].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0a:3-6.
[11][12][14][15] DePanfilis, D. and Salus, M..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A guide for caseworkers[R].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3:39-49, 69, 83-85, 99-100.
[13] The Texas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Understanding Texas’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 system[EB/OL]. http://texprotects.org/media/uploads/10_7_14_combined_cps_systems__flowchart_final.pdf,20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