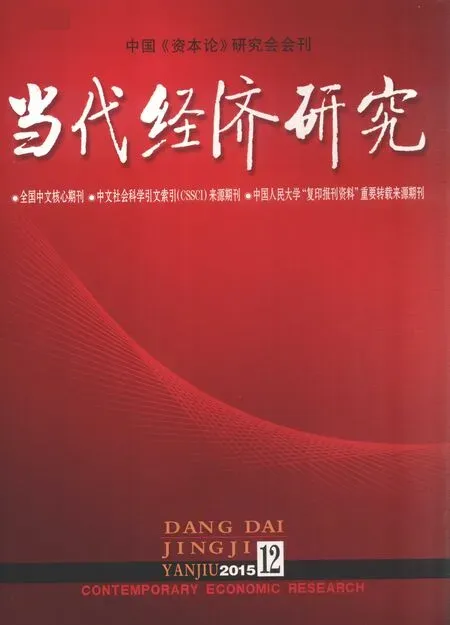國家作用與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一個新李斯特主義的解讀
嚴 鵬
(1.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上海200433;2.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武漢430079)
編者按
國家作用與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一個新李斯特主義的解讀
嚴 鵬1,2
(1.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上海200433;2.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武漢430079)
編者按
李斯特經濟學是系統揭示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體系之一,其關于欠發達國家幼稚產業保護思想得到了晚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并成為推動德國、美國等歷史上后發國家通過抵御英法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而崛起的理論依據。新李斯特經濟學是對李斯特經濟學傳統的創造性發展,其在繼承李斯特有關國家是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石、生產力發展的活動特定性和經濟政策的時空特定性等學說的基礎上,對李斯特有關國富國窮的典型化事實提供了演化經濟學的理論解釋,并在重建世界經濟新秩序、經濟危機的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目前,中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結構轉型、謀求對外經濟發展新空間的重要階段,需要吸收、借鑒各種發展理論。為此,本刊設立了“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專欄,期冀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有所裨益。
摘要:中國作為一個典型的后發展國家,其工業化道路具有由國家主導的特征,偏離了工業化的“自然”模式。然而,國家參與工業化是世界經濟史的常態而非例外,因為工業化本身是與民族國家建構聯系在一起的,具有非經濟的政治—軍事維度。中國的工業化始于軍事動機,但由市場主導并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工業化更具成效。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缺位阻礙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并激起了國家“凌駕”市場的反向運動。一種新李斯特主義的演化圖式認為,工業化是由國際競爭引發的、國內具有不同觀念的精英斗爭的結果。精英可以具有多樣化的動機。當那些具有整體及長遠利益觀的精英占據上風,并找到適宜的手段高強度地參與國際競爭時,工業化就能夠啟動并得以維持,這是國家作用于工業化的一般性機制。
關鍵詞:工業化;國家;新李斯特主義;歷史方法
自19世紀以來,工業化一直是各國競逐富強的必由之路。由于工業化主要表現為一種經濟現象,因此,不少學者主要從經濟或者市場角度對工業化進行了分析。然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學者早已揭示國家對于工業化具有重要作用。[1]這一論點尤其被應用于對所謂后發展國家工業化的解釋。不過,部分以主流經濟學為研究工具的學者,雖強調國家或政府的作用,但對其評價過低,并據此將中國百余年的工業化道路視為低效的路徑依賴。[2]這一主流經濟學建構的歷史圖景,既存在較多歷史事實的錯誤,也未能真正理解國家對于工業化的意義。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呼喚著李斯特經濟學的歸來,而一種新的李斯特經濟學也必然要對工業化的歷史給予解釋,從而得出現實的教益。[3]從新李斯特主義的角度來看,單純的工業化已經不再能確保欠發達國家脫貧致富,這就使透過歷史現象剖析經濟演化機制顯得尤為重要。[4]本文認為,工業化并非單純的經濟現象,而是一個李斯特式的政治—經濟過程,其政治維度決定了國家不但是一個功能性存在,更是工業化的一個基本組成要素。而國家對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作用,與其說是歷史的例外,不如說仍然反映了歷史的常態。
定稿日期:2015-11-10
一、國家與工業化:歷史的普遍性
李斯特作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其研究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歷史與事物本質為依據”[1]8。這一歷史主義方法論的優勢在于對時空特殊性的重視,從而批判了主流經濟學罔顧各國國情的空泛論說,進而抵制了那些無視經濟發展階段性的政策建議。然而,李斯特以及德國歷史學派并未采取過度歷史主義的立場,他們仍然相信具有普遍性的歷史規律是存在的,只不過這種普遍規律會被不同的歷史情境塑造成不同的樣貌。因此,從新李斯特主義的角度出發,欲探討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首先應該考察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是否具有某種共性因素。
一般認為,國家或政府在后發展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要大于起步更早的地區。例如,張培剛在構建其工業化理論時,區分了工業化的不同類型,將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工業化視為“由個人發動而開始者”,并認為這種工業化類型“符合工業進化的自然趨勢”[5]。更為一般性的結論,則如格申克龍所言:“一個國家越落后,它的工業化就越可能在某種有組織的指導下進行。”[6]在這樣的視角下,從19世紀開始,德國、日本等后起工業強國的道路就被視為偏離了“自然趨勢”的例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加入工業化進程的后來者越多,例外國家的名單也就越長。然而,這種例外論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例外論潛在地假定了工業化只是一種經濟現象,這就使國家所起的作用看上去偏離了常軌;二是例外論假定工業化可以具有不同的類型,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其分類是以國家為基礎的,而忽略了無論是先行國家還是后起國家,其內部都存在著因產業、部門差異而導致的多種工業化路徑。因此,通過某種典型化的研究方法,學者們建構出了以發展先后為標準的兩種工業化類型,并將后發展視為偏離“自然”的例外,而所謂“自然”,又被假定為國家的不在場。但從一種更寬廣的歷史視角來看,例外論的兩個立論基礎都是殘缺的。
從純粹的歷史角度看,國家是一種比工業化更古老的現象,因此,工業化并非是在一個無國界的制度真空中發生的。實際上,即使那些對國家作用持消極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分國別來討論工業化問題,這本身就暗示了國家的重要性。當然,那些質疑國家作用的學者,不可能從歷史與現實世界中完全抹殺國家的存在,于是為國家安排了諸如“守夜人”這樣的角色。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內核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史,更是將國家視為“經濟史研究的核心”[7]。然而,這些學者在本質上只是將國家視為一種功能性存在,是給工業化帶來好秩序或壞制度的外生因素。在標準的新制度主義模型中,國家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是西方世界爆發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8]工業革命在這一模型中,主要是由私人資本推動的經濟過程,國家雖然重要,但其作用僅在于為私人資本搭建了適宜的活動舞臺。國家在新制度主義模型中的形象,與主流經濟學傳統的“守夜人”假設,并沒有太大不同,只是由純粹的背景因素,轉變成了更具主動性的背景因素。然而,國家比工業化更古老這一事實,暗示了工業化很可能從屬于由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進程,而非單純的經濟現象。在這一圖式中,國家的重要性不僅在于為私人資本設置制度背景,相反,國家自身是與私人資本同等重要的行為主體,是工業化的積極創造者。而這一圖式,較少割裂歷史的延續性,并體現了更為普遍的共性因素。
新航路開辟以后,西方世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崛起”,但這一“崛起”是以西方世界內部的國家競爭為基礎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歐洲國家間的競爭,其性質是政治性的,體現為領土兼并與大型民族國家的形成。至于競爭的手段,則具有多樣性,涵蓋軍事、外交、經濟等各個方面,而經濟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各國統治階層對國家財富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日益明了,于是產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這一特殊的政治—經濟體系。按照赫克歇爾(Eli F.Heckscher)的經典歸納,重商主義作為增強國家權勢的方法有兩種:或者基于政治、軍事需求直接將經濟活動引導至特定目標;或者更為一般性地創造某種經濟資源的蓄水池,供政權汲取所需。[9]赫克歇爾主要從經濟手段角度審視重商主義,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則更準確地意識到重商主義不僅僅是手段,還是現代民族國家自我建構的進程。[10]因此,早在工業革命爆發前,歐洲各國在重商主義的指引下,已經成為積極的經濟行為主體。也就是說,國家本身是有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與“意志”的,即使這種動機與意志只反映了統治階層的利益訴求,并只由統治階層代理執行。而從歷史來看,重商主義國家的動機也確實產生了相應的行為。馬格努松(Lars Magnusson)指出,近代早期的歐洲重商主義國家,能夠廣泛地運用各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來干預經濟活動。[11]這一歷史事實具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它表明歐洲國家在工業化時代采取的各種干預經濟的手段,并非是工業時代的新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國家已經是積極的經濟行為主體,并非消極的“守夜人”,按照“路徑依賴”理論,歐洲國家的這一屬性完全有可能延續下去。事實也正是如此。而歐洲國家具有經濟行為主體的屬性,恰恰是由國家的政治—軍事動機決定的,并由此產生了國家內部工業化類型的多樣性。
如前所述,在重商主義時代,國家介入經濟的動機主要是政治性的,甚至只是出于為軍事競爭蓄積力量。當時,雖然以非生命能源為動力的現代工業尚未出現,但以手工勞作為基礎的傳統工業(traditional industry)已經成為了國家權勢的重要基礎。一方面,所謂的重工業部門,如冶金、火炮制造、造船等工業,直接為國家提供武器裝備,是國家軍事力量的構成部分;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市場的輕工業部門,如毛紡織、棉紡織、衣帽制造等工業,可以通過出口海外市場,為國家帶來收入,從而為國家純粹消耗性的軍事開支提供資金支持。如此一來,重商主義國家對于發展工業抱有濃厚的興趣,并采取廣泛的保護主義政策。例如,通常被視為“自然演化”典范的英國,在近代早期曾通過授予本國企業特權及大量政府采購的方式,誘導資本進入軍事工業。[12]因此,隨著時間的推演,重商主義體系實際上促成了國家、工業與貿易之間的協同演化。一方面,積極培育工業的國家強化了其軍事力量,通過殖民戰爭而在全球市場上獲得了更有利的貿易地位;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優勢反過來又使國家有了更多資源發展更強大的軍事力量。正因為如此,主張自由貿易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將《航海法案》這一反自由貿易的重商主義法令稱為英國最明智的政策。[13]581~583英國的《航海法案》是針對當時的霸權國家荷蘭制定的。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史看來,英荷兩國都具有完善的私有產權制度,相對于西班牙與法國,都屬于競爭勝出的國家。然而,在英荷兩國之間,英國戰勝了荷蘭,而從更長遠的眼光看,法國在產業革命中也勝過了荷蘭,這表明私有產權并非國家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從根本上說,近代早期歐洲國家間的競爭是綜合性的,不是純粹經濟性的。而國家間的軍事斗爭,對于工業革命的技術突破有直接推動作用。由于蒸汽機使人類開始常態化地利用非生命動力,因此,比起紡織機械的革新,蒸汽機的改良才真正具有革命性。但從歷史角度看,瓦特(James Watt)對蒸汽機的改良依賴于威爾金森(John Wilkinson)發明的鏜床,而威爾金森鏜床最初是用于制造火炮的。[14]這是政治—軍事因素推進工業革命的顯著例證。進一步說,最早啟動工業化的英國,其革命性的突破,既得益于重商主義國家創造的全球市場,又受惠于國家的軍事需求產生的技術外溢。無論從直接還是間接的方面來說,國家都在英國工業革命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這使得英國的工業化看上去并沒有那么“自然”。
當然,國家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不表明國家對于每一個部門都發揮了相同的作用。只不過,傳統上那種以棉紡織工業為中心審視英國工業革命的視角,有必要予以修正,才能完整地展現歷史圖景。歷史的復雜性在于,即使在所謂重工業部門中,直到普遍被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已完成的19世紀40年代,英國金屬制品業仍大量存在使用手工勞作的小規模企業。[11]因此,一國內部是可以存在多種工業發展類型的,甚至在某個產業部門中,也并不存在單一、線性的進化模式。如果必須將紛繁的歷史現象抽象為簡化的模型,則似乎可以認為,各主要國家的工業化道路都存在著二元結構的現象,即:一方面明顯存在著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推動的工業發展,其力量集中體現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戰略部門以及規模巨大的企業,并較多地服務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動機,這種類型可稱為“李斯特式發展”;另一方面,市場可能會隨機性地誘導某些產業發展,但其發展形式具有不確定性,且可能因為演化的漸進性而保留較多的原始性,這也就是學界習稱的“斯密式發展”。承認這兩條道路可以并存有著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對于某些政府明顯主導了工業化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等,由于其地域發展等各方面的不平衡性,很可能某些產業的演化會保留較多原始性特征,但不能據此而否定這些國家的“李斯特式發展”;二是對于那些看上去由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國家,如英國、美國等,同樣要看到其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能動性,這一點或許更為重要。
事實上,在上述二元結構中,兩種工業化類型并非是對等的。由于國家主要是一個政治性存在,因此,對那些以獨立生存為首要目標的大國而言,更具政治動機的“李斯特式發展”也就更具主導性。這種主導性不體現于單純的規模或數量,而體現在對于國家獨立自主的相對重要性。恰如斯密所言:“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13]583不管棉紡織業如何主導了工業革命最初的進程,但支撐大英帝國的主要是冶金、機械、造船、火炮制造這些戰略性部門,而沒有這些戰略性部門供給的“堅船利炮”,曼徹斯特的紡織品也無法撬開中國市場的大門。以通常同樣被視為“自然演化”典型的美國來說,其工業發展伴隨著高關稅等各種國家干預,而其動機同樣并非純粹經濟性的。在鼓勵美國發展制造業的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看來,經濟與軍事息息相關,如果初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想要發展貿易,就必須盡全力組建海軍。[15]曾與漢密爾頓針鋒相對的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后來也改變了其早期觀點,支持美國以保護主義手段發展民族工業,因為“反對民族制造業的人一定會讓我們淪為他國的依附”,而“制造業對于我們的獨立自主和幸福安康是不可或缺的”[16]。這種觀點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利益,而是一種具有政治—軍事視角的戰略觀。而這同樣表明美國的工業化不那么“自然”。
因此,歐美早期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如果將國家的積極介入視為“非自然”狀態,則經濟史上根本不存在“自然”的工業發展。誠然,即使在那些國家明顯起了更大作用的國家,也存在著主要由市場與私人資本主導的工業發展路徑。但是,只要仍然以國別為基礎考察工業化,就不得不承認工業化是嵌入于國家建設進程中的。究其原因,現代國家為了生存,有其自身的利益與動機,也就是國家理由。[17]國家理由是一種政治邏輯,而工業化只是國家為實現其利益而采用的經濟手段之一。國家對于工業化的這種支配性關系,就各國尤其是大國歷史而言,乃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共性因素。這種歷史的普遍性,對于理解中國的工業化道路至為重要。
二、中國工業化的成因與道路多樣性
就現代經濟發展而言,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后發展國家,因此,學者們在格申克龍理論的框架下考察中國工業史乃是極為自然的傾向。從這個角度說,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工業化道路具有“特殊性”而進行“再思考”,卻得出國家“持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一結論,可謂了無新意。[2]然而,國家對于中國工業化的作用雖極為重要,但與經濟一樣,國家本身不是靜態的,而是演化的。同時,中國工業化的內部也存在著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既構成抵消國家作用的力量,又成為強化國家介入的理由。
在西方經濟史學界,有所謂“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論。該理論旨在揭示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制造業的演化機制。在部分地區,這些手工業一度發展出極為龐大的規模,并具有出口導向型等市場經濟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原始工業化”的典型產業是紡織業等消費品產業。[18]部分學者認為“原始工業化”為真正的工業化拉開了序幕,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的關系因地而異,實際上不能視為工業化的前提。[11]這一“原始工業化”理論后來被學者引入到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用以描述和解釋明清時期中國部分地區具有市場導向性的手工業的發展。不管這些學者的動機與結論是否恰當,單從現象上看,明清時代中國部分地區的農村手工業確實具有與歐洲“原始工業化”相類似的特征。例如,在經濟并非最為發達的湖北地區,農村紡織業生產的棉布大量遠銷四川、云貴、山陜等地區。[19]考慮到中國地域的遼闊性,這是堪與歐洲內部的國家間貿易相媲美的遠程貿易,而且清朝龐大的國內市場和省際分工實際上降低了對海外貿易的依賴。[20]因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傳統工業已經有了相當發展。
然而,正如歐洲的“原始工業化”并未直接誘發工業革命,明清時代的手工業也無法使中國自然地演化出現代工業。現代工業與傳統工業的本質差異不在于市場規模,也不完全在于生產組織,關鍵性的區別在于技術。而工業革命時期的技術,一部分是在紡織工業等消費品工業內部自發演化的,大部分則體現為更具戰略性的資本品工業部門的溢出。沒有蒸汽機,英國棉紡織業的機械革新仍然是手工業性質的,并不能建立起相對于印度、中國傳統手工業的絕對優勢。而制造蒸汽機的重工業部門,不是歐洲“原始工業化”的典型產業,更為明清時期的中國所欠缺。所以,中國的傳統工業在鴉片戰爭之前,不可能演化為現代工業。中國的工業化,起始于晚清政府對西方戰略性工業的引進,是典型的國家理由支配的產物。
其實,從純粹的經濟角度審視,西方的現代工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并不具備完全壓制中國傳統工業的競爭力。以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棉紡織業來說,英國用現代機器紡的紗,確實淘汰了中國傳統的手紡紗,但是,機器織的布卻很難取代手工織的布。實際的演化情形是,中國農民從市場上購買機紡紗作為手織布的原料。而手織布能夠長期盛行,一個重要原因是其粗糙的質地使其比機織布更耐用,更能滿足收入較低的中國農民不經常更換衣物的消費偏好。[19]因此,從1840~1894年,機紡紗在市場份額上對手紡紗的排擠度達到25%左右,而機織布對手織布的排擠僅達14.15%。[21]以至于當中國的洋務派仿效西方開辦現代紡織工廠時,一開始創辦的機器織布廠都遇上了銷路不暢的麻煩,不得不轉而創辦機器紡紗廠。[22]這一史實表明,在純粹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即使當西方現代工業的產品已深入中國腹地時,中國傳統工業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中國消費者對于現代工業產品也不存在絕對的需求。事實上,市場只會選擇適用性技術,而非最先進的技術。由此反推,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具有一個相對自足的經濟體系,盡管這一經濟體系的技術程度不高,但其內部的產業循環大體能夠滿足國民需求,并有能力供養一個前現代組織的帝國政府,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對現代工業的經濟需求。在鴉片戰爭之后的十余年,中國對大英帝國的合法貿易仍然保持了出超。18世紀40年代,中國對英貿易平均每年出超350萬鎊,而到1850年代則增至900余萬鎊。為此,英國不得不繼續走私鴉片來平衡貿易。然而,中國彼時尚未開始工業化,完全是依靠絲與茶等傳統工業產品出口。因此,中國直到1860年仍不開始工業化,恰恰是市場經濟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且中國生產者的行為方式高度符合一個理性自利但缺乏前瞻性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形象。
相對于由市場邏輯主導的消費品工業,清朝統治階層在一開始對西方的資本品工業更為敏感。洋務派的所謂“師夷長技”,最初即著眼于火炮、軍艦制造這些純粹的軍事工業,以對內平叛、對外御敵,而中國的工業化也肇端于他們創辦的江南制造局等軍工企業。在創辦這些企業時,部分洋務大員確實有某種更為長遠的經濟眼光,意識到了現代工業不僅具有軍事功能,還能夠帶來更廣泛的經濟變化。但囿于各種因素,最初的動機主要還是政治—軍事性的。[23]對李鴻章等人而言,維護清朝的統治這一政治目標是根本性的,學習西方創辦現代工業,只是一種手段,而且最初毫無經濟上的考慮。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工業化不僅一開始即由國家主導,甚至在其早期階段也根本不是一個經濟現象。當然,工業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早期的軍事企業開始對市場產生技術外溢效應,而且洋務派官員創辦企業的興趣也由純粹的軍火制造轉向航運、紡織等民用部門。
但是,當時的中國還存在著其它的工業發展路徑。如前所述,中國的傳統工業具有強大的市場適應性,而且它們并非一直以傳統面貌示人,相反,部分傳統工業學會了運用現代工業提供的原料、設備乃至動力,呈現出向現代工業漸進演化的趨勢。[24]這種變化,在沿海地區的造船等行業中,甚至可能不晚于洋務派興辦現代企業。[25]自然,這是一種純粹受市場誘導的工業發展。實際上,在多數行業中,二元結構出現了。例如,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機械工業中,一方面,清政府的官員創辦了江南制造局等具有現代性的大企業;另一方面,一些后來表現極為出色的企業,比如制造動力設備的武漢周恒順機器廠,最初不過是為寺廟鑄佛像的手工爐坊。然而,在周恒順機器廠的案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江南制造局這一國營大企業向私人資本擴散了其技術乃至人才,促使后者得到升級發展。[26]至于在紡織、食品等消費品工業中,私人資本就更為活躍了,一些日后稱雄市場的大企業,比如榮氏集團,基本上只是遵循市場需求而不斷擴大投資,靠自我積累而非國家扶持成長壯大。[27]甚至于一批洋務派官員創辦的企業,因經營不善,不得不租給私人資本經營。[28]因此,有學者將清末工業化描繪為一副主要由政府推動的經濟社會連鎖變化的圖景,[2]與歷史事實完全不合。不錯,在晚清中國,國家創造了工業化,也推動了工業化,但國家遠未能主導工業化。而國家的這種弱勢地位,至少要延續到1937年。
綜上所述,中國工業化的成因是政治—軍事性的,但其內部的道路具有多樣性。在工業革命之前,乃至于在工業革命之后的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的傳統經濟都具有較強的自足性,整體上不具備自發工業化的經濟動機。中國的工業化,最初是統治階層基于國家理由而創設的政治—軍事議程。然而,就清末的具體情形而言,國家的作用僅在于引進了現代工業技術與組織,到王朝覆亡之時,國家基本上未能對工業化進行有效引導。相反,清朝末年見證了某些主流經濟學家更加喜愛的由市場和私人資本主導的工業化,以及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的漸進演化。因此,與在19世紀的工業化浪潮中成功應對了挑戰的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國不同,中國的應對是失敗的。如前所述,工業化本身是嵌入于國家建設的,因此,中國的應對失敗,不是指純粹作為經濟現象的工業發展完全失敗,而是這樣一種工業發展與國家建設是脫嵌的。這種脫嵌,在20世紀前半葉最終阻礙了工業化的正常展開,并激起了更為強大的國家建設運動。
三、國家“凌駕”市場:體系演化的選擇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說,在由民族國家構成的現代世界體系中,國家的存在是以其它具有競爭關系的國家的存在為依據的。[29]因此,國家建設也好,工業化也好,都是發生在世界體系內部的演化,受制于體系自身的演化機制。而世界體系的演化,最基本的動力就是各民族國家間的競爭。韋伯(Max Weber)稱:“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斗爭是個自然過程,哪怕斗爭是在‘和平’的外表下進行。”[30]這可謂抓住了要害。因此,在整個20世紀,中國工業化道路中國家的作用不斷強化,乃至于“凌駕”市場,并非某些學者所稱的“利益集團”處心積慮設計的結果,[2]而是體系演化的自然選擇,并且不乏經濟合理性。同時,那種認為存在著某個前后一致的利益集團的歷史想象,更是徹頭徹尾的向壁虛造。
工業化嵌入于國家建構進程中,意味著不僅工業在變化,國家本身也在變化。例如,盡管歐洲國家在重商主義時代已經廣泛采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極具現代性的手段來管理經濟,但往往效果不彰。究其原因,近代早期的歐洲國家在相當時間內仍然保持著傳統的政治組織形式,缺乏高效的行動能力。在所謂舊制度下,即使君主專制國家的權力也可能是“去中央集權化”與“碎片化”的。[11]就國家直接參與工業化的動機來說,往往是因為資源稟賦的自然結構在市場引導下,無法將生產要素吸引到對國家有利的領域,也就無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市場比較優勢結構所施加的瓶頸,對后發展國家來說,又往往由于先行國家產業的競爭而得到強化。國家對于工業化的作用,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打破市場所施加的束縛,并提升工業活動的質量。然而,國家要發揮打破市場瓶頸的作用,就必須具有相應的能力。國家能力不是憑空存在的,它依賴于具體的人在一定的制度組織下去從事恰當的活動。制度組織就是國家的政治體制尤其是行政制度,它劃定了國家汲取、分配與利用資源的基本渠道(制度組織不等于國家的政治體制,可改成:它依賴于具體的人在一定的政治體制下去從事恰當的活動,政治體制尤其是行政制度,它劃定了國家汲取、分配與利用資源的基本渠道)。毫無疑問,某些制度作為渠道是不那么暢通的。然而,大量流于形式的制度表明,人的活動更為重要。而人的活動是受包括非經濟利益在內的動機支配的,因此,思想意識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國家的行動能力,從邏輯上說,取決于統治階層的眼界與意志,以及由此而設定的制度或形成的行為規則。
關于思想文化或意識形態對于工業化的作用,本非新論點。李斯特稱“國家物質資本的增長有賴于國家精神資本的增長”[1],即已將思想意識納入經濟分析中。這一思考方式,此后被德國歷史學派所繼承并發揚[31],在凡勃倫(Thorstein B.Veblen)那里則與對制度演化的分析結合起來。[32]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史將“信念及其演化方式”視為理解經濟變遷過程的關鍵,[33]這誠然是該學派的最新發展,卻不過是復刻了更“舊”的那些學派的精神而已。這一強調思想意識重要性的學術傳統,能夠用以分析國家參與工業活動的演化性。從一種新李斯特主義的角度看,世界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及民族國家間的相互競爭,構成了體系演化的動力,也是國家參與工業化的最主要動機。但這一動機并非某種均質的實體,而是精英階層對國際競爭的性質的認識,以及對競爭的強度的感知。精英階層對國際競爭性質與強度的判斷,與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結合在一起,會形成不同的演化組合。有些精英可能會認為根本沒必要采取工業化作為競爭手段,因為他們根本不打算以較高的強度投身于國際競爭。例如,美國內戰前,南方的種植園主會更傾向于依附英國工業,而為自身牟取經濟利益。追根溯源,早在獨立之初,美國統治階層中的部分精英就不認為維持中央政府、常備軍以及建立海軍有任何必要。而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又基于不少精英認為隔開美國與歐洲的大洋確保了美國的安全。按這些精英的設計,美國只能成為一個由地方上的利益集團主導的軟國家(soft state),經濟上依附歐洲列強,缺乏基本的武備,與日后的拉美國家無異。但包括漢密爾頓在內的另一些精英則認為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是有必要的。為了發展支撐富強國家的工業,漢密爾頓認為可以采用保護主義手段,適度犧牲眼前的局部的經濟利益,來換取長遠的整體性的收益。[34]漢密爾頓的觀念后來贏得了他最大的反對者杰斐遜的支持,而杰斐遜的轉向顯然與1812年英國對美國的侵略有關。[35]因此,美國的歷史極佳地詮釋了一國精英階層對國際競爭的認知與感受是如何塑造工業化路徑的。進一步說,作為有能力推動工業化的精英階層,并非鐵板一塊,國家作用于工業化的路徑與形式,取決于精英階層內部競爭的結果。在美國,這一競爭是以內戰作為最終的表現方式并告一段落的。
因此,以國家為中心來考察,工業化實際上是由國際競爭引發的、國內具有不同觀念的精英斗爭的結果。精英固然是利益集團的實際構成者,但他們可以具有多樣化的動機,其中某些動機并不局限于他們眼前的物質利益。當那些具有整體及長遠利益觀的精英占據上風,并找到適宜的手段高強度地參與國際競爭時,工業化就能夠啟動并得以維持。這是國家作用于工業化的一般性機制。然而,各國歷史千差萬別,是因為在完全偶然性的時空環境中,特殊的情境將一般性機制塑造成了不同的樣貌,并賦予其合理性。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特殊性”,只能從這個意義上加以理解。
回到歷史,顯而易見的是,在清朝滅亡之際,中國的國家遠未能“凌駕”市場,相反,整個國家的工業化看上去走上了主要由市場和私人資本支配的道路。辛亥革命以后,在北洋政府時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列強后撤,中國企業自動地獲得了一個具有保護效應的國內市場,無論輕、重工業部門均欣欣向榮。而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軍閥政權,從工業行政的角度看,沒有太積極的作為,反而具有“掠奪型國家”的特征。因此,北洋時期中國工業的發展也經常被學者舉為市場與私人資本優越性之證據。[36]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家缺位的危害就開始顯現。主導性的輕工業部門棉紡織業,在“黃金時代”結束后迅速陷入結構性蕭條,而中國企業在日資企業的威脅下難以取得發展。[37]日資在華企業的優勢固然是技術性的,但不可忽視的是,直到國民政府時期,日資企業仍能在中國市場上獲得國內稅優待,從而化解了國民政府通過提高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的努力。[38]而日本政府為了給本國企業爭取在華特權,是不惜利用在華軍隊對國民政府進行恫嚇的。[39]而在重工業部門中,一戰后的不景氣也極大地打擊了中國企業,一批領軍企業因為經營困境而被外資兼并,政府則缺乏扶助舉措。[40]但是,同期的日本雖同樣遭遇不景氣的周期,其造船業等戰略性部門仍通過政府的補貼與訂單得以維持。[41]并且日本的戰略性部門此后成為其侵華戰爭的物質基礎。
然而,日本對中國持續不斷的侵略,也成為中國國家建構與工業化進程的轉折點,并使中國的工業化道路看上去又有了某種“特殊性”。伍曉鷹認為,在南京國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后,主導了一場重工業化運動,并認為這一重工業化運動“相當順暢地延續了”晚清洋務派的工業化路徑,而其動因則包含了相關利益集團的“個人利益”。[2]這是徹底不符合史實的。首先,1937年之前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導的重工業建設,是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斗爭中艱難推進的,根本談不上是當時主導性的工業化路徑。在1927年及之后的幾年間,國民政府產業政策制定者的趣味相當符合比較優勢原則,關注點集中于輕工業。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出于民族存亡的考慮,政府內部的蔣介石一系才創辦了資源委員會,并開始從事側重于軍工的重工業建設。而一直到1935年,汪精衛一系的實業部部長陳公博還認為中國應該只發展輕工業,以免刺激日本。即使在蔣介石集團內部,也存在著“造不如買”的思想,并由此延誤了資源委員會創辦重工企業。[26]其次,在伍曉鷹的整個敘事中,仿佛清末以來中國一直有一個不曾斷絕的利益集團,出于自己所在部門的私利而極力推動重工業化。但是,20世紀30年代推動重工業化的技術官僚,主要是懷著救國熱情而從學術界進入政界的知識分子,是一批自命要當“新的官僚”的精英,他們不僅和晚清洋務派沒有直接傳承,而且瞧不起那些缺乏現代技術知識的前輩。[42]其中一些留學生如果繼續留在海外治學,很可能會有更大的個人成就,而他們回國辦工廠挫折不斷,被人認為“后半輩子都浪費掉了”[43]。如果伍曉鷹更細致地閱讀他所引的關于資源委員會的研究成果,就應該清楚他有意無意貶低的那個“利益集團”,在當時的官場是相當清廉的異類。[44]因此,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并沒有很顯著的重工業化運動。1933年,中國的機械、金屬品、電器、交通用具、土石、水電氣、化學品制造等7個制造業部門的總產值為488706000元,而在這7個部門中,有些細分行業是不屬于重工業的。然而,輕工業中僅紡織業一業的產值就有879291000元,為前者的1.8倍。[45]當時中國的工業結構即如此。而推動重工業建設的技術官僚群體,如果非要將他們界定為一個“利益集團”,那么,他們也是和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漢密爾頓等人一樣,是力圖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體系中建設獨立國家的“利益集團”。
由此看來,1927~1937年中國的工業化符合前述圖式:在世界體系內部國際競爭的壓力下,國家內部圍繞著要如何應對競爭,產生了擁有不同觀念的精英間的斗爭。那些主張重工業化的精英,恰好是最具有超越個人私利動機的精英,體現了比較政治經濟學所謂的“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46]但是,到1937年為止,精英間的內部斗爭并未決出明顯勝負,而日本已全面侵華。日本的侵略反而使中國的精英達成了要發展重工業的廣泛共識,并成為某種延續至1949年后的邏輯。這一結論也符合伍曉鷹的推測,但在具體的歷史因果關系上,他又錯了。目前,學術界不乏一些研究,將1949年后中國大陸的重工業優先戰略以及計劃經濟手段的起源,追溯至抗戰時期,[47]只是從抽離具體歷史事實的邏輯角度看,這一觀點具有合理性,因其抓住了某些類似現象背后共通的演化機制。但是,兩個相似的歷史現象即使在同一空間內相繼發生,也不能認為前者一定會是后者的直接起源。所以,那種認為“很難想象”1949年后留在中國大陸的資源委員會人員不會因為自身利益而維護重工業化路徑的論點,[2]也就只是一種“想象”了。歷史事實是,盡管在解放初期,新政權吸納了原國民政府重工業建設系統的大量人員,并對其高層授予要職,但這些前政權人員也僅僅只能起到提建議的作用,而其建議即使被采納,在實際執行時也未必能落實。[48]舊政權人員的這種實際處境,本應是簡單的常識,用不著去“想象”其它的可能性。中共在建政之初,統一全國的解放戰爭尚未結束,因此,大量軍事將領被安排在重工業等戰略性部門擔任領導,這些將領對于重工業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有極為直接的認識,而新政權也極為重視培養自己的技術與管理人才。[26]因此,新政權在觀念上并不依賴舊政權人員,在行動上則采取了全面削弱舊政權人員作用的策略。這樣一來,盡管歷史確實存在著某種一致性的邏輯,卻并不存在一個前后一致的“利益集團”,而基于那種想象中的“利益集團”作出的所謂邏輯一致的經濟學解釋,與歷史無關。進一步說,國民政府留在大陸的重工業廠礦固然為新中國的工業化準備了最初的物質條件,可一旦能夠利用蘇聯提供的技術與設備,新政權就會放棄利用舊廠礦的計劃,而將前政權的“遺產”安在相對次要的位置上。[49]
于是,一個更加歷史主義的解釋是: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的民族危機中,中國的部分精英形成了發展重工業來捍衛國家獨立的共識,這種共識是超越黨派的。而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國家發展缺乏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必須以人為手段扭曲市場要素的自然流動,將其導向重工業部門,這就是國民黨技術官僚也會對蘇聯式計劃經濟表示認可的原因。[42]在戰爭期間乃至戰后,甚至連希望政府救濟的私人資本也主動請求國家采取某種程度的計劃經濟,[50]可見當時的思想氛圍。直接師承蘇聯的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后采取的發展戰略乃是大勢所趨。其實,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內部也不是沒有主張其它工業化路徑的聲音,但朝鮮戰爭這一體系性因素又強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共識。[51]此后,很明顯的事實是,中國政府每一次強化重工業建設,都與國際形勢有關。例如,三線建設是對越南戰爭升級的應對,而21世紀初的所謂第二輪重化工業化,就航空、船舶等工業而言是不能排除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等因素的。但是,這并不表示中國的重工業化缺乏合理性。重工業作為資本品工業部門,其優先發展,不過相當于一種涉及基礎設施、技術設備等物質基礎的先期投資。早在一戰后,國民政府希望通過創建紡織機械制造業來帶動紡織工業的發展,[52]已經具有此種考慮。新中國成立后,紡織工業部部長錢之光采取了自主發展紡織機械工業的戰略,實際地促成了紡織工業的發展,加速了紡織品的擴大供應。[53]因此,中國近代以來的重工業化,雖然經常不符合比較優勢,而且呈現出國家“凌駕”市場的“非自然”態勢,但具有內在的軍事—經濟合理性,是超越私利的精英集團應對體系壓力的產物。換言之,這種“反常”的工業化道路,乃是世界體系的演化機制作用于中國特定時局的產物。然而,如果對日本經濟史加以考察,又會發現這一國家主導的重工業化道路,并不那么“獨特”。[54]
綜上,中國工業化道路中的所謂國家“凌駕”市場這一特征,就整個近代歷史來看,并非是一直延續的結構,而是在特定時期被反復建構的行為。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20世紀30年代以后國家力量的強化,是世界體系內部國際競爭的結果,也是對此前國家衰弱的一種反應,自有其政治—經濟功能上的合理性。然而,在新李斯特主義圖式中不存在歷史決定論,也就是說,中國并不必然走上目前所知的工業化道路。實際的工業化路徑,是由具有不同觀念的精英的斗爭塑造的,而這種事關國家走向的斗爭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只要認識到在抗日戰爭前夜,中國政府內部也好,社會輿論也好,都存在著基于經濟理由要“將海軍根本取消”的論調,[77]就可以想見這種斗爭是何其激烈。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在20世紀后半期由國家“凌駕”市場的工業化道路,是國際競爭迫使精英階層取得共識的結果,是世界體系演化的自然選擇。
參考文獻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商務印書館,2012.
[2]伍曉鷹.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再思考:對國家或政府作用的經濟學解釋[J].比較,2014(6).
[3]賈根良.李斯特經濟學的歷史地位、性質與重大現實意義[J].學習與探索,2015(1).
[4]賈根良.新李斯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何以成立?[J].教學與研究,2015(3).
[5]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上)[M].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89.
[6]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M].商務印書館,2009:53.
[7]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4:20.
[8]道格拉斯·諾思,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M].華夏出版社,1999:192.
[9]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M].Routledge,1994:31.
[10]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歷史意義[M].商務印書館,1936:61.
[11]Lars Magnusson.Nation,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Visible Hand[M].Routledge,2009:41-45.
[12]李新寬.國家與市場:英國重商主義時代的歷史解讀[M].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129-130.
[13]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M].New York:Bantam Dell,2003.
[14]彭南生,嚴鵬.技術演化與中西“大分流”——重工業角度的重新審視[J].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3).
[15]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5:255.
[16]邁克爾·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32.
[17]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馬基雅維里主義[M].商務印書館,2008:51-52.
[18]龍多·卡梅倫,拉里·尼爾.世界經濟簡史:從舊石器時代到20世紀末[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191.
[18]彭南生等.固守與變遷:民國時期長江中下游農村手工業經濟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60-61.
[20]山本進.清代社會經濟史[M].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32.
[21]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5:282.
[22]陳旭麓.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六·上海機器織布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2.
[23]寶鋆等.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4冊[M].中華書局,2008:1467-1468.
[24]彭南生.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M].中華書局,2007:232-239.
[25]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M].人民出版社,2012:1465-1466.
[26]嚴鵬.戰略性工業化的曲折展開:中國機械工業的演化(1900—1957)[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1.
[27]榮德生.榮德生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32.
[28]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8.
[29]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M].三聯書店,1998:5.
[30]馬克斯·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M].東方出版社,2009:11.
[31]季陶達.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選輯[M].商務印書館,1978:346.
[32]托爾斯坦·凡勃倫.科學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M].商務印書館,2008:59-61.
[33]道格拉斯·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5.
[34]Alexander Hamilton.Alexander Hamilton[M].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2001:701.
[35]里亞·格林菲爾德.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68.
[36]杜恂誠主.中國近代經濟史概論[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74.
[37]森時彥.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282.
[38]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M].商務印書館,2011:292.
[39]久保亨.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72.
[40]嚴鵬.企業家精神、國際契機與民族國家建構——辛亥革命前后中國機械制造業的發展(1900—1920)[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
[41]Yukiko Fukasaku.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Mitsubishi Nagasaki Shipyard,1884-1934[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38.
[42]李學通.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M].中華書局,2009:234.
[43]吳大猷,黃偉彥.早期中國物理發展的回憶[M].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108-109.
[44]鄭友揆,程麟蓀.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313-315.
[45]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M].商務印書館,2011:95.
[46]西達·斯考克波.找回國家[M].三聯書店,2009:10.
[47]卞歷南.制度變遷的邏輯:中國現代國營企業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289-292.
[48]張柏春.民國時期機電技術[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223.
[49]關云平.中國汽車工業的早期發展(1920—1978)[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5-60.
[50]嚴鵬.中共建政初期同業公會與產業發展之關系:以上海機械工業為中心(1949—1956)[J].史學集刊,2015(2).
[51]Evan A.Feigenbaum.China's Techno-Warriors: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6-21.
[52]嚴鵬.中國紡織機器制造公司的技術管理(1946—1948)[M]//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17輯.上海三聯書店,2014:117-132.
[53]錢之光傳[M].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388-403.
[54]高橋龜吉.戰后日本經濟躍進的根本原因[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19.
責任編輯:蔡 強
作者簡介:嚴鵬(1984-),男,湖北武漢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4ZDB122)
收稿日期:2015-10-11
中圖分類號:F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5)1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