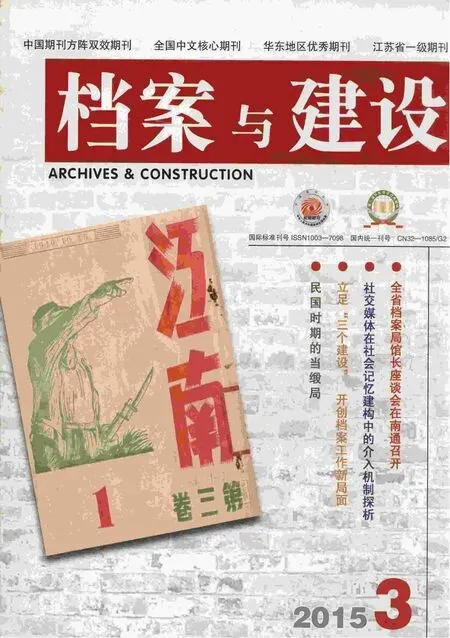社交媒體在社會記憶建構中的介入機制探析
孫洋洋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北京,100872)
萊布尼茨說過:“現在包含著過去,而又充滿了未來。”[1]社會記憶與人類歷史進程密切相關,是與歷史的溝通,也是與現在的對話,更包含著未來,對于民族和人類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自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體記憶”以來,社會記憶作為一種理論已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是立足當下而對過去的一種建構,強調其當下性和社會建構性。后保羅.康納頓在《社會如何記憶》一書中延伸出了社會記憶的概念,更強調“記憶不是一個復制的問題,而是一個建構的問題”,并關注了社會記憶的傳遞與維系,以及權力在社會記憶建構中的作用。上述二人的理論堪稱是社會記憶研究的范式,奠定了社會記憶作為一種建構的理論基礎,后來多方學者對社會記憶展開的研究大都是在他們的理論影響下進行的。
在當今信息時代的背景下,科學技術飛速更新,人類生活瞬息萬變,全球化浪潮強勢來襲,多元的文化不斷沖擊與融合,社會記憶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臺灣學者王明柯認為,社會記憶即所有在一個社會中借用各種媒介保存、流傳的“記憶”。[2]可見,媒介在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媒介已不局限于文獻、行為儀式和形象化物體,社交媒體作為一種更加直接、突出的媒介,依托于自身的特定屬性,通過影響建構社會記憶的主要因素如社會框架、權力架構及記憶的維系與傳遞等,正直接而強烈介入到社會記憶的建構中。
1 社交媒體簡述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也稱為社會化媒體、社會性媒體,指允許人們撰寫、分享、評價、討論、相互溝通的網站和技術。馮惠玲教授將社交媒體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創作發表型,如博客、微博和論壇網站等;2.資源共享型,主要指照片、視頻、音樂分享網站如instagram 等;3.協同編輯型,如wiki 及社交問答型網站;4.社交服務型,如check- in、微 信、iChat、MeChat 等;5.C2C 商 務 網 站,如ebay、淘寶網等。結合社會記憶的內容,筆者所討論的介入社會記憶建構的社交媒介主要指前四種類型,第五種鮮少涉及。社交媒體之所以能夠介入社會記憶的建構與其本身的屬性是不可分離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社會性,主要表現在將社會個體廣泛聯結并促進社會個體間的多重互動兩個方面。二、即時性,社交媒體的即時性是其突出特點,通過信息的即時傳達,加速了信息的產生、流轉、凝結甚至消失的速度。三、開放性,社交媒體具有社交媒介和信息承載體的雙重屬性,必然具備明顯的開放性,促進了信息流通。四、技術性,社交媒體的活躍是以科學技術作為支撐的,并以技術為依托不斷強大。
2 社交媒介的介入機制
2.1 以復合式社會框架介入
哈布瓦赫認為,人們正是在社會交往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加以定位[3]。個人記憶的源起必須置于群體互動的框架,個體溝通交流的過程中保持下來。由此可見社會框架對于社會記憶建構的重要性。隨著時代發展,社會框架已不同以往,由傳統意義上的單一式向復合式轉化,即社交媒體搭建的線上社交框架與現實社會中的線下社交框架相互交織的復合模式,也為社會記憶的建構帶來了新影響。
2.1.1 泛在網絡基礎上的時空虛化
復合式社會框架以泛在網絡為基礎,淡化了社會記憶的縱深感。泛在網絡是指以人為本,利用通信網、互聯網、物聯網的高度協同和融合以及其他一系列新的信息網絡技術,實現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更全面的相連相通,并提供個性化的信息服務和應用的共融網絡[4]。而筆者所言的復合式框架尤其是其中的虛擬框架正是以這種泛在網絡為依托,通過社交媒體即時、全面的互聯共通搭建的。在這種社會框架中,信息“實時”傳播和人際交往帶來了時間的極大壓縮,形同造成時間序列及時間本身的消失[5]。
哈布瓦赫說,每一段“集體記憶”都需要得到具有一定的時空邊界的群體的支持。復合式社會框架正是突破了時空邊界,縱向來看,以微信、IChat 為代表社交媒介具有突出的信息傳播即時性,傳與受實時同步,事實和意見被同時生產和擴散,事實尚在發生之中,情感調性、道德框架、價值底色既已凝結,“實時”、“當下”、“淺思考、淺交往”消解了社會記憶的歷史縱深感及附著其上的情感、倫理和信仰價值[6],社會記憶的“當下性”和“斷裂性”也更為明顯。橫向來看,時間的虛化也跨越了空間的維度,虛實相交的社會框架為社會記憶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更為寬廣的環境,伴隨信息的迅速傳播實現社會記憶的無限外延,相對于社會記憶的縱深感而言,其扁平化和延展性的特征正在不斷凸顯。
2.1.2 身份認同的廣義化和區域化
復合式社會框架造就了身份認同的廣義化和區域化,影響著社會記憶的分合。在以往的社會記憶研究中,社會記憶的探討常常放在宗族、種群、社會組織中來探討,并在身份認同與社會記憶建構的互促關系方面達成一定共識。如鐘年教授在《社會記憶與民族認同》中將流傳于許多瑤族地區的《憑皇券牒》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入手,考察其起到的凝聚瑤族族群認同的作用[7];王明珂研究員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實證性地考察了華夏邊緣族群的擴張以及其社會記憶演變[8]。在虛實共融的社會框架下,影響隨著社會記憶建構的地緣、族群、組織等因素的重要性有所消減,身份認同的達成也不僅僅依賴于此。隨著框架趨于向虛實共融和區域化的方向發展,身份認同呈現出廣義化和區域化的特點。
首先,其廣義化是從一種宏觀視角出發,將復合式框架中的個體均視為社交媒介的用戶,他們在共同的虛擬空間中以社交媒介為聯結點,擁有自己的交往規則和價值觀,線下不同族群間的社會記憶可以在虛擬框架中相互滲透、碰撞或融合,“他人”可以介入“我們”社會記憶的建構,也可使已成型的社會記憶在虛擬空間中重構或者解構。其次,區域化是從微觀視角出發看待社交框架內的身份認同,筆者在此概括為兩種類型:其一是媒介區域化,是指部分社會個體在媒介設備或應用軟件的客觀設置下,形成同一交往區域,達成統一的身份認同,在交互中共享同樣的社會記憶。其二是價值區域化,面對同一社會事實,虛擬框架中的個體時常會集群為持不同看法的多個區域,后來的社會個體多會在淺思考的情況下加入其一,形成同樣的記憶,從而就導致社會記憶的總體結構呈現區域化特點。
2.1.3 虛實交織的社會互動
復合式社會框架打造了虛實交織的社會互動模式,共謀社會記憶的價值形態。同一社會記憶,在不同的時空境遇中往往是不同的。以往的社會學研究中考察的多是同一記憶不同時間的異同,而筆者所強調的是同一記憶不同空間的的異同,即虛實(線上/線下)社會框架間的互動對社會記憶建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實事“虛構”。現實社會框架中的社會記憶可通過任一媒介活化于虛擬框架中,并在其中得到重新審視,一定情況下還會被解構或者重新建構,以新的社會憶形態植根于個人記憶中。二、虛實同構。口述歷史是某個或多個社會個體以講述的方式對過去的記憶的一種建構,而在這種建構過程中,會有很多聲音透過社交媒介傳來,共同形塑社會記憶。三、乘虛入實。以蘆山地震為例,許多人在地震發生后通過微信、微博、發聲,關于汶川地震、日本地震和臺灣地震的各種記憶不斷地被調用、激活和解讀,并被引入到災難反應機制的討論中,促進災害應對機制的不斷完善。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社會記憶通過社交媒介的保存和激活,建構地更加完整,去指導實際的社會活動。
2.2 以制衡式權力架構介入
康納頓認為,“控制一個社會的記憶,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利等級。”相較于哈布瓦赫,康納頓更為明確地將權利與“社會記憶”聯系了起來,認為權利對社會記憶具有統治和控制功能。這也是康納頓的核心觀念,并為后代學者廣泛認同。社交媒介的介入,也使得權利架構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顯性權利隱性化、隱形權利顯性化的趨勢下將權力架構形塑至一種相對制衡的姿態。
2.2.1 政治權利和精英記憶的淡化
盡管康納頓強調權利對社會記憶建構的影響,但是他更為看重的是政治權利的介入。后代學者在本質上也認同這種觀點,認為權利等級在社會記憶的選擇方面有重要影響,并且補充了權力視域下精英記憶在社會記憶建構中地位顯要的觀點。如張學良在1991年前后接受訪談時所談到的蔣介石形象由恭入貶,是權利介入社會記憶建構的典型體現。首先,在社交媒介搭建的社會框架中,每個社會主體都擁有較為完整的話語權,可以借助社會媒介針對過去隨時隨地地發出聲音,在沒有政治權利引導的情況下參與社會記憶的建構。其次,社會個體可通過社交媒介發揮建構社會記憶的主動權,借助廣泛、即時的存儲和共享功能將自己的歷史活動記錄凝結、保留并分享給他人,將其置于社會記憶的建構中,如人們將自己的各地游歷記憶以照片形式分享至Instagram網站,或者將自己的生活見聞以微博形式記錄下來并分享給他人。
2.2.2 意見領袖—另一種權力的凸顯
康納頓曾說過,即使人們不再相信政黨或西方等宏大的支配話語,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消失了,它們已然是作為當今形勢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悄悄地發揮作用。伴隨著社會媒介的介入,政治權利的影響逐漸淡化,但權力之于社會記憶建構的影響卻并未消減,而是在社交媒介搭建的社會框架和再造語境下,發生了形變,我們稱之為“意見領袖”,該詞源自于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及Elihu Katz的“兩級傳播”理論,是指一個對于媒體熟悉、解釋媒介訊息或是做為一個二次傳播的訊息者[9]。他的意見能夠在自己團隊里收到重視,受到追隨,也有可能成為別的意見領袖的追隨者。結合社會框架中身份認同廣義化和區域化的狀況,意見領袖的影響不可小覷,往往能夠引導海量用戶的意見走向。在社會記憶建構的過程中,意見領袖往往充當了權利控制者,在虛擬空間對社會記憶的選擇、調用、激活和保存過程所發出的聲音會得到單個或多個部落跟隨,并形成記憶范式在虛實交織的社會框架中迅速擴散。
2.2.3 反記憶現象凸顯
社會記憶不僅受制于各種復雜的權利關系,對過去事實的選擇和組織也會受到各種主觀感受以及偏見的影響,因而,“社會記憶”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個體化和具體化的[10]。個體在權利運作的過程中,并不是束手無策的,對于權利選擇之外的社會記憶,會主動地進行保留或反抗性強調。特別是在社會媒介介入的前提下,政治因素減少,使得權力架構走向一種更為平衡的態勢,社會個體擁有更為充足的主動性不受權利引導,而是根據個體或小眾的主觀意志去關注和保留邊緣化的社會記憶,并在一定社會條件下逆襲為主導記憶。此外,社會媒介的交互性會促進邊緣的或處于邊緣化層面記憶的多方輻射和長久保存,進而影響社會記憶的建構。
2.3 以催化型維系方式介入
社會記憶如何維系與傳遞是康納頓反思和超越哈布瓦赫的重要體現,在關注記憶“當下性”的基礎上強調了社會記憶的“延續性”。社會記憶本身是維系與忘卻的統一體。康納頓認為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是維系和傳遞社會記憶的關鍵,而忘卻是壓迫性忘卻背景下產生的。社交媒體的介入條件下,社會記憶的快速擴散和凝結伴同著快速冷卻和消散,對其維系和傳遞也產生了新的影響。
2.3.1 文化記憶的凝結
阿斯曼在《文化的記憶》一書中分析了從個人記憶到社會記憶,再通過溝通和分享形成溝通記憶,最后形成一種形式較為普遍和清晰地文化記憶。文化本身具有更為持久的保鮮性和傳遞性,如樂府詩是從民間采制的廣為流傳的詩歌,是民間記憶凝聚為文化形式的體現,時至今日,我們依舊可以通過樂府詩回憶起當時的生活映像。除此之外,戲劇的傳唱也是社會記憶凝聚為文化記憶得以傳遞的典型體現。而社交媒介的介入通過廣泛的交互和分享使得社會記憶向溝通記憶轉化,在達到一定臨界點的時候形成一種文化記憶保存下來,如網絡上的各種語體,在多種社交媒介中的廣泛轉發和應用促使其以一種語言文化形式保存和傳遞,并作為一種文化記憶作用于社會記憶的建構。
2.3.2 網絡操演的流行
哈布瓦赫強調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是維系和傳遞社會記憶的關鍵,其實質是強調在當下社會背景下的一種慣性記憶形式,正如我國古代盛行的祭祀儀式,有利于避免社會記憶在文本傳遞中因記憶差錯出現的增損,便于確保其“記憶穩定性”。而當下的信息時代,社會媒介的介入使得社會記憶的維系漸漸獨立于身體實踐類的慣性記憶形式,而是以一種網絡操演的姿態進入公眾視野,即。例如,在某個重要的紀念日,公眾會借助社會媒介分享文字、圖片或視頻等表達自己情感,并廣泛傳播,在社會框架中蔓延開來,從個體行為變為社會行為,從而促進這種社會記憶的活化。
2.3.3 技術背景下的“累積”和“忘卻”
社會媒介的后臺支撐是強大的信息技術,特別是在云計算和大數據的背景下,社會媒介可在交互的前提下鏈接更為強大的信息存儲和即時檢索設備。以文本、言語和身體實踐等維系社會記憶的形式都帶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而社交媒介附帶的技術使得社會記憶的維系表現為客觀性的信息積累。這種積累的信息量固然可觀,存續的穩定性也比較強,但是在其長期或者跨代存續過程中,避免了人格的熏染和異時代的解讀,更像是被“冷藏”起來的記憶,是否還可被稱為社會記憶有待商榷。記憶本身是維系和忘卻的統一體,在技術積累的前提下,信息推移模式的忘卻方式也應運而生,在信息快速去陳推新的過程中,舊信息隨著推移逐漸消散,一旦不存在于任何數據庫,便有可能徹底銷聲匿跡,堪稱是客觀社會條件下的主觀忘卻,沒有任何壓迫卻自然而然。
3 結語
社會記憶包含著人類社會的歷史,也昭示著未來的發展,是促進社會再生產的一筆非物質財富,正確地、及時地保留社會記憶是每個時代的題中之義。當下社交媒體的介入使得社會框架趨于復合、權利架構趨于制衡、維系方式趨于催化,從而影響了社會記憶的建構。如今的信息時代,新技術層出不窮,社交媒體的介入只是影響社會記憶建構的一方面,我們需要更加科學深入地研究其它介入機制,才能促進社會記憶建構的不斷豐富和完善,彰顯社會記憶的深遠價值。
[1][德]恩斯特·卡西爾.2003.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和歷史心性[J].歷史研究,2001,(5):137-147.
[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2002.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傅維剛,王娜.泛在網絡信息生態系統的構建及失衡防范策略[J].圖書情報工作,2013,(6):64-68.
[5][美]曼紐爾·卡斯特.2001.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6]胡百精.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3):98-106.
[7]鐘年.社會記憶與民族認同[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0,(2):25-27.
[8]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9]Lazar,sfield,P.The people’s choice[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 sity Pr ess,1948.
[10]孫峰.從集體記憶到社會記憶—哈布瓦赫與康納頓社會記憶理論的比較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