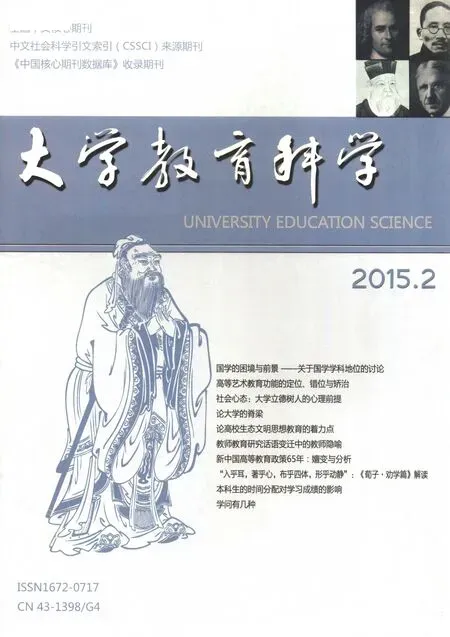論大學的脊梁
□ 李 忠 閆廣芬
一
社會的延續與發展需要創新,創新的關鍵在于人才,培養創新人才是大學義不容辭的職責。然而,目前的中國大學顯然難以承擔這種職責。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錢學森無奈地向溫家寶總理坦言: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按照培養科技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嚴重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大學培養不出創新人才”——“錢學森之問”不僅“很大地刺痛”[1]了溫家寶總理,也成為中國大學以及大學人必須面對并予以解決的問題。
“只有社會上出現更多有靈魂、有眼光、有胸懷、有脊梁的大學,才能真正為創新人才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堅實土壤。”在2012年12月廣西師范大學80周年校慶“高校與社會:高端人才培養的責任與途徑”論壇上,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吳康寧就創新人才培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吳康寧看來,大學要培養創新人才首先要有自尊,這種自尊基于大學的脊梁。“不管你是北大、清華,還是廣西師大、南京師大,我們都應當成為有膽量、有硬度的大學,并因此而成為自尊的大學。你不自尊,別人便不尊你。沒有基于這一原則的脊梁,大學根本就沒有培養創新人才的資格。因為創新人才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依附,拒絕威權。”[2]吳康寧以師范大學教師、副校長的身份對“錢學森之問”予以回應,這種答案不僅來自對教育理論的領悟,更來自切身的教育經歷、體驗與體悟。
脊梁俗稱脊背,為全身骨骼主干所在,引申為有意志、節操、膽識、信念和剛強不屈且能起主導作用的力量。即使無生命物質,脊梁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如山脊是維持山體的重要構成,橋梁是橋得以成形并發揮作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有生命物質,脊梁尤為珍貴,它甚至是物種進化程度的標識。對人而言,脊梁讓人得以直立,是人成為人、人成為自己的標志,也是人與人以及由人構成的組織之間的差異所在。大學脊梁由大學的精神及其支配下的理念、制度與行為鑄成并從中體現。思想自由與人格獨立是大學的精神。如何守護精神,不同大學有不同做法,大學的理念、制度與行為是這種做法的具體體現。作為知識精英匯聚之地與培養未來知識精英、政治精英、財富精英和社會精英的場所,大學需要有自己的脊梁,需要基于這種脊梁的自尊。
大學的脊梁使大學成為大學而非其他社會機構。因為,在所有人類公共機構中,只有大學能夠超越當前準則,注意到未來的多種可能,并通過目前的判斷注意到突發的種種機遇。大學通過自己的研究創新知識、創新價值觀,為未來社會發展提供思想資源、指明方向,使社會按照人們期望的方向發展而非相反;大學通過教學推廣知識并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引領社會發展而非成為現存社會的被動適應者;大學通過專業技能考察知識并通過出版傳播知識,校正可能出現的歧路并擴大影響,帶動社會發展而不是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者。大學是人類把不可或缺的智慧世代流傳的殿堂,大學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她不同于其他社會機構。這需要大學有脊梁、能自主、有自尊、能擔當,能夠承擔這種職責并扮演這種角色。沒有基于這種脊梁的特質,大學將失去自我而雷同于其他社會機構。
二
大學脊梁的性質決定著大學是否在扮演或在多大程度上扮演著大學的角色。依附性的大學脊梁是扭曲的:依附于宗教的大學,扮演著教會角色;依附于政治的大學,扮演著政府機構角色;依附于利益的大學,扮演著企業角色。脊梁挺拔的大學思想自由、精神獨立,扮演著大學角色。她自主而不依附:大學知道,在現代社會,從自由向依附的任何倒退都是精神不健全的標志,因為這種倒退與人類已經達到的發展階段不相符合。她謙虛但拒絕權威:大學知道,與浩瀚宇宙相比,人類所知甚少,人類甚至對自身認識也極為有限,在未知面前,每個人都是小學生。她有遠見且能持續努力:大學知道,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因為人類歷史已經展示了無數的不確定領域,沒有人能準確預測二十一世紀會發生什么事情。正如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莫蘭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復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的報告所言:“今后人類征途的不可知的特點應該促使我們培養準備應付不測事件而處理他們的頭腦。所有身負教育之責的人們應該走向迎擊我們時代的不確定性的最前哨。”[3]教育是“未來的力量”,大學是改變現實與創造未來最強有力的力量之一。正因如此,大學必須有并全力守護自己的精神和脊梁:她有信念但不固執,她自尊但不自負,她謙虛但不自卑。
大學脊梁決定著大學對自己的定位及其思考與行為方式。大學有其共性,但一所大學區別于其他大學的標志在于她所秉持的精神、理念以及對這種理念的堅守與踐行程度,即大學的脊梁還使大學之間有了差異。大學的精神與理念以大學憲章方式體現,從大學的思想、制度與行為中呈現。為了“求是崇真”、追求“真理”而設的哈佛大學,恪守“察驗真理”之旨,致力于“促進知識并使之永存后代”;為了使青年“學習藝術和科學”設立的耶魯大學,追求真理、提倡質疑、反對迷信,永遠強調責任感、蔑視權威、追求自由并崇尚獨立人格;麻省理工學院秉持“手腦并用,創新世界”之理念,謹守學術精神、探究精神和評判精神,致力于解決世界面臨的主要問題;為了讓“所有的人可以學到任何他想學的學科”而建成的康奈爾大學,持續致力于創造公平、平等的未來,反對盲從和不加辨析地接受。大學也在變,但精神不變,變化的是如何能更好地堅守并踐行這種精神,使其脊梁更健壯。
大學脊梁的堅挺需要政府認識到大學特性并給大學以充分的自治,使大學能夠自主,讓大學先成為大學。早在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在著名的《學會生存》報告中指出:“一個官僚主義的、慣常脫離生活的體系會感到難于接受這樣的想法,即學校是為兒童而設立的,而不是兒童為學校而生存的。上面發號施令,下面唯命是聽,建筑在這樣基礎上的政權,不可能發展自由教育。在工作一般處于隔絕狀態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要想培養學生愛好創造性的工作,這將是困難的。”[4]今日中國大學卻正好處在這種困境之中。“錢學森之問”是一種現象、一個問題,吳康寧教授則給出解答:“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前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約束。”政府部門通過校長任命、資源分配、等級區分等做法,“形成對大學的超強控制,我們的大學不是自己在辦學,而是政府部門在辦學,是政府官員在辦學。”歷史學家、前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先生則對“政府官員辦學”的弊端進行了分析。他指出,“政府官員辦學”的最大弊端在于把人當做物,忽視對人的有效關注:“從深層根源來剖析,主要問題仍在于主管教育者本身缺乏正確的認知。……現今教育當局主事者把各項重大措施都名之為‘工程’,實際上是忘記了人性不同于物性。”[5]
依附政治、政教合一是中國古典教育的突出特點,這種教育曾在維護統治以及維持社會秩序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然而,它不健全。因為,依附性教育以工具或適應他人(或物)自居,以隨從附和作為處事原則,無視自我的同時導致平庸,它培養出的是充滿依附性、人格不健全的忠臣孝子。這種教育難以應對社會變革并引領社會發展,在面對列強軍事、經濟、文化侵略時舉止乖張、捉襟見肘、弊端盡顯,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災難,成為眾矢之的,終成被唾棄的對象。正是對單純適應政治的依附性教育的變革,民國時期出現的一批有脊梁的大學,甚至在戰時出現的著名的西南聯大,不僅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引領者與推動者,而且譜寫了中國大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三
大學是國家最高學府而非政府機關的延伸,是培養領袖人才的地方而非官僚養成所。國立中正大學校長胡先骕說:“大學校長的地位極其崇高,政府當局和整個社會應該把他們尊為賓師,決不可以視同一般之高級政府官吏,拘之以功令,困之以事務,使賢者裹足,不肖者濫竽,則庶幾收領袖群英宏獎學術之效焉。”[6]因為,如果校長是官吏,在更高權力面前必須低頭,在學校中又以長官面目示人,這種做法違背大學的基本精神。大學是有夢想的人的聚集之所,是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這不僅需要大學有脊梁,同樣需要大學中人有脊梁。
校長作為大學的舵手,首先要有脊梁。視“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所”的蔡元培,將北京大學改造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所,吸引大批學者云集,這些學者不僅使北大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成為新思想、新知識和新價值觀的集散地,而且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視大學為研究學問之所、實現理想之地的羅家倫,將“為學問殉道”視為人類最光榮、最高尚的事業,將“能喚起他人對于此事的覺悟”視為對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致力于清華建設,終使清華由留學預備機構升格為國立大學;視“大學為大師之謂而非大樓之謂”的梅貽琦,認為大學存在的價值體現在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為達目的,筑巢引鳳,在吸引大師的同時注重培養通才以便成就未來的大師,終使清華成為著名學府。竺可楨視大學為養成公忠堅毅、主持風會、轉移國運領袖人才之所,恪守“務實求學,存是去非”之旨,為浙江大學贏得“東方劍橋”的美譽。為了抵制外來干涉,蔡元培先后五辭北大校長;為了維護校統,羅家倫毅然辭去清華校長。他說:“我的辭職不是對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辭職,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和獨立和清華隸屬系統的正規化。”[7]
作為直接從事學術的研究者與創新人才的培養者,教授必須有脊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竺可楨說: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后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在竺可楨看來,大學的主要職責不是供給或販賣現成知識,而是要開辟新途徑、創造新知識,培養學生批判精神與反省精神,使學習者能夠自動求知、持續研究與創造知識。這要求教授先有這種意識與能力,并具有將其貫徹下去的脊梁。這種脊梁,甚至重于教授擁有的專業知識。因為,具有專門知識的專家也未必具有獨立精神和健全人格。愛因斯坦曾指出,具備了專門知識的人,“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產生熱烈的情感,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8]脊梁扭曲的教授也會培養人,但培養不出脊梁堅挺的人。這樣的人只能阻滯社會的變革與發展,正如吳康寧校長所言:如果我們的大學所生產的是一些陳舊的知識,培養的是循規蹈矩的庸人、貪名逐利的邪人、趨炎附勢的小人的話,那大學不僅不能引領社會,反而會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幫兇和罪人。
大學生是大學人的絕大多數,只有他們有脊梁,我們的未來才會光明。大學生開始接觸高深學問,以便獲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慧;開始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以便從容應對人生中的挑戰;開始思考人生意義,以便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這不僅需要大學生自己做出持續努力,更需大學予以幫助與培養。大學首先要將學生培養成健全的人,即有自我意識——能認識自我;有德性——能成就自我;有理性——能認識他人和周圍世界;有實踐性——能實現自我;有創造性——能展現自我;有情感性——能與他人和周圍世界發生聯系。在此基礎上,幫助學生形成自己的脊梁。蔣夢麟說大學要幫助學生“養成精確明晰之思考力”、“養成健全之人格”、“養成獨立不易之精神”。胡適認為,獨立的精神就是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我們各個人思考的結果。竺可楨指出,浙江大學的學生必須有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大學生本身對現實比較敏感,若大學以權力與功利加以誘導,后果堪憂。“我們不能不認識現實。但我們絕不能陷死在現實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氣消沉,正義感與是非心一道埋滅。”羅家倫曾如是告誡。
正是因為有脊梁,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等等一批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的大學,而戰爭中的西南聯大更是這一時期大學的典范;正是這些大學、大學校長、大學教授致力于學生脊梁的培育,出現了一批精神豐滿、脊梁健碩的學子,成為社會發展的引領者與推動者。我們今天所謂的大師,都曾是那個時期的學生。
四
不可否認,在權力與功利雙重作用下,今日中國大學的脊梁已嚴重扭曲,突出表現在大學對于政府部門、政府官員普遍的言聽計從,亦步亦趨。“有些大學甚至像政府部門手中的機械一樣,沒有自己的思想、意識,完全是落實政府部門的通知、指示、要求。”大學一旦惟命是從、脊梁扭曲,便會失去自我,成為行政命令的被動執行者。脊梁扭曲的大學在管理與培養人才方面會出現嚴重問題:權力之下,惟權是從;功利之下,惟利是圖。在權力與功利之下,人人都得低頭、彎腰,造成諸多內耗與浪費的同時,培養出人格不全、精神萎靡的人。“大學應當成為大學精神的守望者,堅守大學超凡脫俗的‘氣節’。堅貞不屈地走大學自己的發展之路!”[9]因此,當大學沒有脊梁、沒有基于脊梁的自尊時,大學中人難有脊梁與基于脊梁的自尊,大學以及大學人將被異化而失去自己的個性、特點與特色。“只有拒絕依附,我們的大學才能成為有膽量的大學,有硬度的大學,才能算得上是一所有自尊的大學,這樣我們的創新人才培養才有希望。”[2]吳康寧教授如是說。
只要大學還存在,就會發揮作用,只是這種作用有正面與負面之分。今日的痛苦,是昨日努力不夠或努力方向問題造成的;今日創新人才奇缺,是昨日大學出現問題的自然結果。大學的脊梁是大學秉著自己的靈魂、精神、信念和不懈努力鑄成的,不是通過賦予或憐憫賞賜給予的。有自尊的大學脊梁需要政府與環境的支持,同樣需要大學以及大學人的努力。今日大學在培養未來社會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財富精英和社會精英,如果這些精英靈魂失落、精神萎靡、信仰缺失、脊梁扭曲、惟權是從、唯利是圖,那么,我們的未來會是什么樣?從這個意義上看:善待大學就是善待我們自己,培育大學以及大學中人的脊梁就是在培育中國的脊梁,這需要政府、大學以及大學人共同付出努力。
[1] 溫家寶.錢學森之問對我是很大刺痛[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05/c_1273985.htm.
[2] 謝洋.南師大吳康寧:不自尊的大學沒資格培養創新人才[N].中國青年報,2013-01-17(03).
[3] [法]埃德加·莫蘭.復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M].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9.
[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88.
[5] 章開沅.誰在折騰中國大學[EB/OL]. http://www.csstoday.net/Item/16964.aspx.
[6] 張大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上卷)[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423.
[7] 羅家倫.羅家倫史學與教育論著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11.
[8] [美]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許良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74.
[9] 李震聲,李斌,張蔚.論大氣的大學[J].大學教育科學,2013(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