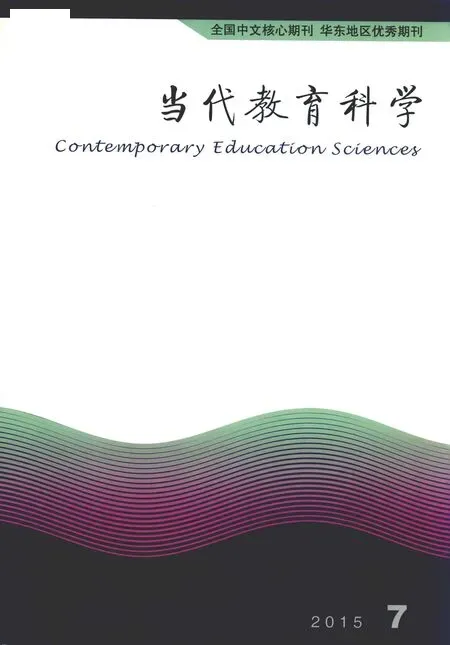論符號學“組合與聚合”的教育價值
●程 然
論符號學“組合與聚合”的教育價值
●程 然
“組合與聚合”是符號學的一對重要概念,它的教育價值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固有的模式,形成帶有創新意義的組合與聚合,就有可能給教育帶來多大的驚喜;而在教育活動中,組合與聚合的科學運用,也是提高教育效率的不二法門。
教育;符號學;組合;聚合
作為符號學創始人之一的索緒爾曾提出了諸多重要的概念,比如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言語、共時與歷時,但是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組合與聚合的原理。符號學家李幼蒸指出:“索緒爾結構語言學中影響最為顯著、最被廣泛接受的結構原理,即他所提出的兩個語言軸列概念。這就是聚合系列和組合系列兩套語法關系,以及在具體語言情境中呈現的組合段(syntagma)和聚合段(paradigma)。”[1]
一、組合與聚合的符號學概說
索緒爾最早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使用的概念不是組合與聚合,而是“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所謂“句段關系”指的是“在話語中,各個詞,由于它們是連接在一起的,彼此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系,排除了同時發出兩個要素的可能性。這些要素一個挨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面”。[2]索緒爾的意思是說,在句段關系中,出現的不是一個詞而是一組詞,它們被選擇之后就排除了其他選擇的可能,并且這一組詞在時間上一個接著一個先后出現,在意義上每個詞都處于與它前后詞的關系中,并因此既顯示各自的意義,同時又因為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意義。所謂“聯想關系”指的是“在話語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合起來,構成具有各種關系的集合”,“句段關系是在現場的(in praesentia):它以兩個或幾個在現實的系列中出現的要素為基礎。相反,聯想關系卻把不在現場的(in absentia)要素聯合成潛在的記憶系列”。[3]按照索緒爾的觀點,聯想關系就是儲存在記憶中各種詞語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既沒有一定的數目,也沒有確定的順序”,[4]但是它們為組合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后來的符號學家對索緒爾的這一理論做了深入的研究,進行了改造和完善。比如他們用組合與聚合取代了索緒爾的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把語言擴展為包括語言在內的所有人類符號,并且這些符號既可以儲存于人的記憶中,也可以直接呈現于人的面前;又把由詞組成的句段看成是由符號組成的文本,這樣組合與聚合不僅存在于語言文本中,還存在于一幅畫、一座博物館、一場演唱會,即人類所有的活動中。進一步研究發現,組合與聚合其實是人類大腦的一種功能和機制,這是雅柯布森得出的結論:“人類的大腦的語言工作區本來就分成兩個部分,分別處理組合與聚合,是人類基本思維方式中兩種功能互相配合的結果。由此,可以再進一步推論:一旦進行符號表意,必須同時使用這雙軸關系。只有同時進行選擇與組合,人的思維和表達才有可能。”[5]這就從本體論上確認組合與聚合是人的本質屬性,從而揭示了存在于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中的一種規律。丹麥符號學家葉爾姆斯列夫從邏輯學的角度探討了組合與聚合間的差別,他認為聚合關系中各單元之間的結合關系是析取關系(用“……或……”的形式表示),組合關系中各單元之間的結合關系是合取關系(用“……和……”的形式表示)。中國符號學家趙毅衡則從辯證法的角度分析了組合與聚合之間的關聯,他說:“一個符號表意開始,從聚合軸進行選擇,用以產生組合段。……表面上看,似乎要先挑選,才能組合。實際上,雙軸是同時產生的,組合不可能比聚合先行:不可能不考慮組合軸的需要進行聚合軸的選擇,而也只有在組合段成形后才能明白聚合的作用。兩個軸上的操作是同時發生的,雖然只有組合操作形成文本,顯現出一個結果。”[6]
組合與聚合是人的一種極為重要的能力,它首先是人的一種基本能力,人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組織能力、交往能力等都離不開組合與聚合,在縱向上他需要把符號聚攏起來,在橫向上他需要把符號排列起來,缺少了這一能力,不要說完成一項重要任務,就連完整地說一句話都非常困難。其次,它可以上升為人的一種更高的能力——創造力,人類的偉大發明和創造無不與組合與聚合相關,李白的一首詩,畢加索的一幅畫,貝聿銘的一座建筑,甚至連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愛迪生發明電燈,瓦特制造出第一臺蒸汽機,都是創造性地進行組合與聚合的結果。
既然所有的人類活動都離不開組合與聚合,教育也是如此。但是教育是一種復雜的組合與聚合,這是因為教育所涉及的關系要素很多,故在組合與聚合中變數更大,難度更大。如果不厘清教育的構成要素,是無法說清教育中的組合與聚合的。筆者認為,教育的構成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媒介和教育活動這四個要素,其中教育活動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運用教育媒介進行教育的過程,它是最基本也是最活躍的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媒介都是因為教育活動而被連接在一起的,如果沒有教育活動,即使有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媒介,也不能稱之為教育。在教育活動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媒介的組合與聚合越是具有創造性,所產生的教育效果就越好。
二、組合與聚合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在教育活動中(這里主要指學校教育)人是最基本的要素,教育活動要通過人去組織和實施,教育的目的則是為了培養人、塑造人,而這里的人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的是,學校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國家教育行政機構的組合與聚合對象。國家教育行政機構根據學校的功能和規模配置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其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雖然有一定的選擇自由,但是一旦被學校所錄用和錄取,那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有相對的穩定性。這就告訴我們,在學校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組合與聚合是受到限制的,只能在某一個范圍內,而不能越出。在學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組合與聚合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往往是一個常數,是不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由改變的。強調這一點的意義在于當一個人總是面對著差不多同樣的對象時,往往會失去組合與聚合的欲望和能力。就像人們會產生審美疲勞一樣,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人們也會產生組合與聚合的疲勞,這恰恰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應該引起注意或警惕的。
但是,組合與聚合作為一種方法,它自身本來就蘊藏著變革的潛能,在學校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改變組合和聚合的模式來激發活力。其前提是,我們要認識到學校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既是被組合與聚合的對象又是自組合與聚合的主體。也就是說,在眾多學校中,當硬件條件相等,教育者的水平和受教育者的起點相差無幾時,誰能通過組合與聚合引發一場教育革命,往往會給學校注入新的生機。這決定于,第一,學校能不能讓教育者和受教育進行自由地組合與聚合;第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組合與聚合能達到什么水平。以上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的劉道玉教育改革為例,今天當我們用符號學觀點來看,劉道玉只不過在當年做了一些在大學教育中具有突破性的組合與聚合。比如他第一個在全國推出了學分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轉專業制、導師制等;又比如,他認為研究生論文答辯可以當面頂撞評審委員,而在本科生學術演講時,校領導都要坐在下面洗耳恭聽。長期以來的大學教育,早已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劃了一條深深的鴻溝,教育者與受教育之間的組合與聚合是由組織決定的,是根據等級來安排的,已經成為一種固化的形態,只有教育者挑選受教育者,不可以受教育者挑選教育者,只有教育者教育受教育者,不可以受教育者教育教育者。其實,在教育活動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的主體,他們既是施事者也是受事者,既可以被組合與聚合也可以進行組合與聚合。當劉道玉打破了大學教育的陳規陋習之后,就為大學教育營造了一種自由、民主、開放的氛圍,從而首先大大釋放了作為受教育者的學生的學習熱情和積極性。反過來,教育者在這種組合與聚合中也不斷受到來自受教育者的激勵和鞭策,使自身的學術水平和教育能力得到提高。如今,不僅在大學,很多中小學都已經遵循著“自主、合作、探究”新的教育理念,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組合與聚合中不再因循守舊。
三、組合與聚合在教育活動中的體現
那么,在具體的教育活動中,組合與聚合是如何展開的呢?如果我們把每次教育活動看作是一個組織有序、表意清晰的符號文本的話,聚合就是為這個文本聚集、比較、挑選一切可以構成文本的符號對象,而組合就是根據教育的目標、效果對這些符號對象的配置、連接。這是一個緊密相連、彼此相依的過程,同時又是分工明確和定位科學的。
第一,組合是君,聚合是臣。組合是動機也是目的,聚合是過程也是手段,如果沒有組合的需要,人們是不會進行聚合的。組合決定了聚合,決定了你將從哪些符號中進行聚合,最終組合成什么樣的文本。但是聚合對組合也有反作用,有時聚合的特殊性會使組合的意義發生偏離和改變,取得意外的效果。教育也是如此。在教育活動中必須要有清晰的目標和要求,比如一堂課是以我講授為主,那么聚合就必須圍繞著講授的內容組合成文本,這時聚合往往以知識對象為主,組合也以知識的串連為重;如果一堂課以學生活動為主,則聚合是以學生為對象,組合也根據學生能力的不同進行搭配。
第二,組合是意義的,聚合是意向的。如上所述,組合既然是有目的的,那么在組合之前、之中和之后必然伴隨著意義的提取、構建和完成,但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離不開聚合,意義的提取需要從聚合中去發現、提煉,意義的構建需要通過聚合進行對比、篩選,意義的完成需要聚合退居幕后,構成背景。總之,意義通過意向去貫徹,而意向則為意義注入生命。這一過程往往是一個回環往復的過程,時常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聚合經過初選、精選,最后經組合形成文本,但如果發現意義表達不準確、不完善則可能放棄,一切從頭做起。在教育活動中,一節課、一次實驗、一場講座可以看作是結構有序的表意文本,但是它的意義并不是對教學大綱的生吞活剝,也不囿于陳舊的教學模式,而是一次新的組合與聚合的過程。因為即使是上同一篇課文,做同一次實驗,作為聚合對象的符號總會發生變化,組合的手段也會進行調整。比如一篇課文又發現了與它相關的“伴隨文本”(“隱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邊緣,卻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嚴重地影響意義解釋”[7]的文本),當聚合的對象發生變化時,組合必然有發現和生成新的意義要求,聚合也必然根據組合的意義進行搜集和挑選。
第三,組合是穩定的,聚合是動態的。我們所讀到的一本小說,聽到的一首歌曲,參觀的一座博物館,都是經過聚合而完成了的組合文本,它是穩定的,不可隨便更改的。上世紀50年代曾有人想打破這一規律,法國新小說派作家馬克·薩波塔為此寫了一部題為《作品第一號》的“撲克牌小說”,全書沒有頁碼也不裝訂成冊,每一張書稿只有正面有文字,反面空白,每頁500至700字可獨立成篇,除了一個前言和結尾外其余的149頁文字任意地放在一個盒子里。讀者在每次閱讀前可以任意“洗牌”從而獲得全新的故事,并隨著不同的“洗牌”組合而產生“作品第一號”、“作品第二號”以至“作品N號”,但是這種實驗似乎再也沒有進行下去。如果我們拿一次教育活動與一本書、一首歌、一座博物館相比的話,則它們之間既相同也不同。相同的是,它有一個腳本即教案,來規范著教育活動的過程,使之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至于在教育活動中臨時起意,隨心所欲的進行聚合。不同的是,教育活動中的受教育者畢竟不是一個劇組,不會按照預先準備好的教案去排練節目,總會出現新的因素,新的問題,組合必然因此而改變,而調整,所以教育活動中組合往往是在變動的聚合中獲得相對穩定性。但是教育活動中的聚合的變動一般不宜太多、太密,以免影響組合的穩定性和一貫性,難以使教育活動沿著既定的方向有序進行。
第四,組合是顯,聚合是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在生活中只能看到組合后的完成品而看不到聚合的過程,比如一本小說,我們看到的是前后勾連的詞語、段落、人物、情節,這是作者選擇后留下來的東西,他剔除的東西我們則看不到。所以,組合完成之后,聚合退隱幕后。但退隱并不是消失,聚合仍然會對組合發生影響,成為組合的背景和參照,人們會根據退隱在幕后的聚合內容去思考組合的意義,質問組合的價值。在教育活動中情況則要復雜一些,備課是教育活動的起始階段,這個階段通常會構造好一堂的教學文本(教案),雖然還只是一個停留在紙上的文本,但是教育者應該意識到,這個教案的背后有著大量的聚合的內容,這些內容有可能在教育實施過程中被再一次提取,進入文本,也有可能成為受教育者提出的問題,成為教學文本新的要素。這表明,教育活動前的一個紙質文本當它轉化為教育實施中的現實文本時,中間有著很多的不確定性,一個教育者只有在備課時聚合的視野越開闊,才有可能在教育活動中的組合越從容、越自信,越能給受教育者提供豐富的內容。
第五,組合目標創新,聚合源自積累。學校教育需要聚合大量的硬件和軟件,從校舍、操場、圖書資料到管理人員、師資、學生,只有聚合軸越寬,才會為組合積累充足的資源。但是,再多的聚合資源,都不可能自動組合成一個表意文本。我們在當代中國不知看到過多少在硬件和軟件上都相當不錯的大學、中學和小學,然而他們的教育水平卻參差不齊,甚至有的相差懸殊,原因就在于缺少具有創意的組合。什么是教育中的創意組合,其實沒有一定之規,如果說有什么標準的話,那就是將各種教育資源組合在一起時,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它的效應,而這種效應最集中地體現在教育的主體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上,看他們能否在這種組合中得到充分的成長。
[1]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44.
[2][3][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70,171,175.
[5][6][7]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165,161,141.
(責任編輯:劉丙元)
程 然/南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人文系教授,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符號學和教育符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