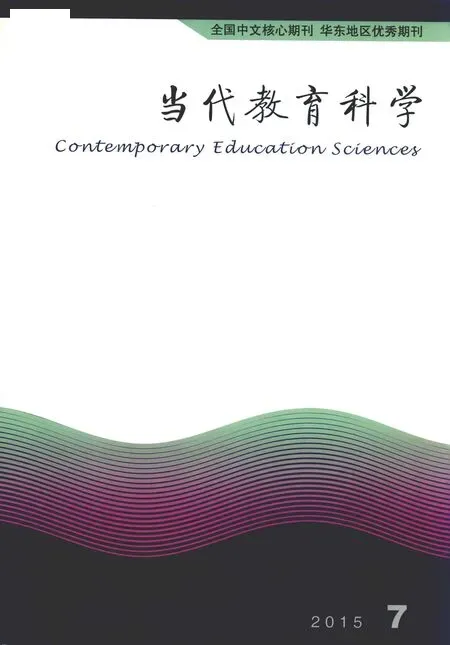俄羅斯高校道德教育中案例教學(xué)的邏輯理路*
●馮永剛
俄羅斯高校道德教育中案例教學(xué)的邏輯理路*
●馮永剛
近年來,隨著案例教學(xué)在世界各國的日漸升溫,引發(fā)了俄羅斯教育界尤其是高校的廣泛關(guān)注,并將其自覺能動(dòng)地運(yùn)用到具體的教育教學(xué)過程之中。通過對(duì)俄羅斯高校道德教育中案例教學(xué)的審視與剖釋,不難發(fā)現(xiàn),其在案例教學(xué)中呈現(xiàn)出宗教性與世俗性交織、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融會(huì)、預(yù)設(shè)性與生成性交互、民族性與世界性依存的邏輯理路。透視與解析這些基本關(guān)系,對(duì)于案例教學(xué)的扎實(shí)推進(jìn)以及大學(xué)生良好道德品質(zhì)的培育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價(jià)值。
俄羅斯高校;案例教學(xué);道德教育
作為一種充滿生機(jī)與活力的教學(xué)手段或形式,案例教學(xué)是指教師與學(xué)生以案例為載體,共同研討以提升問題解決能力為目的的開放式教學(xué)方法。英國學(xué)者達(dá)爾文曾說,最有價(jià)值的知識(shí)是關(guān)于方法的知識(shí)。檢之實(shí)際,確實(shí)如此。方法的科學(xué)、合理和有效,可取的事半功倍的成效。方法的教條、僵化和無效,易陷入事倍功半的尷尬境地。下文以案例教學(xué)法著手,從方法論的視域探究和詮釋俄羅斯高校的道德及道德教學(xué),其目的也正基于此。
一、宗教性與世俗性的交織
將宗教浸透到高校的學(xué)科德育中,利用宗教的形式進(jìn)行道德教育,是當(dāng)前俄羅斯高校案例教學(xué)最顯著的特點(diǎn)。這與俄羅斯的國情密切相關(guān)。俄羅斯是一個(gè)信仰宗教的國家,擁有豐厚的宗教傳統(tǒng)與宗教資源,境內(nèi)存在東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眾多宗教流派。東正教是俄羅斯的國教,是目前俄羅斯社會(huì)占主導(dǎo)的意識(shí)形態(tài)。為了強(qiáng)化宗教對(duì)青少年思想的影響,俄羅斯不遺余力地探尋宗教與道德之間的關(guān)系,力圖將二者緊密銜接起來。一如俄羅斯宗教學(xué)家阿莫納什柯夫所指出,“宗教與道德教育是難以區(qū)分的,他們不但能夠滿足人們的道德需求,而且能夠引領(lǐng)是他們的人生發(fā)展航向。”[1]因而,強(qiáng)調(diào)道德教育中案例教學(xué)的宗教性,自是順理成章。然而,與此不同的是,俄羅斯一些高校的教師卻反其道而行之,對(duì)世俗社會(huì)的道德及道德教育津津樂道,認(rèn)為道德產(chǎn)生于現(xiàn)實(shí)生活,而非對(duì)上帝的篤信。道德教育教學(xué)的現(xiàn)代化也要求案例教學(xué)應(yīng)源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緊密結(jié)合大學(xué)生真實(shí)的思想實(shí)際進(jìn)行。在當(dāng)前的俄羅斯,此種觀點(diǎn)并非空穴來風(fēng),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在前蘇聯(lián),由于道德教育目標(biāo)是要培養(yǎng)共產(chǎn)主義的一代新人,因而學(xué)校用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與道德來熏陶和教育年輕一代,宗教和宗教活動(dòng)被排斥在教育范疇之外。為了削弱宗教勢(shì)力對(duì)年輕一代尤其是兒童的毒害,列寧在《偉大的創(chuàng)舉》中提出了“托兒所和幼兒園是共產(chǎn)主義的萌芽”的論斷,旨在以共產(chǎn)主義思想體系武裝孩子們的頭腦。為了徹底肅清宗教和宗教團(tuán)體在共產(chǎn)主義道德教育中的殘余勢(shì)力,蘇維埃政府下令封閉教堂,解散宗教組織,封查、銷毀宗教書籍,監(jiān)禁、流放、處決信教人士,高校道德教育中有神論的宗教思想受到了嚴(yán)重的打擊和創(chuàng)傷。然而,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共產(chǎn)主義道德體系被徹底打破和否定,原有的主導(dǎo)和優(yōu)勢(shì)地位已經(jīng)不在。共產(chǎn)主義道德價(jià)值已經(jīng)無力控制和左右宗教對(duì)高校道德教育的干預(yù)和滲透,這給宗教以千載難逢的發(fā)展機(jī)遇。俄羅斯的宗教團(tuán)體和宗教活動(dòng)組織抓住這個(gè)有利時(shí)機(jī),發(fā)起宗教復(fù)興運(yùn)動(dòng),迅速占領(lǐng)高校道德教育舞臺(tái),宣傳宗教教義和教規(guī),利用宗教范式和案例教學(xué)潛移默化地培養(yǎng)大學(xué)生的宗教道德情結(jié),樹立宗教在大學(xué)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由于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雙重選擇,使得當(dāng)前俄羅斯高校的案例教學(xué)中出現(xiàn)了宗教性與世俗性交織的發(fā)展情景。
俄羅斯高校案例教學(xué)中的宗教性與世俗性,集中體現(xiàn)為兩個(gè)方面:其一是編寫宗教故事,開設(shè)宗教課程,利用宗教教材進(jìn)行案例教學(xué)。目前俄羅斯不少高校在道德教育中都選用宗教組織編寫的書籍作為案例教學(xué)的教材,這與俄羅斯聯(lián)邦政府和教育行政機(jī)構(gòu)的積極提倡不無關(guān)聯(lián)。俄羅斯聯(lián)邦政府總理梅德韋杰夫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宗教文化基礎(chǔ)知識(shí),了解宗教道德規(guī)范。他建議“在俄羅斯選定幾個(gè)地區(qū)來進(jìn)行宗教文化、宗教歷史和世俗道德基本規(guī)范的實(shí)驗(yàn)性教學(xué)。”[2]俄羅斯聯(lián)邦教育部副部長切普爾內(nèi)赫也認(rèn)為,“宗教在俄羅斯有幾百年的精神道德價(jià)值,不能無視宗教對(duì)人的精神道德的重大影響。他提議,學(xué)生可以通過選修課的方式和學(xué)生自愿接受的補(bǔ)充教育的方式,學(xué)習(xí)包括宗教內(nèi)容的學(xué)科。”[3]俄羅斯眾多高校積極響應(yīng)上級(jí)號(hào)召,組織編寫或選用宗教故事,宗教教材大規(guī)模涌入高校學(xué)校,宗教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jià)值觀通過案例教學(xué)的形式在高校道德教育中得到廣泛傳播;其二是案例教學(xué)中宗教道德與世俗道德的相攝相融。盡管宗教道德與世俗道德在今生與來世、人性與神性、庸俗與神圣等問題上大相徑庭,但二者的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宗教道德和世俗道德在一些價(jià)值取向、行動(dòng)準(zhǔn)則、行動(dòng)規(guī)范等內(nèi)容上或互相重疊,或互相交叉,如均肩負(fù)著促進(jìn)大學(xué)生道德社會(huì)化的共同使命,均發(fā)揮著維護(hù)高校道德秩序與引領(lǐng)大學(xué)生道德生活的功能,等等。因此,俄羅斯高校在道德教育過程中運(yùn)用案例教學(xué)時(shí),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宗教性和世俗性的共性貫穿起來。如通過宗教故事,用以培養(yǎng)大學(xué)生為善、敬老、愛幼、誠實(shí)、勇敢、節(jié)制、勤勞、守信等道德品質(zhì),而這恰恰也是世俗道德所提倡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消緩了高校道德教育中宗教性與世俗性的對(duì)峙,使之并存于整個(gè)案例教學(xué)的進(jìn)程之中。
二、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的融會(huì)
案例教學(xué)既是一門科學(xué),也是一門藝術(shù)。科學(xué)重在求真,而趨美是藝術(shù)的偏愛。道德教育教學(xué)具有科學(xué)與藝術(shù)的雙重屬性。在高校道德教育中運(yùn)用案例教學(xué)法,既要遵循道德發(fā)展的特點(diǎn)及其固有規(guī)律,也要符合道德教育主體——人的獨(dú)特性、審美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情緒情感品質(zhì)。然而,在道德教育中如何認(rèn)識(shí)與看待案例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曾是俄羅斯教育界長期爭論的議題。按照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更多的俄羅斯學(xué)者尤其是前蘇聯(lián)的教育家將道德教育視為一種科學(xué),案例教學(xué)也被定格在科學(xué)的殿堂與領(lǐng)域,以科學(xué)的范式組織與實(shí)施道德教育教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將案例教學(xué)的藝術(shù)性邊緣化。鑒于漠視案例教學(xué)藝術(shù)性所帶來的沉重、僵化、刻板的弊端,以及在一定時(shí)期或局部范圍內(nèi)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彼增此減的不良傾向,莫斯科友誼大學(xué)勃格達(dá)諾娃教授對(duì)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的共性做了深刻詮釋。按照她的說法,“教學(xué)的科學(xué)與藝術(shù)實(shí)則是難以區(qū)分的,二者相輔相成,科學(xué)是精密化的藝術(shù),藝術(shù)是情緒化的科學(xué)。”[4]循此思路,在案例教學(xué)中穩(wěn)步提升教學(xué)質(zhì)量與效果,必須遵循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相統(tǒng)一的原則,不失時(shí)機(jī)地將二者貫穿于整個(gè)案例教學(xué)過程中。在俄羅斯道德教育活動(dòng)中,越來越多的高校既重視科學(xué)的思想性、系統(tǒng)性、連貫性與邏輯性,也關(guān)注藝術(shù)的形象性、情感性、欣賞性與創(chuàng)造性,將案例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
在高校道德教育中輕蔑案例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極易導(dǎo)致道德教學(xué)的膚淺、盲從與失序;鄙棄案例教學(xué)的藝術(shù)性,又容易陷入枯燥、單調(diào)、沉悶的囹圄中無以自拔。俄羅斯高校在道德教育中整合案例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一方面,在案例教學(xué)中用科學(xué)性指導(dǎo)藝術(shù)性的發(fā)展,將科學(xué)性滲透到藝術(shù)性之中。俄羅斯學(xué)者認(rèn)為,在高校道德教育中,案例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是藝術(shù)性的基礎(chǔ)與依據(jù),是藝術(shù)性發(fā)現(xiàn)、鑒賞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的前提與本真。案例教學(xué)缺失科學(xué)性,藝術(shù)性就有可能偏離正確的道德發(fā)展航向。為此,教師要不斷加強(qiáng)自己的業(yè)務(wù)素養(yǎng),廣泛涉獵哲學(xué)、倫理學(xué)、教育學(xué)、心理學(xué)、教學(xué)論等教育科學(xué)知識(shí),升華案例教學(xué)的道德理論厚度與實(shí)踐高度,提高道德教學(xué)藝術(shù)決策的科學(xué)化水平;另一方面,在案例教學(xué)中用藝術(shù)性提升科學(xué)性的格調(diào)與品位,將藝術(shù)性融于科學(xué)性之中。案例教學(xué)的藝術(shù)性是科學(xué)性的生命、延伸與改造,離開了案例教學(xué)的藝術(shù)性,科學(xué)性驅(qū)使下的繁瑣道德說教極易引起大學(xué)生的乏味、抵觸與反感情緒,難以將案例故事中的道德規(guī)則內(nèi)化為個(gè)體心理品德結(jié)構(gòu)的有機(jī)組成部分,使案例教學(xué)成為一潭死水。因此,“每一個(gè)高校教師均要追求教學(xué)藝術(shù),形成自己具有個(gè)性魅力、獨(dú)特深邃與不拘一格的教學(xué)藝術(shù)風(fēng)格”,[5]在傳授道德知識(shí)、培養(yǎng)個(gè)體道德能力的案例教學(xué)中擴(kuò)充道德教育的藝術(shù)元素與音符,增強(qiáng)案例教學(xué)的趣味性與吸引力,點(diǎn)燃大學(xué)生道德求知、求真的激情,在“無意于法則,而自合于法”的藝術(shù)境界中體驗(yàn)美的享受,探尋與領(lǐng)悟道德的真諦,獲得道德的感染與熏陶。
三、預(yù)設(shè)性與生成性的交互
案例教學(xué)的預(yù)設(shè)性與生成性,是案例教學(xué)的科學(xué)性與藝術(shù)性的具體化與可操作化。在高校道德教育教學(xué)中究竟是既定方案按部就班的展開還是圍繞案例發(fā)揮學(xué)生的參與性與自主性,也是案例教學(xué)不得不面對(duì)的現(xiàn)實(shí)問題。案例教學(xué)的預(yù)設(shè)性,是由案例教學(xué)的目的性、計(jì)劃性與規(guī)律性所決定的。案例教學(xué)的生成性,取決于教學(xué)主體以及教育情景的靈活性與多變性。在前蘇聯(lián),為了確保大學(xué)生對(duì)共產(chǎn)主義道德知識(shí)的掌握以及維護(hù)課堂紀(jì)律,凱洛夫極力提倡預(yù)設(shè)性教學(xué),他為教學(xué)準(zhǔn)備、教學(xué)組織和教學(xué)評(píng)價(jià)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都設(shè)計(jì)了完備的模式。受其影響,高校道德教育中案例教學(xué)的預(yù)設(shè)性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當(dāng)然,也有學(xué)者如道德心理學(xué)家包諾維奇教授就認(rèn)為案例教學(xué)不能僅拘泥于固有的設(shè)計(jì)安排,而要注重教學(xué)活動(dòng)的動(dòng)態(tài)生成性。他認(rèn)為,唯有在生成性的案例教學(xué)中才能深入挖掘案例中所蘊(yùn)含的道德哲理,進(jìn)而強(qiáng)化學(xué)生的道德問題意識(shí),不斷提升學(xué)生道德判斷與道德選擇能力的發(fā)展。針對(duì)案例故事中所包括的道德情形或疑難問題,教師和學(xué)生可展開對(duì)話,在集思廣益的積極互動(dòng)中既發(fā)揮了學(xué)生的道德主體性,而且深化了學(xué)生對(duì)道德及道德教育的洞察、接納與認(rèn)肯,醞釀出新的道德生長點(diǎn)。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俄羅斯高校在權(quán)衡案例教學(xué)利弊得失的基礎(chǔ)上,逐漸擺脫了案例教學(xué)中預(yù)設(shè)性與生成性非此即彼的誤區(qū),逐步尋求二者的結(jié)合點(diǎn)。對(duì)于案例教學(xué)的預(yù)設(shè)性與生成性,俄羅斯教育學(xué)家克拉斯諾若夫教授一語中的:“我們既不能簡單地將二者完全等同,也不能將二者截然分開,預(yù)設(shè)與生成是案例教學(xué)的一體兩翼,缺一不可。進(jìn)一步講,預(yù)設(shè)是基礎(chǔ),生成是升華。”[6]
在高校道德教育教學(xué)中,既有確定的、線性的、因果的預(yù)期因素,也有動(dòng)態(tài)的、模糊的、隨機(jī)的非預(yù)期因素。極力探尋道德教育的預(yù)期與非預(yù)期的“結(jié)合點(diǎn)”,加強(qiáng)預(yù)設(shè)性與非預(yù)設(shè)性的互補(bǔ)性,是俄羅斯高校案例教學(xué)的又一基本特征。一方面,在案例教學(xué)前依據(jù)教學(xué)規(guī)律精心預(yù)設(shè),優(yōu)化預(yù)設(shè),為生成奠定基礎(chǔ)。俄羅斯高校在案例教學(xué)中尤為注重教學(xué)目標(biāo)和教學(xué)過程的彈性預(yù)設(shè)。在開展案例教學(xué)之前,教師注重提出實(shí)現(xiàn)道德教育目標(biāo)的多種“緩沖區(qū)間”,盡可能從大學(xué)生已有的道德認(rèn)知、案例本身所承載的道德內(nèi)容以及教學(xué)組織安排等方面提出道德預(yù)期,預(yù)先設(shè)想可能出現(xiàn)的多種道德沖突情景,并針對(duì)學(xué)生不同的反應(yīng)規(guī)劃教學(xué)活動(dòng),提出相應(yīng)的道德問題解決方案,做到胸有成竹,為生成保駕護(hù)航。俄羅斯高校尤為重視案例教學(xué)中時(shí)間的預(yù)設(shè)與分配。誠然,案例是教師授課的基本材料,教授的講解也是案例教學(xué)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教師一定要注意課堂教學(xué)時(shí)間的調(diào)控,倘若教師沉迷于案例故事“滔滔不絕”,這勢(shì)必剝奪學(xué)生的道德話語權(quán),扼殺學(xué)生的道德批判能力與懷疑精神,使得教學(xué)質(zhì)量大打折扣,精彩的動(dòng)態(tài)生成只能成為一種幻想;另一方面,在案例教學(xué)中不拘預(yù)設(shè),注重動(dòng)態(tài)生成,將案例教學(xué)視為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活躍的、發(fā)展的過程。“案例教學(xué)的生命力在于創(chuàng)造,而非簡單的傳授與告知。”[7]在案例教學(xué)中,我們不應(yīng)追求“終極的真理”、“絕對(duì)的答案”或“一律的結(jié)論”。案例教學(xué)的開放性以及不確定性,需教師恰當(dāng)處理教育者、案例文本以及受教育者之間的關(guān)系,既要運(yùn)用案例但又不被案例所禁錮,要做到“道而弗牽,強(qiáng)而弗抑,開而弗達(dá)”(出自《學(xué)記》),自主能動(dòng)地建構(gòu)道德教育教學(xué)活動(dòng),將“授人以魚”和“授人以漁”的雙重道德職責(zé)落到實(shí)處,促使一些新穎的、挑戰(zhàn)性的、富有創(chuàng)意理念噴涌而出,促進(jìn)師生教學(xué)相長。需要指出的是,俄羅斯高校重視案例教學(xué)的生成性并不排斥預(yù)設(shè)性。他們認(rèn)為,沒有預(yù)設(shè)的生成是無序的,因?yàn)榘咐虒W(xué)的靈活與流動(dòng)并不意味著天馬行空,任意妄為。精彩的生成呼喚預(yù)設(shè),預(yù)設(shè)使生成有的放矢,為生成錦上添花。案例教學(xué)的預(yù)設(shè)性與生成性的交相映輝及良性循環(huán),可激發(fā)與提升道德智慧,煥發(fā)課堂的生命活力,引領(lǐng)師生不斷向未知的道德領(lǐng)域挺進(jìn),將案例教學(xué)推向更高的發(fā)展層次,這對(duì)塑造大學(xué)生良好道德品質(zhì)的積極意義是毋庸諱言的。
四、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依存
民族性與世界性一直是俄羅斯哲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與教育學(xué)不懈追問的前沿性與焦點(diǎn)性問題,也是長期困擾案例教學(xué)的一個(gè)突出議題。在俄羅斯,對(duì)此問題的爭議體現(xiàn)為兩種不同的信念與價(jià)值觀:贊同在案例教學(xué)中固守民族性的一方認(rèn)為,民族文化是一個(gè)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化傳統(tǒng)與思想資源,穩(wěn)定和凝固著俄羅斯的價(jià)值取向、倫理精神、社會(huì)習(xí)俗、生活習(xí)慣及行為方式,是一個(gè)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cái)富。民族文化是俄羅斯人的精神家園,是俄羅斯民族歸宿感、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本所在。“倘若不敬重自己的國家,不尊崇祖國的歷史文化與曾經(jīng)取得的輝煌,則意味著拋棄了自己的未來,毀滅了民族的前途。”[8]在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驅(qū)動(dòng)下,一些高校在案例教學(xué)中以對(duì)立的方式御一切域外的思想意識(shí)與道德觀念于國門之外。與之相反,另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前蘇聯(lián)建立起來的道德教育體系已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而坍塌下來,俄羅斯已經(jīng)步入資本主義國家,要完全清除前蘇聯(lián)留下的“共產(chǎn)主義道德陰影”,就必須改頭換面,徹底革新,因而極力主張拋棄共產(chǎn)主義道德傳統(tǒng),全方位地學(xué)習(xí)西方國家的道德文化。隨著社會(huì)轉(zhuǎn)型、經(jīng)濟(jì)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時(shí)代的到來,俄羅斯逐漸放棄了單一、一元的的片面思維,轉(zhuǎn)而強(qiáng)調(diào)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辯證統(tǒng)一性。“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是共為一體的,民族文化屬于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集合體。”[9]這為高校案例教學(xué)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依存作了注解。
在實(shí)踐中,越來越多的俄羅斯高校已在道德教育中將民族性與世界性有機(jī)統(tǒng)籌起來,二者在案例教學(xué)中相得益彰,和諧共生。其一,精選案例,建立既包括民族道德也涵蓋外域道德的案例庫。選擇案例是進(jìn)行案例教學(xué)的必要前提與基本條件。案例在案例教學(xué)中的至關(guān)重要性表明,不僅缺失案例的教學(xué)會(huì)成為無本之木,而且即便有了案例但缺乏高水平的案例,案例教學(xué)也極易流于形式。因此,一方面,俄羅斯高校緊密結(jié)合歷史傳統(tǒng)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篩選或自主編寫彰顯俄羅斯民族道德精神與民族情懷的典型案例。通過案例思維選編,剔除過時(shí)的、陳舊的、異化的道德音符,將俄羅斯民族文化中愛國敬業(yè)、自強(qiáng)不息、勇敢堅(jiān)毅、厚德載物、艱苦樸素的道德精粹發(fā)揚(yáng)廣大,以此充盈道德教育教學(xué)的理論研究與實(shí)踐探索。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經(jīng)濟(jì)一體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國際間交流合作的不斷增強(qiáng),俄羅斯也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以開放的視野、包容的態(tài)度尋求世界上一些國家優(yōu)秀的、先進(jìn)的教學(xué)案例”,[10]特別是翻譯與引進(jìn)哈佛大學(xué)、牛津大學(xué)、巴黎大學(xué)的一些優(yōu)秀的鮮活案例,尋求道德對(duì)話、溝通與整合,加強(qiáng)和國際案例教學(xué)的接軌;其二,加大案例教學(xué)本土化轉(zhuǎn)移的力度。在高校道德教育教學(xué)中選用了世界發(fā)達(dá)國家尤其是歐美等國的案例之后,如何運(yùn)用這些案例就成為有效案例教學(xué)的關(guān)鍵。在實(shí)際的道德教育教學(xué)活動(dòng)中,俄羅斯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進(jìn)行案例教學(xué)必須與俄羅斯的國情相適應(yīng),與本國的道德實(shí)踐相結(jié)合,本土化是案例教學(xué)的應(yīng)然選擇。由于不同國家的歷史傳統(tǒng)以及文化因素之間的差異,因而在案例中必然傾注了體現(xiàn)本國道德文化的獨(dú)特基因,一些優(yōu)秀的案例漂洋過海到了另一個(gè)國家后,盲目照搬可能會(huì)水土不服,產(chǎn)生“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迥然不同的意境。因此,在高校道德教育中運(yùn)用國外的案例不能囫圇吞棗,機(jī)械化一,生搬硬套,否則適得其反。在引入國外案例的過程中,俄羅斯注重積極的改造與轉(zhuǎn)化,強(qiáng)化我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意識(shí)與思維,構(gòu)建俄羅斯案例教學(xué)本土化的話語體系。如此,在案例教學(xué)中既有效避免了“歐風(fēng)美雨”的肆虐,又習(xí)得了歐美發(fā)達(dá)國家案例教學(xué)的有益道德經(jīng)驗(yàn),而且穩(wěn)固、延續(xù)、弘揚(yáng)了契合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的民族精神與道德情愫,有益于營造動(dòng)態(tài)的、多元的、互惠的教學(xué)范式與文化格局。
[1]Амонашков В.В.Религиозные истоки наук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M].Москва:М.пед,2011,193.
[2]俄羅斯設(shè)宗教學(xué)實(shí)驗(yàn)基地 宗教教育有望列入教學(xué)大綱[EB/ OL].http://www.fjxw.net/comnew/2010-09-27/16578.html.
[3]朱小蔓.俄羅斯的教育科學(xué)研究在關(guān)注什么——以《俄羅斯教育科學(xué)院2010年前基礎(chǔ)和應(yīng)用領(lǐng)域的優(yōu)先研究方向》文本為例[J].教育研究,2004,(9).
[4]Богданова Л.В.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воспитания[M].Минск,2008,312.
[5]Марьенко Р.И.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вающего обучения:Опы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г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 ания[M].Москва:Юристь,2003,202.
[6][10]Каратснов С.Т.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Дела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M].Киев,2011,17,227.
[7]Коротав Л.И.Воспита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а средствами в России[M].Москва:Изд-во,2002,13.
[8]М.И.Зезина.О снов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йской фетерации[M].Москва:Гуманит,2009,185.
[9]Рубинштейн Д.Б.Человек: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общение[M].Москва:ПТГ,2009,274.
(責(zé)任編輯:許愛紅)
山東師范大學(xué)教學(xué)改革項(xiàng)目“案例教學(xué)法在高校德育教學(xué)中的運(yùn)用研究”(編號(hào):12JG18)的研究成果之一。
馮永剛/山東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教授,教育學(xué)博士,研究方向?yàn)榈赖陆逃軐W(xué)、教育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