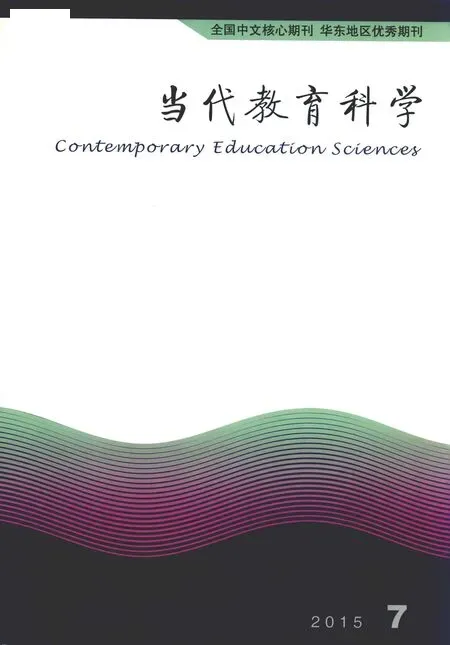教育管理倫理:一個(gè)亟待深化的研究領(lǐng)域
● 金保華 孫綿濤
教育管理倫理:一個(gè)亟待深化的研究領(lǐng)域
● 金保華 孫綿濤
教育管理倫理是當(dāng)前教育管理研究一個(gè)亟待深化的領(lǐng)域。無論著眼于豐富我國教育管理研究的內(nèi)容體系,提高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論品位,還是致力于改善我國教育管理實(shí)踐現(xiàn)狀,提升教育管理的倫理精神,都迫切要求重視并深化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當(dāng)前,深化教育管理倫理研究可以從聚焦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積極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研究成果,加強(qiáng)相關(guān)學(xué)科間的通力合作,注重理論與實(shí)踐的密切聯(lián)系等路徑著手加以展開。
教育管理;教育管理倫理;教育管理理論
一、教育管理倫理:亟待深化的研究領(lǐng)域
長期以來,人類社會(huì)的教育管理活動(dòng)僅停留在經(jīng)驗(yàn)管理的形態(tài),誠如我國臺(tái)灣教育管理學(xué)者林文達(dá)所言:“教育管理學(xué)在20世紀(jì)以前確實(shí)是不存在什么理論的,那個(gè)階段純粹屬于‘教育事物管理時(shí)期’。”到了近代大工業(yè)時(shí)代,隨著教育規(guī)模的急劇擴(kuò)大,過去的那種“從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遺留下來的經(jīng)驗(yàn)式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不能適應(yīng)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大約從20世紀(jì)初起,教育管理開始逐漸由經(jīng)驗(yàn)管理走向科學(xué)管理”。[1]當(dāng)以工業(yè)管理理論為主要內(nèi)涵的科學(xué)管理思想被運(yùn)用到教育領(lǐng)域以后,不僅有力地促進(jìn)了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同時(shí)也逐漸引起了人們對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視。因此,隨著時(shí)間推移及至20世紀(jì)50年代后,教育管理作為學(xué)術(shù)研究和實(shí)踐活動(dòng)的一個(gè)獨(dú)特領(lǐng)域在西方逐漸得以確立,教育管理理論開始出現(xiàn)并最終形成。
澳大利亞學(xué)者依維斯和拉科姆斯基在《探索教育管理:連貫主義之運(yùn)用及批判論爭》中指出:“20世紀(jì)中葉以來,西方教育管理理論發(fā)展迅速,取得了長足的進(jìn)步:一是20世紀(jì)50-70年代在教育管理理論運(yùn)動(dòng)的推波助瀾下促成了現(xiàn)今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的科學(xué)主義教育管理理論的形成;二是20世紀(jì)70年代之后人們在廣泛批判科學(xué)主義教育管理理論的過程中,促使教育管理理論大踏步地邁上蔚為大觀的多元化發(fā)展道路。”[2]據(jù)此可知,雖然說教育管理理論自產(chǎn)生后發(fā)展十分迅速,但迄今為止科學(xué)主義教育管理理論在西方教育管理學(xué)界仍然占據(jù)著統(tǒng)治、主導(dǎo)地位。誠如格林菲斯所言,“無論是過去的研究者還是現(xiàn)在的研究者都是在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理論下開展工作的。只是今日理論的僵硬性少了一些,除此以外,他們在其所宣稱的理論的本質(zhì)上并無任何差異”。[3]
然而,以科學(xué)主義理論為典型代表的西方正統(tǒng)教育管理理論,并非一種真正科學(xué)意義的教育管理理論。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割裂了“事實(shí)”與“價(jià)值”之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片面地追求教育管理的客觀性、科學(xué)化和理性化。反映在教育管理研究中,這種理論認(rèn)定教育管理作為一門科學(xué)只關(guān)涉事實(shí),認(rèn)為惟有事實(shí)才是教育管理知識(shí)獲得和驗(yàn)證的基礎(chǔ),與倫理、價(jià)值無關(guān),要求研究者嚴(yán)守中立立場。然而,教育管理終究是一個(gè)事實(shí)問題和價(jià)值問題相統(tǒng)一的過程。與其他管理活動(dòng)不同的是,教育管理乃是一種服務(wù)、服從于教育的人類特殊管理實(shí)踐活動(dòng)。教育管理的教育性決定了它不是一個(gè)單純的技術(shù)問題,決定了教育“管理者所面臨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是有價(jià)值基礎(chǔ)的:所有的問題和行動(dòng)都有倫理的和道德的涵義”。[4]因此,教育管理中事實(shí)問題與價(jià)值問題是不可分割的,教育管理研究不可能沒有基本的價(jià)值立場和道德取向。
我國近代的“學(xué)校管理學(xué)”和“教育行政學(xué)”最早多來自對西方以教育行政學(xué)為主體的譯介,因此早期的教育管理理論可以說大都是來自外國的“舶來品”。新中國成立后,雖然說在總結(jié)、繼承解放區(qū)的辦學(xué)經(jīng)驗(yàn),同時(shí)積極學(xué)習(xí)借鑒前蘇聯(lián)教育學(xué)和教育管理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我國教育管理學(xué)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實(shí)證主義影響下的教育管理學(xué)”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但應(yīng)該指出的是,它并沒有完全拒絕西方教育管理學(xué)中的那種科學(xué)化的理性追求。直到現(xiàn)今,可以說科學(xué)主義教育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還在主導(dǎo)和支配著我國教育管理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管理學(xué)和教育管理學(xué)致力于全面介紹西方的科學(xué)管理理論、行為科學(xué)理論和系統(tǒng)理論,這就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正統(tǒng)教育管理理論的影響”。[5]“多數(shù)研究都指向技術(shù)操作層面而缺乏相應(yīng)的也是必要的價(jià)值倫理追問”。[6]雖然說已有相關(guān)著作或論文觸及到了教育管理中的倫理、價(jià)值問題,并且形成了一些頗具價(jià)值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開展,但這種關(guān)懷并不多見,也極其有限,并且就已有的研究來看,也存在著不少缺陷:相關(guān)研究要么是簡單地求助于領(lǐng)袖人物或圣人的思想或話語,或求助于某一經(jīng)典理論,而沒有或很少真正從倫理、價(jià)值本身去考慮問題;要么是泛泛而談,停留于簡單的、平面化的或空泛的“應(yīng)該怎樣”,而很少建立在活生生的質(zhì)的研究基礎(chǔ)上或上升到哲學(xué)的層面進(jìn)行深度思考;要么盲目地把公共管理倫理、企業(yè)管理倫理研究領(lǐng)域的成果直接移植、嫁接到教育管理領(lǐng)域,淡化乃至模糊了教育管理與公共管理、企業(yè)管理的區(qū)別;要么求助、運(yùn)用的仍是技術(shù)性話語,看似“應(yīng)該怎樣”的研究實(shí)則是“實(shí)際怎樣”的研究。總之,我國教育管理倫理研究尚存在著普遍的缺憾,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可以說是一個(gè)亟待深化的研究領(lǐng)域。
二、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實(shí)踐價(jià)值
深化并著力加強(qiáng)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實(shí)踐價(jià)值在于:
(一)豐富教育管理研究的內(nèi)容體系,提升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論品位
近年來,我國教育管理學(xué)取得了快速的發(fā)展,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論水平也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在肯定成績的同時(shí)也應(yīng)該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目前我國“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論品味并不令人十分滿意,教育管理學(xué)知識(shí)老化、觀念陳舊、老生常談的現(xiàn)象還依然存在。教育管理理論水平低下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7]因此,“中國教育管理學(xué)的當(dāng)務(wù)之急便是豐富自身的內(nèi)容,提升自身的水平”。[8]
毋庸置疑,進(jìn)一步提高我國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論水平,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chǔ)做支撐。這就要借鑒其他學(xué)科的理論,尤其是哲學(xué)學(xué)科的理論來研究教育管理理論問題。究其原因,“哲學(xué)作為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huì)科學(xué)的結(jié)晶,本質(zhì)上是一種反思的科學(xué)”,[9]它對提高人的理論素養(yǎng)和思維品質(zhì)的作用是其他學(xué)科無法替代的。哲學(xué)的介入不僅能深化人們對學(xué)科基本理論問題的認(rèn)識(shí),并且哲學(xué)思維也有利于促進(jìn)教育管理理論的成熟與完善。我們知道,“哲學(xué)是追求真、善、美的,所謂真,也就是真理,它是哲學(xué)認(rèn)識(shí)論所追尋的目標(biāo);所謂善,就是道德上的正當(dāng)性,它是倫理學(xué)所追求的目標(biāo);至于美,就是事物的審美價(jià)值,它是美學(xué)理論所追求的目標(biāo)。而真、善、美是密切聯(lián)系的”,[10]它也是人類包括教育管理在內(nèi)的一切社會(huì)活動(dòng)必須遵循的三個(gè)尺度。近年來,教育管理理論界已有相關(guān)學(xué)者從“真”(知識(shí)論)、“美”(審美價(jià)值)兩個(gè)方面對教育管理問題進(jìn)行了相應(yīng)的研究。然而,從“善”(倫理學(xué))的角度對教育管理進(jìn)行系統(tǒng)、深入地研究在國內(nèi)學(xué)界尚不多見。教育管理倫理的研究可以說還存在著明顯的缺失,而這無疑是造成我國教育管理的理論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知道,倫理是人類認(rèn)識(shí)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它主要以善惡觀念的形式來認(rèn)識(shí)和把握世界,從中揭示出社會(huì)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和趨勢,為人們提供行為選擇的指南。倫理的這種認(rèn)識(shí)功能對于教育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價(jià)值與意義,它不僅提供教育管理的“實(shí)然”知識(shí),而且也提供教育管理的“應(yīng)然”知識(shí);它不僅描述教育管理“事實(shí)”,而且評(píng)判教育管理行為,告訴教育管理者其行為中的利與害、善與惡、正義和非正義,還能預(yù)測教育管理的發(fā)展遠(yuǎn)景與未來指向,作為一種深層的精神動(dòng)力推動(dòng)教育管理的發(fā)展。誠然,倫理道德對教育管理“事實(shí)”的描述“不如科學(xué)的或理論的認(rèn)識(shí)那樣準(zhǔn)確、嚴(yán)格和根據(jù)充分”,但是“它仍然是客觀現(xiàn)實(shí)的反映,則是毫無疑義的”。[11]它不僅可以從教育管理規(guī)律探尋和科學(xué)發(fā)展方面,“給科學(xué)的、理論的研究提供一條線索”,幫助教育管理者正確把握教育管理運(yùn)行規(guī)律和發(fā)展方向;而且還能給教育管理研究以正確的價(jià)值導(dǎo)向和引領(lǐng),保證研究方向不至于發(fā)生迷失和偏離。正因?yàn)閭惱韮r(jià)值在教育管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關(guān)注、揭示并回應(yīng)教育管理世界中所隱含的價(jià)值倫理問題,將是未來教育管理學(xué)理論發(fā)展的一個(gè)重要走向,也是未來教育管理學(xué)理論必須正面回答的焦點(diǎn)問題”。[12]有鑒于此,進(jìn)一步提升我國教育管理理論研究水平是當(dāng)前面臨的十分迫切的任務(wù)。
(二)改進(jìn)教育管理實(shí)踐狀況,提升教育管理的倫理精神
倫理不僅是人類認(rèn)識(shí)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同時(shí)也是人類“實(shí)踐精神”地把握客觀世界的一種方式。它源于實(shí)踐,離不開實(shí)踐,并且還要指導(dǎo)實(shí)踐的發(fā)展。倫理道德鮮明的實(shí)踐性之于教育管理實(shí)踐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可以通過確立合理的價(jià)值觀導(dǎo)向,規(guī)范、約束教育管理者的行為,引導(dǎo)和推動(dòng)整個(gè)教育組織向著既定的目標(biāo)前進(jìn),而且還協(xié)調(diào)著教育管理中的人際關(guān)系,通過積極構(gòu)建“人和”關(guān)系環(huán)境,確保教育管理活動(dòng)的高效、有序運(yùn)轉(zhuǎn);更為重要的是,它能為現(xiàn)實(shí)的教育管理活動(dòng)樹立倫理道德理想,注入深切的人文關(guān)懷,這種人文關(guān)懷引導(dǎo)教育管理實(shí)踐的開展,提升著教育管理的倫理精神,預(yù)防教育管理活動(dòng)中任何背離人的目的和價(jià)值的偏向。
“管理的一個(gè)重要方面就是敏銳地感受到可能出現(xiàn)的各種道德問題。”[1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管理事業(yè)取得了長足的進(jìn)步,現(xiàn)代化水平獲得了顯著的提升。但如仔細(xì)審視我國教育管理現(xiàn)代化的具體內(nèi)容不難發(fā)現(xiàn),長期以來,教育管理現(xiàn)代化主要集中于管理組織、管理制度以及管理方法等“以經(jīng)濟(jì)和技術(shù)指標(biāo)為基礎(chǔ)的物質(zhì)標(biāo)準(zhǔn)上的現(xiàn)代化”,卻相對忽視了人在教育管理現(xiàn)代化中的地位與作用,體現(xiàn)在教育管理實(shí)踐中就是過于推崇以物為基礎(chǔ)的理性管理范式,淡化了以人為基石的人本管理范式,“管理實(shí)踐中明顯表現(xiàn)出管理制度僵化、管理權(quán)威化、管理形式化、管理操作技術(shù)化,體現(xiàn)了重組織、重權(quán)力、重章法而不重人的特點(diǎn)”。[14]其結(jié)果是造成教育管理活動(dòng)中效率理性甚囂塵上,功利主義泛濫成災(zāi),管理主義大行其道,教育管理中關(guān)于人的價(jià)值關(guān)懷、道德理性和倫理精神日漸萎縮,“管理某種程度上蛻變?yōu)榧兇獾膶I(yè)技術(shù)化或職能化的活動(dòng),甚至異化成為道德與倫理的荒地”。[15]
毋庸置疑,造成當(dāng)前教育管理倫理缺失現(xiàn)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gè)重要原因可以說與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較為忽視教育管理倫理研究有很大的關(guān)聯(lián)。誠如威羅爾所言:“教育管理畢竟存在于特定的社會(huì)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各種價(jià)值倫理問題勢必對教育管理學(xué)理論提出相應(yīng)的要求、產(chǎn)生相應(yīng)的影響。”[16]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很少花時(shí)間來反思我們的管理哲學(xué)或者有意識(shí)地試圖改進(jìn)賦予我們生活以意義的價(jià)值、倫理和正直”。[17]現(xiàn)實(shí)的教育管理實(shí)踐狀況,急切呼吁深化并著力加強(qiáng)教育管理倫理研究,并藉此“對現(xiàn)行管理的實(shí)踐進(jìn)行深入地復(fù)審”,從而“使倫理問題在教育管理中擔(dān)負(fù)起重要作用”。
三、深化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路徑選擇
(一)聚焦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
眾所周知,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是一門學(xué)科研究的基礎(chǔ),對于學(xué)科的發(fā)展與成熟發(fā)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教育管理倫理基本理論內(nèi)容涉及倫理思想、善惡標(biāo)準(zhǔn)(價(jià)值觀)、學(xué)科論、方法論等諸多方面,當(dāng)前特別要重視的是教育管理善惡標(biāo)準(zhǔn)(價(jià)值觀)的研究。這是因?yàn)椋紫龋瑐惱硎且陨茞鹤鳛樵u(píng)價(jià)觀念與實(shí)踐的標(biāo)準(zhǔn)的,善與惡的矛盾是倫理道德領(lǐng)域的特殊矛盾,因此善惡標(biāo)準(zhǔn)問題乃是教育管理倫理基本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聚焦并探索確立合理的教育管理價(jià)值觀導(dǎo)向是教育管理倫理研究深入、有效的重要保證”;[18]其次,教育管理的善惡標(biāo)準(zhǔn)表達(dá)著我們基本的教育管理善惡觀點(diǎn)和倫理原則,要澄清是非、駁斥落后的教育管理倫理價(jià)值觀念,就必須提出科學(xué)的教育管理善惡標(biāo)準(zhǔn),并藉此評(píng)價(jià)管理活動(dòng)或行為的倫理價(jià)值。當(dāng)前教育管理倫理研究之所以一直步履蹣跚、進(jìn)展緩慢,關(guān)鍵原因就在于我們的相關(guān)研究“大多都是針對教育管理活動(dòng)中凸顯的一些實(shí)然性道德問題,進(jìn)而推出了應(yīng)然性的倫理準(zhǔn)則作為解決之道”,[19]但對于所提出倫理準(zhǔn)則的理論依據(jù)和學(xué)理支撐卻鮮有深入地分析與論證。因此,聚焦基本理論問題尤其是善惡標(biāo)準(zhǔn)問題的探討,是當(dāng)前深化教育管理倫理研究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并著力加強(qiáng)的問題。
(二)積極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研究成果
歐美國家在教育管理倫理研究方面起步較早,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展已經(jīng)比較成熟,不僅出版了大量教育管理倫理的著述,而且研究已經(jīng)深化到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倫理、教育組織倫理以及教育決策倫理等方面。鑒于此,積極學(xué)習(xí)、借鑒發(fā)達(dá)國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方能進(jìn)一步提升我國教育管理倫理的研究水平。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要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國外教育管理倫理研究成果的譯介力度。近年來,我們在翻譯、引進(jìn)歐美發(fā)達(dá)國家教育行政、學(xué)校管理研究成果方面獲得了長足的進(jìn)步,翻譯、引進(jìn)了一大批有價(jià)值的教育管理學(xué)術(shù)著述,但是由于在實(shí)際操作過程中存在著以效率、技術(shù)為標(biāo)準(zhǔn)篩選引進(jìn)的傾向,導(dǎo)致鮮有教育管理倫理相關(guān)研究成果的譯介與引進(jìn),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制約了研究的深入開展。除加強(qiáng)譯介發(fā)達(dá)國家教育管理倫理研究成果外,還可以通過“派出去”(派遣國內(nèi)學(xué)者去國外學(xué)習(xí))、“請進(jìn)來”(邀請國外學(xué)者來華講學(xué))以及“雙向互動(dòng)”(舉辦學(xué)術(shù)會(huì)議、開展合作研究)等方式,積極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相關(guān)研究成果。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處理好借鑒與創(chuàng)新、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guān)系,避免一種非此即彼的極端化傾向。只有如此,方能在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之上,逐步形成自身鮮明的特色,從而促進(jìn)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科學(xué)開展。
(三)促進(jìn)相關(guān)學(xué)科間的通力合作
教育管理倫理是一門在教育管理學(xué)、倫理學(xué)相互交叉和滲透基礎(chǔ)上形成的一門邊緣性學(xué)科。它是教育管理學(xué)、倫理學(xué)在發(fā)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科際整合。這一學(xué)科性質(zhì)決定了該學(xué)科知識(shí)體系不僅關(guān)涉教育管理學(xué)、倫理學(xué)(主要是應(yīng)用倫理學(xué))兩大學(xué)科知識(shí)板塊,而且還涉及到教育學(xué)、管理學(xué)、行政學(xué)等教育管理學(xué)基礎(chǔ)學(xué)科與倫理學(xué)相互交叉、相互滲透而形成的一些學(xué)科,如教育倫理學(xué)、管理倫理學(xué)、行政倫理學(xué)等。因此,只有不同學(xué)科的研究人員通力合作,才能從整體上促進(jìn)教育管理倫理研究地深化和發(fā)展。多學(xué)科人員的合作是綜合性、交叉性學(xué)科發(fā)展的客觀需要。事實(shí)上,在教育倫理學(xué)、管理倫理學(xué)等領(lǐng)域,這種多學(xué)科合作的局面早已開始。但與教育倫理學(xué)、管理倫理學(xué)相比,教育管理倫理學(xué)的綜合性、交叉性程度更高,這在一定程度上為研究的深化制造了障礙。因此,當(dāng)前在學(xué)科研究隊(duì)伍建設(shè)以及各學(xué)科合作方面,應(yīng)該堅(jiān)持以具有教育管理學(xué)背景的學(xué)者為主體,鼓勵(lì)他們認(rèn)真學(xué)習(xí)倫理學(xué)、管理倫理學(xué)的基本理論,主動(dòng)加強(qiáng)與倫理學(xué)、管理倫理學(xué)研究人員的學(xué)術(shù)交流與合作,積極克服自身倫理理論知識(shí)的缺陷與不足;同時(shí),適當(dāng)吸納一些從事教育倫理學(xué)、管理倫理學(xué)乃至倫理學(xué)研究的人員積極參與教育管理倫理的研究,促進(jìn)研究隊(duì)伍構(gòu)成的多樣化。
(四)注重理論與實(shí)踐的密切聯(lián)系
教育管理理論與教育管理實(shí)踐正如錢幣的正反面,它們是永遠(yuǎn)纏繞在一起的。[20]教育管理理論與實(shí)踐之間的這種特殊關(guān)系,一方面說明教育管理倫理研究自身具有鮮明的實(shí)踐旨趣,另一方面也彰顯出實(shí)踐之于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重要價(jià)值,提醒我們決不能忽視對實(shí)踐的關(guān)懷,必須注重理論與實(shí)踐的聯(lián)系。首先,研究者應(yīng)該樹立強(qiáng)烈的實(shí)踐意識(shí),經(jīng)常深入教育管理現(xiàn)場,善于在實(shí)踐中發(fā)現(xiàn)問題、探尋原因、解決問題、摸索規(guī)律和積累經(jīng)驗(yàn),藉此進(jìn)一步明確研究目的,豐富研究素材與內(nèi)容,改進(jìn)與完善研究方法,從而促進(jìn)研究的深化與發(fā)展。其次,促進(jìn)理論工作者與實(shí)踐工作者的合作與交流,在兩者之間倡導(dǎo)建立一種新型的合作關(guān)系。這種合作關(guān)系,既可以是短期的階段性合作關(guān)系(如課題合作、項(xiàng)目合作等),也可以是長期的固定合作關(guān)系(如校際合作)。再次,注意思辯研究和實(shí)證研究的綜合運(yùn)用。思辯研究和實(shí)證研究是教育管理研究的兩種基本范式,然而審視當(dāng)前我國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現(xiàn)狀可以發(fā)現(xiàn),思辯研究一直占據(jù)著研究的主導(dǎo)地位,實(shí)證研究相對匱乏。而事實(shí)上,諸如問卷調(diào)查、案例分析等實(shí)證研究方法對于教育管理倫理研究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價(jià)值的。因此,只有兩種研究方法綜合運(yùn)用,方能更好地促進(jìn)教育管理倫理理論與實(shí)踐的聯(lián)系,進(jìn)而使之更好地服務(wù)于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的發(fā)展與深化。
[1]吳志宏,馮大鳴,周嘉方.新編教育管理學(xu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14.
[2]Evers,C.W & Lakomski,G.Explor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Coherentist application and critical debates[M].Oxford:Pergamon Press,1996.1.
[3]Foster,W.P.,Paradigms and Promises:New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M].Prometheus Books,1986.35.
[4][13][美]威廉·G·坎寧安,保拉·A·科爾代羅.教育管理:基于問題的方法[M].趙中建主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20-21,20.
[5]張新平.反思與建構(gòu):教育管理現(xiàn)象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教育科學(xué)版),2002,(2).
[6]張新平.教育管理學(xué)導(dǎo)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57-258.
[7]孫綿濤.提高我國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論品位 創(chuàng)建中國教育管理理論的新體系[J].教育管理研究,2005,(1).
[8]陳學(xué)軍、張新平.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管理學(xué)[J].教育理論與實(shí)踐,2007,(11).
[9]李連科.價(jià)值哲學(xué)引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1.
[10]張傳有.倫理學(xué)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
[11]羅國杰等.倫理學(xué)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85,76.
[12]張新平.新世紀(jì)國外教育管理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趨勢[J].比較教育研究,2004,(3).
[14][19]金保華,孫綿濤.西方人文主義教育管理倫理觀及啟示[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09,(8)
[15]郅庭瑾.學(xué)校管理的倫理追問[J].思想理論教育,2006,(12).
[16]Willower,D.J.Synthesis and Projection[A].Norman J.Boyan(ed)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C].New York:Longman Inc,1988.735.
[17][美]肯尼思·克洛克,瓊·戈德史密斯.管理的終結(jié)[M].王宏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07.
[18]郅庭瑾.我國教育管理倫理研究現(xiàn)狀與反思[J].教育發(fā)展研究,2007,(12).
[20]張新平.關(guān)于教育管理理論實(shí)踐及其關(guān)系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2,(6).
(責(zé)任編輯:劉丙元)
金保華/北京工業(yè)大學(xué)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生導(dǎo)師,教育學(xué)博士,研究方向?yàn)榻逃芾砘纠碚?孫綿濤/沈陽師范大學(xué)教育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所所長、特聘教授,香港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yàn)榻逃芾砘纠碚?/p>